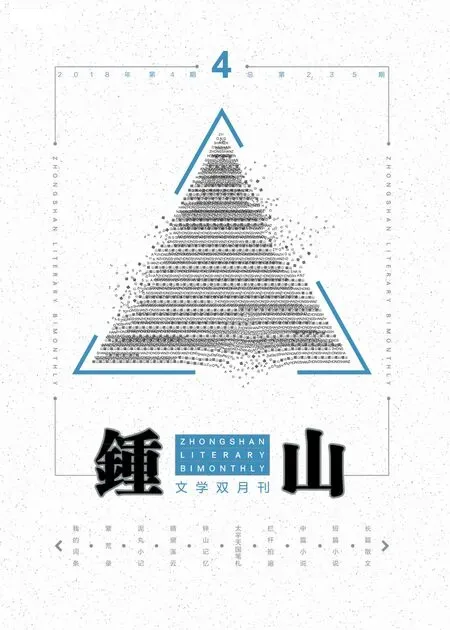罪與罰
——兼及兩性問(wèn)題
李潔非
L I J I E F E I
我們?nèi)缃袼Q的“法”,古代一般名之以“刑”。近代以來(lái)對(duì)“法”的理解,無(wú)論層次與精神都更周密、更辨證,古代則比較片面,基本是作為懲罰和鎮(zhèn)壓工具,假暴力手段維持社會(huì)秩序。所以在古代,“法”大致等于“刑”,或集中體現(xiàn)于“刑”。由于側(cè)重和依賴暴力,古刑比之于今世遠(yuǎn)為慘刻,目的不但在于讓亂法者受懲處,且冀望借助刑的可怖來(lái)威嚇?biāo)腥恕5^(guò)去我們常有個(gè)誤解,以為酷刑惟中國(guó)為多為甚。其實(shí)不能這么說(shuō),對(duì)酷刑的喜好,舊時(shí)代舉世皆然。以歐洲為例,起碼到十五世紀(jì),那里酷刑就未見(jiàn)得較中國(guó)遜色。中國(guó)一方面確有不少酷刑,另一方面中國(guó)對(duì)刑的認(rèn)識(shí)也從來(lái)分處兩端。一種是嗜虐逞威,另一種則主張慎刑求德。后之代表,即儒家口中的上古圣君堯、舜。據(jù)說(shuō)他們治天下之前,蚩尤“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為五虐之刑,自謂得法”,這“五虐”之中,包括劓、 、 、黥等肉刑,“而堯、舜以流放代之,故黥劓之文不載唐、虞之籍,而五刑之?dāng)?shù)亦不具于圣人之旨也”,令以刑殘民的統(tǒng)治成為過(guò)去。堯、舜還主張:“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jīng)。”很了不起,雖距現(xiàn)代“疑罪從無(wú)原則”尚存不及,但在遠(yuǎn)古能持“罪疑惟輕”的認(rèn)識(shí),已經(jīng)相當(dāng)杰出。盡管堯、舜史事尚未從考古上落實(shí),可能是儒家典籍的杜撰,然而作為思想見(jiàn)解,它們存在于中國(guó)是不必否認(rèn)的。
透過(guò)法律制度,一來(lái)能看到社會(huì)的價(jià)值取向,比如保護(hù)什么、反對(duì)什么。二來(lái)能看到社會(huì)的道德觀念,以何為善、以何為惡,法律功能之一就是懲惡揚(yáng)善。還有,能看到政權(quán)的特征乃至權(quán)力背后的哲學(xué),比如權(quán)力是較有自信還是被焦慮所控制,或權(quán)力對(duì)人性的看法偏于正面還是負(fù)面……這些都會(huì)影響法律的面貌,令它寬嚴(yán)相差、剛?cè)嵊袆e。
太平天國(guó)官方文件中,未見(jiàn)頒有正式法典,僅有帶法律性質(zhì)的《天條書(shū)》和軍規(guī)一類東西。正式法典究竟有沒(méi)有,至今存疑。似乎有,張德堅(jiān)從接受調(diào)查的太平軍對(duì)象那里,聽(tīng)到過(guò)“太平刑律”的名稱,不過(guò)直到目前,尚未發(fā)現(xiàn)任何完整的太平天國(guó)律書(shū)。《賊情匯纂》從大量文書(shū)告示中輯錄了六十二條,是目前所知太平天國(guó)法律條文最全的匯總。這是截至1855年亦即《賊情匯纂》付梓時(shí)的條文,法律內(nèi)容總是會(huì)隨時(shí)變更以適應(yīng)現(xiàn)實(shí)變化,比如廣西時(shí)期太平天國(guó)條例就比較簡(jiǎn)單,后則“所增禁令日繁”;因此,《賊情匯纂》所輯也只是一個(gè)參考,我們姑以此為憑,就太平天國(guó)法律情形作一點(diǎn)有限的考察。
先說(shuō)酷刑。太平天國(guó)有些令人色變的野蠻刑罰,如點(diǎn)天燈和五馬分尸,是明確載于其文書(shū)告示的:
凡我們兄弟如有被妖魔迷懞反草通妖,自有天父下凡指出,即治以點(diǎn)天燈和五馬分尸之罪。
故張德堅(jiān)說(shuō):“賊目殘忍,專事威 。”不過(guò),僅此不能對(duì)我們的認(rèn)識(shí)有何幫助。使用酷刑,絕非太平天國(guó)特色。它的敵方清朝,同樣有酷刑。讓我們從“小說(shuō)家言”說(shuō)起,莫言《檀香刑》的主人公,是一位大清劊子手,擅長(zhǎng)“檀香刑”。所謂“檀香刑”,就是凌遲。莫言對(duì)“檀香刑”極盡渲染,自不免虛構(gòu)成份,但凌遲重典明載于清律,卻是事實(shí)。它一直到清朝尾聲,于光緒三十一年經(jīng)沈家本等人奏請(qǐng),方告廢除。《清史稿·刑法二》:
三十一年,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請(qǐng)刪除重法數(shù)端,略稱:“見(jiàn)行律例款目極繁,而最重之法,亟應(yīng)先議刪除者,約有三事:一曰凌遲、梟首、戮尸……”
凌遲作為頂級(jí)酷刑殘忍之極,在它面前,其他酷刑都未免相形見(jiàn)絀。所以我們談?wù)撎教靽?guó)酷刑,如果是為證其格外殘忍,這個(gè)目的恐怕達(dá)不到。酷刑的可談與宜談,其實(shí)在別處,比如說(shuō)文化含義。人類所有造物,不論美丑,都有文化的意義,就連酷刑這樣丑陋的東西,說(shuō)起來(lái)也應(yīng)劃在“文化”范圍內(nèi)。比如中國(guó)正統(tǒng)王朝對(duì)酷刑之設(shè),是有講究的,并非怎么野蠻怎么來(lái),怎么猙獰怎么來(lái),而須“傳承有序”、“其來(lái)有自”,像做文章那樣得有出典。史上沒(méi)有的,不好隨便亂創(chuàng);史上曾有但前朝已廢的,也不宜貿(mào)然恢復(fù)。總之應(yīng)該循例而設(shè)。清朝用凌遲之法,便即如此:
凌遲之刑,唐以前無(wú)此名目。《遼史刑法志》始列入正刑之內(nèi)。宋自熙寧以后,漸亦沿用。元、明至今,相仍未改。原來(lái),凌遲是契丹始創(chuàng),宋朝自神宗熙寧年間仿之,而元、明二代沿用。有了這番傳承關(guān)系,它似乎便正當(dāng)起來(lái),可以堂而皇之地采用。反觀太平天國(guó),耐人尋味的恰也在于,它的酷刑如點(diǎn)天燈、五馬分尸、銅鑼炙背、火鏈纏腿、錐刺谷道等,皆非“相仍未改”而來(lái)。其中個(gè)別的如五馬分尸,史上雖有,古名“刑”——商鞅死于“車裂”即此刑——但久已廢除。那么,為何偏偏太平天國(guó)于酷刑不走“傳承有序”路線?這倒正是歷史可以品味處。加以體會(huì),我以為或含幾點(diǎn):其一,能力所限,“技藝”達(dá)不到。比如凌遲,幾被傳為絕活,神乎其技,“明殺宦官劉瑾,凌遲三日始死,據(jù)云例該三千三百五十刀”,甚是離奇,不知真假,但技術(shù)上有相當(dāng)難度是一定的,太平天國(guó)恐怕暫不具備這么高級(jí)的專家劊子手。其二,察諸太平天國(guó)酷刑,一個(gè)共同特點(diǎn)是全都簡(jiǎn)便易行,人人可為、弗學(xué)而能,包括行刑器具亦屬俯拾即是一類,還不必挑地點(diǎn)場(chǎng)所,隨時(shí)隨地上手,除了沒(méi)有技術(shù)門檻,不能不說(shuō)這很適合太平軍多數(shù)時(shí)間處于流動(dòng)和野戰(zhàn)狀態(tài)的需要。其三,太平天國(guó)酷刑,多數(shù)帶“野刑”味道,不重儀式,比較隨興,宣泄意味濃,與街邊田頭撒野沒(méi)啥差別,自“正統(tǒng)王朝”角度會(huì)覺(jué)得缺乏“明正典刑”的嚴(yán)肅性,但在太平天國(guó),也許反而合它心態(tài);它是一場(chǎng)“革命”,“革命”自不肯循規(guī)蹈矩,不痛快淋漓又如何盡顯“革命”烈焰熊熊之勢(shì)?
由此,也談?wù)剬?duì)太平天國(guó)酷刑的各種記載的考辨。
除點(diǎn)天燈和五馬分尸這兩種外,諸記所載的酷刑,在《賊情匯纂》所輯六十二條里都找不到。《賊情匯纂》一書(shū),不出于作者個(gè)人之述,全部輯鈔自太平天國(guó)正式文書(shū)和告示,故相當(dāng)可信。而諸記所載全屬見(jiàn)聞,有些來(lái)自作者自稱的目見(jiàn),有些卻只得諸耳聞。這就帶來(lái)一個(gè)真實(shí)性問(wèn)題。在過(guò)去,頗有論者置之為“地主階級(jí)知識(shí)分子的污蔑”,予以了斷。這種可能性的確不能排除。然而,同時(shí)也就面臨另一個(gè)不能排除的困難,亦即我們所用到的太平天國(guó)史料,多半都屬于此類“地主階級(jí)知識(shí)分子”撰述,如果“污蔑”的假設(shè)在邏輯上成立,就應(yīng)將它們整體棄用,而沒(méi)有辦法把其中一部分視為“污蔑”、對(duì)其余部分卻視為可信材料加以采用。因此,借口“污蔑”而擱置諸多太平天國(guó)酷刑記載的做法,本身經(jīng)不住推敲。作為形態(tài)有些特殊的政權(quán),“載于明文”未必是甄別太平天國(guó)史跡真贗的依據(jù)。從至今未見(jiàn)一部成文法典論,刑罰在太平天國(guó),極可能始終就并不采取嚴(yán)謹(jǐn)、正式的法律體系的面貌,反而有很大的隨意性、隨機(jī)性。這里有個(gè)例子,沈梓《避寇日記》記述曾見(jiàn)太平軍張貼告示于一寺廟,“系南京偽天皇(王)規(guī)條,有十誡、十囑、十除、十?dāng)厮氖畻l”,“誡者,誡人犯教中之禁也。囑者,勸人從其教也。除者,除去惡習(xí),如烏煙、花酒、釋道之類。斬者,斬違教者也。 ”這“天王四十條”,別書(shū)未見(jiàn),人不能鑒其真假。直到1950年,江蘇金壇縣拆除舊墻時(shí)發(fā)現(xiàn)一份寫于黃綾之上的太平軍 《邴天福令》,中有“讀四十天法,圣心教導(dǎo)精詳”之語(yǔ),適與沈梓“天王四十條”相佐,乃知其雖無(wú)考于太平天國(guó)官書(shū),但《避寇日記》所述確非虛罔。類乎“天王四十條”那樣確實(shí)存在而不見(jiàn)載于正式文獻(xiàn)的情形,提醒我們太平天國(guó)治刑可能有任意、靈活的特點(diǎn)。它的條規(guī)可視乎需要隨時(shí)添改,乃至于握一定權(quán)力者可以 “因地制宜”、“便宜行事”、自頒章則。張德堅(jiān)從繳獲材料見(jiàn)到“偽燕王秦日綱所出告示,亦載應(yīng)斬罪多款”似即為秦日綱法外置法,在所轄范圍自搞一套,另張新規(guī)。做文章講“文”“野”之分,其實(shí)人類做所有事,都存在“文”“野”之別,刑 也不例外。歷來(lái)在國(guó)法之外,不能盡絕暗中的私刑,比如宗族內(nèi)部或秘密會(huì)社一類死角,私設(shè)公堂都司空見(jiàn)慣,所行私刑往往別出心裁、五花八門,以“野”見(jiàn)長(zhǎng)。拜上帝會(huì)原本就帶有濃厚的秘密會(huì)社色彩,兼之建都天京后并無(wú)向常規(guī)國(guó)家形態(tài)轉(zhuǎn)型的鮮明意識(shí),法度偏“野”少“文”是可想見(jiàn)的,其間若有不見(jiàn)諸史的“野刑”即興之作,豈足為奇?
李秀成述天京末期:
自九帥兵近城邊時(shí),天王即早降嚴(yán)詔,合城不敢違逆,不遵天王旨命,私開(kāi)敵人之文、通奸引誘,有人報(bào)信者,官封王位,之知情不報(bào),與奸同罪,命王次兄拿獲,椿砂、剝皮法治。
“椿砂”、“剝皮”這兩種酷刑,均未見(jiàn)于張德堅(jiān)所輯六十二種,此處卻經(jīng)李秀成親筆述記。同治三年六月,上海《新報(bào)》在報(bào)道中對(duì)兩刑曾予描述:

剝皮慘刑古有之,但“椿砂”或“椿臼”則似為太平天國(guó)“發(fā)明”。《能靜居日記》記有一實(shí)例,同治三年二月,天京有圖謀投誠(chéng)的頭目許連芳,失敗后死于該刑:“聞許已監(jiān)押,后聞?dòng)谑沼檬薯贼┧馈!苯杩嵝套屓嗽谒劳鲋鈱?duì)肉體痛苦極度恐懼,這個(gè)效果可以說(shuō)很好地達(dá)到了,以致李秀成冒險(xiǎn)對(duì)天王表達(dá)異見(jiàn)時(shí)說(shuō):“爾將一刀殺我,免我日后受刑……”足見(jiàn)對(duì)“受刑”的恐懼,遠(yuǎn)過(guò)于處死。用刑過(guò)酷的另一證據(jù),是洪仁玕《資政新篇》鄭重建議“善待”人犯。他勸洪秀全“恩威并濟(jì)”,希望他“刑外化之以德,而省于刑”。設(shè)若施刑之毒未至慘不忍睹,干王實(shí)不必作為一個(gè)重大關(guān)切在此誠(chéng)懇提出。
酷刑種類方面,似對(duì)火刑情有獨(dú)鐘。上述剝皮之刑,實(shí)為火刑一種。點(diǎn)天燈亦為火刑:
用棉絮卷人而繃之浸以油,置巨木倒縛于其上,燃以火名點(diǎn)天燈。
謝介鶴所述幾種,俱以用火為主:
越日有出城逃逸者,為賊所獲,即前剪發(fā)人(太平天國(guó)蓄發(fā),剪發(fā)意味著投敵),則怒以火烙火錐之,問(wèn)通妖否……或?qū)⑹肿惴唇樱持勉~鑼,用火?之,呼慘之聲,不忍入耳。或?qū)⒁路摫M用鐵鏈燒紅向脛一盤,但聞?dòng)蜐n鐵聲,肉皆糜爛,痛叫一聲,大半昏絕。或用火箸燒紅,刺入股內(nèi)……
張汝南同樣記有 “跪火鏈”、“爍鐵熨背”、“灼錐刺臂股”,以及另一種鞭刑后的火刑:
竹?鞭背,上鷹架,繩縛手足將指而懸之,紙燃燒油滴鞭破處。
太平刑罰之嚴(yán)刻,溯其由來(lái),當(dāng)是服膺法家思想所致。我們?cè)榻B了商鞅的“怯民使以刑,必勇”,“去奸之本,莫深于嚴(yán)刑”的重典治國(guó)路線。然而,商鞅重典治國(guó)仍注意刀刃之上的力度,求其輕重有別,真正收威懾作用。太平天國(guó)卻有些不分輕重緩急,一味從重。雖然酷刑之外,太平天國(guó)刑罰也有常規(guī)或習(xí)見(jiàn)的一面,如斬首、枷號(hào)、杖責(zé)諸樣式,且應(yīng)說(shuō)此系主流,酷刑只施諸某些特別嚴(yán)重的罪行和特別危險(xiǎn)的罪犯。但終究來(lái)說(shuō),太平天國(guó)對(duì)于治罪,總難抑其打破常規(guī)、不循常理的任性,所以即便習(xí)見(jiàn)的樣式,運(yùn)用上也驚人地表現(xiàn)出輕重失宜、無(wú)所顧忌的特色。比如斬首,作為死刑在古代確屬普通,然而太平天國(guó)用法卻極夸張。張德堅(jiān)注意到,“毛細(xì)之過(guò),笞且不足,賊輒律以斬首。 ”亦即通常來(lái)講的輕罪,太平天國(guó)往往以問(wèn)斬伺候。《賊情匯纂》所列六十二條刑律,處以“斬首不留”的居然多達(dá)四十二條,庶幾無(wú)罪不斬。且舉數(shù)例:“各衙各館兄弟”如果發(fā)生“口角”和“斗架”,將“不問(wèn)曲直,概斬不留”,亦即只要發(fā)生這種事,并不區(qū)分誰(shuí)對(duì)誰(shuí)錯(cuò),全部斬首;所有兄弟,必須嚴(yán)格呆在本館,不得“私自過(guò)館”即私自造訪別館,或在彼處“留宿”,“違者斬”;必須熟背“贊美天條”,如“超三個(gè)禮拜不能熟記”,“斬首不留”;遇各王及丞相級(jí)別官員轎出,必須回避,如果沖撞,“斬首不留”此條應(yīng)是對(duì)丞相以下各官而言;“凡檢點(diǎn)指揮各官轎出,卑小之官兵,亦照路遇列王規(guī)矩,如不回避或不跪道,斬首不留”;在“朝會(huì)敬天父”的場(chǎng)合,如有人喧嘩,“斬首不留”;“夫妻私犯天條者,男女皆斬”;因兩情相悅而“和奸”,“男女皆斬”;私藏金銀和剃刀,就視為“變妖”,“定斬不留”;不準(zhǔn)剪發(fā)、剃胡須和刮臉,這屬于“不脫妖氣”,“斬首不留”;吸鴉片必?cái)兀拔S煙”的普通煙民,初犯打一百枷一個(gè)禮拜,再犯打一千枷三個(gè)禮拜,第三次“斬首不留”;“凡傳令講道理”亦即革命宣傳活動(dòng),“有無(wú)故不到者”,枷七個(gè)禮拜打一千,“再犯斬首不留”;軍中不能搞文藝創(chuàng)作,凡有“編造歌謠及以凡情歪例編成詩(shī)文,迷 兄弟者”,“斬首不留”;如果對(duì)挖筑工事等軍中事務(wù) “口出怨言”,“斬首不留”;膽敢“辱罵官長(zhǎng)者”,“斬首不留”;“一切妖書(shū),如有敢念誦教習(xí)者,一概皆斬”;“妖書(shū)”必須一概毀化,“如有私留者,搜出斬首不留”;文娛活動(dòng)“一概停止”,“如有聚人演戲者,全行斬首”;“凡朝內(nèi)軍中如有兄弟賭博者,斬首”……
以上情形,通常多罪不至死,甚或連處分也夠不上,僅予批評(píng)教育即可,太平天國(guó)則一律視作“活罪難容”。這不特有違常情,考慮到太平天國(guó)的信仰,更是大拂基督戒殺之訓(xùn)。《資政新篇》勸說(shuō)洪秀全慎刑的理由之一,就是基督的教義,“以少符勿殺之圣誡焉”。但遭斷然拒絕:“爺誡勿殺是誡人不好謀害妄殺,非謂天法之殺人也。”“天法殺人”,就不算“妄殺”。又說(shuō):“爺今圣旨斬邪留正,殺妖殺有罪不能免也。”味其語(yǔ)意,認(rèn)為“天妖斗爭(zhēng)”尖銳殘酷、你死我活,容不得溫良恭儉讓。總之洪秀全思想里暴力因子突出,認(rèn)為必須殺殺殺,方能殺出一個(gè)新天地。
人的心靈和意念,非憑空而至。“人的本質(zhì)并不是單個(gè)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xiàn)實(shí)性上,它是一切社會(huì)關(guān)系的總和。”人之言行,貌似發(fā)乎己身,實(shí)則是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歷史文化預(yù)先書(shū)寫的結(jié)果。說(shuō)到嗜殺,中國(guó)有此傳統(tǒng)無(wú)疑,每逢王朝崩解,很少不伴隨殺戮甚慘時(shí)光。東漢末年、西晉八王之亂后的北方,以及明代尾聲等,都曾有殺人如麻的嗜血狂魔。此即為何魯迅筆下“狂人”,將史書(shū)翻來(lái)覆去最后只讀到“吃人”二字。中國(guó)書(shū)籍,正史也好演義也罷,里面殺氣都很重。洪秀全眼中歷史更迭、正邪沖突,離不開(kāi)砍砍殺殺,顯有歷史的陰影。之前我們分析,他夢(mèng)里大戰(zhàn)妖魔,“三十三天逐層戰(zhàn)下”,活脫脫是《西游記》天兵天將捉拿妖猴之翻版,說(shuō)明歷史文化對(duì)他腦子里“成像系統(tǒng)”的作用。進(jìn)而具體驗(yàn)視太平天國(guó)刑罰,像“跪火鏈”、“爍鐵熨背”、“灼錐刺臂股”之類酷刑,嚴(yán)格來(lái)講亦非新發(fā)明,在民間因果報(bào)應(yīng)幻說(shuō)以及所想象的“十八層地獄”景狀里,早有類似的描畫(huà),太平天國(guó)無(wú)非是將幻說(shuō)搬入現(xiàn)實(shí)而已。然而事皆有兩面。中國(guó)歷史文化固隨處可見(jiàn)毒虐筆觸,可是要求克制暴力的思想和聲音并不弱。不單儒家要求仁愛(ài)治天下,道家也強(qiáng)調(diào)“貴生”。故而即便“虎狼之秦”猶有呂不韋一派,主張“圣人深慮天下,莫貴于生”、“害于生則止”,勸誡君主奉“貴生之術(shù)”。北宋時(shí),蘇軾曾總結(jié)到他那個(gè)時(shí)候?yàn)橹沟闹袊?guó)歷史,說(shuō):“予觀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者致之。其余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fù)分,或遂以亡國(guó)焉。”這樣的道理,在中國(guó)也源遠(yuǎn)流長(zhǎng)、代有傳人,并不輸于對(duì)暴力的崇尚,所以中國(guó)史能夠涌現(xiàn)賢明如漢光武帝、宋仁宗的人主,而不只有石虎、張獻(xiàn)忠之類暴虐強(qiáng)人。可見(jiàn)歷史文化善惡并現(xiàn),何去何從,仍視乎自我選擇。
洪秀全對(duì)于歷史不認(rèn)為應(yīng)以善制惡,而信以暴抗暴,或許還可推求于個(gè)人原因,即精神專家所斷言的其人格與心理帶有病態(tài)傾向,使他更難以積極的目光面對(duì)世界、借鑒歷史。自他著作來(lái)看,他對(duì)中國(guó)歷史幾近一筆否定,尚未否定者,僅限于不可鑒知的上古——“壞自少昊時(shí)”,少昊以下一團(tuán)漆黑。這意味著中國(guó)歷史良善之一面,他都拒不承認(rèn)了。由此帶來(lái)一個(gè)教訓(xùn),一味反歷史,往往失去擇善相從的明智,從而受到毀壞的欲望的掌控。不能不說(shuō),太平天國(guó)對(duì)罪與罰的觀念,打上了洪秀全個(gè)人心態(tài)的烙印。太平刑罰拒不參酌、依循通行的法理和視點(diǎn),尺度任意,從心所欲,跟洪秀全排拒歷史的言談是相一致的。
人類立法,是在長(zhǎng)期社會(huì)實(shí)踐中,對(duì)犯罪問(wèn)題加以總結(jié)和摸索,提取理性認(rèn)識(shí),而形成有其規(guī)律與沿革的體系。國(guó)有興亡,代有移換,法理精神與認(rèn)識(shí)卻體現(xiàn)出恒通性,不隨江山易代而棄廢。以清朝為例,它作為異族入主中原,在敲訂《大清律》時(shí)就經(jīng)歷了這樣的過(guò)程:
刑之有律,猶物之有規(guī)矩準(zhǔn)繩也。今法司所遵及故明律令,科條繁簡(jiǎn),情法輕重,當(dāng)稽往憲,合時(shí)宜,斟酌損益,刊定成書(shū)。
以明朝舊法為基礎(chǔ),結(jié)合自身需要,有依有違,有增有損,完成《大清律》撰修。雖然清之于明本是敵國(guó),但考慮法制時(shí)卻未因此刻意相拗。此蓋因法律作為歷史結(jié)晶,非某朝之私貨,是代代延傳增損而來(lái)。清律所繼承的貌似為明律,實(shí)際則是當(dāng)時(shí)歷史條件下中國(guó)法制的通識(shí)。何止明清之間,我們看今天世界各個(gè)國(guó)家,雖然意識(shí)形態(tài)或至相左,但考其法律制度,對(duì)罪與罰的認(rèn)知及繩衡,共性都大于差異性。總之,法律制度愈是接近于“放之四海而皆準(zhǔn)”,愈表明其理性意味較強(qiáng),較能涵蓋和反映一般人性尺度;凡是過(guò)于別出心裁或另類的情形,不可避免都對(duì)法的正確性和正當(dāng)性有所斫損。
太平天國(guó)法制偏于后者,“破”字當(dāng)頭,不肯準(zhǔn)古酌今。我們不僅要知其如此,更須探它所以如此的原因。
一來(lái),太平天國(guó)有一種情懷,自命為開(kāi)天辟地,以為將要?jiǎng)?chuàng)造人間前所未有的嶄新國(guó)度,因而對(duì)舊律陳規(guī)不屑理會(huì)。二來(lái),它不把立法的基點(diǎn),置于犯罪現(xiàn)象與社會(huì)之間利害關(guān)系的理性、精細(xì)評(píng)估,而是先入為主,將拜上帝教教義置于至高無(wú)上的位置,很多從社會(huì)危害性看通常是輕微罪衍以至非罪的現(xiàn)象,從教義的角度都變?yōu)橹刈铮缕湓O(shè)刑不可理喻。三來(lái),是實(shí)用主義傾向過(guò)于嚴(yán)重。我們說(shuō)法律不妨服務(wù)于政治現(xiàn)實(shí),但不可為政治捐棄理性觀照下的公平正義尺度,太平天國(guó)為求政治功用則不惜亂立名目、夸大性質(zhì),視法律如政治奴妾,致使法律自身無(wú)尊嚴(yán)可言。四來(lái),對(duì)法的認(rèn)識(shí)存在根本錯(cuò)誤,缺乏辯證觀念,一味寡恩、不知市恩。凡屬良法都應(yīng)寬嚴(yán)相濟(jì)、有張有弛,借此分寸真正收其繩墨社會(huì)之效。太平刑律卻惟知兇暴、務(wù)求剛猛,這種認(rèn)識(shí)不特極為表皮,且根本處在誤區(qū)。
以上四者,令刑罰在太平天國(guó)成為一件乖序失常、怪狀奇形之事。典型的如夫妻之間幽會(huì)“男女皆斬”,此等罪名與處置,僅出于禁欲戒令和捍衛(wèi)男女分營(yíng)制度,罔顧天倫,根本到了逆天的地步。余如口角、打架當(dāng)斬,勞累有怨言當(dāng)斬,未能熟記 “贊美天條”當(dāng)斬,作詩(shī)、吟曲、演戲都要斬首……環(huán)顧人間,古往今來(lái),法度從未至于如此之濫。有些條文,本意雖好,如禁止劫毀民財(cái)民物等,然而概以問(wèn)斬對(duì)待,亦殊為無(wú)理。這樣不分青紅皂白,動(dòng)輒置之死地,似乎會(huì)使治國(guó)治軍變得容易,但公正全失,歸根到底必“得”不償“失”。法律一旦不講“理”,無(wú)異于自為廢紙。失當(dāng)之法,絕不可能抑制犯罪,只會(huì)增加犯罪。太平天國(guó)后期,公開(kāi)無(wú)視、逾越律例的行為,從吸煙、飲酒到侵掠民財(cái)、“強(qiáng)帶外小”,形形色色, 拾即是。表面看是法紀(jì)弛渙所致,往深處追究,不得不說(shuō)那些異于常情、悖乎常理的約束,人們從內(nèi)心就無(wú)法報(bào)以敬畏信服。
在此順而談?wù)勌教靽?guó)與兩性有關(guān)的問(wèn)題。
太平軍視男女為大防,迄至楊秀清頒 “給配令”,禁家室、禁婚姻、禁私情;設(shè)男館、女館,男女分營(yíng),這種制度似乎直到“給配令”后,仍維持不變。由此造成形形色色犯罪,涉性罪名也因而在刑罰中占有一突出位置。然而兩性問(wèn)題除了造成犯罪,還帶來(lái)很多復(fù)雜的現(xiàn)象或奇特景觀,是太平天國(guó)時(shí)期非常值得關(guān)注的側(cè)面。
比如太平軍中“娘子軍”的存在,頗有人目作“男女平等”、提高婦女地位、婦女解放之類的表征,至言在中國(guó)歷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經(jīng)濟(jì)、民族、男女四大平等”、“男女平等是它的革命政綱之一”、“是婦女解放思想的第一個(gè)實(shí)行者,這樣廣大徹底的婦女解放運(yùn)動(dòng),是俄國(guó)十月革命以前,世界歷史上不曾有過(guò),真是人類最光榮最先進(jìn)的運(yùn)動(dòng)”。 美譽(yù)之丕揚(yáng),措辭之熱烈,令人咋舌。
其實(shí),太平軍并非清一色男性,乃關(guān)乎兩點(diǎn)。一是“舉家團(tuán)營(yíng)”政策所致。金田起義動(dòng)員投營(yíng)者闔家加入,既基于規(guī)避官府迫害,次者也是出于聚攏財(cái)力物力和根除家庭羈絆,令會(huì)眾舍“小家”就“大家”,正如李秀成所說(shuō):“將里內(nèi)之糧谷衣食等,逢村即取,民家將糧谷盤入深山,亦被拿去……臨行營(yíng)之時(shí),凡是拜過(guò)上帝之人,房屋具(俱)要放火燒之”,這是太平軍形成拖家?guī)Э诰置娌⒀苌澳镒榆姟钡恼鎸?shí)原因。二則離不開(kāi)客家風(fēng)俗這一背景。兩廣客家,女不纏足甚至光腳,日后江南士民見(jiàn)了彼等每呼“大腳蠻婆”。她們吃苦耐勞,登山涉水、負(fù)重挑擔(dān)、力耕采薪,無(wú)不能為、無(wú)不能至,數(shù)百年來(lái)舊俗如此,并非太平軍加以“解放”的結(jié)果。相反倒應(yīng)該說(shuō),“舉家團(tuán)營(yíng)”策略成立,系以客家女人獨(dú)特風(fēng)貌為前提。設(shè)若太平起義不舉于兩廣,而換作中原江南地帶,以婦女普遍纏足、三寸金蓮移步維艱的景狀,即欲“舉家團(tuán)營(yíng)”,在流徙千里的前途考驗(yàn)面前,也必然難克其成。
故而太平軍之有女流,自起因來(lái)說(shuō),與“婦女解放”八竿子打不著。至于“男女平等”,尤不知從何談起。那些引吭謳歌的學(xué)者,莫非沒(méi)有讀過(guò)洪秀全的數(shù)百首詩(shī)篇?里面歧視女性、男尊女卑的言辭,比比皆是。姑拈數(shù)例:
爾為夫主心極真,永配夫主在天庭。爾為夫主心極假,賤莫怨?fàn)斈菇恪?/p>
一眼看見(jiàn)心花開(kāi),大福娘娘天上來(lái)。一眼看見(jiàn)心火起,薄福娘娘該打死。大福薄福自家求,各人放醒落力修。
狗子一條腸,就是真娘娘。若是多鬼計(jì),何能配太陽(yáng)?
摘不勝摘,引不勝引。
又以所謂“一夫一妻制”,指證“男女平等”。誠(chéng)然,這種條文可以找見(jiàn),例如:“一夫一妻,理所宜然。”但引用者往往藏頭露尾,孤立地摘出一句,同時(shí)對(duì)太平天國(guó)基本婚配制度避而不談。婚姻在太平天國(guó)斷非為“男女平等”而設(shè),實(shí)際上它反而是嚴(yán)苛等級(jí)關(guān)系的產(chǎn)物與體現(xiàn),妻房數(shù)量與爵秩品級(jí)掛鉤,地位越高,可擁有妻妾配額則愈多,往下遞減,及至下層卒眾,則減為一夫一妻。眾所周知,天王陛下“娘娘”無(wú)數(shù)。又一證據(jù)是1862年左右洪秀全曾頒《多妻詔》,正式公布可依官階大小享受的妻子數(shù)額:
今后均須依照朕諭,妻數(shù)應(yīng)依官階大小而多少不等。朕詔婚配情況如下:朕長(zhǎng)、次兄以及干王、翼王、英王、忠王、贊王、侍王、輔王、章王、豫王,不足六妻者,自行擇配,共迎朕之壽辰,屆時(shí),望各官員補(bǔ)足其數(shù)。
白紙黑字。面對(duì)此詔,凡噪呼太平天國(guó)行“一夫一妻制”者能不赧顏?詔中還特別補(bǔ)充說(shuō):“此詔前已逾所允之?dāng)?shù)者,朕寬容之。”說(shuō)明高級(jí)干部早就私自過(guò)上一夫多妻生活,此詔不過(guò)是追認(rèn)而已。
所謂“婦女解放”、“男女平等”的神話,應(yīng)該散作煙云了。還有一個(gè)問(wèn)題,就是所謂婦女“地位”提高。此又如何呢?
論及此點(diǎn),曲意回護(hù)者也很眉飛色舞——理由是太平天國(guó)有女官和女官制度。自古,出來(lái)做“公家人”、吃“公家飯”、封官晉爵的,沒(méi)有女流之輩。偶爾出現(xiàn)一個(gè)例外,比如大周皇帝武 御前,據(jù)說(shuō)有個(gè)“代天子巡方”的女官謝瑤環(huán),當(dāng)年田漢如獲至寶,拿她編了一幕大劇。類似這樣的角色,在太平天國(guó)卻非零星一二,而是成批成群。難道這不是婦女地位空前提高的標(biāo)志么?
我們?nèi)圆患庇诮Y(jié)論,先把事情弄清。
里頭要點(diǎn)有二,一是太平天國(guó)為何能有女官?二是太平天國(guó)拿她們來(lái)做什么?對(duì)于第一點(diǎn),又得提到“大腳蠻婆”的特性。她們?cè)诠世锛凹抑校琼斕炝⒌氐哪樱苣苋问拢图夷腥艘嗖挥X(jué)得讓她們獨(dú)當(dāng)一面有何不可。這是先決條件。對(duì)第二點(diǎn),太平天國(guó)用女官究竟是對(duì)她們刮目相看,還是有些事非她們不可?這就要按實(shí)詳究。在記載中,太平天國(guó)女性幾乎做過(guò)所有事,包括搬磚、砍柴、割麥等各種重體力活。只不過(guò),這些職役近乎苦力,還不能視為婦女“地位”提高的證明。有辨析必要的,應(yīng)是客家“老姊妹”中間被恩賞了“指揮”、“將軍”等職的那群人。她們得職的原由,從史料看似非積軍功所致,否則總會(huì)有一些女戰(zhàn)士陷陣殺敵的突出故事流傳,但我們幾未見(jiàn)過(guò)這樣的報(bào)道。所以,她們相對(duì)高的授職應(yīng)是出于其他作用的任命。這里“其他作用”,劃分一下,蓋為三種:一、女營(yíng)管理;二、女監(jiān)工;三、女內(nèi)侍。
男女不得私相授受,分館而居,它的實(shí)施需要大量女營(yíng)管理人員,且只能由女性充當(dāng)。這是太平天國(guó)龐大“女干部”隊(duì)伍的第一個(gè)由來(lái)。《金陵雜記》述之:
每館定以二十五人,其中立館長(zhǎng),亦謂之兩司馬。或十余館,或數(shù)館,有一賊婦督之,謂之女偽百長(zhǎng),即偽卒長(zhǎng)。其上又有女偽軍師(應(yīng)為“軍帥”之誤)、女偽總制等賊婆,皆廣西山洞潑悍大腳婦女為之。
女官名稱有“司馬”、“百長(zhǎng)”或“卒長(zhǎng)”、“軍帥”、“總制”,與男營(yíng)相同。
日常另一用得著“女干部”的地方,是監(jiān)工。太平天國(guó)強(qiáng)迫所有女館居民勞動(dòng),從挖溝、運(yùn)輸、伐薪、割麥到紡織等,所有這類場(chǎng)合,皆須人布置、督持、驗(yàn)看,單是女館兩司馬顯然不夠,需要另外委員司事。且不言而喻,凡此輩,亦非得是女性。以織工為例,派設(shè)專員如下:
設(shè)女錦繡指揮二百四十員,職同指揮,女錦繡將軍二百員,職同將軍,女錦繡總制一百員,職同總制,女錦繡監(jiān)軍一百六十員,主督各婦女制刺金?冠服的工作。
最后一處大量需求女官的地方,當(dāng)然是天王宮和諸王府。天王宮除洪氏父子自己,以外概為婦女,甚至護(hù)弁亦系裙釵。其所設(shè)女官,“宮禁城女檢點(diǎn)自左一右二次至三十六,共三十六員。女指揮自左一右二次至七十二,共七十二員。女將軍分炎、水、木、金、土正副,共四十員”。又有供奉各種雜務(wù)的女侍應(yīng),“設(shè)有統(tǒng)教、理文、理袍、理靴、理茶等女官,惟員數(shù)官階都不詳”。記載中說(shuō),天王宮“其鳳門以內(nèi),皆系賊婦在內(nèi),以供洪逆役使”,乃至造屋起殿這種高強(qiáng)度工作,亦由女人承擔(dān):“賊婦中并有能造房屋者,去冬洪逆住處失火,燒去樓房數(shù)間,傳聞旋經(jīng)賊令木匠將房架造成送入,賊婦即在內(nèi)蓋成房屋。”不但天王宮純用女官,諸王府亦然。韋昌輝北王府:“其中婦女亦不下數(shù)百人,門內(nèi)除韋逆外,別無(wú)男人。”翼王府“其中婦女亦有數(shù)百,時(shí)常騎馬出入”。秦日綱燕王府“選服侍婦女多人,類皆廣西大腳者多”。諸王府女官設(shè)職比照天王宮,員額品級(jí)相應(yīng)減降。例如:“天朝內(nèi)掌門,東殿、西殿內(nèi)貴使,都職同檢點(diǎn)。東殿、西殿內(nèi)掌門,南殿、北殿內(nèi)貴使,都職同指揮。南殿、北殿內(nèi)掌門,翼殿內(nèi)貴使,都職同將軍。翼殿內(nèi)掌門,燕第內(nèi)貴使,都職同總制。 ”
由這三種主要用途,終于生成了太平天國(guó)極具規(guī)模的女官群。《賊情匯纂》卷十一,列有太平天國(guó)各類女官的詳細(xì)數(shù)目,其中“偽女卒長(zhǎng)一千人”,與謝介鶴所述接近;而“偽女管長(zhǎng)”亦即“兩司馬”之職為“四千人”;再加上其他各官,太平天國(guó)女官總數(shù)為“六千五百八十四人”。這是截止于1855年的記錄。
綜上可知,太平天國(guó)大量使用女官且形成制度,殊非有意提高婦女“地位”,實(shí)出乎不得己。倘若不搞“女性干部隊(duì)伍建設(shè)”,“男有男行,女有女行”就沒(méi)法實(shí)施。好在機(jī)緣湊巧,客家女人不裹腳、能任事的特質(zhì),剛好很堪驅(qū)馳。
話題未完,還要繼續(xù)深挖——大量需要女官的背后,其實(shí)隱藏著一個(gè)秘密。我們已經(jīng)知道,天王宮中以及權(quán)貴府邸,乃女官充職之一大去處。有些野史涉筆及此,故弄玄虛,導(dǎo)人淫邪之思。然而,天京深宮高墻之內(nèi)性別比例的巨大懸殊,與所謂欲壑難填基本無(wú)關(guān)。實(shí)際上,它關(guān)乎一個(gè)難言之隱。
那就是:對(duì)宦官苦不能致。
汪堃《盾鼻隨聞錄》,兩次出現(xiàn)太平軍閹不得法記錄。卷五提到楊秀清曾“閹割幼童,十難活一”,復(fù)于卷八又說(shuō):“賊取十三四歲幼童六千余人,盡行閹割,連腎囊剜去,得活者僅五百余人。”如果私家筆記不足憑信,那么再看《賊情匯纂》的記載:
癸丑八月楊逆下令選各館所擄幼孩十二歲以下、六歲以上者二百余人閹割之,欲充偽宦官,因不如法,無(wú)一生者。楊逆知不可為,又詭稱天父下凡指示,再遲三年舉行,以掩群下耳目。
有確切的時(shí)間和地點(diǎn),即1853年,南京太平軍入城半年后。有年齡范圍,即十二歲以下、六歲以上未成年男童。還有被用于閹割試驗(yàn)的具體人數(shù):二百余人。以此驗(yàn)諸《盾鼻隨聞錄》,知其確有訛失之處——將試閹對(duì)象說(shuō)成六千人,過(guò)于夸大;又說(shuō)存活者十能有一,豈非猶有成功之例?至《賊情匯纂》明指“無(wú)一生者”,始與理相合。我們多次講過(guò),《賊情匯纂》是應(yīng)曾國(guó)藩之命結(jié)撰的調(diào)研報(bào)告,注重情報(bào)價(jià)值,沒(méi)有必要捏造事實(shí),所涉內(nèi)容悉有文書(shū)、采訪為憑,故敢稱“事務(wù)求實(shí),不尚粉飾”。 此書(shū)既將試造太監(jiān)未果之事寫入,就可以斷定并非謠傳。
事情的可信度,亦能于反方向求證。天王及以下各王,對(duì)于有宦官在宮府供役的需求,極為強(qiáng)烈。癸丑年1853正月二十八日,由武昌兵發(fā)南京途中,洪秀全發(fā)下詔旨,專申宮禁之嚴(yán):
咨爾臣工,當(dāng)別男女,男理外事,內(nèi)非所宜聞;女理內(nèi)事,外非所宜聞。朕故特詔,繼自今,外言永不準(zhǔn)入內(nèi),內(nèi)言永不準(zhǔn)出。今凡后宮,臣下宜謹(jǐn)慎,總稱娘娘。后宮姓名位次永不準(zhǔn)臣稱及談及,臣下有稱及談及后宮姓各名位次者斬不赦也。后宮而(面)永不準(zhǔn)臣下見(jiàn),臣下宜低頭垂眼,臣下有敢起眼窺看后宮面者斬不赦也。后宮聲永不準(zhǔn)臣下傳,臣下女官有敢傳后宮言語(yǔ)出外者斬不赦也。臣下話永不準(zhǔn)傳入,臣下話有敢傳入者傳遞人斬不赦,某臣下斬不赦也。朕實(shí)情詔爾等:后宮為治化之原,宮城為風(fēng)俗之本,朕非好為嚴(yán)別,誠(chéng)體天父天兄圣旨,斬邪留正,有偶不如此,亦斷斷不得也。自今朕既詔明,不獨(dú)眼前臣下宜遵,天朝天國(guó)萬(wàn)萬(wàn)年,子子孫孫暨所有臣下俱宜遵循今日朕語(yǔ)也。內(nèi)宮與外臣,一般的敬避之規(guī)雖屬必要,但如此忮刻,以至于言及姓名位次即死、瞄一眼即死之類,真可謂匪夷所思。我們以清宮為例。清宮有“垂簾儀”:“凡召見(jiàn)、引見(jiàn),仍升座訓(xùn)政,設(shè)紗屏以障焉。”即,外臣可以抬頭、與后妃照面,二者間紗屏相隔,以增朦朧。對(duì)比之下,洪氏忌褊之心未免世所罕見(jiàn)。
透過(guò)這道詔旨,足可想見(jiàn)思求宦官之渴,也足可想見(jiàn)使能握得閹割之術(shù),將何等歡欣鼓舞。問(wèn)題又回到了一個(gè)相似之點(diǎn),前面講到凌遲不見(jiàn)諸太平極刑與人才和技術(shù)有關(guān);此刻,拿二百余名男童做實(shí)驗(yàn)竟“無(wú)一生者”,正好兩相輝映。明末,沈德符從南方赴京,一過(guò)河間、任邱以北,時(shí)于“敗垣”之中得見(jiàn)自腐之輩,他心驚肉跳寫道:“聚此數(shù)萬(wàn)殘形之人于輦轂之側(cè),他日將有隱憂。”可知首善之區(qū)周邊,連民間都已掌握了閹割之法。只是“帝都”幾百年獨(dú)特歷史的氤氳造化,別處不能望其項(xiàng)背。楊秀清試閹全敗,證明至少在十九世紀(jì)中期,從兩廣到長(zhǎng)江流域這一帶,閹割術(shù)仍是沒(méi)有破解的秘密。
中國(guó)正史都有“志”的板塊,其中一項(xiàng)內(nèi)容曰“職官”,而“職官”必講到宦官。 《清史稿》里,這個(gè)部分稱“內(nèi)務(wù)府”,列于卷一百十八志九十三職官五。假設(shè)今人援古例為太平天國(guó)修史,則相應(yīng)部分的組成人員,便是天王宮及各王府里那些女流之輩。她們除開(kāi)“內(nèi)掌門”、“內(nèi)貴使”等官銜與歷代有別,功能及角色可以說(shuō)一模一樣、不分軒輊。易言之,她們無(wú)非就是清朝內(nèi)廷的敬事房、御膳房、掌禮司、尚衣監(jiān)以及總管、副總管之類,抑或明代“十二監(jiān)、四司、八局,所謂二十四衙門”以及提督、掌印、秉筆太監(jiān)之類。惟一不同,是明清此類機(jī)構(gòu)人員由閹后男宦充任,太平天國(guó)因不能閹腐,不得已由女人充任。
注釋:
(1)馬端臨《文獻(xiàn)通考》卷一百六十二刑考一,頁(yè)4838。
(2)同上,頁(yè) 4837。
(3)張德堅(jiān)《賊情匯纂》卷八,《中國(guó)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guó)(三)》,頁(yè) 227。
(4)同上。
(5)同上,頁(yè) 229。
(6)同上,頁(yè) 227。
(7)《清史稿》卷一百四十三,志一百十八,頁(yè)4199。
(8)同上。
(9)《中國(guó)歷史大辭典》“凌遲”詞條,上海辭書(shū)出版社,2010,頁(yè) 2502。
(10)沈梓《避寇日記》,《中國(guó)近代史資料叢刊續(xù)編·太平天國(guó)(八)》,頁(yè) 57。
(11)太平天國(guó)起義百年紀(jì)念展覽會(huì)編《太平天國(guó)革命文物圖錄》,上海出版公司,1952。
(12)張德堅(jiān)《賊情匯纂》卷八,《中國(guó)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guó)(三)》,頁(yè)227。
(13)《李秀成親供手跡》,排印文,頁(yè) 41。
(14)轉(zhuǎn)自羅爾綱《太平天國(guó)史》,頁(yè)1181。
(15)趙烈文《能靜居日記》,頁(yè) 739。
(16)《李秀成親供手跡》,排印文,頁(yè) 37。
(17)洪仁玕《資政新篇》,《中國(guó)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guó)(二)》,頁(yè) 537-539。
(18)張汝南《金陵省難紀(jì)略》,《中國(guó)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guó)(四)》,頁(yè)716。
(19)謝介鶴《金陵癸甲紀(jì)事略》,同上書(shū),頁(yè)662。
(20)張汝南 《金陵省難紀(jì)略》,同上書(shū),頁(yè)716。
(21)張德堅(jiān)《賊情匯纂》卷八,《中國(guó)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guó)(三)》,頁(yè)227。
(22)同上,頁(yè) 228-232。
(23)洪仁玕《資政新篇》,《中國(guó)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guó)(二)》,頁(yè) 538。
(24)同上。洪仁玕《資政新篇》,《中國(guó)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guó)(二)》,頁(yè) 538。
(25)馬克思《關(guān)于費(fèi)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頁(yè)18。
(26)《呂氏春秋集釋》, 中華書(shū)局,2013,頁(yè)38。
(27)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zhǎng)編》卷一,中華書(shū)局,2012,頁(yè) 5。
(28)《清史稿》卷一百四十二,志一百十七,頁(yè)4182。
(29)范文瀾《中國(guó)近代史》,上編第1分冊(cè),人民出版社,1951,頁(yè)186。
(30)羅爾綱《太平天國(guó)史事考》,三聯(lián)書(shū)店,1955,頁(yè) 318。
(31)同上,頁(yè) 340。
(32)《李秀成親供手跡》,岳麓書(shū)社,2014,排印文,頁(yè)01-02。
(33)《天父詩(shī)》,《中國(guó)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guó)(一)》,頁(yè) 436。
(34)同上。
(35)同上,頁(yè) 438。
(36)《國(guó)宗提督軍務(wù)韋石革除污俗禁娼妓鴉片黃煙誨諭》,《太平天國(guó)文書(shū)匯編》,頁(yè)90。
(37)《多妻詔》,《洪秀全集》,頁(yè) 206。
(38)同上。
(39)滌浮道人《金陵雜記附續(xù)記》,同上書(shū),頁(yè)622。
(40)羅爾綱 《太平天國(guó)史》卷二十八,頁(yè)1024-1025。
(41)同上,頁(yè) 1024。
(42)同上,頁(yè) 1025。
(43)滌浮道人《金陵雜記附續(xù)記》,《中國(guó)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guó)(四)》,頁(yè)627。
(44)同上,頁(yè) 628-629。
(45)羅爾綱 《太平天國(guó)史》卷二十八,頁(yè)1024。
(46)張德堅(jiān)《賊情匯纂》卷十一,《中國(guó)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guó)(三)》,頁(yè)309。
(47)汪堃《盾鼻隨聞錄》,《中國(guó)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guó)(四)》,頁(yè) 398。
(48)同上,頁(yè) 424。
(49)張德堅(jiān)《賊情匯纂》卷十二,《中國(guó)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guó)(三)》,頁(yè)326。
(50)張德堅(jiān)《賊情匯纂》凡例,同上書(shū),頁(yè)34。
(51)《天命詔旨書(shū)》,《中國(guó)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guó)(一)》,頁(yè) 69。
(52)《清史稿》卷八十八,志六十三,頁(yè)2619-2620。
(53)沈德符《萬(wàn)歷野獲編》卷六,中華書(shū)局,1997,頁(yè) 178-179。
(54)《明史》卷七十四,志第五十,中華書(shū)局,2013,頁(yè) 1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