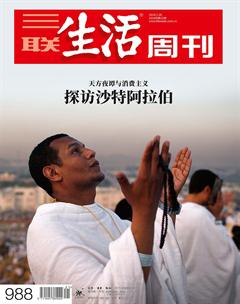川航緊急備降背后:民航如何保證飛行安全?
黃子懿

5月16日,川航3U8633重慶—拉薩機組在成都召開媒體見面會,機長劉傳健接受采訪
萬米高空驚魂
5月14日早上8點多,中國國際航空公司(下稱“國航”)資深機長林云所在的飛行員微信群內炸開了鍋。
一張飛機駕駛艙的照片被發在群里——如果那還能被叫作駕駛艙的話。艙內開了一個大口子,右側的風擋玻璃已經完全脫落,艙內靠近玻璃一側,駕駛艙控制臺被吹得七零八落。畫面右下角,有一只呈展開狀的手掌靜止著,時間好像停滯了。那是四川航空(下稱“川航”)3U8633航班機長劉傳健被凍得發紫的手。
根據川航披露,當日早上7:07左右,川航執飛重慶至拉薩的3U8633航班在過四川雅安后開始爬高,達到32000英尺左右(約9800米)的高空。但就在此時,駕駛艙右側的風擋玻璃先出現了裂紋,后脫落飛出。飛機緊急下降,4分鐘后下降至24000英尺(約7300米),此后再次下降,直至7:43平安在成都著陸。
過程遠比官方概述驚險。5月16日的媒體見面會上,機長劉傳健回憶了驚魂40分鐘全過程:飛行中,風擋玻璃突然出現裂紋,成小塊狀、網狀。玻璃有好幾層,他的第一反應是去摸,判斷是內層還是外層的裂紋。同時決定調頭備降成都,并向空管報告。
“砰!”突然一聲巨響,劉傳健下意識地閉上了眼睛。待他再睜眼時,看見副駕駛半個身體已被吸到了外面,飛機在急劇下降,飛行速度也在增加。而在駕駛艙內,氣流瞬間涌入造成設備嚴重破壞,駕駛艙高度表撥定值,電子飛行儀器系統吹歪,部分儀表功能喪失。
“現在飛機很多都是自動駕駛了,沒有儀表怎么飛?”駕齡超過20年、飛行時長達2萬小時的某國有航空公司資深機長王軍評價劉傳健當時面臨的處境,說“很難很難”。
當時,飛機已時速800公里左右,前方玻璃脫落導致缺氧、極度寒冷、強氣流等惡劣條件會聚。劉傳健身體變形,除了風聲,耳朵聽不到任何聲音,和其他駕乘人員只能用手勢交流。但他硬生生地在零下40℃的機艙,穿著短袖將載有128名旅客的飛機安全著陸在成都雙流國際機場。除副駕駛和一名乘務員輕傷外,其余人員均無大礙。
一名資深空軍飛行員也對此次迫降表達了贊許。“這種狀況比開車沒有儀表盤還要嚴重,只有完全通過飛行經驗判斷。”他表示,風擋玻璃脫落還會對飛行員產生巨大的心理壓力,打亂正常的注意力分配,對飛行員的心理素質與操控判斷觀察能力“要求非常非常高。因為民航對航線的高度使用非常密集,還要及時跟地面協調求助,快速打開緊急備降通道”。
更重要的在于,玻璃脫落后可能產業的減壓癥(Decompression Sickness),即人在原有的高壓條件下,被突然暴露在低壓環境下,溶解在體液內的氣體會突然釋出,導致身體產生各種不適、運動功能障礙等,更嚴重者會產生氣體栓塞、血管破裂,甚至威脅生命。
高空氧氣稀薄,壓力小,飛機在起飛后往往會在客艙增壓,“至少也是海拔1000米左右的壓力水平”,風擋玻璃脫落,會導致急劇釋壓,“相當于人在1000米左右的高度,突然上升到一萬米”。前述飛行員解釋,再考慮到萬米高空比地標溫度低近60℃,還迎著約800公里/小時的狂風,因故本次降落極為不易。
根據氣象探空數據顯示,玻璃突然破碎時,9520米高度的氣溫約為零下35.9℃,氣壓300百帕,10760米高度的溫度是零下43.1℃,氣壓250百帕。有氣象愛好者在解釋:“當時川航飛行員,面臨1秒之內降壓500百帕、1秒之內降溫近70℃、1秒之內由靜風到140米/秒,相當于在零下40℃的最高級別的龍卷風中心,而且穿的是短袖。”
在世界航空史上,機艙失壓導致的飛行事故并不罕見。1999年,一架利爾35噴氣公務機在上升過程中出現機艙失壓,機內所有人昏迷,最終飛機燃油耗盡,在南達科他州墜毀。遇難者中,有美國知名高爾夫球運動員佩恩·斯圖爾特(Payne Stewart)。
更為人熟知,也是更類似于本次事件的,是英國航空5390號班機事故。1990年6月10日,這架由英國伯明翰飛往西班牙馬洛卡的航班起飛后不久,駕駛室的一塊風擋玻璃突然脫落,飛機爆炸性釋壓并將機長吸出機外。憑著副駕駛的努力,航班安全降落于南安普敦,機長經治療后奇跡生還。
業內人士普遍認為,川航本次的緊急備降比5390更難,壓差、缺氧、低溫和飛行時速都高于英航5390。英國路透社、BBC、《每日郵報》也報道了本次緊急備降,詳述了備降的全過程。《每日郵報》則將川航飛行員稱作“英雄般的”(heroic)。

發生故障的川航3U8633次航班在停機坪上,相關工作人員正在檢查飛機
風擋玻璃疑問
川航出事之后第二天,林云有一趟國內航班任務。他進到駕駛艙內,猛捶了幾下風擋玻璃,玻璃安然無恙。“這玩意兒怎么可能會脫落?”
據英航5390事故調查報告表明,5390風擋玻璃脫落的起因是由于維修人員安裝擋風玻璃時沒找到合適的螺絲釘,使用的90顆螺絲釘全都過短或過細。并且,那時的風擋玻璃均是從外部安裝,不易承受高空壓力,這是一大設計瑕疵。
據南方某國營航空公司飛機工程師梁爽介紹,這直接促成航空器上的一次技術進步。從英航5390之后,幾乎所有機型的飛機都已采用內嵌的方式安裝風擋玻璃。“這種設計上就是即使外層出現裂紋,那樣也可以飛,速度降下來就行。”林云說。
事件發生后,中國民用航空局立即牽頭成立了由副局長擔任事件調查組,飛機制造商空中客車(Airbus)也有參與其中,目前在進行持續深入調查,尚無定論。
據披露,執飛該航班的飛機是空客A319-100。該機于2011年7月26日進入川航,截至目前共使用19912小時。根據飛行小時或起落架次,飛機檢修一般分為A、B、C、D檢等級別,其檢修力度依次遞增。該執飛飛機最近一次A檢為4A5,于2018年4月12日在昆明完成。最近一次C檢為3C,2017年3月9日對外委托四川飛機維修工程有限公司完成。飛機當日無保留故障項目。查詢近15日維修記錄,該機無風擋故障信息。風擋玻璃為出廠原件。
前述飛行員解釋,風擋玻璃破碎可能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低空的飛鳥等外來物撞擊,而在高原航線等高空,可能由于部件老化等原因,導致縫隙擴大,“在高空氣流沖擊之下可能會松動,以至破碎”。
就在4月17日,美國西南航空一架從紐約飛往達拉斯的航班因引擎爆炸緊急迫降費城。該航班被鳥撞擊到引擎引發爆炸,引擎碎片擊碎了客艙風擋玻璃,以至于一名乘客被“吸”出窗外。
梁爽介紹,無論機型,從結構上講,飛機的風擋玻璃可有三層。內外兩層均為層狀玻璃,中間為塑料層,有的玻璃有加熱系統而有的則沒有,但都具有抗鳥撞擊的能力。一般來講,內層玻璃比外層厚,是主要結構部件,承載機艙內部的壓力載荷。中間的乙烯塑料為次要結構部件,同時也是一個失效裝置,當內層玻璃破裂時,可以防止受損的風擋碎裂。
祥鵬航空一位工程師介紹,目前民航飛機駕駛艙玻璃基本是原裝進口,多為美國PPG、法國SGS和德國GKN廠家生產。本次爆裂玻璃是法國SGS生產,其重量約在35kg,總厚度約3~4cm,由一層3~4mm厚和兩層8mm厚的加強鋼化玻璃組成。常見外物擊傷導致碎裂是在設計安全內的,但很少見到整塊玻璃內外兩層碎裂崩潰,“本次事件實屬罕見”。
“這個事情我們都覺得很蹊蹺。”梁爽說。據航旅縱橫專業版查詢,該飛機前序航班為5月13日執飛杭州到重慶的川航3U8936航班,“為什么前序航班沒問題,而次日第一班就有問題了呢?”他介紹,一般當日前序航班飛完都會進行航后檢查,排除可能故障后,才會執行第二天的飛行任務。
如果是風擋玻璃,其內外側在航前、航后檢查中都不允許有裂紋、“V”形碎屑,內側不允許有超標或者明顯影響視線的刮痕,風擋匯流條區不允許出現飛弧,風擋中間層的龜裂、分層、氣泡不能影響能見度。“工程師也不是萬能的,一些肉眼看不到的細小裂紋必須用高精度儀器檢測。”
他表示,考慮到故障發生路段正處于向高原爬升的階段,不排除是原件功能老化的可能,跟爬升高原途中極端天氣情況可能也有關系,但“都不好說,推測不來的,具體還是等官方調查說話”。
在發布會上,川航總工程師陳建中表示,客機駕駛室無監控視頻,無法還原玻璃破裂并脫落全過程。該飛機在此前的各種檢查,包括C檢、起降前后的常規檢查,都未發現問題。事件發生后,工作人員已立即排查該公司全部24架同機型客機,均無異樣。
“這24架同機型客機全部執行高原航線。”川航總經理石祖義補充稱,破碎的玻璃為原裝,未進行過任何更換和維修,處于一種良好的狀態,“一架飛機將近有200名工作人員圍著這架飛機轉。每一個航班的航前、航后都是必須要檢查的。而且哪一個地方該檢查都是有規定的。檢查沒檢查,也一定是有記錄的。”
最長安全紀錄
截至事發時的5月14日,中國民航的飛行安全天數紀錄已達2820天,有史以來最長的安全紀錄。中國上一次發生有生命遇難的事故是在2010年8月24日,河南航空VD 8387在黑龍江伊春的空難。再上一次,則需要追溯到2004年。
“第一不敢說,但世界前五是肯定有的。”林云說,考慮到中國民航運輸量已連續13年是全球第二大,這個成績殊為不易。舉例來說,2012年11月至2017年9月之間,中國運輸航空百萬小時重大事故率為0,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約為0.0872。與此同時,中國航空出行市場規模迅猛增長,飛行量顯著增加,中國年飛行量從327.5萬班增到466.8萬班,如今每年運輸超5億人次。
但2016年東航發生跑道入侵、兩機差點相撞,以及這次川航風擋玻璃脫落,都險些讓這個紀錄停滯。“都是一個起落一個起落飛出來的。”王軍說,最長安全紀錄都是靠著平日極度嚴苛的訓練累積和精細嚴格管理取得的。舉例來說,劉傳健所遇到特情,在平日民航飛行員模擬機訓練中原本就是一門科目。一個民航飛行員,即使是最高級別的機長,也需要完成復訓和考核。針對特殊情況的訓練和能力測評,在飛行員業內叫作熟練檢查,也稱年度復訓。
所謂熟練檢查,是指針對飛行中所遇到的特殊情況所進行的年度專場訓練,能使飛行員對機載設備使用和應急情況處理保持一個較高的熟練度。訓練每年2次、每次12小時,其中8小時訓練、4小時考試。如果考試未能通過,則會停飛、安排補充訓練。
林云說,因為多數飛行是風平浪靜、按部就班的,所以飛行員都需要通過地面訓練對各種特情保持高度的熟悉度,靠訓練熟練特情處置程序,甚至形成條件反射式的記憶動作。“空中特情你可能一輩子都遇不到,但一旦遇上了,如果你不熟練、無法第一時間開展處置程序就完了。”
常見的特情訓練科目有,單發(單個發動機)喪失推力、增壓系統故障、液壓系統故障、風切變等等。劉傳健的這次備降,至少包含了其中三個訓練科目:急劇釋壓+緊急下降+自動飛行系統故障。采訪中的機長,都能對整個處置程序倒背如流,甚至一邊背誦一邊對著空氣做出相應動作:戴好氧氣面罩,調定100%,建立機組通訊,提醒旅客戴好安全帶和氧氣面罩,看座艙高度是否可控,宣布緊急下降,報告塔臺,調高度,扭航向,調速度,拉減速板……整個過程,都需要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否則會因缺氧失去意識,成為2005年塞浦路斯“幽靈航班”的翻版。
林云曾在國外某地降落時遭遇過平生最險的一次“風切變”,3秒內有16米風速變化,“相當于突遇一個七級大風”。“屁股都夾緊了”,全靠記憶動作才復飛脫險。但他也認為,模擬訓練無法涵蓋所有情況。比如,模擬機上模擬的急劇釋壓特情是發生在客艙的,“從來不會想過會發生在駕駛艙中”。林云說:“誰又會受過副駕駛半身飛出去的訓練?”
中國民航飛行員考核非常嚴格,僅副駕駛(First Officer)就分為F1~F5五個等級,機長(Captain)則可細分為八個級別。除飛行時間要求外,還“逢升必考”,已是機長的林云“每升一級,就得脫層皮”。
要當機長,最基本的條件是需要2700小時飛行經歷時間(注:指坐在正駕駛位置的時間)。王軍如今已是級別最高的機長,是民航飛行檢查委代表和ATPE(航線運輸駕駛員執照)考試官,他在模擬機考試時會設置各種障礙和特情,“就給他搗亂”,以訓練飛行員臨場應變能力和心理素質。他能在5秒內完成急劇釋壓+緊急下降的全部流程,而根據劉傳健的13660小時的飛行時間,他估計劉傳健也是屬于能做模擬機B類教員的機長,屬于機長中的高級別。
林云說,中國民航的考核比國外“嚴得多”,在全球民航飛機愈發側重儀表飛行和信息化管理的情況下,中國對民航飛行員駕駛術的重視依然并未減弱,這是受到老一代空軍的影響。一個佐證是,大約10年前,波音集團首席飛行訓練官來中國觀摩了一場模擬機訓練,他看完之后一直搖頭,對中國同行說:“我們的飛機沒那么差!你們模擬的情況太極端了。”
相對的高要求不僅體現在駕駛術訓練上,還體現在實踐中的飛行品質監控(QAR)考核中。以王軍常飛的波音737-800機型為例,其所在的航空公司對飛行品質監控的指標達到107項目,包括直線滑行速度、起飛/復飛收起起落架等,都有硬性指標,超過指標則有輕微超限、嚴重超限等多個違規級別。其中,僅著陸一個動作的指標監控就達十余項。
采訪期間,他接到了自己所帶徒弟的一個電話。徒弟也是一個機長,在剛剛結束的一場飛行中,著陸時的著陸垂直載荷達超過1.7g(注:g=重力加速度),而公司規定超過1.68g就達到了輕微超限,超過1.89g就屬嚴重超限。達到輕微超限者,都需要其所在飛行大隊開安全分析會,復盤此次著陸的天氣條件和技術動作,結合該飛行員平日技術水平做出評估、分析原因。如果達嚴重超限,機長就要停飛,安排包括模擬機訓練和評估在內的檢查和整改。這些標準都相對嚴苛,曾經民航局還規定,著陸載荷超1.6g就算重著陸,當超過2.0g后必需做探傷,而波音737、空客A320系列飛機只是把大于等于2.0g的著陸定為重著陸。
“這都是必要的。”王軍以1997年南航深圳“5·8”空難舉例。這架波音737-300型飛機由重慶飛往深圳,在大雨中發生重著陸,飛機第一次接地即是一個“三級跳”,飛機結構受損,復飛后二次著陸后,飛機解體、起火。整個過程造成35人死亡。
那次空難屬于嚴重事故。而在民航界,不構成事故但影響或可能影響安全的事件被稱為“事故征候”,分為嚴重事故征候、一般事故征候,川航風擋玻璃脫落和東航的跑道入侵,均屬于嚴重事故征候。
事故征候的嚴重性再往下,是航空安全差錯,也分為一般和嚴重兩個等級。差錯標準比征候要低,“類似于開車壓黃線”,比如飛行過程中無關人員進入駕駛艙屬于一般差錯,起飛或著陸過程中尾撬擦地屬于嚴重差錯等。王軍所在飛行大隊有上百個飛行員,全年差錯率的安全指標僅僅是不超過兩起。“即便只發生夠不上差錯標準的不安全事件,機隊的各級領導都要被上級罵個狗血淋頭。”
各大航空公司近年不再公布事故征候率,但據知情人士透露,國航的征候率應該保持在兩位數。
這些考核也體現在地勤工作上。梁爽告訴我,比如飛機上的某個部件,如果制造商規定的是1000小時更換,他們通常800小時就換掉了。“飛機部件的維修期限上,制造商會給畫一個圈,民航局在這個圈里再畫一個圈,航空公司在民航局的圈里再各畫一個圈。”
而在空管上,林云說,基本執行的是能不飛就不飛,“用極低的正班率換來了極高的安全率”。采訪當日上午,他剛好從南方某城市飛到北京,因為天氣原因,飛機出發前被延誤兩小時,工作群里同事一片哀鴻遍野。大領導看到后告訴他們,“延誤算什么?安全更重要。”
(文中林云、王軍、梁爽為化名。記者王珊、實習記者童淑婷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