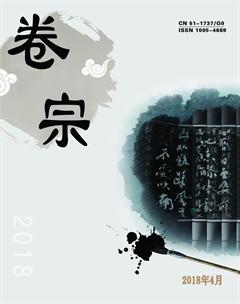探究趙匡胤杯酒釋兵權(quán)的智與不智
向莉莉 王桂鋼 文逸博
摘 要:“杯酒釋兵權(quán)”是很多人都熟知的歷史典故,在大部分近代歷史學(xué)家眼中,這是宋太祖趙匡胤的機智之為,也有人說這僅僅是趙匡胤的小人之舉,甚至也有史學(xué)家認(rèn)為“杯酒釋兵權(quán)”實為子虛烏有,并非歷史事件。本文謹(jǐn)從“杯酒釋兵權(quán)”這一事件確實發(fā)生為起點,探究一代明帝宋太祖在此事件中的智慧和不智之處,以及探究該類做法隱含的道理與對后世的影響。
關(guān)鍵詞:杯酒釋兵權(quán) 宋太祖 北宋
1 “杯酒釋兵權(quán)”是義不是疑
公元961年,乾德初,趙匡胤在退朝后留下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張令鐸諸高級將領(lǐng)飲酒。酒至半酣,宋太祖對軍將們說:“我非爾曹不及此,然吾為天子,殊不若為節(jié)度使之樂,吾終夕未嘗安枕而臥。”守信等頓首曰:“今天命已定,誰復(fù)敢有異心,陛下何為出此言耶?” 趙匡胤說道:“人孰不欲富貴?一旦有以黃袍加汝之身,雖欲不為,其可得乎?” 石守信等將領(lǐng)跪下磕頭,哭著說:“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帝曰:“人生駒過隙爾,不如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君臣之間無所猜嫌,不亦善乎。” 大臣們答謝說:“陛下念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病,乞解兵權(quán),帝從之,皆以散官就第,賞賚甚厚。此為杯酒釋兵權(quán)之故。
杯酒釋兵權(quán)這個歷史事件是宋朝加強中央集權(quán)制度的重要反映,然而幾百年來,世人對宋太祖此舉倫理方面眾說紛紜,評價不一,大致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多數(shù)人是宋太祖的仁德之舉,宋太祖趙匡胤去掉開過將領(lǐng)的兵權(quán),是給曾經(jīng)一起出生入死的將領(lǐng)們明哲保身的機會,幾乎所有的開國皇帝都有殺功臣的行為,但宋太祖“杯酒釋兵權(quán)”卻使用和平手段,不傷君臣和氣就解除了大臣的軍權(quán)威脅,成功地防止了軍隊的政變,這是歷史上有名的安內(nèi)方略;另一方面,也有史學(xué)家認(rèn)為“杯酒釋兵權(quán)”實為小人之舉,無非是“狡兔死,走狗烹”的一種變相存在。曾有評價說“皇位剛坐穩(wěn),就想打發(fā)走那些為自己浴血奮戰(zhàn)的將士們”,趙匡胤披著一件“偽善”的外衣,一點糧田,一點銀餉就把功臣們打發(fā)了,反過來,將士們還要對他感恩戴德,實在是讓人感慨。
單單評論一件事本身,只可作為一時的談資,而研究中華文明,我們就必須要聯(lián)系時代背景與對后世的影響。公元960年,趙匡胤通過發(fā)動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奪取了后周政權(quán),建立了宋王朝。從公元907年朱溫建立后梁帝國,到960年大宋帝國誕生,短短53年間,中原大地歷經(jīng)五代八姓十三帝。趙匡胤從小校步步為營地走上皇帝寶座,深知兵權(quán)對于王朝興衰有著決定性的作用。事實上,他自身登上皇位的起始就是對他自己最直接的警示:后周皇帝曾視他為最為親信的將領(lǐng),作為皇帝最為信任的將領(lǐng),所有人都可能叛變,只有他絕對不可能叛變。而當(dāng)他此刻剛登皇位,想起后周之亡,因此他必須早作防范,以免重蹈覆轍。所以政權(quán)集中,是趙匡胤亟待解決的事。
從狹義上看,“釋兵權(quán)”的起因似乎在于趙匡胤的多疑,趙匡胤俯視群臣,任何一個人有兵權(quán)的大臣都可能像自己,隨時準(zhǔn)備叛亂,隨時準(zhǔn)備拿起屠刀砍向自己。但事實并非如此,不妨設(shè)想,若是不釋兵權(quán),這些將領(lǐng)日后將如何自處,開國皇帝濫殺功臣幾乎是為穩(wěn)固權(quán)力而形成的一種自然規(guī)律,而宋太祖通過和平手段,不傷和氣就解除了大臣們的權(quán)力威脅,顯然是一種很高明的統(tǒng)治藝術(shù)。“杯酒釋兵權(quán)”之舉趙匡胤先后進(jìn)行了兩次,第一次就解除了石守信、王審琦、高懷德、張令鐸這四位,曾與趙匡胤出生入死的同袍的兵權(quán),這實際上是趙匡胤在顧及同袍之情,仕場上居高則險,此時不除兵權(quán),日后這幾位稍有紕漏,即便自己容得下,撩臣也容不下,必是十分兇險。宋太祖不顧當(dāng)時風(fēng)評,解除了開國將領(lǐng)的兵權(quán),并且對這些去除兵權(quán)的有功之臣封賞田地,讓他們廣納錢財,安樂一生,實為義舉,而這些開國大臣們大多本為后周將領(lǐng),又和太祖一起推翻了后周,心中惴惴,此刻攜良田,金銀回家,有何樂而不為。故而我們要說宋太祖“杯酒釋兵權(quán)”之舉是義而不是疑。
2 “杯酒釋兵權(quán)”是智不是計
盡管多數(shù)人贊揚趙匡胤“杯酒釋兵權(quán)”的做法,但卻僅僅停留在著眼在此舉防范了叛亂,兼顧了仁義的角度上,認(rèn)為這是趙普的定國之計策,是趙匡胤的裁斷果決。但實際上,“杯酒釋兵權(quán)”卻不是簡單的解決問題的計策,而是趙匡胤治國大智的體現(xiàn)。計與智的區(qū)別在于,計可解境地之窮,可保一時無憂,而智在于統(tǒng)籌規(guī)劃,可傳承造福后世。
趙匡胤所施行的杯酒釋兵權(quán)之法,并非僅限于宴請開國大臣借機收攏兵權(quán)上,而是有計劃的、分階段的落實了一系列集中政權(quán)的政策。建隆二年(961年),宋太祖鑒于已控制局勢,著手陸續(xù)采取了一些措施,把殿前都點檢鎮(zhèn)寧軍節(jié)度使慕容延釗罷為山南東道節(jié)度使,侍衛(wèi)親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罷為成德節(jié)度使,殿前都點檢從此不再設(shè)置。七月初九日,第一次設(shè)酒宴請石守信等人,二日石守信等人,交出兵權(quán),紛紛辭去軍職,為地方節(jié)度使。建隆三年(962年),晉趙普為樞密使、檢校太保。乾德元年(963年),用趙普謀,第二次設(shè)宴,罷王彥超等地方節(jié)度使和漸削數(shù)十異姓王之權(quán),安排他職,另以文臣取代武職,于是武臣方鎮(zhèn)失去弄權(quán)的基礎(chǔ),另一方面,收廂兵之驍勇,天下精兵皆歸樞密院指揮。地方雖無精兵,但地方廂兵仍可制約禁軍。這就形成了強干弱枝而內(nèi)外上下相互制約之制。
宋太祖為加強皇權(quán),鞏固統(tǒng)治所采取了一系列政治軍事改革措施,“杯酒釋兵權(quán)”的酒宴僅僅只是開始。
在軍事上,宋太祖趙匡胤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建立不同于前朝的樞密院制度。長官為樞密使和樞密副使,主管調(diào)動全國軍隊,分掌軍政大權(quán)。樞密院與三衙統(tǒng)領(lǐng)各有所司。三衙雖然掌握禁軍,但卻無調(diào)兵和發(fā)兵的權(quán)力。樞密院有發(fā)兵、調(diào)兵之權(quán),而不能直接掌握軍隊。調(diào)兵權(quán)與領(lǐng)兵權(quán)分離,各自獨立,相互制約,有利于皇權(quán)的控制;內(nèi)外相維,宋太祖把全部軍隊分為兩半,一半屯駐在京城,一半戍守各地,使京城駐軍足以制止外地可能發(fā)生的變亂,也使外地駐軍合起來足以制止京城駐軍可能發(fā)生了內(nèi)變;兵將分離,無論駐屯京城的禁軍,還是駐在外地的禁軍都必須定期調(diào)動。京城駐軍要輪流到外地或邊境戍守,有的則要到產(chǎn)糧的地方就糧,這種輪流駐防的辦法稱為“更戍法”。這種方法名義上是鍛煉士兵吃苦耐勞,實際上是借著士兵的經(jīng)常換防,造成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將官再也不能同士兵結(jié)合,在士兵中建立自己的聲望,也就再也不能率兵同朝廷皇帝對抗了。由此,宋太祖的釋兵權(quán)的治國方略正式完成。
在地方政治的改革上,宋太祖趙匡胤始終銘記著“杯酒釋兵權(quán)”時趙普所言“稍奪其權(quán)、制其錢糧、收其精兵”,為削弱節(jié)度使的行政權(quán)力,趙匡胤把本屬于節(jié)度使的駐地以外兼領(lǐng)的的州郡歸屬權(quán)收回京師,知州、知縣等地方官由中央直接派遣文官出,官員直接對中央負(fù)責(zé)、奏事,不再聽令于節(jié)度使。對于一些前朝留下的節(jié)度使,宋太祖再擺酒宴,將其逐一罷免。為分知州之權(quán)設(shè)置通判,使通判與知州在行使權(quán)力時相互制約,防止偏離中央政府的統(tǒng)治軌道。在制錢糧方面,各路設(shè)置轉(zhuǎn)運使,每一路所屬州縣的錢糧,僅留少量供于本地消耗,富余部分盡皆有轉(zhuǎn)運使運往京師。乾德三年(965年)八月,宋太祖“酒宴”再起,令各州長官把藩鎮(zhèn)所轄軍隊中驍勇的人,都選送到京城補入禁軍,從此各路軍隊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殘,只能供勞役用,稱為廂軍。這一舉使自唐末五代開始藩鎮(zhèn)專制,荼毒一方的現(xiàn)象徹底消失。
宋初的一系列“釋權(quán)”的改革措施,大大加強了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quán)制,造成了統(tǒng)一的政治局面,為經(jīng)濟、文化的高度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良好條件,也為后來更為嚴(yán)苛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埋下了伏筆,具有劃時代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