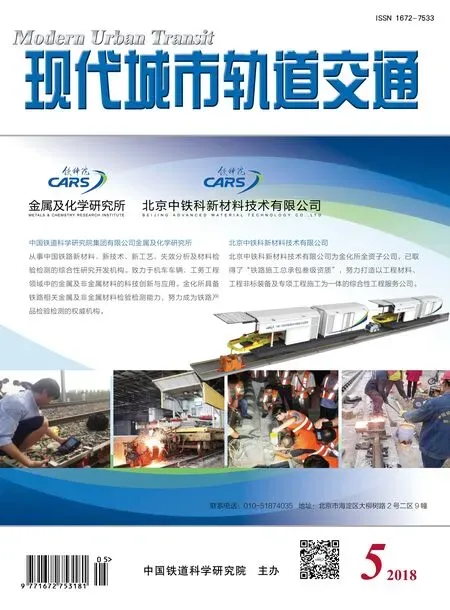城市軌道交通換乘站運營設施能力匹配性評價方法研究
彭 丹,劉 悅,寧 佳
(西南交通大學交通運輸與物流學院,四川成都 611756)
0 引言
隨著城市軌道交通的不斷發展及網絡化運營,客流增長迅猛。目前車站設計主要基于客流預測,鑒于預測客流與實際客流之間的差異,很多車站出現了能力匹配性不足,甚至嚴重擁擠的情況,如何對其匹配性進行有效評價一直是重難點。國內外學者大都基于乘客滿意度的角度,采用模糊綜合評價法、層次分析法等評價車站服務水平[1-3]。城市軌道交通換乘站是軌道交通網絡構成中的重要節點,大部分研究偏向于換乘站宏觀布局以及與其他交通方式銜接的協調性[4-5],缺乏站內基于實際客流的設施能力匹配性研究。本文基于換乘站運營設施實際能力分析,本著客觀科學的原則,構建了相應的評價指標體系,并建立模糊綜合評價模型,對換乘站運營設施的改造優化提供一定的參考建議。
1 換乘站運營設施能力及其與客流匹配性分析
乘客在換乘站的活動主要分為進出站、換乘和上下車3大類,根據換乘站客流路徑,主要對進出站運營設施、換乘設施以及上下車站臺等能力進行分析。由于車站性質不同,所吸引的客流類型也有所差異,車站運營設施的實際通過能力不盡相同。因此,對某大型換乘車站S在高峰小時進行實地調研,以確定各運營設施的實際通過能力。
車站S為城市軌道交通3號線和5號線(以下簡記為L3和L5)的交匯換乘站,L3呈南北向分布,L5呈東西向分布。在車站S中,站廳層和站臺層分布如圖1所示。

圖1 車站 S 站廳層與站臺層分布示意圖
1.1 進出站運營設施
根據乘客進出站活動,其運營設施可分為售票機、進出站閘機以及進出站樓扶梯。
1.1.1 售票機
售票機一般分為人工售票機和自動售票機2種,車站S人工售票窗口不提供進站購票服務,其自動售票機的實際服務能力為:

式(1)中,NSPJ為自動售票機服務能力,人/(h·臺);tSPJ為每位乘客平均使用自動售票機耗時,s。
車站S為辦公商業型,早高峰出站客流和晚高峰進站客流較大,但是由于絕大部分為通勤客流,多使用一卡通,購票比例小,早晚高峰進站乘客購票比例分別為15.2%、4.4%。早晚高峰小時自動售票機能力富裕度如圖2所示。車站S共計20臺售票機,服務能力十分充裕,其早晚高峰平均富裕度分別達到89.3%、61.7%。

圖2 高峰小時售票機能力富裕度分析
1.1.2 進出站閘機
進出站閘機是車站站廳付費區和非付費區的分界,一般有門扉式和三桿式2大類。車站S均為門扉式,有單向和雙向2種,其實際服務能力分別如下:

式(2)中,NDXZJ、NSXZJ分別為單向和雙向閘機的服務能力,人/(h·臺);nDXZJ、nSXZJ為高峰小時客流連續情況下,平均每臺單向和雙向閘機每分鐘服務人數,人/(min·臺)。
車站S站廳層進出站閘機數分布如表1所示。車站S早晚高峰小時各區域閘機能力利用富裕度達21%~96%不等,如圖3所示。早高峰出閘能力富裕度較小,約為30%;晚高峰進閘能力富裕度較小,約為50%。整體而言,車站S各方向閘機服務能力比較充裕。

表1 車站 S 站廳層進出站閘機數分布 臺

圖3 高峰小時各區域閘機能力富裕度分析
1.1.3 進出站樓扶梯
站臺與站廳一般靠樓扶梯連接。樓梯一般為上下行混合通行。樓梯混合通行能力以及扶梯的實際疏散能力分別如下:

式(3)中,NLT-HH、NFT分別為樓梯混合通行能力以及扶梯的疏散能力,人/(h·m);nLY-HH、nFT分別為高峰小時客流連續情況下,平均每組樓梯和扶梯每分鐘疏散人數,人/(min·組)。

表2 車站 S 進出站樓扶梯分布 組
車站S站廳層進出站樓扶梯分布如表2所示。早晚高峰小時各區域進出站能力利用富裕度達26%~97%不等,如圖4所示。早高峰出站能力富裕度較小,約為45%;晚高峰進站能力富裕度較小,約為42%。整體而言,車站S各區域進出站樓扶梯服務能力比較充裕。

圖4 高峰小時各區域樓扶梯能力富裕度分析
1.2 換乘樓扶梯設施
L3與L5在車站S的換乘樓扶梯分布如表3所示。根據乘客乘車行為習慣和偏好,乘客優先選擇扶梯而非樓梯。基于此,通過計算得到早高峰L3和L5之間各換乘樓扶梯能力富裕度如表4所示,早高峰L3換乘L5的客流較大,換乘樓扶梯能力不足。

表3 L3 和 L5 線路間換乘樓扶梯分布 組

表4 早高峰 L3 和 L5 線路間換乘樓扶梯能力富裕度 %
1.3 上下車站臺設施
站臺是供乘客上下車和候車的活動場所,主要有島式、側式和混合式3種類型。L3和L5在車站S的站臺形式分別為島式站臺和側式站臺。
已知站臺容納能力NZTRN與站臺有效面積SZTYX正相關,與站臺客流密度ρKL負相關。

式(4)中,NZTRN為站臺容納能力,人;SZTYX為站臺有效面積,m2;ρKL為站臺客流密度[6],m2/人。其中ρKL—般取0.33~0.75m2/人,綜合考慮站臺利用率及乘客安全,通常情況下取0.75m2/人。
以列車行車間隔為時間段,考慮站臺最大程度擁擠。假設乘客均遵守“先下后上”的乘車規則,則當列車車廂內所有下車乘客剛好下完未乘坐樓扶梯疏散,同時上車乘客還未上車,此時站臺乘客最多最擁擠。對于島式站臺考慮極端情況——2個方向列車同時到達,對于側式站臺主要考慮大客流方向。
當站臺客流密度ρKL分別取0.33m2/人、0.5m2/人和0.75m2/人時,早高峰車站S各站臺容納能力富裕度如圖5所示。L3在車站S的站臺P3,站臺面積及有效面積小,站臺容納能力不足;L5在車站S的站臺P5E和P5W,站臺面積及其有效面積較大,且2個方向客流無交叉,站臺容納能力基本滿足需求。

圖5 早高峰小時車站 S 各站臺容納能力富裕度分析
2 評價指標與模型
2.1 評價指標
根據對換乘站運營設施能力的分析,建立的評價體系分為2層:第1層共3個指標,第2層共7個指標,如圖6所示。
2.2 模糊綜合評價模型
城市軌道交通換乘站運營設施能力與客流的匹配性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其影響因素是多方面的,各影響因素的權重也略有差異。為了恰當地評價換乘站運營設施能力匹配性,利用模糊數學原理,從進出站設施、換乘設施以及上下車站臺3個方面,建立換乘站運營設施能力匹配性的模糊綜合評價模型。

圖6 城市軌道交通換乘站運營設施能力評價指標體系
2.2.1 建立因素集
設因素集U是城市軌道交通換乘站運營設施能力評價指標體系第1層的3個指標的集合,U={U1,U2,U3},其中U1、U2、U3是U的子因素集,分別表示進出站運營設施能力匹配性、換乘樓扶梯能力匹配性和上下車站臺能力匹配性。
設因素集u是城市軌道交通換乘站運營設施能力評價指標體系第2層的7個指標的集合,u={u1,u2,u3,u4,u5,u6,u7}。
2.2.2 建立評價集
設V是城市軌道交通換乘站運營設施能力評價集。V ={V1,V2,V3,V4,V5},其中V1、V2、V3、V4、V5分別表示對應的評價等級為十分富裕、富裕、匹配、不足、嚴重不足。
2.2.3 建立權重集
由于各評價因素對事件產生影響的輕重程度不一樣,所以需要建立相應的權重集。可視為因素集上的1個模糊集,模糊集由 m 個權重元素構成:w ={w1,w2,…,wm},滿足,wj≥0。
記第1層指標權重為W=(W1,W2,W3),記第2層指標權重分別為。
2.2.4 模糊綜合評價
單因素模糊評價是指從1個因素出發確定評價對象對評價集V的隸屬程度rki。本文構建的指標體系分為2層,因此需要進行2次分級評價。
(1)一級模糊綜合評價
記為單因素評價集,。則第1層3個指標的單因素評價矩陣分別如下:

記Pk為一級模糊綜合評價集,,其中“°”表示模糊算子,本文取M(∧,∨)。則這3個一級模糊綜合評價集所組成的評價矩陣R如下:

(2)二級模糊綜合評價
記Q為二級模糊綜合評價集,基于第1層指標權重W以及一級模糊綜合評價矩陣R,進行整體評價:

根據此計算結果,按照最大隸屬度原則來確定能力匹配性等級。選擇二級模糊綜合評價集Q中最大的模糊綜合評價指標所對應的評價集V中的等級,作為城市軌道交通換乘站運營設施能力匹配性評價的綜合評價結果。
3 案例分析
3.1 數據整理
模糊綜合評價是各因素權重和單因素評價的復合,因此權重確定至關重要,其方法主要有專家估計法、AHP法和頻數統計法等。由于對車站能力匹配性研究專業性較強,因此本文采用專家估計法確定權重。
基于城市軌道交通換乘站運營設施能力匹配性分析,采用專家估計法確定各級因素指標權重以及因素集模糊評價數據,分別如表5和表6所示。
3.2 模糊綜合評價
3.2.1 一級指標模糊綜合評價
基于第1層3個指標的單因素評價矩陣,分別計算模糊綜合評價集P1、P2、P3:


表5 各級因素指標權重

表6 因素集模糊評價數據統計
同理可得。

3.2.2 二級指標模糊綜合評價
基于以上3個模糊綜合評價集所組成的評價矩陣R,進行模糊綜合評價:

3.3 評價結論
根據計算結果,按照最大隸屬度原則來確定能力匹配性等級。對于一級模糊綜合評價集,分別選擇P1、P2、P3中最大值所對應的評價集V中的評價等級作為一級模糊綜合評價結果;對于二級模糊綜合評價集,選擇Q中最大值所對應的評價集V中的評價等級作為二級模糊綜合評價結果,也就是城市軌道交通換乘站S運營設施能力匹配性評價的綜合評價結果。
模糊綜合評價結果如表7所示,P1中最大值為0.55,則評價值為0.55,表示進出站運營設施能力匹配性評價等級為“富裕”;P2中最大值為0.50,則評價值為0.50,表示換乘樓扶梯能力匹配性評價等級為“匹配”或“不足”;P3中最大值為0.60,則評價值為0.60,表示上下車站臺能力匹配性評價等級為“不足”。整體上,換乘站S運營設施能力與客流匹配性為中等偏下;具體而言,換乘樓扶梯能力匹配性較弱,上下車站臺能力不匹配。
3.4 改善措施
基于以上分析,換乘車站S運營設施能力匹配性較弱的關鍵在于車站換乘客流大,換乘樓扶梯能力略有不足,以及上下車客流較大,站臺面積小,站臺容納能力不足。因此,可以從樓梯改造、擴大站臺面積以及引導客流3個方面入手,對車站進行改善。
3.4.1 換乘樓梯改造
基于車站換乘樓扶梯疏散能力與實際客流的匹配性分析,薄弱之處在于站臺P3與P5W之間,其換乘方式包括2組1m寬扶梯和1組1.4m寬樓梯。由于同等寬度下,樓梯的疏散能力遠小于扶梯,因此,可利用這1組1.4m寬的樓梯,將其改造為扶梯,或者利用該面積將2組1m寬扶梯更換為1.2m或1.4m的更寬的扶梯,提高兩站臺間換乘扶梯的疏散能力。

表7 模糊綜合評價結果
3.4.2 擴大站臺面積
島式站臺P3面積小,上下車客流大。站臺上6組進出站扶梯以及4組換乘扶梯和2組換乘樓梯占據了很大部分面積,導致站臺可供乘客上下車活動的可使用面積小,且早高峰下車客流大、晚高峰上車客流大,使站臺容納能力嚴重不足。
因此,可考慮對車站S站臺P3進行擴建,在原有的島式站臺的基礎上,擴建1個側式站臺,形成“一島一側”,增加站臺面積,提高站臺容納能力。
3.4.3 引導客流
利用工作人員或者欄桿對客流進行引導,讓乘客按秩序乘車、候車、下車,減少客流沖突,以減輕站臺客流壓力。
4 結束語
城市軌道交通換乘站運營設施能力匹配性是提高車站運營服務質量的先決條件。對其進行有效的評價,找到能力的薄弱環節并進行改善,有利于車站提供更好的服務。以車站S 為例,根據城市軌道交通換乘站運營設施的特點,構建了換乘站運營設施能力匹配性評價指標體系,并建立了相應的模糊綜合評價模型。經過詳細的分析,結果表明該評價方法具有一定的實用性和可操作性,可為城市軌道交通優化改造提供依據,對提高車站運營服務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1]張馳清. 城市軌道交通樞紐乘客交通設施服務水平研究[D]. 北京:北京交通大學,2007.
[2]牟能冶,張錦,陳菊. 城市軌道交通規劃模糊綜合評價方法研究[J]. 鐵道運輸與經濟, 2007,29(1):60-62.
[3]Kittelson,Associates Inc.Transit capacity and quality of service manual 2nd edition[M]. Washington DC: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2004.
[4]楊梅,徐瑞華. 城市軌道交通換乘客流組織的仿真[J]. 城市軌道交通研究,2011,14(9):48-51,78.
[5]白雁,韓寶明,干宇雷. 城市軌道交通換乘站布局綜合評價方法研究[J]. 都市快軌交通,2006,19(3):30-33.
[6]馬德芹,藺安林. 地下鐵道與輕軌交通[M]. 四川成都: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