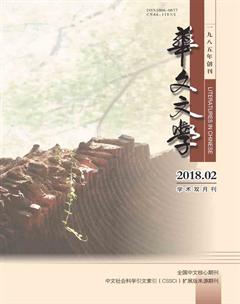美國華裔文學中的“越界”文本
唐書哲
摘 要:全球化語境下人口的跨國流動加劇了族裔混居和文化混合現象。同時,隨著華裔生存經歷和體驗的改變以及華裔作家的創作轉向,華裔文學中出現了一批超越傳統華裔文學邊界的“越界”文本。這些“越界”文本或超越了華裔文學的傳統主題,或呈現出“作家的身體”和“文本的身體”之間的差異,對華裔文學的傳統邊界及華裔文學批評提出了挑戰。論文借用巴赫金的邊界思想和德勒茲“根莖”的概念,對華裔文學中的“越界”文本進行討論,認為華裔文學應當放開邊界,將“越界”文本納入其中,在解轄域化的過程中增強異質性和生命力。這種做法也是與華裔文學反種族主義的精神是一致的。
關鍵詞:華裔文學;邊界;“越界”文本;根莖;解轄域化
中圖分類號:I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677(2018)2-0052-08
引言
2008年,最佳亞裔小說獎被授予白人作家楊科(James Janko)的《水牛男孩和杰羅尼莫》(Buffalo Boy and Geronimo, 2006)。小說以越戰時期的越南邊境地區為背景,通過一位奇卡諾軍醫和越南少年的交替敘事,再現了越南的風土人情及美越人民之間微妙的態度。楊科的這部小說無論從作家的族群身份還是作品的內容來看,都難以稱得上是嚴格意義上的美國亞裔文學。楊科的獲獎引起亞裔文學研究界的一片嘩然,珍妮弗·何(Jennifer Ho)以楊科獲獎為切入點,討論了亞裔文學中的“越界”書寫現象。楊科獲獎挑戰了亞裔文學的傳統邊界,是跨國語境下愈益異質化的亞裔文學的一個縮影。從上世紀60年代末誕生以來,美國亞裔文學一直是一個充滿張力和異質性的概念,不斷經歷著重劃邊界的過程①。蘇珊·科賽(Susan Koshy)指出,“美國亞裔文學是一個極其不穩定的、暫時性的和未完成的概念,它會隨著新的移民群體的到來而不斷變化”。②1965年移民法案就導致了亞裔作家族裔構成上的變化。③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劇,人口的跨國流動和族裔混居現象越來越多。加之亞裔作家創作轉型等原因,亞裔文學中出現了不少“越界”文本。④它們或超出亞裔文學的傳統主題,或呈現出“作家身體”和“文本身體”之間的差異,對亞裔文學的定義提出了挑戰。同樣的現象也發生在華裔文學內部。當前的華裔文學中有湯亭亭等經典華裔作家探討戰爭與和平等普適性主題的作品,有謝耀(Chay Yew)等新生代華裔作家以華裔同性戀情等為題材的作品,有哈金等新移民華裔作家⑤以白人為主人公的作品,還有加西亞(Cristina Garcia)等非華裔作家以華裔為嚴肅主人公的作品。面對這些“越界”文本,華裔文學是該維持現有邊界、固守現有疆域,還是該放開邊界、拓展其疆域?巴赫金對學科邊界問題的討論以及德勒茲以“根莖”(rhizome)為隱喻的邊界思想為這一問題提供了理論基礎。華裔文學應當放開邊界,將這些“越界”文本納入其中,在解轄域化的過程中增強異質性和生命力,而這種做法也和華裔文學成立時反種族主義的精神是一致的。
一、定義
要討論華裔文學中的“越界”文本,首先要確定華裔文學的邊界,因為邊界和越界相互依存,沒有邊界就沒有越界,只有越界才能證明邊界的存在。福柯指出,邊界是為越界而設置的,“如果某個邊界是絕對不可跨越的話,那么這個邊界根本無法存在;相反,如果跨越只是由影子構成的界限,這樣的越界也沒有意義”。⑥可見,邊界與越界是一種相互依存的關系,邊界需要跨越,而越界才能證明邊界的存在。華裔文學中的“越界”文本與華裔文學的邊界正是這樣一種辯證關系。國內外學界對華裔文學的定義基本沿襲金惠經等對美國亞裔文學的定義方法,從作家族裔、作品語言和作品題材三個方面來界定華裔文學。張子清對華裔文學的概念進行梳理,認為華裔文學是指有中國血統和在美國出生、成長、受教育、工作或生活經歷的華裔作家用英語創作的關于他們在美國生活經歷和體驗的文學作品。⑦華裔文學的這一定義有三條邊界:作家的族裔是華裔,作品的語言是英語,作品的題材是華裔在美國的生活經歷和體驗。這三條邊界對華裔文學進行結域,確定了華裔文學的疆域。當然,華裔文學的邊界和疆域一直存在爭議,在美國多元文化和多語言的社會語境中更是如此。金惠經認為亞裔作家用本族裔語言書寫的關于他們在美國生活經歷和體驗的文學作品也應當屬于亞裔文學。⑧吳冰也質疑華裔文學的語言邊界,認為美國是一個多元文化國家,華裔文學也應該包括華裔用漢語創作的關于他們在美國經歷的文學作品。⑨費希金(Shelley Fisher Fishkin)、索羅斯(Werner Sollors)、謝爾(Marc Shell)等也質疑美國研究和族裔文學研究中的語言邊界,認為應多關注非英語書寫的文學作品。⑩金惠經、費希金、吳冰等對華裔文學語言邊界的質疑就表現出某種程度的越界和解轄域化思想,試圖通過打開語言的邊界來破除華裔文學原有的畛域。可見,華裔文學創作語言的邊界存在爭議,界定華裔文學的核心在于作家的族群身份(這種族群身份往往與作家的族裔文化身份聯系緊密)和作品的題材,即作家要有華裔族裔身份,其創作應當再現華裔在美國作為少數族裔的生活經歷和體驗。本文對華裔文學創作語言這條存在爭議的學科邊界不多論述,以華裔作家用英語創作的文學作品為研究對象,重點從作家的族群身份和作品的題材與主題來論述華裔文學中的“越界”文本。
索羅斯用“異裝癖”(transvestism)喻指文學創作中的“越界”書寫現象,即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新教徒(WASP)作家冒充非WASP族群對該族群進行書寫。在索羅斯看來,這種族群身份的轉換拷問了人為建構的文化邊界,表明人們依然在圍繞種族、族群、性別、階級,以一系列復雜的形式進行文化邊界的建構。{11}索羅斯所說的文學創作中的“異裝癖”現象應當是一個雙向乃至多向的過程,白人作家可以以某一族群內部成員的身份,對該族群進行文學書寫,族裔作家也可以以白人族群內部成員的身份,對白人進行書寫,不同族群身份的作家也可以互相以其他族群內部成員的身份對該族群進行書寫。在《廢除美國文學研究中的種族隔離》一文中,費希金以非裔文學為研究對象,從作家的族群身份和作品題材兩方面提出了“越界”文本的概念,把“越界”文本定義為“非裔作家創作的以白人為嚴肅主人公的作品或白人作家創作的以黑人為嚴肅主人公的作品”。{12}按照邊界與越界的辯證關系,費希金對非裔文學中“越界”文本的定義暗示了非裔文學學科邊界的存在,而跨越這些邊界的文本便構成了相對于傳統非裔文學的“越界”文本。費希金指出,非裔文學的學科邊界是種族隔離思想在學術建制上的體現,非裔文學的創作和研究與主流文學的創作和研究各有自己的美學和批評范式:“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文學創作和研究呈現出一整套互相隔離的假設——白人作家的創作以白人主人公為主(便是提到種族問題也是處于邊緣的位置),黑人作家則著力刻寫黑人主人公(種族問題在文本無處不在并居于中心位置)”。{12}費希金認為,非裔文學中的“越界”文本質疑了學科建制中的二元對立思維和身份政治,在多元文化主義的語境中,文學研究應當跨越種族邊界,破除非裔文學和白人文學固有的畛域。費希金對非裔文學中“越界”文本的討論表現出明顯的解轄域化思想,要求打破學科邊界,破除非裔文學和主流文學間的對立,用對話的思想來取代隔離的狀態。她對非裔文學中“越界”文本的討論并不僅限于非裔文學,而是有著更為廣泛的批評關懷。費希金指出她在文中提出的問題不僅適用于黑人和白人作家,“也適用于其他族裔的作家,比如亞裔和墨西哥裔作家”。{12}鑒于費希金是從作家的族群身份和作品題材來界定“越界”文本,珍妮弗·何認為“越界”文本之定義的核心標準在于“作家身體”和“文本身體”之間的差異,即作家的族群身份和作品中主人公的族群身份之間的差異。{13}也就是說,作家的族群身份和作品中主人公的族群身份呈現出差異的文本都是“越界”文本——族裔作家以白人或非本族裔人物為嚴肅主人公或白人以少數族裔人物為嚴肅主人公的作品都是“越界”文本。索羅斯、費希金、珍妮弗·何對“越界”文本的討論和定義及定義背后所折射出的意識形態對探討華裔文學中的“越界”文本有啟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