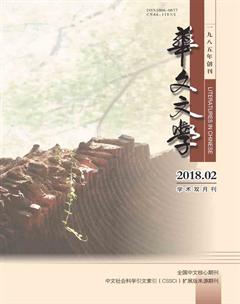亞裔美國女性的療傷之旅
董秋芳
摘 要:創傷書寫是鄺麗莎2015年小說《中國娃娃》的焦點。通過對3位亞裔女性的創傷敘事,小說揭示了父權、戰爭和種族主義帶給亞裔美國女性的傷害,而這樣的創傷敘事對于亞裔美國女性治療創傷和建構主體意義重大。
關鍵詞:鄺麗莎;《中國娃娃》;創傷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677(2018)2-0066-08
在當代美國華裔作家群中,鄺麗莎(Lisa See, 1955-)是非常特別的一位。她僅有八分之一的中國血統,卻始終堅持自己的華裔身份,懷著濃厚的中國情結筆耕不輟,自1995年發表《百年金山》以來,鄺麗莎已經公開出版了9部小說,全部都以中國或美國華裔生活為背景。作為《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上的知名作家,鄺麗莎深受讀者好評,其家族傳記《百年金山》發行后很快成為全美暢銷書,2000年被改編為歌劇在洛杉磯上演,在華裔中反響熱烈;《花網》(1997)曾獲愛倫坡獎提名;《雪花秘扇》(2005)吸引了近百萬讀者,被翻譯為包括中文在內的35種語言,并于2011年被美籍華人導演王穎搬上熒幕;《上海女孩》(2009)和《喬伊的夢想》(2011)也廣受讀者歡迎。
《中國娃娃》是鄺麗莎2015年的作品,該書由蘭登書屋出版后,迅速登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書榜單,被《華盛頓郵報》評為“年度最佳書籍”。小說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背景,主要記述了3位熱愛舞蹈的亞裔女性格蕾絲、海倫和露比追尋夢想的曲折經歷。通過對這3位亞裔女性的創傷生活的描寫,小說表現了創傷的持久性影響和創傷運作的心理機制,治療創傷的藥方自然地被融入到她們的奮斗歷程中。目前,國內外對這部小說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國外僅有少量書評,國內還鮮有學者公開發表與之相關的研究成果。本文擬以創傷理論為參照,從表征創傷之痛、尋求解決途徑和實踐創傷寫作等方面解讀《中國娃娃》,揭示小說對于美國亞裔女性治療心理創傷、建構主體等方面的獨特價值。
一、創傷之痛
從20世紀末開始,“創傷理論”作為一種新的知識話語和研究范式被國內外學者廣泛關注。在《沉默的經驗》中,美國學者卡魯斯將創傷定義為“對某一突發性或災難性事件的沉痛經歷”。①而國內學者陶家俊則認為創傷理論的當代核心內涵是:“人對自然災難和戰爭、種族大屠殺、性侵犯等暴行的心理反應,影響受創主體的幻覺、夢境、思想和行為,產生遺忘、恐怖、麻木、抑郁、歇斯底里等非常態情感,使受創主體無力建構正常的個體和集體文化身份”。②在《中國娃娃》中,3位敘事主體格蕾絲、海倫和露比都是創傷性事件的受害者,種族主義、戰爭暴力和父權制的合謀使得各種創傷后應激障礙在她們身上集結,主體難以得到解脫和救贖。
第一位敘事者華裔女性格蕾絲是父輩所遭受的種族暴力和父權統治下的犧牲品。格蕾絲從小乖巧伶俐,放學之余努力做工幫扶家用,但她和母親卻長期遭受父親毒打,其原因非常復雜。格蕾絲的父親原本是一名出生于美國的華裔礦工,地位低下,母親出生于中國,被拐賣至美國,因其華裔身份無人收養而淪落風塵,從良后與格蕾絲的父親結婚。這對華裔夫婦婚后生活艱難,深受白人歧視。格蕾絲出生后,他們搬離舊金山,來到俄亥俄州的普萊恩城,以開洗衣店為生,成了小鎮唯一的一戶華裔居民。格蕾絲的父母之所以搬遷到內陸,是因為他們決心要擺脫華人世界,完全像白人一樣生活:只說英語、不說漢語,只吃西餐,不吃中餐,定期去教堂,只和白人來往。“父母將自己與華人世界完全隔絕開來,全力融入白人的世界”。③當代美國亞裔學者安林·成(Anne Anlin Cheng)認為:
“美國的自由、民主和進步意識形態掩蓋了白人/黑人/亞裔之間種族認同的抑郁創傷。主流的白人政治話語建構的美國民族認同,以對黑人、亞裔等種族他者的抑郁癥式內并、憎恨和排斥為底色。作為種族他者的少數族裔之主體建構,也以對種族自我身份的抑郁癥式憎恨和責難為基礎”。④
格蕾絲的父母以種族自憎的策略來應對種族主義歧視,他們隔斷與族群的聯系,試圖抹去自己的華裔身份,將自己改造成精神層面的“白人”,目的是希望得到白人社會的接納。但是,這種努力收效甚微,一家三口依然被小鎮居民視為另類的“中國佬”,父親遭受的羞辱格外突出,格蕾絲的母親曾這樣對格蕾絲描述父親的悲劇:“你父親在這個國家毫無尊嚴可言,在這里,中國男人根本就不被當成男人,他永遠都只是被看作做著女人工作的洗衣工”。⑤趙健秀等在《哎呀!美國亞裔作家文集》前言中就曾指出亞裔美國男性歷史實際上是被“閹割”的歷史,是被美國主流社會“邊緣化”、“女性化”的歷史,而這種來自種族主義的歧視和迫害使得亞裔男性“處于一種輕視、排斥自我和精神崩潰的狀態”。⑥格蕾絲的父親便是如此,但壓垮他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母親曾經的失貞。盡管父親和母親結婚時已經知道了她過往的歷史,卻無法對此真正釋懷。在父權社會中,女性的身體與性屬于男人和家庭,男性主體身份的穩定性要靠女人的貞操來構筑和凝聚,妻子的失貞會嚴重影響該男子的榮譽以及他的社會地位,因此,對男性來說,妻子的貞潔至關重要。“父權文明把女人奉獻給了貞操”。⑦隨著女兒日漸長大,身體逐漸發育,他愈加擔心女兒可能會重蹈母親覆轍。父親走不出心理創傷,暴躁易怒,成為精神分裂者,將仇恨的拳頭揮向了自己的愛人和女兒。
家庭暴力給格蕾絲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創傷。父母最初對她隱瞞了過去的經歷,她完全不理解父親為什么經常暴打母親和自己,內心充滿了驚恐。卡魯斯指出,創傷事件因其暴力的本質和駭人的破壞性而具有不可理解的特征,在發生當時不能被充分地體驗或吸收,只能“延遲性地”表現在它持續的、侵入式的返回上。⑧17歲時,格蕾絲在遭受了一次毒打后逃到了舊金山,盡管自此她在地理空間上遠離了父親,她依然無法消除心中的恐懼,如驚弓之鳥般脆弱。她時常夢到父親責罵她“一無是處”、用皮帶狠狠地抽打她,她渾身大汗地醒來,抱住頭盡力想把恐懼和無助趕出腦海。父親的暴力也直接影響到她與男性的交往。在與男友喬相處時,對方臉上的一點不愉快立刻能被她捕捉到;喬因為和別人起沖突差點誤傷到格蕾絲時,她害怕到嘔吐,進而渾身發抖,因為這讓她再次回憶起父親打她的經歷。數年后,父親去世了,她依然感覺“毒打給我的肋骨、手指和脊柱帶來的僵硬感、疼痛感永遠留在了我的骨頭里;只要受到一點威脅,我就開始膽戰心驚”。⑨
第二位敘事者露比是一名日裔“二世”⑩,她和父母之間由于文化觀念不同產生了激烈的矛盾沖突,而她對自身的美國身份的絕對認同也成為她二戰中所遭受的心理創傷的根源。露比的父母是第一代移民,雖然身在美國,卻心系日本,希望孩子親近日本文化。母親要求露比每天必須要上日語課、唱日本國歌、學習忠君、孝長和恭順為核心的日本精神,還經常教導露比如何做一名傳統的日本女人:走路時要采用小碎步、說話時永遠使用敬語、把未來的丈夫當成“主人”等等。但是,露比強烈認同自由獨立的美國精神、厭惡男尊女卑的日本文化。露比酷愛跳舞,為了在娛樂業發達的唐人街附近找到工作,她脫離親友,假扮華裔在“紫禁城”歌舞俱樂部工作。日本偷襲珍珠港后,美國政府公開宣稱要驅逐所有日本人。露比此時雖然對外宣稱自己是華人,內心卻惶恐不安,最終露比即將進入拍電影的錄影棚、馬上要實現成為電影明星的夢想時被FBI抓走,關進了位于猶他州沙漠里的日裔拘留營。盡管露比認為自己是美國人,但在美國白人和華裔眼中,她始終是一名“日本鬼子”(Jap)。
鄺麗莎在小說中審視了拘留營經歷對包括露比在內的整個日裔群體造成的集體心理創傷。美國的日裔移民在20世紀初已達10萬人,不同于早期作為“苦力”來到美國的華人,他們大都受過良好的教育,境遇比華人移民好得多。{11}但是二戰的爆發,尤其是“珍珠港事件”給日裔美國人帶來空前的災難,盡管日裔“二世”都出生、成長于美國,同其他美國人一樣地反對日本侵略者,仇日情緒依然開始在美國主流社會蔓延開來。當時,《洛杉磯時報》的一篇社論曾露骨地宣稱:“毒蛇總歸是毒蛇,不論它在哪里產蛋;一個由日本父母所生的日裔美國人依然是日本人,而不是美國人”。{12}羅斯福總統最終下令出于軍事需要關押在美日裔。近12萬日本人財產被無償征收,只帶著換洗衣物住進了拘留營。拘留營散布于美國的荒漠地帶,冬冷夏熱,條件艱苦,四周圍著鐵絲網和瞭望塔,有士兵執搶看守,人們的生活毫無隱私。凱·埃里克森{13}認為,集體創傷是指對社會生活基本組織的打擊,該打擊損壞了維系人們的紐帶,削弱了人們的團體感,破壞了組織之間的聯系、相應的價值觀和固定的社會關系。日裔美國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集體創傷。他們原有的家庭結構和社區團體被瓦解,過著噩夢一般的生活。以露比一家為例,她的一個哥哥在夏威夷打魚時被美軍炸彈炸死了,她的叔叔全家、另一個哥哥和她被關進了位于猶他州的托佩茲拘留營,父母則因被懷疑是間諜關進了看守更加嚴密的地方。昔日完整的家庭四分五裂。面對突如其來的重擊,露比被迫反思自己的族裔身份:
“有時候我會來到鐵絲網邊盯著那無邊的沙漠。外面無處可藏,即使我逃出去,也只會活活餓死。我問我自己,為什么他們要這樣仇恨我們?我們究竟犯了怎樣無法寬恕的罪過需要把我們鎖在這樣一個地方?…早上我經過拘留營的學校時,聽見孩子們在背誦效忠美國的誓詞,還唱著‘上帝保佑美國”。{14}
露比和大多數被關押在拘留營里的日裔人士一樣,熱愛美國,認同自己的美國人身份。所以,被當作“日本鬼子”隔離起來,他們內心的傷痛是無法言表的。露比的哥哥因為無法忍受被猜疑的命運,主動報名參加了對日戰爭,用生命的代價向美國表明了自己的忠心。而露比被羈押兩年后才得到釋放。露比一家的悲劇折射出了戰爭背景下美國種族歧視政策所導致的日裔社群的集體創傷。
第三位敘事者海倫是一名華裔,她自幼成長于中華文化氛圍濃厚的唐人街,自然地親近華族傳統,認同華裔身份。海倫的家庭是非常典型的父權制家庭。她的父親是一名成功的商人,是整個家庭的經濟支柱和精神統治者,母親、哥嫂、海倫和后輩們都必須要聽從于他。在海倫家里,男女地位不同。雖然家境富裕,父親卻不允許海倫上大學,“哥哥們可以上大學,但是爸爸說‘女子無才便是德,我就只能呆在家里。我不能開車,不能露胳膊和腿,只能在家學學做飯、清潔、縫紉和繡花”。{15}16歲時,海倫的父親安排她回中國與素未謀面的蘇州富商之子來凱定婚,她欣然接受并在18歲時嫁回了中國。來凱是一名建筑師,他鼓勵海倫參與到他的事業中。海倫擺脫了壓抑個體和否定女性價值的唐人街后,逐漸意識到自己并不像父親說的“一文不值”。丈夫的鼓勵使她的女性主體意識逐步萌發,開始從長期的失語狀態中覺醒。
但是,二戰爆發后,海倫親歷了日本侵略者的殘酷殺戮,遭遇了嚴重的心理創傷,其創傷在父權制占主導的唐人街里無法得到救贖。1937年,日本侵略軍突然在杭州灣登陸,逼向南京。海倫和丈夫全家倉皇逃難。海倫的丈夫和兒子在她眼前被日本人刺死,她自己也慘遭日本士兵輪奸,僥幸逃脫后,爬行數十公里來到上海,在美國領事館的協助下,重新回到美國。在儒家傳統文化中,女性價值是通過照顧公婆、丈夫和為夫家生育男性后代來實現的。海倫從小在唐人街接受的傳統教育就是長大之后離開父母,結婚生子,照顧丈夫和家人。一夜之間,丈夫和兒子都死了,她失去了生活的意義。而整個華裔族群也未能給海倫提供治療創傷的環境,父母把重回大宅子的海倫當成“尷尬的存在”:
“來凱死后,我的生活跌入了深淵,日日都像置身于水深火熱之中。除了門羅,所有的家人,包括我的父母、哥哥都開始排斥我,視我為家族的恥辱。爸爸說作為一個被日本人輪奸過的寡婦,我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等死。沒有任何一個體面的中國人還會愿意跟我結婚,我是家族族譜里一個無用的分支。”{16}
不但家人排斥她,她以前的伙伴也不愿和她交往,海倫無處傾訴心理創傷,只能將其壓抑到內心深處。為了逃避創傷記憶所喚醒的負面情感如恐懼、害怕和焦慮,切斷不斷侵回的創傷記憶和痛苦感情之間的聯系,海倫順從地接受了父親的安排,每天由哥哥陪著走著到唐人街的電話交換中心上班,下班后又由哥哥陪著回家,過著固定而單調的生活。這種回避和情感分離能夠讓海倫不再反復糾纏于過去的噩夢中,但它會阻礙海倫與他人建立正常聯系,享受日常生活和計劃未來。而且她的創傷記憶只是暫時地被壓制在大腦的記憶深處,一旦相關的場景觸發了創傷機制,創傷記憶就會突然閃回。日本偷襲珍珠港后,海倫重新陷入了驚恐之中,終日擔憂日本人會隨時來襲。鄺麗莎以對海倫的境遇的書寫表明了父權制統治嚴重阻礙了海倫治療創傷。
二、療傷之旅
由于創傷記憶負載著痛苦的感情,受創者本能地要回避它,但是創傷記憶如果不經合理的途徑進行轉化或升華,會以噩夢的方式不斷地閃回,干擾受創者的生活。受創者要走出創傷,就必須要直面創傷,尋找途徑將創傷記憶從潛意識上升到意識,回到該事件中,設法將各種碎片整合起來以獲得對該事件的理解,{17}才能邁出創傷治療的第一步。鄺麗莎在小說中針對如何治療創傷提供了兩種基本的解決方案。
建立與外部世界的聯系是受創者復原的基本條件。弗洛伊德{18}在《悲悼與抑郁癥》中認為,受創的抑郁主體會拒絕恢復與外在現實正常的認同關系,長時間地陷入自責、沮喪、冷漠等心理情感,并排斥心理移情。赫爾曼{19}也認為,創傷使人們失去了對人性的信任,對家庭、朋友和社區的依附斷裂,自我建構認同坍塌,所以,重構受創者的自我意識、創建新的人際聯結是復原的關鍵。只有“在關系中”,創傷才有治愈的可能。赫爾曼在臨床治療中發現,如果幸存者能夠向其他個人或集體見證或講述自己的創傷經歷,“就有可能改變創傷記憶的非正常處理過程,而隨著記憶的轉變,創傷后應激障礙的很多主要癥狀都會緩解,由恐怖造成的軀體性神經機能癥可以通過語言得到扭轉”,{20}通過講述和見證,講述者和傾聽者之間形成了一種互動,這種互動不僅能夠幫助幸存者整合創傷經歷,還能夠提供一種認同感。這種認同感對于重建受創者與他人的聯系十分重要。在《中國娃娃》中,格蕾絲、海倫和露比的創傷能夠順利得到治療,與他人和集體的聯系密不可分。
首先,姐妹情誼在心理療傷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姐妹情誼”這一理論術語出現于20世紀西方后現代女權運動中,由貝爾·胡克斯{21}首次提出,意指女性在共同受壓迫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互相關懷、互相支撐的情感紐帶。不少美國少數族裔女作家都將姐妹情誼作為重要的書寫內容,黑人女作家愛麗絲·沃克的《紫色》、托尼·莫里森的《秀拉》和《寵兒》等都強調了姐妹情誼對于黑人女性爭取自己的權益起到的獨特的作用,而鄺麗莎在《雪花秘扇》、《戀愛中的牡丹》、《上海女孩》和《中國娃娃》中也持續表達了姐妹情誼對女性反抗壓迫、建構主體的重要性。這是因為身處父權制和白人文化的雙重壓迫下,少數族裔女性之間的愛和聯系可以成為她們謀生存、求發展的精神支柱。因為她們擁有共同的被壓迫的境遇,她們可以以父權制和種族主義為靶子站在一起并肩戰斗,分享苦難,互相汲取生存力量,對抗男性中心價值觀和白人至高論。正如小說中三姐妹之一的露比所言:“我們三個像吸附力強大的海洋生物一樣黏在了一起。這種感覺非常奇特”。{22}格蕾絲為逃避父親的家暴離開故鄉、來到舊金山時舉目無親,海倫熱心幫她在唐人街租房,使格蕾絲和露比有了安全的居所,后來格蕾絲離開唐人街、到好萊塢尋求發展時受盡白人歧視,海倫的到來和陪伴令她增添了堅持下去的勇氣;海倫失去丈夫和兒子、被親人孤立時,是格蕾絲把她拉進了歌舞俱樂部應聘,同露比一起教她學會跳舞,海倫才有機會通過舞蹈來接觸唐人街以外的大千世界,逐步擺脫舊日創傷陰影;露比被關進集中營后,海倫的來信給了她莫大的安慰。在生活中姐妹三人互相照應和關懷,精神上她們相互勤勉和撫慰。共同的亞裔和女性的身份背景使她們能夠認同彼此所遭受的壓迫,為創傷的治療提供強大的精神援助。
其次,加強與族裔群體的聯系有助于美國亞裔建構主體、治療創傷。美國少數族裔長期接受強勢的白人文化的熏陶,會因為自身所具有的種族特征而厭惡自己,內化民族自卑感,遠離族群,竭力迎合白人主流文化。但是這種種族自憎的策略不利于亞裔美國人的生存,只會加劇其傷痛。出于不同的原因,三姐妹最初都顯示出疏離族群的傾向,格蕾絲是由于父母刻意的隱瞞對華裔文化一無所知,海倫是因為戰爭創傷在唐人街被孤立,想要跳出華裔圈子,而露比則因自然地認同于美國人身份而想要擺脫日裔群體。但是遠離族群會導致美國亞裔的歸屬感和安全感的缺失。要改變這種狀況,恢復與族裔群體的聯系是必須的。小說中的“紫禁城”和“中國娃娃”這兩個歌舞俱樂部給格蕾絲和海倫提供了與族群共存的主要空間。在這兩個俱樂部里,大部分演員和工作人員都是華裔,他們共同致力于為展現華裔演員的獨特性、打破白人社會刻板印象而努力。無論是明麗泰的女高音還是馬杰克的魔術,技藝之高超都令臺下的白人觀眾“難以置信”,格蕾絲、海倫和同伴們在舞臺上專業而活潑的舞蹈徹底粉碎了華裔女性羞怯、沉默的形象,她們自己也因為觀眾的認可增強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而露比原本完全否認自己的日裔身份,被關進拘留營后,每天都和自己的日裔同胞生活,看到數以萬計的日裔在拘留營的悲慘境地,她內心悲痛難忍,開始學會從以母親為代表的日本文化中汲取力量:“請你永遠記住,白鬼聽不懂我們是哭還是笑,因為他們從來不把我們當人看。保持游戲的心態,很快你就可以展翅高飛、笑對過去”。{23}
最后,當亞裔女主人公超越族裔的藩籬,思考戰爭和種族主義給其他種族和整個人類帶來的巨大傷害時,個體的苦難在對他人和他族的關愛中得到升華。海倫在中國被日本侵略者殺死了丈夫和兒子,內心充滿了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美國對日宣戰后,她努力為戰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除了直接到醫院里去幫助護理戰爭中受傷的傷員,即使是外出巡演,她也盡力援助抗日戰爭:“海軍發布消息說需要O型血,我安排所有的演出團成員到伯明翰當地的紅十字會去捐血;在蒙哥馬利縣時,我看見有人擺攤售賣戰爭債券,我號召大家到旁邊的人行道上唱歌跳舞,希望能吸引更多的人來買”。{24}走出唐人街后,海倫還把關注的目光投向了種族之外,她外出巡演的演出團里有幾名黑人演員,“許多州專門針對黑人實行了宵禁,半夜之后有不少區域不允許黑人進入”。{25}海倫對黑人所遭受的種族歧視十分同情,她主動幫他們購買食物和飲料,解決生活中的實際困難。卡魯斯{26}曾指出,創傷本身可以提供跨文化連接的橋梁,海倫用自己的善良和同情心將身陷創傷中的個體聯結在一起,超越了種族、階級和性別的界限,在相互的關愛中一起應對創傷。海倫在與他人的聯系中,也重塑了自我,從一個封閉、無助的受創者成長為獨立、堅強的主體。
與外部世界的聯系為創傷復原提供了前提條件,而創傷敘事則是受創者緩解和治療創傷的決定因素。赫爾曼{27}認為,創傷記憶是“無語靜默的”,通常在“行為重演、噩夢或閃回中”展現。由于創傷經歷往往超出了人們日常生活經驗的理解,受創主體會本能地將它壓抑到潛意識中。創傷研究的鼻祖弗洛伊德{28}率先認識了創傷敘事的作用,指出敘事能夠引導意識和激發潛意識,把“談話療法”(talk therapy)作為治療心理疾病的一種基本方法。創傷敘事能夠幫助受創者把創傷經歷從無意識轉到意識、探究和理解事件的成因和內涵;在敘事的過程中,受創者能從自己的角度重構事件的過程,從而找到有意義的關系和有價值的生活。因此,臨床醫學大量采用引導受創者回憶和講述創傷經歷的方法來治療心理創傷。小說中,露比和海倫的創傷治療都受益于創傷敘事,但是,她們的創傷敘事呈現出不同的特點。
露比的創傷敘事是對話式的,具有強大的交流功能,所以,她的創傷復原之路非常順利。作為少數族裔,她同兩位華裔姐妹一樣遭受了種族主義歧視,找工作時只能找到女仆、餐館服務員和電梯看管員這樣的工作,但是,露比從不把受挫的經歷埋在心底,她選擇了把這些當成笑話講給好友聽。露比被關進拘留營后,她設法找到關在同一個拘留營的哥哥,兩人的溝通使他們意識到他們的遭遇并非特例,而是屬于所有日裔美國人的集體創傷。在關押期間,露比還不斷地寫信給海倫,將拘留營的非人生活和內心混亂、復雜的感受直接表達出來。在與哥哥和海倫的敘事交流中,她有機會去質疑美國政府大規模關押日裔美國人的公正性,而對方正面的回應也讓她的創傷敘事渠道保持了暢通,使得露比能夠對當時的創傷經歷進行客觀的審視和評估,對創傷保持積極的應對姿態。因為,在創傷敘事中,傾聽者的參與是至關重要的,對方的關懷和同情能夠給受創者以情感的慰藉。從拘留營出來后,露比坦然接受了自己的日裔美國人身份,不再刻意隱瞞,倍加珍惜獨立和自由,將近70歲時依然活躍在娛樂圈。
比起露比,海倫的創傷敘事更加曲折和隱蔽。在華日軍的戰爭暴行是海倫創傷記憶的原始場景,是導致她飽受噩夢、閃回和幻覺的干擾的根源。最初由于得不到家庭和族群的關懷,海倫的創傷無處宣泄,完全處于封閉狀態。走出唐人街后,海倫才有機會講述自己的故事。小說中海倫對自己的創傷經歷的描述有三次,第一次發生在她和格蕾絲、露比相識之初,“當時我住在中國,日本人進行轟炸的時候,我們…我是指我哥哥門羅和我正走在路上,我們看到飛機邊上紅色的太陽,聽到附近村里傳來的警報聲,然后眼睜睜地看著一個日本士兵端著刺刀向我們沖來。”{29}海倫第一次對她的創傷經歷的敘事是含混不清的,她當時為什么會住在中國?日本人向他們射擊后發生了什么?她之所以沒有進行深層的創傷敘事,原因有二:第一,她不能確認格蕾絲和露比是否為安全的見證者和傾聽者;第二,還不存在刺激她將創傷記憶轉化成創傷敘事的誘因。海倫第二次的創傷描述發生在日本偷襲珍珠港后,此時海倫再次有了兒子,出于對日本人的仇恨和可能再次因為戰爭失去兒子的恐懼,她向格蕾絲和露比首次講述了她幸福地嫁回中國、丈夫卻被日本人刺死的經歷,但是截止此時海倫還沒有把兒子慘死和自己曾被輪奸的經歷講述出來,因為這是她內心最不愿意面對的噩夢。小說結尾處,露比控訴海倫不應該向FBI揭發她時,為了得到好友的諒解,海倫才被迫揭開所有的秘密,來向露比解釋她為什么這樣仇恨日本人:
“刺刀刺穿了我們母子,那個士兵抽回了刺刀,大軍掛在了他的刺刀上。我的兒子死了,他才三個月大。他用他的小身軀救了我,而我卻只能眼睜睜看著。然后,那些士兵糟蹋了我…一個接一個…我快要死了,卻沒死。”{30}
這三次的敘事逐漸從破碎含混變得清晰、條理分明,通過循環往復、不斷修正和添加的追憶過程,海倫將碎片重整為完整的記憶,最終戰勝了自身的恥辱感和沉默,將創傷經歷用語言表達出來。廓爾克和哈特{31}認為,創傷得以治療和修復的標志之一,是受創者能夠講述他們的故事,回顧所發生的一切,并將其經歷納入自己的人生經驗之中。海倫曾這樣回顧過去:
“如果來凱還活著,我們現在應該有了好幾個孩子,住在我們自己的大宅子里,美滿恩愛。不過他要是還在,我永遠也不會有機會遇到格蕾絲和露比,我也永遠不可能會到俱樂部里去跳舞,不會和埃迪一起去好萊塢闖蕩,也不會有機會看到那么多美國的城市。”{32}
在這里,海倫盡管依然顯示出了對丈夫的懷念,卻已經將創傷記憶外化,基于現實的原則對創傷經歷重新進行評估,走出了創傷的陰霾。
三、創傷敘事之意義
鄺麗莎在《中國娃娃》中從格蕾絲、海倫和露比的視角追憶和再現了亞裔個體、家族和族裔的創傷歷史。這種以追憶和再現為核心的創傷敘事對于當今亞裔女性的現實生存意義重大。它不僅有助于亞裔美國女性建構自我,還承擔著重構族裔歷史、確立族裔身份的重任。
首先,美國亞裔女性作家及其作品中的主人公需要通過創傷敘事來表達自我、探尋身份和建構主體。威廉·布洛姆(William Bloom, 1990)指出:“身份確認對任何個人來說,都是一個內在的、無意識的行為要求。個人努力設法確認身份以獲得心理安全感。”{33}但長久以來,無論是亞裔美國男性還是女性都一直面臨著身份認同的困境,其身份的“間際性”(in-betweeness)令自身陷入了艱難的境地。這些人出生、成長、受教育都在美國,接受美國文化的熏陶,思想上傾向于美國的價值觀。可是無論他們美國化到何種程度,白人主流社會依然把膚色相異的他們當做少數族裔,他們既不是白人眼中的“美國人”,也不是本族人眼中的“自己人”。正如林英敏(Amy Ling)曾說:“從隱喻的意義上講,他們變成了拉爾夫·埃里森小說主人公那樣‘看不見的人。”{34}兩個世界之間的夾縫生存的創傷體驗令這些亞裔美國人感到困惑和挫敗,鄺麗莎也是其中一員,她曾在《百年金山》前言中提到:
“我所采訪的許多華人談及白種人的時候都用‘老番、番鬼、白人和‘白鬼這樣的字眼。往往會有人解釋說‘知道嗎,她和你一樣,是白種人。他們絕對不會知道我聽到這話的時候是多么驚訝。因為多年來在店里或是參加婚宴的時候,我以為我是華人。”{35}
同亞裔男性相比,亞裔女性身處雙重邊緣化的境遇。除了要面對美國主流社會的歧視,她們還要應對父權制的禁錮。為了打破束縛、表達自我,不少亞裔美國女性選擇了寫作作為創傷敘事的手段。華裔女作家湯亭亭、譚恩美、鄺麗莎等,在作品中不僅重寫了亞裔女性的創傷經歷,還在虛構和非虛構、編造和再造之中,大膽顛覆了白人主流社會和父權對亞裔女性的統治。湯亭亭的《女勇士》以講故事的形式描繪了幾位不同的華裔女性所遭受的種族與男權壓迫,抒發了她對這種雙重壓迫的憤恨,也展現了她從自我憎恨到反抗、最終確立自我身份的成長過程;譚恩美在《喜福會》中書寫了四對母女如何應對婚姻和生活的不幸遭遇,以此來表達華裔女性對過去和當下生存狀況的反思;而鄺麗莎的《中國娃娃》除了探討以格蕾絲和海倫為代表的華裔女性成功擺脫創傷、重塑自我的歷程,更首次在作品中把焦點投向以露比為代表的日裔女性,塑造出一個充滿反叛精神和斗爭意識、追求多元文化身份的女性形象。作家們通過寫作實踐改變了亞裔女性被噤聲的狀況,不僅為自己贏得了一定的話語權,也為解構和重構美國少數族裔身份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此外,鄺麗莎的創傷敘事對于重新構建亞裔美國歷史也起著重要的作用。托尼·莫里森指出:“掌握自己的歷史是非常必要的,要了解自己,人們必須首先了解他們的歷史。”{36}現代歷史代表了統治階級的利益,它是官方的、殖民的現代歷史,具有全知敘事、抽象和客觀的特點。處于被統治地位的群體如少數族裔的歷史盡管充滿了創傷,卻被官方歷史刻意地壓制和隱瞞。弗雷德里克·詹姆遜認為:“歷史是傷痛,它拒絕欲望,對個人和集體行為進行無情限制。”{37}鄺麗莎反對這種文化帝國主義的行徑,在《中國娃娃》中,她以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為切入點,重寫亞裔女性在二戰前后所遭受的種族、戰爭和父權制所帶來的創傷,以個體的、活的創傷敘事來對抗官方的檔案式記憶。對于親近華族文化的鄺麗莎來說,小說創作本身就是對亞裔創傷的表征。因為從書寫手段來說,小說能比歷史敘事更靈活地表現創傷。鄺麗莎通過整合、重新編輯現實中亞裔美國女性所面臨的矛盾和沖突,構造出了文學世界中的“事實”。這樣的事實表征不僅可以“解構主流社會廣泛認同的‘大眾所知的歷史,以文學的真實還原歷史的真實,破除種族刻板印象”,{38}還能將原本屬于亞裔個體的創傷記憶與集體的、世界的和整個人類的發展聯系起來,從而補充歷史真相,反思現實,建構未來。
四、結語
鄺麗莎的《中國娃娃》表現出反男權、反東方主義和反他者化的鮮明立場。鄺麗莎小說中的創傷敘事不僅能夠啟發亞裔美國女性進行自我身份建構,還能夠記錄歷史、修正歷史。此外,鄺麗莎以小說人物應對創傷的方式隱喻地指出,要治療創傷,必須打破孤獨和封閉,在與他人和世界的聯結中將隱秘、難以言說的創傷記憶逐步地轉化為創傷敘事,積極重塑自我、建構主體和客觀評估過去,才能走向創傷治愈之路,重拾共同抵御災難和邪惡的信心。21世紀,全球頻發暴力沖突和自然災害,人類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創傷體驗,對于如何療治創傷,鄺麗莎的《中國娃娃》給出了極有意義的啟發。
①⑧{26} 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1, p6, p3.
②④{18} 陶家俊:《創傷》,《外國文學》2011年第4期。
③⑤⑨{14}{15}{16}{22}{23}{24}{25}{29}{30}{32} Lisa See. China Doll.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5, p117, p288, p289, p272, p32, p185, p52, p215, p306, p307, p51, p356, p305. 文中所有China Doll引文為本人翻譯。
⑥ Frank Chin, et al. Aiiieeeee! An Anthology of Asian American Writers. Washington, D. C.: How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viii-xxviii.
⑦ 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鐵柱譯:《第二性》,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30頁。
⑩ 日本移民被稱為一世(Issei),他們的子女被稱為二世(Nisei),第三代為三世(Sansei)。
{11} 薛玉鳳:《美國文學的精神創傷學研究》,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48頁。
{12} 戴超武:《論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美國對日裔美國公民的拘留政策》,《日本問題研究》1997年第4期。
{13} Kai Erikson.“Notes on Trauma and Community”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Cathy Caruth, ed.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95, p187.
{17} 柳曉:《通過敘事走出創傷—梯姆·奧布萊恩九十年代后創作評析》,《外國文學》2009年第5期。
{19}{20} Judith Herman. Trauma and Recovery: The Aftermath of Violence-From Domestic Abuse to Political Terror. New York: Basic Books,1997,p14, p83.
{21} 貝爾·胡克斯著,曉征、平林譯:《女權主義理論:從邊緣到中心》,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頁。
{27}{31} 王欣:《創傷敘事、見證和創傷文化研究》,《四川大學學報》2013年第5期。
{28} 轉引自劉蕩蕩:《表征精神創傷 實踐詩學倫理—創傷視角下的〈極吵,極近〉》,《外國語文》2012年第3期。
{33} 萊恩·T·塞格爾斯:《“文化身份”的重要性—文學研究中的新視角》,樂黛云、張輝主編《文化傳遞與文學形象》,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31頁。
{34} 蒲若茜:《多元·異質·雜糅—論亞裔美國文學之族裔身份批評的分化》,《當代外國文學》2014年第2期。
{35} 鄺麗莎著,王金凱譯:《百年金山:我的美籍華人家族奮斗史》,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36} Philip Page. Dangerous Freedom: Fusion and Fragmentation in Toni Morrisons Novels.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5, p29.
{37} 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02.
{38} 蒲若茜:《華裔美國作家筆下的歷史再現》,《暨南學報》2009年第4期。
(責任編輯:黃潔玲)
A Healing Journey of Asian-American Women: China
Dol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uma Theory
Dong Qiufang
Abstract: Trauma writing is the focus of China Dolls, a novel published in 2015 by Lisa See. With its trauma narrative on three Asian-American women, the novel reveals the hurt patriarchy, war and racism have done to Asian-American women and such a trauma narrativ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sian-American women in healing their trauma and constructing subjectivity.
Keywords: Lisa See, China Dolls, trau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