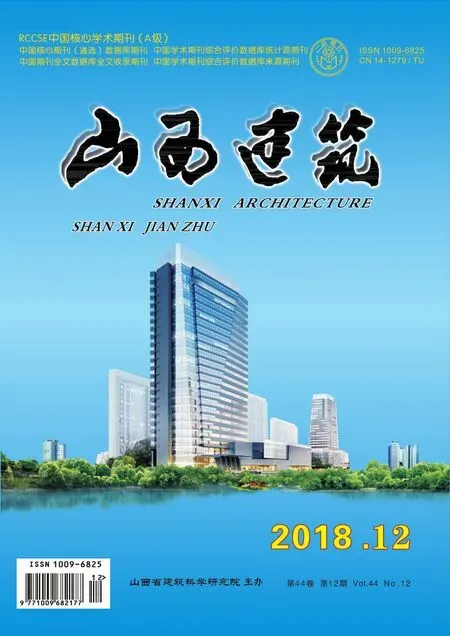以平遙為例談晉中地區市樓與城市空間關系
閆 順 凱
(中國建筑西南設計研究院,四川 成都 610041)
0 引言
晉中地區位于汾河谷地,是明清時期晉商活動的核心區域。該地區許多傳統城鎮保存有完好的歷史城市格局。區別于中國其他地區城鎮以鐘鼓樓為城市中心,晉中地區城鎮中心多為跨街而立的高大市樓,其中平遙市樓即為典型。市樓是比鐘樓更為古老的建筑類型,因位于市場之上而得名,是商業的象征。早在漢代畫像磚中即有位于街市中心的市樓形象記載(見圖1)。晉中地區市樓作為城市中心的標志物,對城市格局、街巷空間、商業氛圍均有重要影響。
1 平遙市樓選址與城市格局
平遙古城平面輪廓基本呈正方形,東西北三面城墻為直線,長各約1 500 m,南城墻沿中都河蜿蜒。與中國傳統城市十字街模式略有區別,平遙古城北大街與南大街稍有錯動,北大街位于古城正中,南大街則略偏東。南大街是平遙古時最繁華的商業街,亦是城市傳統中軸線,縣治、武廟、城隍廟、文廟等重要建筑于其左右對稱布局。在此基礎上,平遙古城于明清時期形成土字形分布的商業街,即南大街、東大街、西大街、衙門街、城隍廟街。平遙市樓跨立于南大街中段,即平遙商業街區中心。
中國傳統城市選址定向關注周邊地質、氣候,及山水資源。河流、水井等是城市的重要生產生活資源,因而成為城市選址的重要定位依據。平遙市樓的獨特意義在于其樓下有井,因而亦名金井市樓。在井田制社會中,井是人們生產生活的中心,并因其人群匯聚發展出交易行為,演化為市。高大華麗的樓閣強調出城中水井,形成“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的神性場所,將水井這一生產資源神圣化。金井市樓成為將城市錨固于一方大地的重要標志物。城市由此在原始自然環境中定位,產生基本的方位感。又因“市井者貨賄之所通,金幣之所聚”,水井亦強化了市樓的精神價值。金井市樓在當地人長期的生產生活中日漸成為重要的文化認同。
從今日平遙古城格局看,金井市樓偏于東南,但依平遙縣志記載,明洪武三年平遙城池曾向西北擴展。擴建前其西北邊界約位于今沙巷街、窯場街處,彼時南大街正是城池中軸,金井市樓亦位于平遙城正中,正符合“鑿井于中”的城鎮選址理念。可見此井對于平遙城的重要風水意義,金井市樓因而成為平遙古城的場所中心。即便金井市樓于清代已不是城市幾何中心,光緒年間的平遙縣志縣城圖中,市樓仍位于圖面正中。中國傳統縣志輿圖不追求比例尺寸的精確,而以抽象方式著重反映城市重要建筑、街道、周邊山水之間的空間與等級關系,是當時人們對所處地方空間秩序認知的形象化再現。由此可見平遙市樓作為平遙城市結構中最重要的標志點,始終是人們認知上的城市中心。
2 平遙市樓形制與街巷空間
平遙市樓為木質三層重檐歇山頂樓閣,高18.5 m,是平遙縣城內最高建筑,下方由8根木柱撐起。過街通道現今約4.5 m高,基本與街同寬。閣樓飾有華麗的斗拱與彩畫,屋頂南北兩側由黃綠兩色琉璃瓦分別拼出巨大的“囍”“夀”字樣。高聳的市樓構成平遙城舒展天際線中的高潮,聳立于廣袤的晉中平原。在街巷尺度,底層架空的市樓如同門與坊的演化,標示出南大街的商業地位。在更近尺度,市樓因其自身縱深,底部八棵金柱限定出市樓底部的停頓空間,并借由金井與碑刻建立起歷史地理記憶與當下地點的時空關聯,強調出局部場所的紀念性。

隨著歷代城市建設中路面的不斷抬升,平遙市樓于1963年修繕改造中將首層平座去除,抬升樓板1 m有余(見圖2)。與原造型相比,改造后市樓上部體量過于集中,比例欠勻稱。改造前首層屋檐下的平座是近距離尺度下市樓的重要視覺焦點,是南大街行人對市樓所供奉神靈近距離感知的重要平臺。改造后市樓頂層平座與路面相距較遠,市樓在近距離尺度下的標志物作用相對減弱。但另一方面,改造后上部集中體量的自我完型得到強化,下部基座掩于路面之下,使中間木柱缺失了頂部與底部的元素限定,存在感被弱化,增強了市樓騰空于街市之上的動勢。
晉中地區諸多傳統城鎮均有市樓存在,除木柱架空的形制外,還有一類為建在十字拱夯土臺上,例如清源縣(今清徐縣)西關市樓。清源市樓位于清源最繁華的西關十字街交叉口,重檐攢尖頂。因西關地勢顯著高于縣城,西關市樓成為城內比城門樓更突出的視覺焦點,是重要的方位標志物。因墩臺及十字拱對近距離的場所限定作用更為突出,平遙市樓與清源市樓均在大尺度空間里領導著城市空間秩序,但二者對街道空間氛圍影響不同。平遙市樓底層架空較高且由少量木柱撐起,與街道等寬的通道使市樓在近距離產生消隱,更具通過性;而清源市樓底層墩臺露于街道之中,大面積磚墻形成視覺停頓,夯土臺內十字拱交叉區域又形成穹隆般遮蔽空間,強化了場所的停頓性。

表1 晉中市樓對比
3 平遙市樓功能與城市商業發展
“市樓”稱謂在先秦文獻中即已存在。在中國早期里坊制城市中,市是由四面圍墻封閉并定時開閉的區域,居中建有高層官署建筑,即進行監管與報時的市樓。自北宋起,里坊制逐漸瓦解,封閉的坊市逐漸變為開放的街市。隨著明清晉商活動的興盛,通衢要道的沿街商業成為晉中城市的重要生活模式,市樓進而成為整個城市的中心標志性建筑。此時的市樓不再是秦漢時期的官署建筑,而成為祈愿商業興盛的精神性建筑,并在供奉神靈之余,兼具緝盜、報時、登高望遠的城市功能。
明清晉中市樓主要由當地商人、商鋪集資修繕,并立碑記傳。據清平遙縣志收錄的重修市樓碑記可知,市樓于清朝年間至少進行過五次大規模修繕,商人捐資隨商業繁榮而逐次增多。因地處通衢要道,市樓的華麗對外展示出當地商業的興盛,也展現出當地商會的團結。捐資修繕的行為展現出晉中商人對家鄉商業昌盛的共同祈愿,形成對家園的精神向心性與歸屬感。市樓在滿足保佑商業繁榮的同時,與中國諸多紀念性建筑相似,更融合了民眾的多重精神祈愿。平遙市樓內就供奉有關帝、觀音、魁星等諸多神像,進一步強化了市樓的精神價值。
4 結語
明清時期晉中商業重鎮,如平遙、太谷、孝義、文水、榆次、清源、徐溝等,均于城市最繁華處建有跨街而立的市樓(見表1)。作為晉中地區傳統城鎮的特色風水建筑,市樓是在明清時期晉中地區重商文化與發達建筑技術的基礎上,結合當地環境特質與當時晉商群體行為模式而形成的獨特建筑類型。在商業文明盛行的社會歷史環境中,保佑商業興旺的市樓成為城鎮的中心建筑,獨特的地理位置與精神意義相結合,成為控制城市格局的中心標志。市樓高大華麗的形制對城市空間產生重要影響,成為城市的重要標志物。市樓隨著商業的繁盛而參與到城市更新的進程中,并不斷演化精神內涵,成為明清晉中百姓生活中的重要一環。總之,晉中地區市樓是扎根地區與時代的建筑類型,與當地城市空間環境及人的生活模式有著積極而深遠的互動關聯。
參考文獻:
[1] 王綏修,康乃心.康熙重修平遙縣志[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20-23.
[2] 董培良.平遙文史資料(第二輯):平遙古城現存歷代碑記輯錄[M].平遙:政協平遙縣委員會,2000:156-163.
[3] 郝岳才.尋找母親的平遙[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23-49.
[4] [挪]諾伯格·舒爾茲.場所精神──邁向建筑現象學[M].施植明,譯.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0:10-22.
[5] 裴 欣.明清商業影響下的晉中地區市樓研究——以平遙為中心的考察[J].西安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1):35-38.
[6] 張 楠.從旗亭到鐘鼓樓——由市的變遷析市樓演化[J].新建筑,2015(4):116-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