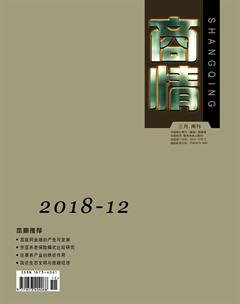環境規制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研究
陳紅
【摘要】本文從國家層面和企業層面理論分析環境規制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國外環境規制指標顯著影響我國對外投資的決策和規模,表明我國OFDI尋求污染避難所,國內環境規制強度則不然。中國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除了環境規制在投資決策和投資規模中都同樣重要以外,以尋求自然資源為目的。對于發達國家的投資則不在于自然資源,在更加發達的制度環境中.對投資規模的影響也更大。當然,中國OFDI也表現出一些共性決定因素:雙方市場的增長潛力則不在決策范圍之內:經典引力模型中的變量對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決策和規模都有顯著的影響。
【關鍵詞】環境規制;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
1978年改革開放,外商進入中國市場,中國經濟迅速發展,與對外貿易一起促進了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發展,規模不斷增長。王永欽等(2014)認為全球化是一個雙向的過程,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也是積極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過程。資本流動方面,吸引了大量FDI的同時,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OFDI)也走向了世界。1999年開始,為進行經濟全球化,響應國家號召,我國企業OFDI由此增長。雖然2003年以后投資限定才對民營企業放松,但目前其投資已占一半。2013年以來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三大OFDI國家。由聯合國貿發會議《2014世界投資報告》可知,當年全球流量、存量中國依次占比為9.1%和3.4%。
投資規模的擴大也給環境造成了很大影響。日益凸顯的環境問題和經濟發展之問權衡,愈發引起各國政府的高度重視。所以OFDl與環境規制之間的相互作用引起了眾多學者的廣泛關注。隨著環境問題的日益沖突,根據污染避風港理淪,任力和黃崇杰(2015)認為污染型產業會從環境規制相對嚴格的國家轉移到相對寬松的國家,各國環境規制也越來越嚴格。目前中國經歷了經濟高速增長和嚴厲的環境降級,企業雖然面臨日益加強的環境標準,但仍依靠傳統生產技術。盡管修改并運用了全新的整個體系的環境法律,是環保技術問題的有利環境。但是中國企業,特別是中小型企業仍然依靠老式污染型生產技術,使得環保技術的應用之后于法律的變化。在經合組織中的國家的二氧化碳、能源和一些物質消耗強度指標依舊保持在最高狀態。隨著環境標準日益提高而有限的環保技術,中國企業尋求污染避難所的動機非常強。
中國在經濟方面的表現確實有目共睹,但碳排放也位列全球第一,造成國際社會對其標準施壓。在經濟轉型關鍵時候的中國,更需要將此壓力轉化為構建可持續發展經濟的動力,協調好對外直接投資、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關系。
之前學者重在研究諸如熟練勞動力和物質資本這樣的生產要素,發現在給定條件下,生產要素豐裕的國家能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資。在另一些文獻中,更為寬松的環境規制也被視為比較優勢的潛在來源。理論分析的過程十分簡單:污染企業為了減少生產成本,有動機將生產系統遷移到環境規制寬松的國家。再運用傳統H—O模型可以估計,環境規制寬松的國家將專業化生產污染密集型產品,反之亦然。但不同于要素稟賦理論,對所謂的污染天堂假說(污染避風港效應)檢驗并沒有顯著的影響。閻大穎(2013)以中國跨國公司在國外設立的分支為對象,基于市場尋求型動機、效率尋求型動機、自然資源尋求型動機和戰略資源尋求型動機的視角,研究影響OFDI區位選擇的因素,除了傳統的優勢因素,發現東道國經濟制度質量的影響最大。王永欽等(2014)則從制度性因素、稅收因素和自然資源因素的視角探討了中國企業的獨特性,為避稅和獲取資源,中國愿避開法律嚴格的國家,更注重政府效率、監管質量和腐敗控制。陶攀,荊逢春(2013)以企業異質性理論為研究框架,發現了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行為中的自我選擇效應,企業生產率越高,母國對外投資的數量越大。類似的,羅偉和葛順奇(2013)引入資本需求,以國家層面的數據對中國OFDI區位分布進行研究,中國OFDl傾向市場規模大、勞動力成本低、出口固定成本差異小二貿易成本高的國家或地區。王勝,田濤(2013)將研究的東道國分為經濟發達國家、資源豐裕類國家、新興經濟體及其他不包含資源豐裕類的發展中國家三類,發現我國對經濟發達國家的投資以市場規模和較低的貿易成本為主:對資源豐裕國家的投資則是雙方經貿的穩定性:而第三類國家擇優東道國投資自由程度和對外開放水平決定。同樣的,有學者(2009)使用中國FDI流入模式的省份數據,檢驗更少采用減排技術的公司是否更受環境規制省際差異的影響,結果證明省際差異顯著影響華人投資者,對運用相對先進技術的非華人投資者沒顯著影響。
邱立成,楊德彬(2015)則細化了研究對象,認為中國企業OF—D1的區位選擇之所以不符合傳統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原因在于,進行對外投資的主體,70%為國有企業,其擁有一種不完全遵從標準的獨特性。李宏兵和趙春明(2013)認為環境規制對發達國家的影響小于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他們利用中美制造業面板數據發現環境規制水平的提升有利于我國的出口,尤其在環保產業。在舍棄單一污染物衡量的環境衡量指標后,許和連和鄧玉萍(2012)采納綜合指數法測算環境規制強度,聯合探索性空問數據分析方式,發現我國省級FDI和環境污染都存在空間自相關性。地域上的“路徑依賴”特性形成各自的聚集地區,促進優化我國的環境質量,所以在中國天堂假說還有待觀察。
總的來說,目前的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現有文獻在環境規制對中國OFDI的影響研究還非常欠缺,目前的研究中國往往是接受投資的一方,但隨著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顯著增大,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因素與作用機制值得探究。其次,大多數文獻僅從國家或企業單一層面出發,存在局限性。現有研究所使用的樣本量常常較小,也沒有采取更詳細的基于企業層面的微觀數據。為我們深人了解我國企業OFDI的問題,研究人員已整理了豐富的相關數據以待使用。盡管有一些實證文獻已經開始研究中國企業OFDI的影響因素和發展趨勢,以及OFDI的動機、進入模式及影響機制,但目前環境規制對OFDI東道國區位選擇的影響的研究仍存在不足。
參考文獻:
[1]王永欽,杜巨瀾,王凱.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決定因素:制度、稅負和資源稟賦[J].經濟研究,2014(12)
[2]任力,黃崇杰.國內外環境規制對中國出口貿易的影響[J].世界經濟,201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