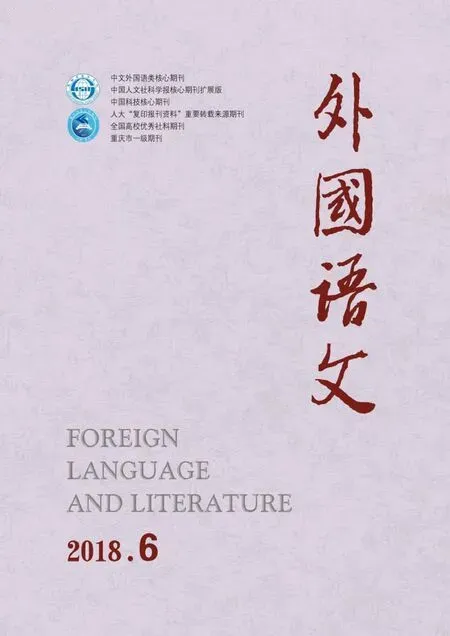古希臘語的“作詩”詞源小辨
劉小楓
(中國人民大學 文學院,北京 100872)

古典語文學家們追究的更多是poiētikē[詩術]的語義。這個語詞看似與以ikē結尾的形容詞衍生而成的名詞如aulētikē[簧管術]-politikē[城邦術]-rhetorikē[言辭術]沒有什么不同,其實不然。與“簧管”“城邦”“言辭”不同,poiē-的原初含義來自行為動詞poiein[制作](to make),帶有相當寬泛的作為意涵,如果直譯的話,poiētikē當譯為“制作的[技藝]”(省略technēs)[注]古希臘的“簧管”(aulos)是帶簧片的吹奏樂器,發音原理有如現代的單簧管,形狀雖類似蕭或笛子卻不是“簫”或“笛子”。參見威爾森,《奧樂斯在雅典》,戈爾德希爾 / 奧斯本編,《表演藝術與雅典民主政制》,李向利、熊宸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4年,第73-122頁。。有注疏家建議,最好將這個書名徑直轉寫為poietic [art],以保留“制作”(making)原義,突顯the poet的本義是maker[制作者]。據說,亞里士多德并未區分art[藝術]和craft[技藝],與此相應,所謂poiēsis[詩]實際指制作過程(the process of making)(Whalley,1997:44)。
1 作詩”與荷馬




17世紀的A. De Sommaville和A. Courbé的法譯本(1645)譯作enseigner[教給],1889年的P.-H. Larcher法譯本譯作décrire[描述],1913年的P. Giguet法譯本直譯為faire[制作],權威的Les Belles Lettres版中的Ph.-E. Legrand譯本(1930)譯作fixer[確立/擬定],晚近的A. Barguet譯本(1964)又譯作donner[給予]。
18世紀的J. E. Goldhagen德譯本(1756)譯作gemacht算直譯,但M. Jacobi譯本(1799)譯作dichteten[作詩]也算得上直譯,隨后的Adolf Sch?ll譯本(1829)同樣譯作gedichtet。半個世紀之后的F. Lange譯本(1885)譯作gebildet明顯是意譯,C. F. B?hr譯本(1898)和W. Marg譯本(1973)均譯作geschaffen,而A. Horneffer譯本(1955)和Josef Feix的希德對照本(1963)則譯作aufgestellt。可以看到,唯德語學界不斷有人譯為“作詩”:Heinrich Stein的箋注(1901)譯作gedichtet,H.-G. Nesselrath的最新譯本(2017)譯作dichterisch dargestellt,可謂信達雅兼備。
迄今,古典學家沒有發現公元五世紀之前的散文作品,僅有為數不多的歌體韻文作品。歌手與作歌者(后來稱為“詩人”)并未區分,所謂aeidō[誦唱]也可能包含“作歌”。古典時期之前,與“作詩”含義最切近的用法,僅見兩個孤例,而這兩個孤例恰好傳達了源于荷馬的古希臘“詩術”的兩個根本特征(Ford, 2012:132-133)
第一個孤例見于梭倫,他在表達人生情感時說,要從差不多一百年前的訴歌手米姆涅默斯(Mimnermos,活躍期大約在公元前630—600年間)的一首訴歌中“摘取”(meta-poiēson)一部分放進自己的訴歌中來“歌詠”。“摘取”這個復合動詞的詞干是“作”,但加上介詞后其含義就不是發明式的“造作”,而是相當于“拼置”(sun-tithenai,即拉丁文com-positio)。梭倫的這種訴歌“作法”當然是一種技藝,但并非技巧意義上的技藝,而是一種分享前人的人生情感和經驗的技藝。米姆涅默斯的訴歌深受荷馬影響,但他在傳承荷馬所表達的人生情感和經驗的同時,也添加了自己的在世體驗,某些方面甚至表達了不同的人生體驗(鮑勒,2017:16-22)。
第二個孤例見于忒奧格尼斯的訴歌,其中說到“編造謊話”(《忒奧格尼斯集》,713-714),動詞“編造”的原文即“作”(poiois),似乎作詩就是編造謊話。這種說法恰恰來自荷馬的《奧德賽》:奧德修斯返鄉后對妻子佩涅羅佩“說了許多謊話,說得如真事一般”,佩涅羅佩聽得淚流滿面(《奧德賽》,19.203-204)。人們有理由設想,荷馬詩作未必不是“說了許多謊話,說得如真事一般”,讓后人聽得淚流滿面。至少,后世的自然哲人的確因此而指責詩人。
2 “作詩”與蘇格拉底
與柏拉圖的作品相比,希羅多德的《原史》中出現的poiētēs[詩人]和poiēsis[詩]用法其實并不算多。在柏拉圖的作品中,不僅大量出現poiētēs[詩人]和poiēsis[詩]用法[注]Liddell希英辭典在poet一詞下列出的首位例詞作者是希羅多德,隨后是一連串柏拉圖作品。,何謂poiētēs和poiēsis也成了一個重大哲學問題。如果要說古希臘的詩學由此誕生,那么我們就得說,古希臘詩學的首要問題是:何以poiētēs和poiēsis會成為一個哲學問題。顯然,若不了解poiētēs[詩人]和poiēsis[詩]在柏拉圖那里何以成為一個哲學問題,就無從理解“作詩”一詞的語義。中古早期的阿拉伯學人用shā‘ir[詩人]來譯poiētēs,相應的動詞是sha‘ar[知道、覺察到],這意味著,“作詩”基于一種認知行為。海德格爾喜歡憑靠現象學-解釋學式的詞源學做大文章,按理他應該會對poiētikē[制作術/作詩術]的雙重語義感興趣,并利用這個語詞大做文章,但他沒有,頗令人費解。

蘇格拉底作為口頭詩人,成了他的兩位學生的寫作對象,而這兩位學生也因此成為著名詩人。就寫作方式而言,柏拉圖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哲學家,他的作品雖以蘇格拉底為主角,但還出現了大量有聲有色的其他各色人物,整個看起來有如希羅多德《原史》中的人物故事。柏拉圖的傳世之作一向被視為仿戲劇的擬劇,其實,這些作品更為突出的性質是紀事,有的作品敘事性還很強。稱柏拉圖為善于紀事的戲劇詩人,絕不為過[注]參見張文濤選編:《神話詩人柏拉圖》,董赟、胥瑾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0年;張文濤選編.《戲劇詩人柏拉圖》,劉麒麟、黃莎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0年。。
蘇格拉底的另一位學生色諾芬則主要以紀事體來記敘蘇格拉底的生平,他還追仿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續寫了雅典政治史。凡此都把我們更深入地引向了“作詩”與民主政治時代的關系問題。施特勞斯在閱讀古希臘的經典史書時曾有過這樣一則心得:

“索福克勒斯背后究竟隱藏著什么東西——恐怕同樣是哲學”,這話是什么意思?與古希臘人的“作詩”有什么關系?為了更好地理解古希臘語的“作詩”的源初含義,我們需要初步了解一下這個問題。
2.1 蘇格拉底問題與智術師
不妨先回憶一下希羅多德在《原史》中說的那句話:


第二處見于《普羅塔戈拉》,這次是希羅多德的老熟人普羅塔戈拉編的故事,但由蘇格拉底轉述。普羅塔戈拉在他即興編造的故事中說,世人的生存賴以憑靠的基本“技藝”,是普羅米修斯這個神族成員從兩位諸神即赫菲斯托斯和雅典娜那里偷來的(《普羅塔戈拉》,321c6-d3)。不過,普羅塔戈拉講這個故事的言外之意在于:普羅米修斯沒法替世人偷竊到最為重要的生存技藝即政治生活的技藝或“政治術”。言下之意,這門技藝得靠他普羅塔戈拉這樣的智術師“發明”出來。
普羅塔戈拉宣稱自己發明了“政治術”,我們斷乎不會想到,正是他的這一發明引發了“作詩”問題。在“普羅米修斯偷竊技藝”這個故事中,普羅塔戈拉沒有提到作詩的技藝,而從他善于制作故事來看,他顯然深諳作詩之道。什么是作詩之道呢?這是一種“智術的技藝”——既泄露又不泄露真相的技藝。不過,普羅塔戈拉頗為得意地對蘇格拉底宣稱,他要與古風詩人們的技藝傳統決裂:
我說啊,智術的技藝其實古已有之,古人中搞這技藝的人由于恐懼這技藝招惹敵意,就搞掩飾,遮掩自己,有些搞詩歌,比如荷馬、赫西俄德、西蒙尼德斯,另一些則搞秘儀和神諭歌謠,比如那些在俄耳甫斯和繆塞俄斯周圍的人。……所有這些人,如我所說,都因為恐懼妒忌而用這些技藝作掩飾。我呢,在這一點上可不與所有這些人為伍。(柏拉圖,《普羅塔戈拉》,315d4-317a1)
蘇格拉底隨即以既泄露又不泄露自己的高妙言辭警告普羅塔戈拉:在民主的雅典也得說話小心哦,謹防犯政治不正確的錯誤,吃不了兜著走。普羅塔戈拉表面上對蘇格拉底的警告滿不在乎,但在自己即興制作“普羅米修斯偷竊技藝”的故事時,仍然采用了荷馬傳統的既泄露又不泄露真相的作詩術。
民主的雅典以城邦公民的isēgoriē[平等議政權]為基礎,公民參政的政治權力的資格標準僅僅取決于他憑靠言辭說服公民大會同胞的能力(沃迪,2015:43)。普羅塔戈拉以為,既然如此,最為重要的政治技藝就應該是修辭術——這并非僅是普羅塔戈拉的看法,也代表了多數智術師的看法。因此,普羅塔戈拉在前面所講的普羅米修斯故事中暗示:發明政治技藝的是掌握修辭術的智術師(尤尼斯,2017:217-236)。
為了教育普羅塔戈拉,蘇格拉底也隨口編了一個關于熱愛智慧[哲學]的故事說給他聽(《普羅塔戈拉》,342a6 -343b3)。這個故事同樣具有典型的希羅多德風格,它不僅讓我們得以充分領略蘇格拉底的口頭作詩才能,也為我們理解古希臘詩學的起源與蘇格拉底的關系提供了決定性指引:在講過這個故事之后,蘇格拉底就對著名詩人西蒙尼德斯的一首詩做出了解釋,堪稱如今可以看到的最早的古希臘詩論。施特勞斯說,“索福克勒斯背后究竟隱藏著什么東西——恐怕同樣是哲學”——這句話有如謎語,理解起來很費解,蘇格拉底的這個希羅多德式的故事為我們揭開了謎底。(劉小楓,2015:213-278)
柏拉圖記敘的蘇格拉底與普羅塔戈拉的交鋒讓我們看到,蘇格拉底與“作詩”的關系,表面看來是與智術師的關系問題,實質上是與民主政治的關系問題。智術師大多與希羅多德是同時代人,而且與希羅多德一樣,都不是土生土長的雅典人,而是來自外邦:高爾吉亞( 公元前485—380)僅年長希羅多德一歲,普洛狄科(約公元前465—395)和希琵阿斯(大約生于公元前460年)則比希羅多德年輕差不多一代。這些來自異邦的智識分子在民主政治時代的雅典非常活躍,因為他們覺得自己的智識追求在民主政治中找到了用武之地(沃格林,2009:350-417)。反過來說,民主政治為哲學的繁榮提供了條件——如今天的我們也可以看到的那樣,民主的時代是哲學普及的時代。
由此可以理解,在雅典民主政治時期,出現了極為錯綜復雜的政治思想斗爭,這首先體現為來自外邦的智識人(智術師)與雅典戲劇詩人的關系。在索福克勒斯的劇作中,人們可以看到這位雅典詩人與智術師纏斗的思想痕跡,而論爭的焦點竟然是王者問題。但僅比希羅多德小幾歲的歐里庇得斯(公元前480—406)則幾乎成了智術師的學生,他筆下的主角不再是諸神、英雄或王者,而是市井女人、販夫走卒甚至奴隸,打造出如今所謂的“市民”劇主題,還以如今所謂的科學觀解構神話,借劇中人物咒罵諸神。[注]參見戴維斯,《古代悲劇與現代科學的起源》,郭振華,曹聰,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8年;阿倫斯多夫,《古希臘肅劇與政治哲學》,袁莉等,譯,崔嵬,校,北京:華夏出版社,2013年;羅峰編/譯,《自由與僭越:歐里庇得斯〈酒神的伴侶〉繹讀》,北京:華夏出版社,2018年。
諧劇本來比肅劇出現得更早,但長期僅是即興表演,沒有形成文字。諧劇詩人起初與智術師關系曖昧,后來出了個阿里斯托芬(公元前446—386 ),這位諧劇詩人對智術師和民主政治都討厭至極,在公元前411年上演的《地母節婦女》中鞭撻歐里庇得斯和阿伽通的“市民”肅劇,在公元前405年上演的《蛙》中,而且直接尖銳攻擊智術師的政治理想[注]Christopher Carey,“Old Comedy and the Sophists”,見David Harvey / John Wilkins編,The Rivals of Aristophanes: Studies in Athenian Old Comedy,London,2000,419-435頁;Christopher W. Marshall / George A. Kovacs編,No Laughing Matter: Studies in Athenian Comedy,London,2012,77-176頁;尤其Davis Konstan和Thomas K. Hubbard對阿里斯托芬《鳥》的解讀,見Gregory Dobrov編,The City as Comedy. Society and Representation in Athenian Drama,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8;28-43頁。比較James F. McGlew,Citizens on Stage:Comed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Athenian Democracy,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2。。由此可見,在雅典民主時代的巔峰時期,政治思想極度混亂。
蘇格拉底(公元前470—399)僅比希羅多德小十多歲,由于是土生土長的雅典人,他與外邦來的智術師們以及雅典詩人的關系,遠比希羅多德這個異邦人密切。畢竟,希羅多德待在雅典的時間并不長。由于在不少雅典人包括朋友如諧劇詩人阿里斯托芬眼里,蘇格拉底是個地道的智術師,他最終被雅典的民主法庭判處了死刑。蘇格拉底成為“[口頭]詩人”并由此促發古希臘詩學的誕生,與此有直接關系。由此可以理解,對于蘇格拉底的學生柏拉圖來說,為老師辯誣成了首要的問題。
在《泰阿泰德》中,我們可以讀到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關于智術師的一段說法:除了帕默尼德外,智術師與其眾前輩一樣,都是荷馬麾下的成員。他們都是詩人或“制作世界的人”,即根據屬人的視角設定的尺度或比率來制作世界,并否認有一個不依人的視角而存在的世界,進而認為無物曾“在”,因為,萬物無不永遠處于變化生成之中。
這種看法令所有這些聰明人——除了帕默尼德——都聯合在一起了:普羅塔戈拉、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以及每種詩歌中最優秀的詩人們,諧劇[詩人]如伊皮卡爾莫斯、肅劇[詩人]如荷馬,意思是說,萬物皆源出于流變與運動。
這話把自然哲人、智術師以及詩人一鍋煮,似乎智術師派的相對主義與萬物流變的本體論有內在關聯。鑒于蘇格拉底旗幟鮮明地反對相對主義(《斐多》,65d1-67b3,90b3-90d7),這句話興許也為我們理解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問題提供了指引。這意味著,要理解蘇格拉底問題,就得理解蘇格拉底與智術師和戲劇詩人的關系。由于智術師和戲劇詩人都與民主政治的興盛相關,這也意味著理解蘇格拉底這種人與民主政治乃至政治本身的關系。畢竟,蘇格拉底生活在民主政治興盛的時代。蘇格拉底在民主的雅典被判刑,究竟是因為他像個智術師,抑或因為他質疑民主政治的正當性,其實迄今仍然是個謎。
《泰阿泰德》是柏拉圖的一出三聯劇對話的第一部,以人物名字為題。開篇場景是泰阿泰德正被人從軍營抬回雅典,他在公元前369年的科林多戰役中身負重傷,還染上了軍中爆發的瘟疫。《泰阿泰德》主要記敘的是他年輕時的一次談話,似乎這次談話與他后來從軍的政治表現有什么關系似的。隨后兩部(即《智術師》和《政治家》)以人的身份為題,這三部對話都與澄清蘇格拉底被控告的原因有關(克萊因,2008:9-91)。《泰阿泰德》與《智術師》和《政治家》構成三聯劇,似乎泰阿泰德年輕時熱愛智慧,以后不是成為智術師,就是成為政治人。
“智術師”與“政治家”的聯結,則意味著“政治術”與智術即修辭術的聯結。因為,《政治家》中的對話涉及各種技藝與智術師的關系時(286b10-291c6),明顯與民主政治有關,而民主政治的重要特點是全民議政,這當然要求議政者懂得修辭。問題在于,在一個政治體中,并非每個人都對言辭或文字感興趣。為了實現真正的民主,就得強制每個公民對言辭或文字感興趣。如異鄉人所說:
如果我們強制我們所說的每一個遵守文字,又強制通過舉手或抽簽碰運氣選出的人掌管我們的文字,可這些人根本不關心文字,要么因為某種利益,要么因為私人的喜好,他們試圖做出違反它們的相反的事情,對此毫無知識,這難道不是比前面的壞事更大的壞事?(柏拉圖,《政治家》:299e3-300a7)
智術師屬于那類天生對文字或言辭有極大興趣的人,他們發明修辭術,為的是培養民主政制的公民。對于智術師來說,修辭術就是“制作”言辭的技藝,顯然,在民主政治的語境下,這種制作言辭的技藝大有用武之地。蘇格拉底熱愛智慧,但他恰恰不相信民主政治,從而不可能是個智術師。事情的復雜之處在于,雅典的公民也不喜歡智術師,但又分不清智術師與蘇格拉底那樣的熱愛智慧有什么差別。常人分不清智術師的追求技藝與蘇格拉底的熱愛智慧倒不奇怪,不可苛求,重要的是,熱愛智慧的蘇格拉底自己是否清楚自己與智術師的追求技藝有差別。因此,在《智術師》這篇對話中,我們會看到,如何區分熱愛智慧者與智術師是個很大的難題(郝嵐,2012,204-214)。讓我們多少會感到有些意外的是,恰恰在《智術師》這篇對話中我們碰到了poiētikē這個語詞,但其語義卻沒法譯成“作詩術”。



區分制作術的具體樣式時,異鄉人提到建筑術和繪畫術,卻沒有提到屬于制作言辭作品的“作詩術”,這是為什么呢?是否因為這里談論的制作術與“作詩術”是同一個poiētikē,從而沒法區分?
情形也有可能是,《智術師》這篇對話的基本主題是理解智術師,也就是看重修辭技藝的智識人。對話臨近結尾時,異鄉人對泰阿泰德說:

緊接著異鄉人就說,既然智術師是兩類造像術當中的一類,因此他希望:
抓住智術師共有的東西,直到剝離他身上一切共同的東西,留下他自己的本性[天性]。我們就可以展示這一本性[天性],首先展現給我們自己,然后展現給那類生來與這種探究最有緣的人看。(《智術師》,264e1-265a3)
異鄉人提醒泰阿泰德,他致力于展示智術師的“本性/天性”為的是“展現給我們自己”。這意味著“我們”作為熱愛智慧者應該對號入座,反觀自己的“天性”是否有點兒像智術師的“天性”。接下來的一句更有意思:“然后展現給那類生來與這種探究最有緣的人看。”這意味著,即便我們自己沒有這種天性,但世上肯定有人具有這類天性。如果我們不認清這類天性,我們就無法區分智術師與熱愛智慧者。
智術師的“本性/天性”是什么呢?在區分制作術與獲取術時,異鄉人就已經說過:
我們說,整個樂術、繪畫術、變魔術,以及其他許多關涉靈魂的技藝,從此城的某處收買,運往彼城的某處出賣——其轉運、出賣有的是為消遣,有的則出于嚴肅的目的——那么,把這些轉運、出售者稱為商人,不比稱那些販賣吃喝之物的人有欠正確吧。(《智術師》,224a1-7)
蘇格拉底在《普羅塔戈拉》中對傾慕普羅塔戈拉的年輕人希珀克拉底說過類似的話。在這里,異鄉人首先列舉“樂術”,而“樂術”庶幾等于“作詩術”,與“繪畫術”一樣屬于“關涉靈魂的技藝”。問題來了:既然所有屬人的制作術本質上都是“模仿”,作為“關涉靈魂的技藝”,“樂術”或“作詩術”以及“繪畫術”都是“模仿”靈魂的技藝,那么,模仿什么樣的靈魂——高貴的抑或低劣的靈魂——乃至模仿靈魂本身抑或圖像,就成了關鍵問題。這意味著,屬人的制作術——詩人或散文家也好、畫家也罷,都與屬神的制作品相關。
說修辭術等于欺騙術,是對智術師最為嚴厲的指責。我們值得問,在民主政治的語境中,智術師的修辭術究竟隱瞞了什么?施特勞斯在比較馬基雅維利與蘇格拉底的哲人德行時說過的一句話透露了關鍵要點:
色諾芬,這個蘇格拉底的學生,對政治的苛刻與嚴酷,對那種超越言辭的政治的要素不抱任何幻想。在這一至關重要的方面,馬基雅維利與蘇格拉底結成了一條對抗智術師的共同戰線。(施特勞斯,2012:308)
我們自己所熟悉的經驗也許能夠印證這一點:現代的普遍理想主義正是“對政治的苛刻與嚴酷,對那種超越言辭的政治要素”完全盲目。另一方面,施特勞斯又指出,馬基雅維利“隱瞞了”蘇格拉底的另一半,而且是“在色諾芬看來更好的一半”(同上,頁307)。要理解蘇格拉底的這一半,就得理解蘇格拉底與詩人的關系,而涉及這一問題最重要的柏拉圖作品莫過于《會飲》。恰恰在這篇作品中,柏拉圖讓我們看到,poiētēs[詩人]和poiēsis[詩]如何從poiētikē[制作術]中被區分出來。
2.2 游于藝:詩術抵制智術
如我們所知,這篇作品記敘了蘇格拉底與諧劇詩人阿里斯托芬和肅劇詩人阿伽通比誰對愛欲的理解更全面更深刻。按比賽規定,各位需制作一篇贊頌愛欲的講辭,比誰的講辭美。肅劇詩人阿伽通的講辭具有智術師的修辭術風格,十分優美,諧劇詩人阿里斯托芬則編了一個明顯虛構的故事,也很優美。
輪到蘇格拉底時,他講的卻是自己年輕時受女先知第俄提瑪教育的一段經歷。這聽起來像是在講自己的個人經歷,換言之,蘇格拉底用自己親身經歷的歷史故事挑戰肅劇詩人的智術式講辭和諧劇詩人的虛構故事。嚴格說來,我們無從確知,蘇格拉底講的這段受教經歷是否真有其事,抑或不過是編的一個故事。不僅如此,第俄提瑪的教誨也以講故事起頭:她首先講了愛若斯在宙斯的園子里誕生的故事——這顯然是個仿古神話。
然后,第俄提瑪轉入與學生蘇格拉底的引導性對話,她問蘇格拉底:
如果每個世人都愛欲而且總在愛欲同樣的東西,為什么我們不說每個世人在愛欲,而是說有些人在愛欲,有些人不在愛欲呢?(《會飲》,205a9-b2)
為了啟發蘇格拉底理解這個問題,第俄提瑪舉了一個例子:
無論什么東西從沒有到有,其原因就是種種制作(poiēsis)。所以,凡依賴技藝制作出成品都是制作品(poiēseis),所有這方面的高超藝匠都是制作者(poiētai)。
這個句子中出現的poiēsis顯然不能譯作“詩”,poiētai(即poiētēs的復數形式)也不能譯作“詩人”。但是,制作這個行當五花八門,制作者的名稱也五花八門。鞋子不是本來有的東西,有人憑技藝制作出鞋子,人們把這種poiētēs[制作者]叫“鞋匠”。同樣,人們會把憑技藝制作出房子的藝人叫“建筑師”,把憑繪畫術制作出一幅畫的藝人叫“畫師”。因此,第俄提瑪緊接著說:

這段話中出現的poiētai的語義起初仍然含混,譯成“制作者”或“詩人”都行,直到第俄提瑪明確界定憑靠“樂術和音步”制作,poiētēs的含義才明確為“詩人”。

但與希羅多德僅僅跟隨雅典人用poiētēs來稱“詩人們”不同,蘇格拉底從這一習稱引出了一個哲學問題:利用區分希臘文poiēsis的雙重含義(“制作”和“作詩”),第俄提瑪巧妙區分了不同品質的“愛欲”。世人都有欲求或者說人人都追求幸福,對幸福的欲求似乎都可以被稱為愛欲,但人們并不把所有人叫做“愛欲者”,就像世人的生存需要憑靠各種技藝的制作,但我們并不把所有搞制作的人都稱為poiētai[詩人]。畢竟,雖然所有人都有愛欲(欲求某種東西),但并非所有人都欲求美:只有欲求美才能稱為“愛欲者”,正如欲求美的制作才是“作詩”。我們應該能夠體會到,在民主時代的意識形態語境中,這種區分對有心的讀者有何教育意義。

柏拉圖的《會飲》僅展示了蘇格拉底嫻熟且高超的詩術,并未具體展示蘇格拉底所理解的作詩術原理。在《斐德若》中,柏拉圖不僅展示了蘇格拉底的作詩之術,也展示了蘇格拉底所理解的詩術原理,這兩部作品恰好構成所謂“愛欲”姐妹篇絕非偶然。
我們應該注意到,《斐德若》是蘇格拉底提到智術師最多的作品,尤其還提到智術師們傳授修辭技藝的手冊(書名往往就叫technai,即technē[技藝]的復數形式),相當于如今所謂的“文學寫作技藝手冊”(尼采,《斐德若》266c2-274b1;尼采,2001:14)。這類技藝不僅涉及如何謀篇布局,還包括如何設計吸引世人眼球的論題,比如,應該愛欲一個沒愛欲的人。由于智術師的這類“文學寫作技藝手冊”沒有流傳下來,今天的我們無從窺其原貌。不過,從《斐德若》中再現的呂西阿斯的愛欲范文來看,這類“技藝手冊”大致與如今種種后現代主義者談論欲望書寫一類的智術式文章差不多,不外乎把“抽象的制作”還原到常人的生殖水平——讀讀羅蘭·巴特的《戀人恕語》,也就能知道個大概。
有人會說,《斐德若》討論的是rhetorikē[修辭術],而非poiētikē[詩術]。按第俄提瑪在《會飲》中的說法,“詩”指守音步的樂體作品,從而poiētikē[詩術]似乎與探究演說技藝的rhetorikē[修辭術]不屬同一文類。但是,我們應該記得,《斐多》中的蘇格拉底說,他的“作詩”就是模仿伊索式的故事[敘事]。可見,對蘇格拉底來說,“作詩”并非專指守音步的樂體作品。《斐德若》中的蘇格拉底“作”了一首很美的“悔罪詩”,而且篇幅很長,這首“詩”明顯是敘事,而非守音步的“詩”。由此看來,如果在蘇格拉底那里有一種poiētikē[作詩術],那么,這種“技藝”明顯刻意與作為智術的修辭術作對。
智術師制作修辭技藝知識手冊旨在培育民主政治中的普通公民——尤其年輕人具有參政的技藝能力。在《斐德若》中我們可以看到,蘇格拉底對斐德若的教育,同樣意在培育他的參政能力(《斐德若》257d4-258b5)。柏拉圖讓我們看到,蘇格拉底采用的教育方式有兩種:首先是講故事即作詩,然后是引導性對話——專業術語稱為“辯證的交談”。由此可以說,蘇格拉底是以作詩的方式(模仿紀事詩人和戲劇詩人)來對付民主時代的智術,而柏拉圖的作品則是對蘇格拉底的施教行為的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