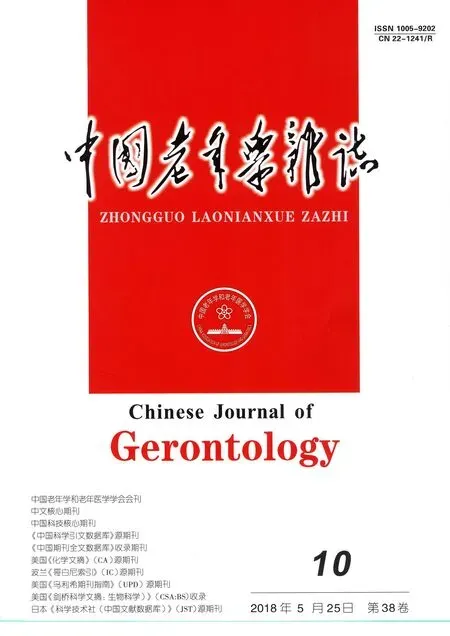房顫射頻消融術對老年心臟搭橋合并心臟瓣膜手術患者心功能的影響
滕 飛 張 強 孟國偉
(山東大學第二醫院,山東 濟南 250033)
冠心病與心臟瓣膜病變常同時存在,心臟瓣膜病變容易誘發房顫〔1,2〕,多次手術不僅增加患者的經濟負擔,也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3〕。單純的心臟瓣膜手術或心臟搭橋手術效果較差,而房顫只通過內科藥物治療或者只進行電復律治療效果均有待提高〔4〕。本文觀察房顫射頻消融術對心臟搭橋合并心臟瓣膜手術患者心功能的效果。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2013年6月至2016年7月山東大學第二醫院收治的心臟搭橋合并心臟瓣膜手術患者120例,納入標準〔5〕:①符合心臟搭橋、心臟瓣膜手術的手術標準;②符合房顫的診斷標準;③既往無心臟手術史;④心功能分級〔美國紐約心臟病學會(NYHA)標準〕≥Ⅲ級,左心室射血分數(LVEF)≤0.40;⑤資料完全;⑥患者意識清醒,自愿選擇并積極配合治療方案。排除標準:①具有其他器質性疾病或合并其他疾病;②惡性腫瘤,全身感染;③精神異常;④凝血功能異常;⑤失訪。患者均簽署知情同意書,且通過山東大學第二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將患者按照隨機數字表法分為兩組,每組60例。實驗組男32例,女28例,年齡60~72歲,平均(66.31±4.15)歲;病變類型:二尖瓣置換31例、主動脈瓣置換14例、主動脈瓣合并二尖瓣置換15例;LVEF(59.53±9.15)%。對照組男34例,女26例;年齡60~73歲,平均(65.86±3.52)歲;病變類型:二尖瓣置換29例、主動脈瓣置換16例、主動脈瓣合并二尖瓣置換15例;LVEF(60.25±9.26)%。兩組性別構成(χ2=0.135,P=0.714)、年齡(t=0.641,P=0.523)、病變類型(χ2=0.200,P=0.905)及LVEF(t=0.428,P=0.669)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1.2方法 患者均在手術前停用華法林,改用肝素(低分子)皮下注射,口服及靜滴強心、利尿藥,低流量給氧及營養心肌治療以改善心功能;并進行全身麻醉,整個手術在低溫體外循環下進行〔6〕。在胸骨正中切口暴露心臟,開胸后取左乳內動脈和大隱靜脈(備用)。肝素抗凝化后,行升主動脈、上、下腔靜脈或右心房常規插管,建立體外循環。當體溫降至30℃左右阻斷主動脈,阻斷后切開房壁探查左心房,然后采用Medtronic公司的雙極射頻消融系統行房顫射頻消融術(若房內存在血栓,則心臟停跳后進行)。冷血心臟停搏液經冠狀動脈順行或冠狀靜脈竇逆行灌注(若有中度以上主動脈瓣關閉不全,則將升主動脈橫向切開,直接從左右冠狀動脈開口灌注),并行冰屑心外降溫保護心肌〔7〕。具體消融方法〔8〕:先將右側上下肺靜脈鈍性分離,在尿管的引導下過射頻消融鉗,左房與肺靜脈交接1 cm處行射頻消融術,每消融完一處后,徹底松開消融鉗,稍微改換位置后再次行消融術,連續操作3次。相同方式行左側上下肺與左房交界處。切除左心耳,分別先后從左心耳切口和左心吸引處置入消融鉗,之后按如下消融順序操作〔9〕:①左心房后壁,左、右肺靜脈環狀消融;②左心耳與左側上下肺靜脈環狀消融;③左心耳到二尖瓣環狀消融;④左心房后壁及右下肺靜脈至二尖瓣環的環狀消融;⑤右心房界嵴、下腔靜脈口、右心房壁、右心耳、冠狀靜脈竇及冠狀靜脈竇至三尖瓣環狀消融。消融操作結束后,左心房反復沖洗后再行心臟搭橋手術和瓣膜置換或成形術。術后常規監測心率(術后早期維持在90~110次/min)、血壓、尿量等生命體征,并放置心外膜臨時起搏線,對于部分患者必要時予以臨時起搏,術后常規肝素抗凝,2 d后予口服華法林抗凝治療,注意及時監測凝血酶原時間,并根據實際情況調整劑量。出院前患者均至少行心電圖檢查一次,必要時可行24 h動態心電圖檢查。患者均隨訪復查6個月。囑患者門診每2個月復查心電圖1次,術后4個月行動態心電圖,若無房顫復發,之后門診每月復查心電圖1次。若發現患者房顫再次發作即予24 h動態心電圖檢查,如房顫再次發作≥15 min,可確診為術后復發。
1.3觀察指標 ①兩組手術情況,包括呼吸機使用時間、主動脈阻斷時間、加強護理病房(ICU)入住時間及住院時間、體外循環時間和恢復竇性心律的例數。②手術前后心臟結構指標(包括左心室舒張末期內徑、肺動脈收縮壓及射血分數)。③術后6個月心功能分級療效〔10〕:分為4個等級分別為顯效、有效、無效、惡化。心功能改善2級或者恢復到1級為顯效;心功能改善1級但未恢復到1級為有效;心功能無改善為無效;惡化即心功能惡化。總有效率=(顯效例數+有效例數)/總例數×100%。
1.4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9.0統計軟件進行t、χ2、U檢驗。
2 結 果
2.1兩組手術情況比較 兩組術中呼吸機使用時間、主動脈阻斷時間、ICU入住時間及住院時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實驗組體外循環時間和恢復竇性心律例數均顯著優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見表1。

表1 兩組手術情況比較
2.2兩組手術前后心臟結構指標變化比較 手術前,兩組左心室舒張末期內徑、肺動脈收縮壓及LVEF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6個月,兩組左心室舒張末期內徑、肺動脈收縮壓及LVEF均明顯改善,且實驗組改善幅度更大(P<0.05)。見表2。
2.3兩組術后6個月心功能比較 術后6個月,實驗組心功能分級療效(88.33%,顯效3例、有效23例、無效7例)明顯高于對照組(55.00%,顯效13例、有效20例、無效27例,u=4.187,χ2=16.416,均P=0.000)。

表2 兩組術前與術后6個月心臟結構指標比較
3 討 論
心臟瓣膜病變是一種不可逆轉的心臟器質性病變,常可誘發心力衰竭;冠心病是一種由冠狀動脈器質性狹窄或阻塞引起的心肌缺血缺氧或心肌壞死的心臟病〔11〕。心臟瓣膜病變合并冠心病伴有房顫患者通常需要心臟搭橋和心臟瓣膜手術同時進行。因合并有兩病的患者常無心絞痛等冠心病的典型癥狀,常常被漏診。超過50歲的心臟瓣膜病患者有必要做冠狀動脈造影〔12〕,以免漏診貽誤治療。心臟瓣膜病變容易誘發房顫,臨床研究表明,心臟瓣膜病患者有七成左右患有房顫〔13〕,而房顫可以使心臟瓣膜病變進一步加重。有學者報道,在心臟瓣膜手術中,若出現房顫將大大增加手術的死亡風險〔14〕。
臨床研究證實,房顫只通過內科藥物治療,或者只進行電復律治療效果均有待提高〔15〕。房顫射頻消融術是目前臨床最常用的除顫治療,其作用機制是將射頻電流轉化為熱能,高度集中的熱能使組織細胞脫水炭化,細胞和膠原纖維遭到破壞,心肌凝固性壞死產生不可逆損傷,形成連續、透壁的消融線,阻斷產生和維持房顫的折返環,從而達到根治房顫的目的。雖然心臟搭橋手術和心臟瓣膜手術的同時進行射頻消融術存在較大的風險,但同期行房顫射頻消融術手術時間短、創傷小、能有效降低心律失常風險,且對左房收縮功能影響較小,患者的康復與預后較好〔16〕。有研究表明,同期手術相對于單純瓣膜手術或心臟搭橋手術生存率較高,且可明顯改善患者心肌缺血的癥狀〔17〕。相關文獻的數據證明,單純瓣膜手術患者術后5年生存率僅有60.00%,而同期行房顫射頻消融術患者5年生存率可高達85.00%〔18〕。同期手術減輕了患者的痛苦,改善了患者的預后,提高了患者的生存率,提升了患者生活質量,是治療心臟瓣膜病變合并冠心病并伴有房顫患者的一種安全、有效的技術〔19〕。本研究說明同期行房顫射頻消融術更有助于患者恢復竇性心律并改善心功能,這與房顫射頻消融術阻斷了房顫的折返環密切相關,對于術后房顫短期內復發或者未恢復為竇性心律的患者應及時予以控制心率等對癥處理。本文說明同期行房顫射頻消融術對體外循環的依賴性更小。左心室舒張末期內徑、肺動脈收縮壓及LVEF均是反映心功能的結構指標,左心室舒張末期內徑越小、肺動脈收縮壓越低則左心室射血越充分,本文結果說明房顫射頻消融術通過使產生異常心律的心房部位心肌凝固性壞死,改善患者心律失常,心臟恢復原有的節律性,射血更加充分,左心室舒張末期和肺動脈收縮壓也相應降低。由此可見,心臟搭橋和心臟瓣膜手術同期行房顫射頻消融術能有效改善患者的心功能〔20〕。
對于心臟瓣膜病變合并冠心病并伴有房顫的患者,術前應該積極監測患者心率、血壓、尿量等生命體征,常規予以強心、利尿、營養心肌等治療。術后常規呼吸機輔助呼吸,并給予硝酸甘油、異丙腎上腺素等藥物強心處理,胺碘酮靜脈維持竇性心律,肝素、華法林抗凝治療。如患者術后使用正性肌力藥物維持血壓不滿意,應及時對癥處理。
4 參考文獻
1Nasso G,Moscarelli M,Fattouch K,etal.Mid-term performance of bipolar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for isolated atrial fibrillation through a right minithoracotomy〔J〕.Semin Thorac Cardiovasc Surg,2017;29(2):160-72.
2李庫林,鄭 杰,張常瑩,等.陣發性心房顫動射頻消融術后早期復發和C反應蛋白的關系〔J〕.臨床心血管病雜志,2014;30(3):195-7.
3張 超.二尖瓣和主動脈瓣病變行心臟瓣膜手術對患者電解質及體液因子水平的影響〔J〕.中國老年學雜志,2014;34(6):1503-5.
4陳 娟,陳 琦,查燕紅,等.PDCA循環疼痛管理模式在房顫射頻消融術中的應用〔J〕.江蘇醫藥,2014;40(11):1338-40.
5中國心臟內外科冠心病血運重建專家共識組.中國心臟內、外科冠心病血運重建專家共識〔J〕.中華胸心血管外科雜志,2016;32(12):707-16.
6李春芝,李素彥,劉 瓊,等.退行性心臟瓣膜病患者血清骨橋蛋白水平、血漿B型利鈉肽水平與心功能的關系〔J〕.中國循環雜志,2016;31(5):459-62.
7田 野,楊 龍,鄭亞西,等.CARTO3三維標測系統快速解剖建模在陣發性心房顫動射頻消融術中的應用〔J〕.中國循環雜志,2016;31(8):764-7.
8Iwasawa J,Koruth JS,Petru J,etal.Temperature-controlled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for pulmonary vein isolation in patients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J〕.J Am Coll Cardiol,2017;70(5):542-53.
9劉 艷,彭淑華,付曉麗.冠狀動脈旁路移植同期行心臟瓣膜置換術治療冠心病合并心臟瓣膜病的臨床觀察〔J〕.實用醫學雜志,2016;32(1642):2686-8.
10中華醫學會心血管病學分會,中華心血管病雜志編輯委員會.中國心力衰竭診斷和治療指南2014〔J〕.中華心血管病雜志,2014;42(2):98-122.
11Kalla M,Sanders P,Kalman JM,etal.Radiofrequency catheter ablation for atrial fibrillation:approaches and outcomes〔J〕.Heart Lung Circ,2017;26(9):941-9.
12李 巖,胡繼強,林 謙,等.51例房顫射頻消融患者證候分析〔J〕.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2016;22(10):1363-5.
13陳愛華,宋旭東,楊平珍.房顫射頻消融治療的現狀與困境〔J〕.解放軍醫學雜志,2015;40(2):85-91.
14Li JY,Jiang JB,Zhong GQ,etal.Comparison of empiric isolation and conventional isolation of superior vena cava in addition to pulmonary vein isolation on the outcome of paroxysmal atrial fibrillation ablation〔J〕.Int Heart J,2017;58(4):500-5.
15張登沈,梁貴友,劉達興,等.心臟瓣膜置換術后早期死亡原因及相關因素分析〔J〕.臨床心血管病雜志,2015;31(8):874-8.
16劉洪沛,曾 戀,黃 濤.支架植入術治療房顫射頻消融術后嚴重肺靜脈狹窄的療效觀察〔J〕.重慶醫學,2015;44(24):3365-6,3369.
17Masuda M,Fujita M,Iida O,etal.Association between local bipolar voltage and conduction gap along the left atrial linear ablation lesion in patients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J〕.Am J Cardiol,2017;120(3):408-13.
18張 健,李發鵬,甘天翊,等.心功能不同的風濕性心臟瓣膜病心房顫動患者超極化激活環核苷酸門控陽離子通道4的表達水平研究〔J〕.中國全科醫學,2015;18(26):3170-2.
19張文斌,張大國,劉秀倫,等.房顫射頻消融治療巨大左房型風濕性瓣膜病的效果〔J〕.中國老年學雜志,2017;37(6):1355-7.
20齊 鑫,趙 岳,李 杰,等.心臟搭橋手術患者術后感染因素分析與預防〔J〕.中華醫院感染學雜志,2017;27(16):36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