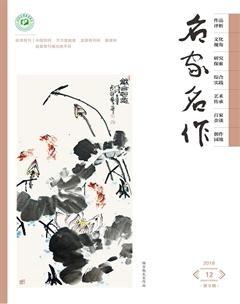林旭埜詩中的哲學意蘊探析
開始讀到林旭埜的詩,是在微信中一個評論家轉發的名為“曠馥齋”的公眾號上。微信公眾號由詩人和同樣是詩人的妹妹林馥娜一起建設,以分享詩歌文學作品為主,有原創專欄,有朗誦翻譯,辦得豐富活潑,有聲有色。
可以說,在詩歌創作上,林旭埜是有才華的。他在學生時期寫過詩,后來自2014年才開始重拾詩筆,短短幾年間,創作頗豐。
后來讀到林旭埜的詩集《放鶴孤山》,開篇便被《筆墨春秋》組詩吸引。之所以被吸引,是因為本來也有過寫一組此類題材詩的想法,但遲遲未能動筆,只在腦中有所勾勒。而看了《筆墨春秋》之后,就覺得和心中所畫頗有幾分相似。雖和詩人素未謀面,因為這組《筆墨春秋》便感覺近了許多。
《放鶴孤山》讓人見證了詩人“從日常生活中提取詩意的能力”。詩之所起,皆來自日常生活及所思所想。有旅途中的遐思,如《地球是只轉經筒》《只認此處是江南》《入埃及記》;有對平常事物的關注,如《雪》《神時代》;有失眠時的掙扎抵抗,如《失眠組詩》;有對親情的回眸,如《歲月的痕跡》;有對日常瑣事的辯證思考,如《黑色說》《盲道》等。順應時代的節奏,詩篇大多簡潔凝練,很適合在快節奏的時代進行碎片化閱讀。但讀過之后,不覺細碎,反而感覺禪韻悠然。這個禪韻,不是因為詩中有寫到木魚、山門石、講經,而是通篇所氤氳的哲學意蘊。正如吳思敬先生所說: “詩, 不僅是情感的抒發, 也是靈魂的冒險, 詩人是人類心靈的探險家, 這種探險, 只有借助哲學的光亮才得以進行。”
林旭埜的詩,習慣通過獨特的視角、辯證的思維觀照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于細微處見詩意,進而展示獨特的生命體驗和對事物的辯證思考,給人以哲思和啟迪。《紙上春秋》中,寫了一張脫胎于草木的紙,描寫了其喑啞的前世和燦爛繁復的今生,“蟬翼般的薄,與折疊數千載歷史的厚/用煙云般的輕,承托萬里山河的重”,通過厚薄與輕重之間的懸殊對比,烘托出紙這一古老發明的文化底蘊和承載的歷史厚重感。《瑪尼石》則透出一種遍閱世間繁華后的頓悟和大隱隱于市的淡泊。人生路漫漫,高又如何,低又如何,要高,就“在極寂的高處,感受世間的寒涼與澄明”,而在喧嘩的低處可以“領悟禪坐入定的寧靜”。有了這般領悟,所以即使“從天際滾落地心也安然面對”。《磨刀》一詩中把每個人都看成磨刀手,無時無刻不在打磨一把刀,而“幸福就是一把不經打磨的刀”“越打磨/損耗越多/越鋒利/越難觸碰”。表面寫磨刀,實則寫對幸福的經營過猶不及,度之拿捏彰顯分寸之重要。《父親的球藝》明處寫球藝,球藝之外則暗藏著父親的處世哲學。打球技術上嫻熟的“防守推擋”與生活中面對沖突時的“避實就虛”相互映照,又從側面反映出老輩人看似責備實為關愛的親情表達方式。“如果有夠大的球拍,父親肯定會把太陽從東邊扣殺到西邊/把月亮從西邊推擋回東邊”,奇崛的想象中不難看出,只要胸襟足夠寬廣,日月如乒乓球皆可控于掌中。《提燈的人》中別具匠心地把太陽和月亮想象成兩盞燈,提燈的人,一個隱于光芒背后,一個以夜幕披身,在不經意間排布著世間的色調與冷暖,絕妙的想像不禁讓人拍案。
兒時都玩過踩影子的游戲,而詩人對于影子則有著自己的思考。《踩著自己的影子前行》中,通過影子聯想到人的靈魂,“靈魂比影子更薄,薄得沒有形狀”,但“當你恣意踩踏靈魂行前退后,靈魂遲早令身心喊痛”。《春天的密碼》中讓冬雪這種雪墨繪寫春天的密碼,打開密碼后便“柳綠桃紅,泉清鏡明”。而“夏雨畫秋,冬雪繪春”,寥寥幾字悄然道破四季輪回的秘密,鮮活的詩意躍然紙上,與雪萊的“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有異曲同工之妙。
通過對比手法來詩意表達自己的所思所想,是詩人慣用的手法。小詩《盲道》中,“在崎嶇不平處/盲道引導磚、提示磚/常常了無蹤影/我不禁猜想/盲人到此處/或許能奇跡般、短暫復明/而不像明眼人,路遇不平時/習慣于閉上眼睛”。盲道在生活中甚為平常,在普通人看來微不足道,對盲人來說卻是非常重要,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會的文明程度和人文關懷。但很多人不會注意到盲道,更別說關心其是否順暢與完整。詩人則通過對生活中這個小細節的提煉,將聯想盡情展開,于是在眼睛的明與盲之外,還有人心的明與盲。一個轉折,世事百態展現得淋漓盡致。
參考文獻:
周旭方,呂穎.李壯萍詩歌中的哲理意蘊及女性存在意識[J].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39(1):109-114.
作者簡介:任巖巖(1983—),男,安徽阜陽人,廣州番禺職業技術學院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現當代文學、高等職業教育。
作者單位:廣州番禺職業技術學院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