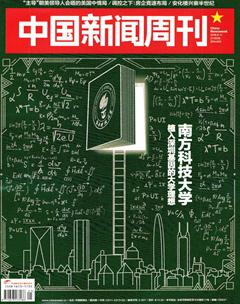教育投入應成為地方財政的優(yōu)選項
閆肖镩
因待遇發(fā)放問題,安徽省六安市部分學校教師集體討薪,引發(fā)關(guān)切。六安市政府回應,事發(fā)區(qū)域并沒有拖欠教師基本工資,只是未出臺相關(guān)“一次性獎勵”政策。
在此輪輿論中,什么是公眾關(guān)切的“真問題”?“一次性獎勵”政策又是怎么回事?
這其實涉及《教師法》及中央2017年印發(fā)的《關(guān)于深化教育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規(guī)定,教師工資不低于或者高于公務員平均工資水平,這項政策落實是否到位的問題。這其中最具爭議的就是工資外補助部分。有些地方先補助公務員,再補助教師,分步實施;有些地方先補市區(qū)、核心區(qū),再補郊縣、農(nóng)村地區(qū),拖欠現(xiàn)象時有發(fā)生;有些地方則刻意調(diào)低公務員補助數(shù)額,造成體制性分配不公……
要使類似教師欠薪事件不再成為新聞,真正地關(guān)心教師的權(quán)益,關(guān)鍵還需地方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門強化主體責任,真正落實《關(guān)于深化教育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的明確要求,確保教師平均工資水平不低于或高于當?shù)毓珓諉T平均工資水平。
教師危機,實際是教育危機,民族危機,這決不是危言聳聽,應當引起全社會和各級部門的重視。
對教師的政治和社會地位的尊重,整個社會是走過彎路的。1981年3月全國政協(xié)會議上,17位政協(xié)委員聯(lián)名提交了一份提案,呼吁建立教師節(jié)——“尊師重教遠沒有形成一種社會風氣。毆打教師的事件時有所聞。廣大教育工作者真正樹立以教書育人為終身職業(yè)的思想也還不普遍。”
從1985年9月10日的第一個教師節(jié),到1993的10月3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終于頒布,可以說教師的政治地位得到了根本的改善,這是中國社會的進步。但同時,也應該看到,《教師法》所規(guī)定的教師權(quán)益,并沒有得到充分的保障。
這里面,最根本的原因是要解決法律軟約束問題,不光是如何讓“確保教師平均工資水平不低于或高于當?shù)毓珓諉T平均工資水平”這樣的權(quán)利落到實處,還要看怎么樣把軟約束變成硬約束。即,把是否落實《教師法》,貫徹中央《關(guān)于深化教育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列入當?shù)毓賳T的政績考核。
從整個社會和民族的更長遠的發(fā)展來看,這是一個要解決教育優(yōu)先的根本問題。有些地方經(jīng)濟發(fā)展了,教育卻嚴重“拖后腿”。辦教育的經(jīng)濟效益遠遠沒有招商引資、基建甚至房地產(chǎn)等來得快,能馬上見效益、見成果、有好處。但教育功在當代、利在千秋,有利于提高全民素質(zhì),從長遠看,也有利于經(jīng)濟的長遠發(fā)展。教育是百年樹人,執(zhí)政理念尤其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理想。
簡言之,教育投入包括教師薪資應成為地方財政的優(yōu)選項。《關(guān)于深化教育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提出,堅持把教育擺在優(yōu)先發(fā)展的戰(zhàn)略位置,要讓我同教育總體發(fā)展水平進入世界中上行列,為13億多人民提供了更好更公平的教育,為經(jīng)濟轉(zhuǎn)型、科技創(chuàng)新、文化繁榮、民生改善、社會和諧提供了有力支撐。
而當下,要直面當前我國教育存在的問題:一是教育投入總體處于世界平均水平,與發(fā)達國家更有差距,2016年我同教育經(jīng)費投入GDP占比超過4%,而美國、德國2015年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例達到4.9%,英法等國均高于5.5%,丹麥更是達到了8.6%。顯然,我國教育投入仍要急起直追。二是我國的教育投入在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失衡問題。地方是負擔財政性教育經(jīng)費的主要責任主體(教育財政投入九成以上由地方政府負擔),對教育發(fā)展起著關(guān)鍵性作用。但在分稅制下,地方政府沒有相應的財權(quán),從而出現(xiàn)了財權(quán)與政府支出責任劃分不匹配的現(xiàn)象,最終導致教育投入不足的現(xiàn)象。三是我國的教育投入存在區(qū)域性的差異和不平衡。在資金配置上又極不合理,存在重高校、輕基礎(chǔ),以及重城市、輕農(nóng)村的問題。
解決以上問題非一日之功,但可以有個優(yōu)先序列,那就是先提高教師薪資,穩(wěn)定教師隊伍,讓教師成為全社會令人羨慕的職業(yè)。再窮不能窮教育,再緊不能緊教育,再擠不能擠教師,讓教師群體切實享受到改革發(fā)展帶來的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