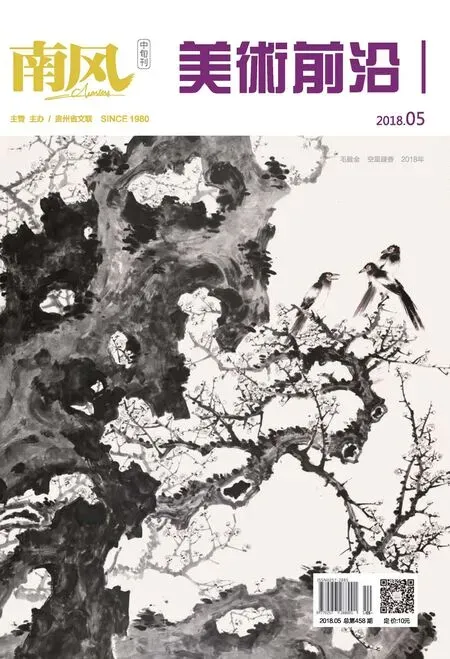寫山川精神 抒胸中浩氣
——山水畫研習隨感

荊兆林 人在秋色白云中 68cm×136cm 2014年

荊兆林 移舟尋幽 68cm×136cm 2016 年
中國山水畫作為一個完整的藝術體系,它的發展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它的不斷完善和成熟,是歷代無數畫家心血和智慧的結晶。從東晉的“人大于山,水不容泛”到唐代的“金碧山水”、從五代的“全景山水”到宋代的“文人畫”萌芽、從元代的“元四家”到明朝的“吳門畫派”、從清代畫家的“循規蹈矩”到近現代的再度興盛,無不體現出歷代畫家,特別是歷代山水畫大師們的不懈奮斗與追求。
歷代山水畫大師為我們留下浩如煙海的寶貴精神財富,同時也在我們面前豎起了座座藝術豐碑,使后人難以超越。然而,社會的變遷、時代的進步為山水畫的創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清代山水畫家石濤也曾提出“筆墨當隨時代”。可見任何一種藝術形式的存在都不是一成不變的,都要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斷發展和創新。中國山水畫的發展和創新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道難題,也是需要我們付出畢生精力去不斷探索的。我是人物畫家,然而對山水畫也情有獨鐘。人物畫的創作,特別是寫意人物畫的筆墨借鑒均來自山水,山水畫是人物畫家的必修課。每當我在人物畫與山水畫的交替探索過程中,總會產生新的感受,使我的創作受益匪淺,這也許是我對山水難以割舍的原因吧。
我是一個興趣愛好較為廣泛的人,孩提時代對民族樂器如醉如癡,因條件所迫曾自己動手制作竹笛、二胡、板胡,在自我的“音樂”世界陶醉。真正對繪畫產生濃厚興趣還是在中學時代。但那個年代是漫畫、連環畫、年畫的天下。對山水畫產生興趣大約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記得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里,從一本小冊子上見到了一幅黑白山水畫,心里感到一種莫名其妙的表現沖動,也試圖照葫蘆畫瓢,但結果不言自喻。后來有幸進入藝術院校,方才認識曾讓我產生表現沖動的藝術大師——黃賓虹。這一時期,我對歷代的山水畫大師有了一些了解。范寬的《溪山行旅圖》、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沈周的《廬山高圖》《雪霽停舟圖》都是我學習的范本。我還大量臨習了文徵明、石濤、石溪、龔賢、黃賓虹、張大千、黃秋元的山水畫。為我學習傳統打下了基礎。多年來,我在創作之余,還是手不離卷,或讀畫或選臨,從傳統中汲取營養。在學習傳統基礎上,我堅持走向自然,走進生活,感悟大自然的美麗和神奇,做到有感而發,為大自然傳情寫照,創作出具有時代氣息的山水畫。我先后到五臺山、太行山、華山、泰山、張家界、黃山、十渡等地寫生,親身感受到北方大山的雄渾博大和南方山川的秀麗壯美,積累了大量的一手創作資料。在山水畫的創作過程中,我采用了循序漸進的方法,不斷尋找繼承傳統和為自然寫照的契合點,使我的山水畫逐漸成熟老道。收藏家對我作品的厚愛、社會對我山水畫的肯定認可是對我的最大褒獎。我在山水畫創作的實踐中逐步體會到以下幾點:傳統是山水畫創作的基石、神韻是山水畫創作的靈魂、出新是山水畫創作的根本。

荊兆林 雨后更覺山色新 96cm×180cm 2013 年
傳統是山水畫創作的基石
中國畫強調“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強調“書法入畫”。它的獨特作畫材料工具,決定了它更適合于意向的表現形式——注重作者心源的表達。因此,不同的畫家形成不同的畫風。在長期的實踐中對一幅畫優劣的判定標準也形成了共識。所以,學習中國畫必須先從傳統開始,先把傳統的一招一式學到手,再到大自然中尋找創新的靈感。這里需要強調的是必須把握好一個度,太傳統可能流于形式,淪為為人作嫁的結果。太注重對物象的描畫,追求所謂的“是”,反倒會似是而非,失去中國畫的特定表現語言。我在創作實踐中,感到判定中國畫優劣的標準應該是作品要有過硬的基本功,畫家要有造型能力。中國畫的特殊工具,要求做到“意存筆先,畫盡意在”,達到以形寫神,形神兼備,氣韻生動的效果。畫家能較好地把握造型變與不變的度,做到夸張有度,形象具有強烈的感染力。正像國畫大師齊白石一再強調的:“作畫要在似與不似之間,太似為媚俗,不似為欺世”;畫家要有合理的章法架構能力。早在南朝齊謝赫的《古畫品錄》中就提出了“經營位置”,即要求章法構圖必須嚴謹,不能草率從事。國畫大師潘天壽先生對此也有精辟地論述:“畫事之布置,須注意畫面內之安排,有主客,有配合,有虛實,有疏密,有高低上下,有縱橫曲折,然尤須注意于畫面之四邊四角,使與畫外之畫材相關聯,氣勢相承接,自能得趣于畫外矣”;畫家要有過硬的筆墨功夫。

荊兆林 家園 240cm×80cm 2013年
中國畫的用筆包括“起筆”“ 行筆”“轉折”“提按”“收筆”等。最關鍵是要把握好力度速度、筆鋒筆順、用筆用墨等幾個環節。力度、速度:有力度的線條才能給人以美感。用筆的提按就是體現力度的重要方法,也是體現作品風格和氣質的重要標志。行筆時用力往下按線條則粗壯,往上提筆線條則秀逸。行筆的快慢本無絕對標準,行筆快未必草率,行筆慢未必澀滯。行筆的快慢全在畫家的秉性和氣質。總的要求是平穩、沉著、有韻致。古人講的“棉里裹針”“如錐畫沙”“屋漏痕”等都是用筆力度、速度的極好形容。用筆、用墨(用色):此項的關鍵是能否處理得恰到好處。 如在石濤大師的畫中時常可見,其運筆用墨干中帶濕,有著 “ 有血有肉有骨”的效果。再如山水畫大師錢松嵒的繪畫作品,其設色往往是隨畫境而定,于每幅畫中均能達到重而不滯、艷而不俗,既有對比又不顯刺目,既有統一又不覺單調。
神韻是山水畫創作的靈魂

荊兆林 雨過千峰潑黛濃 68cm×68cm
一山一水皆有靈性,為山水寫照絕不是畫山水標本,要力求抓住一草一木、一水一石的神韻,創作出具有時代氣息的大山水。在創作中我的體會是:作品神韻是指一種理想的藝術境界,其美學特征是自然傳神,韻味深遠。重點把握三點:一是氣韻生動。謝赫在繪畫 “ 六法 ” 中首推 “ 氣韻生動 ”。一千多年來它一直是衡量中國畫的最高標準。“ 氣 ”派生出氣勢、骨氣、風氣,是指畫面中貫注的一種激情。“ 韻 ”派生出趣味、滋味、韻味,偏重指畫面的節奏、旋律等構畫要素的和諧。 因此,“氣韻生動 ”是繪畫作品的最高境界。二是意境深邃。 意境是指作品中傳達出的情景交融、虛實相生、活躍著生命律動的韻味無窮的詩意。意境深邃的中國畫作品,能引起人們對自然、社會、人生的聯想和進一步的思考,并使人產生健康向上的動力。三是格調高雅。格調是指中國畫作品中表現出來的美學品格和思想情操,是藝術家藝術造詣、文學修養、審美理想和思想品格的匯總體現。中國畫作品的格調有雅俗之分。格調不僅取決于作者的思想境界,同時也取決于作者所能達到的藝術境界。高格調一般不僅要表現深刻的思想,健康的內容,還要求藝術家有精湛的藝術表現力。從創作角度來看,格調是藝術家思想境界和藝術境界的最高體現。
出新是山水畫創作的根本
在山水畫的創作過程中,傳承和變革歷來就是一對矛盾,繼承難,創新更難。我感到,在創作中尋求個性是每個畫家能否確立自己藝術面貌的重要標志,是一個成熟畫家的立身之本,也是能否得到社會認可的重要因素。個性是藝術家發展的自然流露,也是發展的必然結果。個性的形成與畫家的修養、性格、環境、師承等有著密切的聯系。好的藝術品都有被社會認可的獨特創新面目。
綜上所述,是我在從事山水畫創作實踐中的一點初淺感想體會,懇求得到同道指正。

荊兆林 清夏松風圖 68cm×136cm 2014 年

荊兆林 源遠流長 240cm×80cm 2014年

荊兆林 青山綠水悅人心 68cm×136cm 2014 年

荊兆林 家山疊翠積云深 136cm×68cm 2017年

荊兆林 尋源入谷水潺潺 136cm×68cm 2017年

荊兆林 清雅山居 180cm×96cm 2016年

荊兆林 扇面之一 2014年

荊兆林 扇面之二 2014年

荊兆林 扇面之三 2014年

荊兆林 扇面之四 2014年

荊兆林 門外青山苒苒多 68cm×68cm 2017 年

荊兆林 山鄉幽居圖 68cm×68cm 2017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