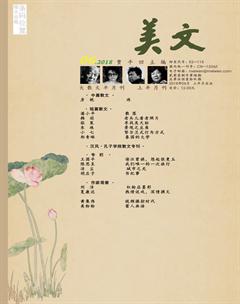什么是現代性?
張華
一直以來,“現代性”概念長期受到學術界高度關注,不同學科、不同思想派別、不同時期的思想家,對現代性有著不同的理解,對其具體內容的描述也是千差萬別。但是,我們至少在一點上可以達成共識,即現代性是一種精神理念或思想形態。馬克思·韋伯就是通過將“現代性”一詞放在與之密切相關的另外幾個同根詞—— “現代”“現代化”和“現代主義”—— 一起加以比較甄別來確定現代性的特殊性質的。韋伯認為,現代社會結構特質的生成過程,就是理性化的過程。依據他的觀點,理性化和合理性是區分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的關鍵:所謂現代化就是理性化,而“現代性”則是“合理性”。這種解釋經哈貝馬斯、約翰·威爾森等現代性問題專家的發展和闡釋,形成一種較為通行的觀點:“現代”是一個相對于“古老”“傳統”而言的時空概念,因而是隨時間而變遷的;“現代化”主要是一個社會學術語,指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之后西方世界建立起來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社會制度體系;“現代主義” 則由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一個特定的文學藝術流派擴大為泛指所有精神文化生產領域;而“現代性”則更多地用來指稱社會現代化和文化現代主義背后所共有的哲學或形而上學基礎理念,是一種精神的或意識形態的力量。因而,在更多時候人們傾向于在一種更廣泛的意義上使用“現代性”,以之涵蓋“現代化”和“現代主義”,把這二者視為“現代性”精神在不同領域的不同表現方式。顯然,“現代性”與時間意義上的“現代”密切相關。但是,由于時間性的“現代”是一個恒久地發生著的事情,每個歷史時代相對于該時代的人來說都是“現代”,如果僅僅從時間維度去把握現代性概念,就失去了它的特定內涵。
在某次座談會上,有學界朋友把西方馬丁·路德新教改革視為“現代”的起源和分界點,把自由視為“現代性”的最根本特征,把美國視為“現代社會”的代表,并將“現代”等同于“先進”。我不反對對“現代性”進行多元的開放式理解,但我認為把“現代的”等同于“好的”是不全面的看法。其實,“現代性”是以“現代性問題”或“現代性危機”的面貌而吸引思想學術界的全力關注的。現代性之所以成為思想學術界的關鍵詞,就在于它是一個問題叢生的領域。現代社會問題太多,以至于吉登斯將現代社會稱為“風險社會”,最嚴重的就是社會秩序與人心秩序失范,價值虛無化。物質和技術層面上的“現代化”在“方便”人們生活的同時,也給人類帶來一些災難性后果,比如大氣污染、生態破壞、核廢料等等,而“現代化”代表性產物——汽車,卻成為現代社會“殺人”最多的單項發明。如果回顧西方列強利用堅船利炮等“現代產物”蹂躪我中華大地的歷史,“現代性”則更是骯臟的。
應該重溫,上世紀末75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曾在巴黎呼吁:人類要生存下去,必須回到25個世紀之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而今,社會越向前發展,人們就越驚訝地發現,運用中國傳統智慧更能解決人類面臨的很多矛盾和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