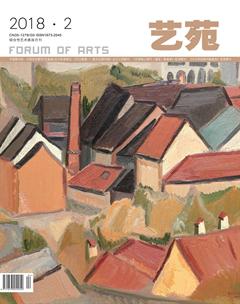民俗文化視域下的莆田木雕工藝
林蘊臻
【摘要】 莆田木雕以“精微透雕”的技藝風格揚名,同東陽木雕、樂清黃楊木雕和潮州金漆木雕并稱中國四大木雕。本文將從民俗文化的視角審視莆田木雕工藝的歷史沿革,據此分析莆田木雕工藝在民俗文化的視野影響下形成的審美特質和盛衰流變。從而管窺莆田木雕工藝在民俗文化視域下對中國“以藝悟道”的傳統文化的繼承,對新時期莆田木雕工藝的發展提供啟示和思考。
【關鍵詞】 莆田木雕;工藝美術;民俗文化;場域;民間美術
[中圖分類號]J52 [文獻標識碼]A
莆田,地處福建中部,臺灣海峽的西岸,三面臨山,一側瀕海,閩江水橫貫興化古城,莆仙雙城相峙,被稱為海濱鄒魯、文獻名邦,其工藝美術發展更是歷史悠久,底蘊豐厚。其中莆田木雕工藝發端于唐宋,繁盛于明清二朝,憑借著獨特的明快線條和雅致清凝的造型而揚名于世,被稱為“中國四大木雕”之一。
木頭溫潤而質樸,傳統匠人們依據其品形,在原始形態中注入主觀情思,創造出渾然天成的傳統木雕工藝。但任何工藝美術的誕生發展與變革絕不是一種工匠藝師們自我的偶發性的純粹表達。它的形式的誕生與嬗變都在間接或直接地反映某一地區人的生存經驗和民俗文化中的理想憧憬。
民俗文化是一個區域人民長期積淀而成的在審美理想、思想主張、生活習性上的完全的心理認同。而民間美術之美,就是通過人們對包括節日慶典、吃穿住行等諸多外顯民俗事象進行藝術表現來感受其豐富內蘊的。本文將從四個方面具體闡述民俗文化視域下的莆田木雕工藝之美。
一、民俗文化的樂生感性之美:莆田木雕工藝的生活性與人文性
為了滿足物質生產生活的需要,為了順利經歷人生的不同階段,百姓們總是通過一些藝術樣態來表達對吉祥如意生活的向往,對生命充盈完滿的追求。中國各地的民俗文化提倡樂生之美,以生為樂,追求現世滿足。
樂生首先要對自己生活的環境與生產資料有著充分的感知力,《興化府志》記載:其近山地宜種荔枝、龍眼。興化地區有著豐富的荔枝、龍眼樹木資源,樹木的質地堅硬結實同時紋路細密,有著較為柔和的色澤,特別適合進行木雕創作,這直接為民間藝人因地取材提供了原料保障。莆田木雕工藝的發展過程體現了莆仙地區百姓對生活質量的探索和對生命之熱忱,中國人格外講究“衣、食、住、行”。在傳統的莆仙兩地民間觀念里,“住”是人生首要追求的主題。時至今日蓋房子、結婚生子和做事仍然是興化人心目中的三件大事,這種世代相傳的習俗與觀念,是莆田民間民眾普世的價值追求。在如此強烈的民俗意識指引下,莆仙人民特別注重、講究房子的整體格局、用料和外在的裝飾技藝。其中表現最為突出的莫過于清代,國力的強盛帶來風氣的轉變,莆田木雕技藝從以祭祀崇拜、風俗禮葬等儀式性的生活產物向為現實大眾觀賞、市場收藏娛樂的文化奢侈品轉變。而這種變化的出現,與市民階層的異軍突起和市民經濟發展存在著密切關系,市民階級對木雕工藝需求量的提高正是出于陶養情操、格物致知的個人意趣,是一種雅道樂生的表現。
自彼時起,莆仙兩地私宅民居建筑裝飾漸趨于奢靡、繁瑣,相當一部分富商、僑民追求精雕細琢的視覺效果。這種對于生活品質的追求催生了“雕花師父”們大顯身手。在府邸的主要部位,如廳堂、門樓、匾額、山墻和藻井各處皆體現著莆田木雕藝人精雕細鏤的匠心天工。如仙游度尾鎮明朝尚書鄭紀故居的木雕裝飾,古樸典雅,自然流露著風雅和氣韻。莆田地區民居建筑中的雕刻工藝建立在市民階層崛起的基礎上并得以發展,其本質是根源于莆田繁榮的民俗“樂生感性”文化。莆田的工匠藝人們感應著民間百姓的“樂生”需求,用他們高超的藝術創造在這些民居建筑上留下了精湛的“雕花”技藝,成為了活躍于八閩大地木雕技藝上鮮活、生動的歷史范本。
除了“樂生”之外,莆仙人的民族性格中還暗含著一種文化傳承的內動力和“學而優則仕”的思想追求,對于世事成就的個人追尋是對自我生命價值和宗族門楣榮光的肯定之舉。莆田素有“文獻名邦”“海濱鄒魯”之譽,重教興學蔚然成風。梁、陳時期,鄭露、鄭莊、鄭淑三兄弟開館授業,來莆開學。宋代民間書院風靡,“學宮壯偉,甲于閩都”;民間更是世代流傳著“地瘦栽松柏,家貧子讀書”的祖訓和“一家九刺史”“一門五學士”“文武魁天下,兄弟雙宰執”的佳話。
在莆田,自啟蒙開學起,幾乎每一個宗祠都建有一所學堂,宗族的福利總是優先給予讀書求學問道之人,而這種對刻苦讀書考取功名青睞有加的民俗綿延上千年之久。如今散落于莆仙各地的古民居中有很多歷朝歷代遺留下來的宗室書院。這些學堂祠堂內的槅扇、額枋、梁架、斗拱上都存有大量精致秀雅的梅蘭竹菊、飛禽走獸的浮雕。位于仙游縣鯉城鎮的文廟,初創于北宋,其間經歷了多次興廢和改建,文廟的主體建筑大成殿面闊三間,進深四間,是招梁與穿斗混合結構的殿堂建筑。房屋脊背上以灰雕雙龍裝飾,大殿頂部為疊拱藻井,同時飾以木雕工藝,結構精致而又華麗繁復。大殿前廊排列著四根圓雕龍柱,雕工細膩,廳堂中自外而內依次懸掛著清朝五代天子的御書復制品,有咸豐的“德齊禱載”,嘉慶的“斯文在茲”,乾隆的“與天地參”,康熙的“萬世師表”和順治的“生民未有”。走出大成殿看到的是月臺,古時候這里是獻牲、獻果、獻花的祭祀場所,月臺下是丹墀,前方以浮雕神龍連接通道并直通戟門,門前的一對抱鼓石據考證是宋代年間的遺物。[1]仙游文廟系福建省四大文廟之一,工藝之精可見地區對文化教育的重視程度。
同時,莆田歷史上還出現了蔡京、蔡卞兄弟同朝拜相,黃公度、陳俊卿、劉克莊等位及尚書的佳話。這些“學而優則仕”的文人仕士為官宦游于各處,作為文人士大夫的精英代表,他們既追求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志趣,又渴望著奢華優雅的物器享受,這種感性的文化性格主要是源于他們渴望得到社會認同。因而這些在外為官者的思潮雅好經由社交酬贈傳回故里,與民間文化碰撞從而產生了民間木雕工藝。相傳,宰相蔡京曾召集了家鄉的木雕工匠,制作紅木雕刻家具。現如今藏于故宮博物院的名畫《聽琴圖》,畫面中放置古琴的琴桌據傳正是蔡京呈獻給宋徽宗的莆田木雕家具。莆田木雕的興起和在全國范圍內的影響力正是基于這些精英文化的代表們逐步注重自我形象,對他們而言,無論是宦游出仕于廟堂之高,還是歸隱山林閑居處江湖之遠,修養性靈與立德立言都是不可忽視的功課。他們試圖以這樣的方式努力向世人展示博雅好古、超逸出塵的不凡人生理念。
總之,人們通過一定的藝術創造,讓生理疲乏得以休養,心靈精神得以調劑,普世情懷得以撫慰,最終實現全身心的平和泰然,卸下過往包袱,投入嶄新的生活。莆田木雕工藝正是廣大民眾基于深刻的人生體驗而大膽創造出的藝術產物;為了表現生命的豐富與“樂生”的需求,通過奇絕的幻想、自由的實踐、夸張的形式,展示中國民俗文化中浪漫的色彩,從表面的“悅耳悅目”,經過“悅己悅意”的本心滿足,最終達到“悅志悅神”的審美巔峰體驗。
二、民俗文化的天人貫通之美:莆田木雕藝術的神秘性與超越性
當原始先民們在面對萬物時,他們經常會把自己置于自然生長之境中,在“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的文化觀念中,企盼著天地共生、萬物為一。于是乎東方式的思維方式和萬物有靈的觀念,使得民間對神靈產生了不同的理解和想象:天堂地府、陰陽兩界、海上女神……形形色色的神仙信仰,構成了民俗文化中的原型因子,極大地影響了民間美術的基本形態。
以人合天,這始終是人的歸宿,也是中國傳統審美的歸宿,中國傳統藝術的歸宿。因此,我們的民間藝人相信只有達到神人以和、天人貫通,才能觀物之天性,才能由形入神、體察氣韻、緣心感物,實現“神與物游”的審美觀照。
眾所周知,福建的民間信仰源遠流長,向前追溯可至春秋閩越族時期。莆田于唐武德五年開立縣后,社會經濟迅速發展,佛教也達到了盛極。《仙溪志》記載:“晚唐以來,地有佛國之號。”佛教文化在興化地區的廣泛傳播帶來佛塔寺院的廣泛興建,代表建筑廣化寺,也是2018年世界佛教論壇的主辦地。可以說,寺院的興建從客觀上推進了莆田木雕的發展。
莆田地處閩中,在思想上深受北方正統孔孟之道的影響,在民間信仰上又雜糅著特殊的地方鬼神崇拜。道光年間編撰的《福建通志·風俗志》記載:“閩人好鬼,習俗相沿。”莆田民間信仰的盛行具有復雜及區域獨創的特性。自宋起,由于民間傳說的大力推動和歷朝歷代帝王的褒獎分封,湄洲本土的媽祖信仰文化逐步發展并形成鼎盛之勢。媽祖信俗隨海上絲綢之路在沿海及周邊島國傳播,進一步擴大了莆田木雕在宗教造像成就上的影響力。現今存放于莆田市博物館和文峰宮內的幾尊宋代媽祖木雕造像,造型嚴謹,形象柔美,刀法凝練,雖歷經千年,至今看來仍散發著神性的光芒。[2]
因各朝代媽祖受封的身份不同,歷代木雕工藝中的媽祖型像都各有不同。宋朝初期,媽祖高綰發髻,袖袍寬大,體格修長,神態平和,是普通世家夫人的真實寫照,表現出溫婉賢淑的女性特征。宗教民俗推動藝術發展,而后媽祖冊封為妃,頭戴金色冠冕,一身華服的造型成為元明時期媽祖雕像的主流形象。清康熙二十三年,媽祖受封為“天后”。此后,媽祖造像的身形逐漸趨于圓潤豐滿,整體形態的轉變體現出雕刻的審美性格與民族觀念在藝術上的相互滲透。
從宋起到清代媽祖雕像中的這種形象轉變,正是工匠藝師們基于民俗事象和民族時代價值取向的選擇,前期的媽祖修長剛毅,體現的是百姓們對堅強的海上女神的推崇,后期的媽祖光滑圓潤,則更容易傳達一種圓滿的生命形象,體現著民俗文化中對慈悲、包容的向往。以媽祖造像為代表的莆田木雕神像,記錄了莆仙民眾審美理想的變遷,承載著地方延續千年傳承有序的精神信仰。
當諸多病痛、生死、災難、困苦的人生際遇侵襲而來,無助的人們只能通過祈求神靈的無上能力普照眾生得以超脫于危局中,正是如此多樣敏感的神秘心理創造出了這樣極具神秘性的藝術符號。從藝術文化史的角度來看,一切文化的發生、文明的發展的原始驅動力,無不來自于人類對自身生存和生命體驗的真切關懷。莆田木雕工藝與民眾的現實生活緊密相關,它始終在社會歷史作用下的文化場域中活動,又通過不同的形式與內容潛移默化地塑造人格,處于這種文化場域作用下的民間美術復雜多樣但又蹤影縹緲,帶有一定的超越性與神秘性。在科學技術、物質條件落后的年代里,以媽祖為題材的木雕作品以神秘的民族信仰給當時的人們以勇敢面對自然、開發自然的勇氣。
在民俗生活中,世世代代的莆仙民眾在日常辛酸苦辣中體味塵世生計冷暖,在奔波勞碌之余惦念那給予慰藉的冥冥力量。莆田木雕工藝所蘊含的民俗信仰為民眾普通而瑣碎的生活增加了快意,平添了幾分熱愛,夾雜著些許憧憬,以超脫的力量將他們從泥潭中救起向生活和解,復歸于美好與安寧,在周而復始的祈禱庇佑中重獲新生。不論民眾對于在地宗教的信奉遵從是否發自本心,究其初心他們都只不過希望通過木雕技藝所建構的“神圣藝術空間”來舒展身心、告慰靈魂,獲得個人的生命滿足感和群體的社會認同。
三、民俗文化的多元共生之美:莆田木雕工藝的混融性與民族性
民間美術的形成和發展是群體參與的結果,是群體智慧的結晶。莆田在地的民俗文化是儒、道、釋三家為主相輔相成的傳統文化,不同宗教混融的風俗習慣、生活方式、藝術創造互相浸染、互相效仿、互相滲透,最終趨于交融互涉的局面。
前文提到莆田是個宗教氛圍濃厚的地方,自唐起,這里就興建廟宇佛堂道觀僧院,由此帶來的宗教造像和廟宇裝飾,對木雕工藝有著大量的行業需求。除了媽祖信仰,佛教佛法的傳播對于莆田木雕工藝的推進作用也是不容小覷的。廣化寺里外的建筑構件、神龕佛像、木作裝潢,任何一樣都離不開泥塑、木雕和石刻技藝。20世紀,以佘國平、閔國霖為代表的莆田木雕技藝傳承人們應邀承制了廣化寺復建工程的部分工作,成功完成了廣化寺“護法神”“四大金剛”“觀音”菩薩和“五百羅漢”的泥塑、雕刻任務。
莆田木雕工藝的混溶性正是體現于此,多種宗教在此匯合又衍生出多種藝術創作題材。道教自唐代起便在興化大地上傳播開來,最早興建的道觀是現位于荔城區北龍街的元妙觀三清殿,而后又相繼建造了五帝廟、九仙祠和凌云殿。在莆仙一帶,對于道教教義的區域化解讀主要是對東汾五帝祖廟的進香謁祖以及對臨水夫人順天圣母的朝謁。順天圣母是道教中救助婦女難產之神。順天圣母名叫陳靖姑,因斬蛇于宮中,閩王封為“臨水夫人”。莆田市秀嶼區嵩山陳靖姑祖廟,尚存一尊木雕陳靖姑像。
還有關帝信仰對木雕技藝的影響,清末雕刻名手廖熙,是莆田木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人物。在福建省博物館收藏了兩件廖熙的關公造像木雕作品,堪稱廖氏木雕的經典之作。整體來看,關公身披文武官袍,左腳微微向前邁出,相貌堂堂威風凜凜;細看其局部刻畫,丹鳳眼臥蠶眉,長髯散落胸前似有勁風拂過,赤膽忠心之形象呼之欲出。廖熙對人物衣褶關系的交代清晰,不拖泥帶水,整體雕刻線條抑揚頓挫富于韻律,大有“曹衣出水”“吳帶當風”之氣度,極具藝術感染力。[3]
在莆田的地域文化傳統中一般百姓更關心的是通過一定的藝術方式,實現祈福攘災、逢兇化吉、增福增壽、風調雨順的心愿,至于所祈求的是哪方神明、哪門宗教似乎并不那么重要。這是不同歷史階段莆田民眾在工藝美術發展過程中的形象寫照,也是人類文明進程中所表現出的另一種征象。
莆田木雕工藝的這種世俗追求與神圣信仰的混融,實用與理想相結合的情形,正是民俗文化多元共生的體現。同時,莆田民俗文化的這種混融性和民族性還體現在了多種藝術門類的互為表里、相融相合中。隨著時代的更迭與民俗生活的變化,民間美術也必然相應地產生變異,有的式微,有的消亡,有的隨著新的民俗生活方式的產生而帶來新的藝術。但不論怎樣,民俗藝術形式之間總是相伴而生的。
前文提到,濃郁的民俗信仰從一個方面造就了莆仙兩地民間繪畫和木雕工藝的繁榮景象。說到底,莆田木雕工藝最終成型的美學氣質和審美取向得益于莆仙大地獨具特色的社會文化土壤的浸染與滲透。閩中之地自古以來文化底蘊十分豐厚,書畫文學的發展更是活躍,歷朝歷代皆有書畫名家涌現,明清二朝書畫藝術更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黃金時代,文人畫與商品畫交相輝映,以莆田曾波臣、吳文中為代表的人物畫畫家在宗教人物造像、人物形象刻畫、筆法線條處理上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對后世莆田木雕工藝中一部分以人物圓雕為主的雕刻風格、表現語言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清末民初,仙游畫派的代表人物李霞、李耕、黃羲等人在吸收同為閩地畫家的上官周、黃慎的傳統筆墨章法后自成一派,形成了具有莆田地域特色的古典人物繪畫風格。
由于眾多畫師畫匠的介入和參與,民間繪畫和木雕工藝這兩種藝術樣態開始融合,繪畫的圖像形式和藝術追求以及有意的美學探索開始反哺于木雕工藝,使莆田木雕的創造性和藝術表現力獲得了進一步提升拓展的空間。如僻居仙游故里的李耕,他將水墨寫意的情趣與工筆重彩的謹嚴相結合,在工細的體格中蘊涵寫意的韻律,用筆靈動,汲取古人流暢之長,以行草筆意入畫,勁利多變,人物形象適當變形,皆前所未有,也無儕類,極具夸張意味的藝術安排賦予了作品強烈的視覺張力,令人過目不忘。李耕在潛心繪事的同時好作黃楊木雕像。其刀法老辣,衣紋褶皺變化無方,發自由心,躍然像上。其造像極大程度地發揮了國畫“取舍”“向背”的傳統,形神兼備。國畫中的筆簡意遠、率真韻味在其木雕作品中得以表現。而作為李耕門生的黃羲所作人物畫《獻壽圖》中童子、仙人的形象與動勢風格在莆田木雕工藝第二代傳承人閔國霖的作品《達摩》《壽星》中亦可找到影子。莆仙大地上的這些書畫名家們在繼承傳統的同時,以自覺的藝術創新不但迎和了中國近現代新興的市民階層精神形態,也為拘泥古法、不知往何處去的木雕工藝發展開拓新的思考門徑,他們的畫本成為后世莆田木雕宗教、人物題材創作的形象范式摹本。
莆田木雕工藝始終是混融于民眾的日常藝術生活之中,除卻繪畫對其的滲透,戲劇藝術也為莆田木雕工藝打開了新的視野。莆仙戲是興化地區民眾喜聞樂見的劇種,其表現內容多是莆仙地區為人們所熟知的歷史人物故事、民間傳奇和神話傳說,或是謳歌善良,鞭撻丑惡,或是宣揚美好,表達愿景。盡管藝術的快時代擠壓了中國人的藝術空間,但莆田人對古老的莆仙戲始終是情有獨鐘,只要逢年過節、家有喜事,請上戲班,鑼鼓一響,百姓們就從各自家中搬出長椅桌凳,傾巢出動,“相呼入市看新場”。[4]50-53
莆仙戲劇目的豐富生動以及在民間民俗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普遍性為莆田木雕藝人創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這些木雕的藝師工匠們把民眾喜愛的歷史英雄人物、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富有生趣的生活圖景,雕刻裝飾于建筑物或日常器皿用具之上,日日得見,不僅僅滿足了百姓的民俗審美,同時因為是戲曲中的內容,一下子又能激發起他們彼時觀戲的愉悅心境,隨著雕刻的內容自然引發聯想,藝術的二次巔峰體驗和藝術感動自然流露。同時,家境稍好的新婚夫妻,常將雕滿各種民間故事的家具作為聘禮相贈。民俗文化形態間的混融性由此可見一斑。
四、民俗文化的精妙絕倫之美:莆田木雕工藝中的造物思想與造物技巧
木雕工藝同繪畫書法一樣,創作觀照之道,都飽含著深刻的造物理念,道家認為,雕琢有道,復歸于樸。中華傳統文化內核中強調的是本真本心自然原初之美,反對任何外力的干涉與矯揉造作,民間美術同樣也力求古人神韻,避免匠氣和僵冷;同時不斷創新,“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不落窠臼。
造物本身即是一種感情抒發,寄寓生活理想的重要途徑,傾注了勞動者維系生命活動,熱愛生活的純樸情感。從民俗宗教信仰中如何取意,其中的高下、深淺,是造物者知識經驗、個性氣質和審美趣味的綜合體現,反映于木雕工藝中的不同風格,或淳樸、厚實,或別致、精巧,或莊重、威嚴,或艷麗、隨意,或秀雅、清靈,或丑陋、笨拙,等等。由此形成的藝術風格能夠對民眾的審美情趣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同時也影響著民間風俗傳承中趨美向善的歷史發展傾向。
中國傳統民間工藝強調寓美于實用之中,同時特別倚重于技藝之美的表現。技藝是對常規性的生活行為敘事的超越,經過程式化的操演,成為民眾價值觀念、信仰形式、審美感受和生命意識的表達方式。莆田木雕工藝的發展始終體現了對藝術作品技法的把握和追求,“巧思”的目的在于更好地“致用”,藝術的傳承是為民眾的生活實用服務。這一目的能否實現,有賴于“巧技”,工藝之美即是“手作之美”。[5]
莆田木雕作為一種民間的傳統手工藝,它“精微透雕”的傳統審美取向是木雕工藝世代沿襲、得以傳播發揚的原生動力。今藏于莆田市博物館的清代晚期金漆木雕果盒代表了清代莆田木雕工藝的杰出水平,盒呈八面框架,頂部外圈圓雕并蒂蓮花,蓮上立仙人與鳳凰。內盒板上透雕三國人物故事圖,板的背部透雕幾何圖案,雙層裝飾。樞與樞之間雕刻著雙手托舉起龍柱的力士神,果盒腰部纖細緊窄,果盒內部浮雕各樣的吉祥鳥,外面一層又用圓雕手法刻畫了將軍侍衛各八名。腳座底部設計呈張口毗牙的昂首獅子的造型,形態生動,憨態可掬,整體線條流暢自然。整個果盒匯集了浮雕、圓雕、透雕等多種雕刻技藝,卓然自成一體,雕法細膩嚴謹,構圖布局活潑,設計安排精妙,具有濃厚的地方藝術色彩。[6]116-119
我們知道,民間美術連接著民間風俗與社會文化的豐富意涵,承載著區域民眾質樸的生活愿景和由此產生的美學價值導向。隨著社會文明的演進,民間美術一次次的入古出新都是為了豐富民俗文化內涵,肯定個體生命意義,促進群體性的文明發展和社會繁榮。流散在不同年代的莆田木雕工藝,都以其頑強的生命力深深地扎根于民間,在群體性社會生產生活精神享受的基礎上應運而生,經由眾多能工巧匠、藝師作坊的文化傳播、演繹創新,在看似隨意的制作中遵循著內在的規定性,傳承著著約定俗成的文化內涵。
結 語
有學者曾經說過:中華文化是藝術的文化。莆田木雕工藝,屬于文化一體的產物,它背后的審美意蘊與美學品格,源自于中國傳統文化、區域民俗文化看待世界、對待世界的東方式思維體系,源自于本土的世界觀方法論,它強調樂生與神秘,追求氣韻生動,崇尚生趣自然。莆田木雕工藝的發展就是在民俗文化視域下對中國“以藝悟道”的傳統文化的繼承,燦爛的“藝”賦予“道”以形象和生命,精妙的“道”給予“藝”以深度和靈魂。
當今社會正處于轉型期,對藝術發展也提出了新的問題。莆田木雕工藝這一優秀的區域非物質文化遺產正面臨著機械化和技藝消彌的處境。而讀圖時代的到來亦彰顯出一種圖像與藝術作品相抵牾的文化瓶頸,因而這種關注民俗文化、時代氣息與生活土壤緊密聯系的藝術創作理念應當成為今天民間工藝美術實踐的啟示。“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正如莆仙人在木雕工藝的藝術表達中融入對民俗文化的尊重和對大眾生活的關切,藝術家需要重視民俗文化底蘊的挖掘,必須重視從民俗內核中感受人與現實的真諦。這樣的藝術才能更讓人接受,藝術的傳播才能帶來更大的積極作用。[7]
只要民間美術還在,民俗文明就不會死。在這其中你能明白,萬物有情。講好民俗文化故事,弘揚獨具一格的區域民間美術是中華文化的自信。這樣的中國藝術才能真正代表中國,堅定這樣的文化自信才能使中國日益走向世界舞臺中心,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參考文獻:
[1]陳高.莆田木雕的淵源與流變[D].福建師范大學,2009.
[2]陳俁霖.以形寄神:莆田木雕中的宗教文化[N].中國民族報,2016-04-12(008).
[3]陳偉.莆田木雕研究與我的木雕創作[D].中國美術學院,2016.
[4]李精明.場域視野中的莆田木雕[J].藝術生活-福州大學廈門工藝美術學院學報,2017(01):50-53.
[5]鄭新勝.審美文化視域中的民俗[D].福建師范大學,2015.
[6]詹偉鋒.論莆田木雕傳統文化意蘊的傳承與發展[J].新美術,2015,36(12):116-119.
[7]黃波.文化認同與社會網絡:轉型期民間藝術的發展路徑[D].上海大學,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