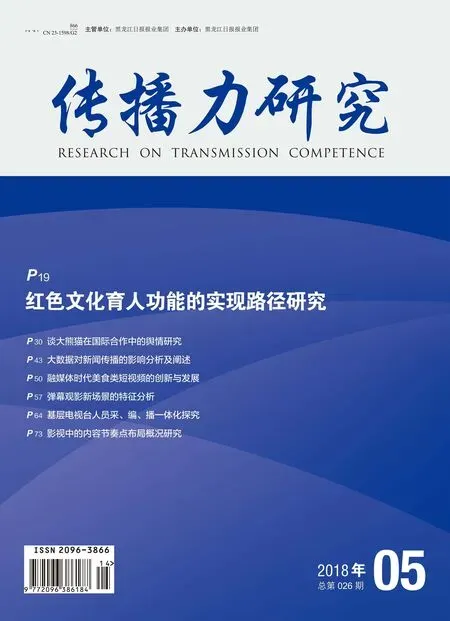社交化傳播策略下的預期落差探析
河海大學新聞傳播學系本科生
根據CNNIC在2018年1月發布的《第4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我國的手機網民規模相較2016年底新增5734萬人,總數已超過7.53億。隨著移動終端的全面普及,移動互聯網市場的這塊蛋糕越來越大,三大互聯網巨頭BAT(百度、阿里巴巴、騰訊)的市值截至2017年底分別達到0.5萬億元、2.9萬億元以及3.1萬億元,這一切與內容生產型媒體和服務類平臺的營銷方法密不可分。
最近一段時間,“社交化”成為學界談論熱烈的一個詞語,不難理解,“社交”指的是個體為在適應和融入社會而進行的人際交往,它是一種以信息、情感、價值觀念為載體的溝通和交流,社交緣起于面對面的接觸,伴隨著相對新型的媒介的不斷出現,人們獲得了更加豐富和便利的社交途徑,尤其是進入web2.0時代后,社交的成本更是大大降低。“社交化”一般是說新聞媒體在生產和傳播方式上呈現的一種新形態,基于“信息網絡化”理念以改變整個新聞在傳播過程中的各個環節,強調用戶角色的升級。①
平臺和媒體的“社交化”策略
由于媒體的存在意義或多或少與社會化相關,加之在實際運營中,“社交化”實為媒體發展與壯大的一劑良方,漸漸地各類媒體與平臺紛紛將“社交化”作為一種營銷思路。通過將產品與用戶的社交網絡圈相連接,一方面可作為延長用戶鏈的工具,另一方面更可以憑借共享和互動來增強用戶黏性,提高忠誠度。
近幾年,在市場營銷領域中,口碑營銷的影響力水漲船高,是指產品通過人際或群體之間來傳播和擴散。除商品評價外,移動優惠券也屬于口碑營銷的形式之一,目標顧客可以通過社會分享行為獲得社會獎勵以及互惠交換。微信、微博為代表的社交媒體(social media)便成為了移動互聯網口碑營銷的重要平臺,將社交網絡與人際影響相聯系,體現了“社交化”策略的應用。
但是從近幾年來看,網絡社交圈中的口碑營銷熱度仿佛有所下降。有學者曾尖銳地指出,“在某些情況下,網絡人際傳播超越了面對面交往行為中的正常情感范疇”。②也就是說,僅從傳播者一方來看,在網絡社交中,傳播者會對所要傳遞的訊息進行有選擇性的整理和裝扮,以能呈現出自己期待的模樣和結果,因此很容易使傳播理想化,與現實情形和環境存在一定差距。
“社交化”之下的用戶畫像
當用戶接近和使用傳統或新型媒體時,面對其創設的“社交化”形態下,態度和行為可分為以下兩種,一種是仍遵循傳統不做改變,以旁觀式的看客心理面對一切,不卷入媒體互動行為;另外一種是積極運用和開拓自己的社交網絡。從媒體目標實現的角度來看,第二種的確更為正向和積極。
以微信小程序為例,2017年5月,“匿名聊聊”正式上線,短短幾個小時便創造了2000萬瀏覽量的記錄,成為小程序爆紅的序曲。“匿名聊聊”恰好就是利用社交網絡拓展用戶規模的典型,用戶通過掃描他人發布在朋友圈的小程序二維碼進入特定界面,通過驗證后可與朋友匿名留言交流。而只要激發了用戶的好奇心完成第一步二維碼識別,整個傳播擴散過程就完成了大部分內容。繼“匿名聊聊”之后,相似形式互動小程序“小紙條”、“包你說”層出不窮。
但是如果仔細分析,盡管開發人員利用了用戶社交關系與互動的需求,然而傳播最終的歸宿并不是互動,用戶之所以會依照媒體的意愿主動借助朋友圈或微信群聊擴散,是因為這一行為可以帶來符號意義的傳遞或直接的獎勵,也就是說從傳播效果的角度來看,媒體的商業流量目標得以實現,用戶的原初需求也得以滿足,但深層次意義上的交流互動卻不一定真正達成。
權力關系的存在與單向傳播現象
(一)傳播中的權力觀
隨著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萌芽出現,封建制度受到質疑和挑戰,人們開始高舉人人生而平等、獨立理性的旗幟呼喊,但直到如今的現代社會,毋庸置疑,無論是經濟領域還是社會生活,但凡存在資源掌握的不平均現象,就沒有絕對的平等,只能是從國家制度和政策調控等手段盡量保證相對的平等。傳播領域更是如此,由于人們掌握不盡相同的媒體資源和信息數量,特別是在新媒體更迭快速的時代,學習和操作不同媒體的能力不同,“數字溝”長期存在。
批判學派的代表人物,法國著名社會思想家福柯早在著作《主體與權力》中提出,權力是在權力關系、交往關系和客觀能力三種關系的交織中運作的。③在福柯看來,權力關系是指個體對個體或群體對群體有意識地施加權力,可以被形象地理解成是一種游戲關系,而交往關系是一種以符號為媒介聯系個體或群體的交往類型,其中也總是夾雜著客觀能力,暗示目的性行為,通過“對伙伴之間的關注域的設定和信息域的修正來產生權力效應。”④也就是說,盡管福柯重點強調了權力關系和交往關系之間的區別,比如前者強調人作用于他人的不平等,而后者強調意義的生產和通過符號的交互性傳播,但究其本質,都是一種互相利用。這種利用放置在媒體語境中,傳播的含義便可以這樣理解:以實現主體一定的目的而進行的系列行為。
時間再早一些,庫利提出的“社會互動理論”和米德提出的“社會動作理論”以及之后布魯默的“符號互動”說法,也曾對早期心理學研究中認定的“刺激——反應”模式發起了挑戰。早期心理學研究把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看作是一種本能行為,等同于動物間的互動。這一觀點顯然不足以解釋現實生活中的社交現象。在“符號互動論”中,傳播的是帶有意義的符號,基于對符號的理解行動得以產生。因此采取行動必須有一個重要的前提:人們分析和預判事物對于自身是具有意義的,并在實際互動中,意義得以形成(可能是與預期相悖的意義)。
(二)權力關系的不平等
目的性行為一旦產生,主動方與被動方的相對處境隨之形成,表現為權力傾斜和權力缺失兩種角色。德萊弗斯曾說“穩定性的固有邏輯是不存在的。”⑤在社交行為的權力關系中,并非歷史上建立在封建王權之上的君主制話語,兩種角色的位置是相對的,沒有絕對的權力傾斜方。20世紀60年代帕羅阿爾托小組(the Palo Alto Group)提出互動理論,揭示了在傳播交流中的強勢與弱勢、平等與不平等的權力關系雖不可避免,但是可以通過有序的互動、協商與談判解決。也就是說,場景和語境的不同,每個人都有機會掌握互動權力,但卻不是人人都能掌握,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上文提到的在面對“社交化”情境時或旁觀或卷入的不同態度。
一旦這種主導行為產生或率先發出,權力關系便失去了平衡。比如用戶的媒體使用,信息獲取多的一方在目的性行為的驅使下,通過符號傳遞要求“社交化”互動,但被動接收符號傳遞的一方相關信息獲取少甚至可能完全一無所知,對于主導方的信息發出又無控制能力,導致了在“社交化”中的權力缺失。
當下社交媒體中的“轉發”行為尤其能體現這種權力關系,根據QuestMobile在2018年5月發布的微信游戲小程序報告數據顯示,微信游戲小程序的累計用戶數已突破4.5億,而小程序的總用戶數不過5.6億,也就是說,80%使用過小程序的人都玩過微信小游戲。
早在2017年底,“跳一跳”以其簡單的界面操作和輕松的競技氛圍引發全民浪潮后,“最強彈一彈”、“紀念碑谷2”、“海盜來了”、“神手”等小游戲均借助微信這個龐大的社交媒體收到了較佳的市場反響。由于微信小游戲的開放體系,開發者為了擴散和拉新,小游戲無一例外地運用“社交化”邏輯,設定各種故事性場景,例如游戲體驗結束、情節激烈、環節精彩的時候會及時引導用戶分享,鼓勵用戶通過轉發給好友或微信群獲得“免死金牌”或其他獎勵,權力關系隨之有所體現。
接收方可能并不對該事物存在參與的動機甚至完全不知曉其內容,那么在這種互動關系中,權利平等關系失衡,用戶通過轉發行為獲得相應獎勵,實現了自身目的,使處在社交網絡的接收方陷入無法拒絕接收的狀態(如圖1)。
(三)權力傾斜導致的單向傳播
如上所述,權力傾斜方的要求互動與權力缺失方的被動接收,導致的結果可有多種情況:第一,目的性行為達成,成功實現壓制性權力,通過社交網絡彼此互動,構建出媒體期待的“凝聚”狀態;第二,權力缺失方感知到自身的被動境地,拒絕卷入互動,甚至退出權力嚴重失衡的社交網絡;第三,單方向的“偽互動”現象產生。“偽互動”即目的性“社交化”行為達成,但接收到訊息的一方并未卷入互動,或者說看似雙方有連結跡象,實際卻不存在雙向互動的情況。
在媒體營造的眾多社交化情境中,權力關系不平衡時,“偽互動”現象更為普遍。以“滴滴順風車空姐遇害”一案為例,其中滴滴平臺隱晦的信息不平等公開制度剛好可加以說明。順風車司機有權查看乘客的照片、職業、年齡等私人信息,甚至司機們可對乘客使用露骨的標簽進行評價,而這些標簽都會展示給下一位有意接單的司機,然而在乘客的界面,只有車型、牌號等車輛信息較為完整,卻也存在車人與實際不符的情況。

圖1
面對這種信息交換不平等和雙向選擇權力不平等,滴滴順風車的“社交化”邏輯也露出一些端倪,單向傳遞現象尤為明顯。司機在較為充分地知曉乘客的信息之后,抱有社交愿望要求與其產生互動,但乘客作為信息掌握不足的一方,在權力缺失中卷入愿望極低,只能出現的是被動信息接收,而不愿接受互動請求或拒絕建立社交化網絡的態度和行為。
由此可見,社交化作為傳統媒體轉型蛻變的重要路徑,越來越在傳播行為中得到應用,均想借此擴大影響力,增加營收。需要注意的是,社交化是一種理想狀態,強勢地借由社交網絡和人際影響,以達到某個人或群體的目的性行為,在實際情況中,可能面臨著權力關系失衡帶來的互動斷裂狀態。處于權力缺失的劣勢地位的人和權力主導者面對社會互動時的態度是存在差異的。
若要將單向傳播的“偽互動”轉變為“準互動”,除了要重視處理雙方的權力關系之外,如何將主導“社交化”一方的目的性行為發展成雙向的互惠和獎勵機制,以此提高另一方卷入互動的可能性,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
注釋:
①常江:《新聞生產社交化與新聞理論的重建》[J],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6期。
②趙云澤,張競文,謝文靜,俞炬昇:《“社會化媒體”還是“社交媒體”?——一組至關重要的概念的翻譯和辨析》[J],《新聞記者》,2015年第6期。
③[法]米歇爾·福柯著,汪民安主編:《福柯讀本》[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④李敬:《傳播學視域中的福柯:權力,知識與交往關系》[J],《國際新聞界》,2013年第2期。
⑤[美]L·德賴弗斯著,張建超譯:《超越結構主義與解釋學》[M],光明日報出版社,1992年版。
[1]CNNIC.第4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18,1:9,79.
[2]Shu-Chuan Chu,Sejung Marina Choi.Electronic Word-of-Mouth i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J].Journal of Global Marketing,2011,24(3).
[3]王怡紅.關系傳播理論的邏輯解釋——兼論人際交流研究的主要對象問題[J].新聞與傳播研究,2006(02):21-26+94-95.
[4]QuestMobile.微信游戲小程序報告:爆款不斷、轉化效應已經顯現…….2018,5.http://www.questmobile.com.cn/blog/blog_14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