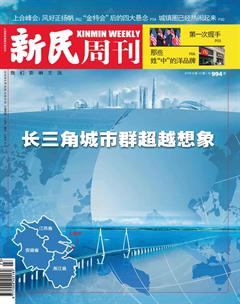“跨國聯姻”的喜與悲
吳雪

吉利收購沃爾沃、聯想并購 IBM、中化集團收購先正達,海爾并購美國GE……中國一系列“出海”觸角,裹挾著資本、懷揣著夢想,借著“中洋聯姻”橄欖枝,謀劃占據海外并購的“未來高地”。
據聯合國發布的《2017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16年,從傳統能源業、礦業到制造業、金融業,中企跨境并購交易額,以2210億美元超越2015年兩倍多的成績,創下歷史新高,中國亦首次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對外投資國。似乎,中企海外并購的“紅利大時代”已然來臨。
然而,奔著“全球化戰略布局”的終極目標,縱觀十年的并購時間線,這場世界級“逐鹿”,真正的昭示遠不止于此。專家坦言,2017年,是海外并購熱潮“拋物線”的一年,一面是并購數量節節攀升,另一面是平均交易額連續下降。
據統計,“走出去”企業中僅有52%盈利,持平及虧損的各占24%;并購實際有效率僅為30%,綜合“加權跨境跨文化整合”的關鍵因素,最終成功嶄露頭角的可能還不到20%。在“冷熱不均”大數據的推波助瀾下,大多數項目折戟沉沙,恐在意料之中。
聯姻要“純粹”
傳統行業大刀闊斧改革,帶動技術管理創新轉型升級,絕非始于今朝。近年來,互聯網科技一鍵激活創新“快車道”,新興商業模式不斷裂變、融合,消費升級和產業升級雙驅動,正在重組國人新理念,注入新動能。許多人的消費動因由最基礎的功能性,轉而更關注情感、品位、品質,并且愿意為其支付溢價。在消費群體更愿意為情感、品質、品位支付溢價的大氛圍下,購買先進技術、成熟品牌和渠道、探索發達國家市場的“價值洼地”,成為中企“走出去”邁向全球化的“首要功課”。中西歐、北美作為海外“目標棋子”一步步被中國企業收入囊中,修成正果。
“中洋”并購恰如婚姻,因真愛而相守,目的純粹,方能闊步前行。但也不得不承認,“中洋”基因的天然本土屬性,不同“聯姻”走向亦會天差地別。在30%的并購成功數值中,無論關乎品牌戰略、全球拓展或技術轉讓,初衷均為彼此“貼金”。吉利與沃爾沃這樁“窮小子與貴公主”的聯姻歷來值得稱道。2010年8月,吉利斥資18億美元,完成了對沃爾沃全部股權的收購,跨越了試探磨合期、七年之癢,8年“相濡以沫”,頂著“門不當戶不對”的輿論旋渦,吉利由早年虧損到持續盈利,由前兩年銷量增幅稍有起色到2018年在中國市場完成銷量超1.1萬輛、連續5個月破萬的傲人成績,創造了進軍全球高端車市場的“反轉奇跡”。
于吉利而言,它要的只是沃爾沃的技能、經驗及未來的國產車型;于沃爾沃而言,金融危機下的“賠本業務”由中國市場接盤,是再好不過的“重生機會”。雙方一拍即合,聯手互補、深耕進階,可以說是“逆襲成功”了。然而,在外界看來,吉利與沃爾沃并不般配,以小吃大的“蛇吞象”并購,到底能走多遠,看好的人不多。十年前,作為中國企業第一宗大型跨境收購案,聯想收購了IBM個人電腦業務,也是“蛇吞象”的典型代表。“誰都以為,聯想攀上了‘高枝,實際上十年前的IBM是打算放棄PC業務,而十年后的聯想,也并未想過將雞肋一樣的PC業務復活,搞出點名堂。”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學院陳宏民教授認為,有些看似成功的并購案背后,除了企業的雄心壯志之外,其實還有政府的無形之手。
麥肯錫發布的《2017中企跨境并購袖珍指南》證實了這點:“那些搶占頭條的大型并購案并不具有代表意義。”極少數企業的并購成功與坊間傳說的政府背景智囊團指導跨境并購行動,不無關系。固然,跟著政策走,批文下得快,貸款早到位,甚至獨家競爭福利,為不可控風險“兜底”,通通有了“保險杠”,但最終對并購決定負責的并非政府,仍是企業本身。因此,在中國累計達成650多宗1億美元以上的并購交易中,多數決策仍出于商業利益考慮,而這個“大多數”才是30%成功案例的最該探討的范疇。
如今,中國作為國際戰略及財務投資的常客,打開海外并購“天時地利人和”的金鑰匙,源于“純粹”二字,簡單解讀,即為互惠互利的純商業化初衷。“何為純商業初衷,無非兩層含義,第一,開拓國外市場,實施全球戰略布局;第二,反哺中國市場,提升品牌價值,完善產業鏈。”陳宏民解釋道,真正成功的海外收購,即雙贏。
中國紡織巨頭山東如意集團,自2010年就打著“全球戰略布局”的如意算盤,8年時間,順利將12個海外品牌改名換姓為“中”,其中,包括日本NO.1服裝品牌RENOWN,法國Sandro、Maje、Claudie Perlot,英國Aquascutum三大輕奢品牌,涉及上游原材料、制造企業以及品牌服飾。“產能過剩、市場低迷、品牌弱化,讓如意在內的眾多實力企業踏足海外并購,以求拓展新的增長點和轉型之路。”要客研究院院長周婷表示。據貝恩發布的《2017年中國奢侈品市場研究》報告,2017年中國內地奢侈品銷售額達1420億元,創歷史新高。借著中國奢侈品最大的紅利增幅,如意集團,將完成從服裝加工供應商向全球頂級服飾奢侈品牌集團的華麗轉變。
當然,具備戰略眼光的不止如意,2014年11月12日,錦江國際一舉拿下喜達屋集團旗下盧浮集團100%控股,經此一役,錦江國際躋身全球酒店排名前8位,2800家酒店、34萬間客房,遍布全球52個國家和地區,至此,錦江國際版圖更顯“世界范兒”。
借力國際化,反哺中國市場,眾多品牌也“鉚足了勁兒”。2017年1月6日,美的集團支付37億歐元,并購德國工業機器人公司庫卡,持股比例94.55%,這意味著中國終于有機會進入機器人產業的第一陣營,推動智能制造的發展。
2016年6月7日,海爾斥資55.8億美元收購美國通用電氣公司家電業務,通過雙方人才及用戶基數的文化基因整合,實現了從傳統的家電領先品牌到智能家電社群平臺轉型,更實現了強強聯合必定取得“1加1大于2”的喜人成果。
回顧所有跨境并購,以505宗交易為樣本,控股類投資,成功率高達45%;非控股類投資,其成功率僅為30%。似乎,控股比例對投資成敗起著關鍵性作用。其實不然,并購是個復雜的過程,控股比例變化只是表象,前期的預估,中期的觀察,后期的融合,步步走好,方可步步為贏。客觀來講,從任何單一層面,來評估一宗收購案的成敗,都不夠準確。因為我們永遠不知道如果沒有此項收購,買賣雙方現在會是什么情形。“并購很難界定成功或失敗,如果說結婚十年離婚了呢,品牌效應發揮后又賣出去了呢。這都很難說。”陳宏民告訴《新民周刊》,并購成功與否,必須追根溯源,衡量交易雙方既定目標是否實現,而真正并購后的“小日子”,才是幸福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吧。
1+1不等于2
并購如婚姻,“領證”是一回事,“過日子”又是另外一回事。一紙合同的簽訂、蓋戳嫁入“豪門”,并不代表“萬事大吉”,恰是真正挑戰的開始。要客研究院院長周婷說:“中企海外并購時常面臨著‘吃得下卻‘吞不下的尷尬局面,如何消化得好,轉化得妙成為難題。”一加一的結合,并非一定等于二。如果雙方不懂“剝離一半”的妥協藝術,“有舍有得”的婚姻之道,一加一不僅不等于二,反而還會小于二。
麥肯錫2017年4月發布《中企跨境并購袖珍指南》顯示,中企過去十年的跨境并購成績并不如意。過去近300單交易中,近60%并沒有為中國買家創造實際價值,而這部分的交易總額高達約3000億美元。一邊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戰略布局,另一邊卻是被稱作“七七規律”的“并購魔咒”,即70%的并購未達到預期商業目的。
2005年,轟動一時的上汽與韓國雙龍汽車“聯姻”,堪稱“教科書級”案例。從銷量下滑、經營困難,到法院托管、申請破產,這個被稱作中國汽車工業史上“首個跨國并購案”,在風險預估不足的情況下,經歷了先進技術爭議、文化相悖整合、韓國公司中國化,直到最后一根“稻草”倒塌,上汽花了40億元落了個“賠了夫人又折兵”的下場。
按照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副院長兼教務長、會計學教授丁遠的說法,中企出海分“三步走”。第一,中企收購優質技術公司和工廠,求得資源和產能。第二,通過新技術、新人才,修煉“內功”,深耕國內市場。第三,做好以上兩點,才是全球擴張。顯然,上汽與雙龍,在毫無坦誠及信任的泡沫之上,建立起的“中洋聯姻”,第一步沒走好就“倒下”了。
只注重有形資產和財務上的整合,追求短期效益,卻忽略了成本相對高的企業文化整合,是大多數企業夭折的共性。陳宏民教授對此有一套“可行性理論”——“兼容前提下的差異化”,即“求同存異”。“兼容的基礎,即夫妻雙方三觀一致,聯姻后的文化整合、協同效應才擲地有聲,達到100分滿意。”當然,為保持并購雙方的獨立性,還要講求“差異化”,即不能太熟,樹立一定的界限感及距離感,很重要。嚴守兩點準則,“德國技術”“法國工藝”“英國制造”也就不是徒有虛名了。
如果說上汽與雙龍的“半路夭折”是文化整合不夠、管理經驗不足,那么中投集團與美國私募基金巨頭黑石集團價值30億美元的10%“聯姻”,虧損額達12.18億美元,將其失敗歸咎于人才短板,一點不為過。“實際上,大多中企缺少國際資本市場的歷練,更沒有系統的國際運營能力,從失敗中積累經驗,不如從人才入手,控制風險,把握投資時機。”要客研究院院長周婷表示。
“并購以后,中企的套路是依然保留原班人馬,這是偷懶的做法,許多企業不懂,并購的意義不在于資本合并,而在于價值延伸。”陳宏民說,中企最原始的收購意圖,多半是最初的管理團隊沒做好,重復成本高,即便你技術、產品、研發再強,不狠下心來好好“炒魷魚”,資本“打水漂”、彼此“拉下水”,只是時間問題。
表面“強強聯合”的并購,實則“原地退步”的內耗,為了避免掉進“中國特色”的并購怪圈,就必須首先消除“沒有團隊來接管”的人才壁壘,以復星集團海外收購路線為例,為了引領全球藥品創新市場戰略方向,復星提出國際化招聘不能“來了就要”,需從專業性、背景能力及海外經驗,綜合考慮。復星高管曾表示,收購日本資管平臺,哪怕是財務的人,都要使用當地的日本人。
按照聯合國和有關人口普查的統計,中國的國際人口比例只有0.04%,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比例是1.6%,發達國家是10%以上。CCG主席、原外經貿部副部長、原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表示,國際化不是語言的問題,而是一種視野及心態,消除國際人才、國際人口比例的壁壘,是中國提升軟實力進程中,最該花時間努力的事情。
未來,理性當道
十年,中企海外并購,經歷了2016年的爆發式增長、交易數量翻了近4倍之后,2017年前三季度的增長步伐變得更加合理。由感性到理性,由磨合試探到把酒言歡,“悲歡離合”的路徑,唯有企業內心自知。站在國家戰略層面,“走出去”大方向一直未變,一方面處在價值鏈低端的中國企業,迎合國際趨勢,必須參與國際化分工。另一方面,老百姓消費升級、眼界開闊,迫使企業調整產業結構、創新自我。而實現“走出去”的最快捷徑正是“收購和兼并”。
丁遠也贊同此觀點。無論是出于企業轉型,資產保值,海外并購都是一家現代化企業資產配置的“重要一步”。只要不出現劇烈的外匯波動,中企出海的大趨勢都不會改變,海外投資將成為未來“新常態”。
2018年,隨著交易的理性回歸,境外并購的特點趨勢越發凸顯。例如,民營企業“走出去”越發積極,并購基金正成為推進跨境并購的新力量,“一帶一路”政策等也將積極推動跨境并購業務。專家推測,未來5年,中企出海收購失敗率仍可能高達八成。于中國時代而言,海外并購仍然是個“全新的課題”。

而想要成功做好這一課題,需要抓住兩大趨勢,第一是消費心理變化。“時代在進步,中國人對國外品牌的扭曲度小了,一線城市明白人多了,但二三線城市仍有很大營銷空間。”陳宏民告訴《新民周刊》。除了地域及思想上亟待深耕的空白點,隨著精通國際運營的管理人才越發增多,過去并購后出現的“能力有限”“協同缺乏”的問題,或將有大幅度改善。企業更認同深度整合,也更尊重在文化與運營模式上“求同存異”的改變。
鑒于日本海外并購的“前車之鑒”,中企如不想“黯然收場”,要學會最基本的技能“養雞生蛋”。即保住已收購資源,打破一到手就“縮水”的魔咒。接著,重整且穩固管理團隊,進行文化融合。最后,結合中國資本及市場“大展拳腳”。比如,在歐洲工業發達國家德國和瑞士,失業率極低,一旦中企在收購后的管理中讓當地團隊水土不服,就會造成無法挽回的人才流失。
“今后并購的數量會減少,并購的質量會提高。‘買幾年虧幾年的例子,未來,會越來越少。”陳宏民分析,政府的無形之手或將“退出舞臺”,純商業化并購將成“主旋律”。“在跨國并購中,組織架構和跨文化管理需要長時間的摸索,是一個非常漫長甚至無聊的過程。”丁遠坦言。
為了降低風險及貿易摩擦,“中洋聯姻”模式也正在逐步由產品“走出去”、企業“走出去”轉向產業集群“走出去”。“未來,平臺型企業并購將會是主流,經營汽車的平臺收購汽車廠,經營服裝的平臺收購服裝廠。”陳宏民以蘇寧打了個比方。蘇寧作為一個家電平臺,它的優勢正是對中國電器相當熟悉,比聯想熟悉,比海爾還熟悉,比制造商更熟悉,那么,蘇寧就可以通過大數據了解中國消費者,接著去收購空調、手機等方面的國外制造商,通過生產技術、戰略合作、行業聯盟、兼并控股,全方位滲透到制造業里去,從而完成一整個產業鏈的“用戶遷移”。
“中洋”聯姻,作為全球化大趨勢,于雙方來說,都是一樁互利共贏的大事,中企得渠道、技術,外企得資金、經濟支持。何樂而不為?只是在海外并購進程中,應多點理性,少點武斷,錢才花得更值,路才走得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