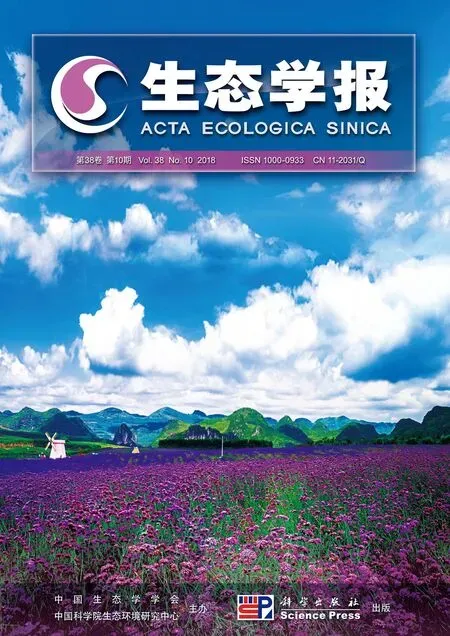旅游開發對景觀邊緣植物溢出效應的影響
劉炳亮,蘇金豹,馬建章
1 魯東大學商學院,煙臺 264025 2 東北林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哈爾濱 150040 3 東北林業大學野生動物資源學院,哈爾濱 150040
溢出效應是海洋自然保護區中某些成年魚類個體因逐漸增加的種群密度和空間資源壓力而趨于向保護區邊界外部擴散、并由此導致周邊區域種群數量增加的一種現象[1]。在海洋自然保護區中,該效應對保護區周邊的漁業管理具有重要意義[2- 4];在陸地生態系統中,溢出效應則主要被應用于森林周邊農業景觀中的昆蟲傳粉生態服務[5- 7],但在生物多樣性保護領域的應用尚不多見[8]。
作為一種運動機制,溢出效應體現了物種個體向景觀外部擴散的能力,是其運動生態學與外部環境因子綜合作用的結果[9]。對于植物物種而言,溢出效應不僅與其生活史特征——種子形態結構有關[10],同時也與擴散媒介的數量、景觀連通度等環境因子有關[9]。尤其在破碎化景觀中,植物種群通常以隔離形式存在[11],因此外部環境因子對其溢出效應的影響更為明顯。對此,Damschen等[9]在Nathan 等[12]提出的有機體運動生態學框架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植物個體的運動生態學模型。該模型描述了植物個體運動生態學與外部環境因子之間的關系,強調了外部環境因子如景觀邊緣結構、鳥[13- 14]、風[13]等擴散媒介對植物個體運動生態學的影響。
為了檢驗該模型,Brudvig和Damschen等[8]以植物的個體運動生態學——種子擴散模式為分類依據,對美國東南部薩凡納河(Savannah River)流域森林景觀中的動物擴散物種、風擴散物種和無助力擴散物種3個類群的溢出效應分別進行了對比實驗,以此反映外部環境因子(景觀邊緣結構)對不同植物運動生態學的影響。結果發現,不同的景觀邊緣結構和連通效應對動物擴散物種、風擴散物種以及重力擴散物種的溢出效應均產生了明顯不同的影響。其中,動物擴散物種和風擴散物種在具有高連通度的景觀邊緣均產生了明顯的溢出效應,但重力擴散物種無明顯響應;而在低連通度的景觀邊緣,3種溢出效應均不明顯。該結果證明了外部環境因子對植物運動生態學的影響[15]。
基于以上研究的思考:(1)如果外部環境因子對植物的運動生態學具有重要影響并最終導致不同的邊緣溢出效應,那么在旅游景觀中,旅游開發導致的景觀邊緣結構的改變以及游憩活動將對不同擴散模式的植物溢出效應產生何種影響?這種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2)旅游開發形成的交通廊道因其增加了景觀在空間上的連通性是否會使其具有生態廊道功能而促進物種向邊緣溢出?對此,本研究以Damschen 和Brudvig等提出的植物個體運動生態學框架為理論基礎,同樣以植物的個體運動生態學——種子擴散模式為分類依據,對旅游景觀中不同擴散模式的植物邊緣溢出效應進行對比分析,以此驗證旅游開發活動對植物溢出效應可能產生的影響。
1 實驗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本研究選擇中俄邊境的興凱湖自然保護區(45°01′—45°34′N,131°58′—133°07′E)進行野外實驗。興凱湖自然保護區是亞太地區候鳥遷徙的重要通道,具有較高的鳥類多樣性。據最新統計,興凱湖有鳥類237種,包括丹頂鶴(Grusjaponensis)、東方白鸛(Ciconiaboyciana)等國家一級保護鳥類9種,國家二級保護鳥類41種。除了鳥類之外,興凱湖也具有較高的野生動植物物種多樣性,其中脊椎動物363種,包括國家二級保護動物5種;獸類40種,包括赤狐(Vulpesvulpes)、雪兔(Lepustimidus)、馬鹿(Cervuselaphus)等;高等植物691種,其中國家級珍稀瀕危植物10種,包括興凱湖松(PinustakahasiiNakai)、胡桃楸(JuglansmandshuricaMaxim.)、水曲柳(FraxinusmandschuricaRupr.)、黃檗(PhellodendronamurenseRupr.)、紫椴(TiliaamurensisRupr.)、野大豆(GlycinesojaSieb. Et Zucc.)等。
興凱湖自然保護區內氣候溫差較大,年平均氣溫3℃,其中1月份最低達-39℃;7月份最高可達36℃;年均降水量654 mm;年平均風速4.0 m/s,年均大風天數38 d;無霜期147 d,湖水封凍期160 d。
興凱湖自然保護區包括了森林、濕地、湖泊等多種景觀類型,部分景觀由于人類長期的生產、生活活動已經發生了明顯改變。尤其是近些年旅游開發進一步導致了部分景觀的破碎化,形成了大量的生境斑塊、邊緣結構以及人工廊道。同時,旅游業的迅速發展也使旅游者數量大幅增加,這為溢出效應干擾實驗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1.2 調查方法
野外實驗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游憩帶與非游憩帶的邊緣溢出效應對比分析,另一部分是交通廊道與非交通廊道的邊緣溢出效應對比分析。前者是為了驗證旅游開發導致的景觀改變和游人干擾是否對植物溢出效應產生了顯著影響;后者是為了驗證交通廊道是否具有生態廊道功能而有利于物種向景觀邊緣溢出。
地點選擇興凱湖自然保護區的蜂蜜山景區進行。調查時間為2015年8—9月。該區域景觀植被主要包括興凱湖松(PinustakahasiiNakai)、蒙古櫟(Quercusmongolica)、黃檗(PhellodendronamurenseRupr.)、色木槭(Acermono)、榛(Corylusheterophylla)、胡桃楸(Juglansmandshurica)、烏蘇里苔草(Carexussuriensis)、胡枝子(Lespedezabicolor)、大葉章(Deyeuxiapurpurea)、小葉章(Deyeuxialangsdorffii)、柳葉繡線菊(Spiraeasalicifolia)、玉竹(Polygonatumodoratum)、黃連(Coptischinensis)、車前(Plantagoasiatica)、野艾蒿(Artemisialavandulaefolia)、狗尾草(Setariaviridis)等。
游憩帶與非游憩帶的調查方法是在同一景觀中選擇有旅游干擾的游憩帶和無旅游干擾的非游憩帶兩個實驗地點,分別采用樣方調查法對所有維管植物進行調查統計。為了保證調查樣本的獨立性,避免可能因環境差異帶來的影響,兩個實驗地點的距離大約為3 km,具有相似的植物組成和微氣候條件。兩個實驗地點的林緣朝向一致,坡度均 ≤ 20°。其中游憩帶存在大量游人活動和人工景觀,旅游活動頻繁;而非游憩帶未經旅游開發,無游憩活動干擾存在。
樣方設置參照López-Barrera等[16]和Brudvig等[8]的方法,在兩個實驗地點分別建立10條(間距50—150 m不等)垂直于景觀斑塊邊緣(視喬木形成的邊界作為景觀邊緣)的樣帶,每條樣帶總長80 m,寬10 m。由于景觀外部的灌木和草本植被覆蓋大約30 m的寬度,因此樣帶在景觀外部的長度設置為30 m,內部為50 m。將每條樣帶劃分為8個10 m×10 m的連續樣方,然后對樣方內所有當年生的維管植物實生苗進行調查統計。
廊道溢出效應的測度方法與游憩帶相似,即選擇交通廊道(有大量機動車)和非交通廊道(無機動車的狹長開放空間)進行對比分析,兩者寬度相近,約30 m。交通廊道中由于存在大量的機動車,其產生的交通噪音對鳥等擴散媒介的干擾幅度可能較大,因此將調查距離延伸至景觀內部100 m。外部樣方連續設置(0—30 m),內部樣方為間隔設置,距離林緣分別為10,20,40,60,100 m。然后對樣方內所有當年生的維管植物實生苗進行調查統計。
1.3 物種識別與分類
首先對野外調查發現的所有維管植物物種進行識別和分類。物種識別主要參照《中國植物志》、中國植物物種信息數據庫(http://www.plants.csdb.cn/eflora/Default.aspx)、《黑龍江省植物志》以及保護區專家和現有資料等進行綜合判別。然后再將所有記錄到的物種以擴散模式作為分類依據劃分為動物擴散、風擴散以及無助力擴散(這里主要指重力、彈射等只能幫助其在短距離內擴散的物種)物種3個類群。之所以采用該劃分模式,是因為自然界中絕大多數維管植物都是通過這3種方式實現擴散的,而動物和風等擴散媒介受外部環境因子的影響較為明顯,因此這種劃分方法可以有效反映環境因子對物種運動生態學的影響。由于某些物種可能同時存在多種擴散模式[17],因此在本研究范式中只采用對其擴散距離產生顯著影響的擴散方式作為分類依據。
擴散模式的判別主要通過已有文獻或觀測果實、種子的形態結構來進行判別。動物擴散的種實通常為漿果、堅果,具有適合動物擴散的特征,如某些具有鮮艷的顏色、假種皮或脊,某些具有粗硬的鬃毛或棘刺等;風擴散的種子通常細小且數量較多,或具有適合風力擴散的細軟冠毛及翅狀結構,能隨著風、空氣遠距離傳播;無助力擴散物種通常不具有助其長距離擴散的明顯結構,體積通常較大,只能通過彈射或重力進行擴散。對無法識別的物種可以參照同科、同屬植物果實和種子特征進行綜合判定。
1.4 數據處理
本研究采用物種豐富度(物種數量)指標對溢出效應進行測度。測度方法采用統計學中的獨立樣本t檢驗(Two samplet-test)來分別比較游憩帶與非游憩帶、交通廊道與非交通廊道的物種溢出效應的差異性。顯著性水平設置為α=0.05;相關圖形通過Origin 8.5軟件來完成。
2 結果分析
調查期間共記錄89個物種,分屬38個科。其中,動物擴散34種,風擴散39種,無助力擴散16種。非游憩帶中所有物種在游憩帶中均有記錄,兩者的總體多樣性并不存在顯著差異(P> 0.05)。但某些數量較少的物種在游憩帶的部分樣方中未見記錄。
對比結果顯示,游憩帶與非游憩帶中動物擴散物種、風擴散物種、無助力擴散物種均表現了明顯不同的邊緣溢出效應(圖1)。非游憩帶動物擴散物種表現了明顯的邊緣溢出效應,且隨著與邊緣距離的增加溢出效應逐漸衰減。其中,在外部0—-10 m的林緣,物種豐富度均值達到7.1,比景觀內部高出17.5%(t=-15.62885,df= 4,P< 0.001);在-10—-20 m和-20—-30 m,物種溢出明顯減少,平均只有6.2和5.4個物種,比0—-10 m分別減少12.7%和23.9%。與非游憩帶相比,游憩帶中動物擴散物種盡管也表現了一定的溢出效應,但明顯較弱,其在外部空間中的物種豐富度均值分別只有3.5(0—-10 m)、2.2(-10—-20 m)和1.8(-20—-30 m),均顯著低于非游憩帶(-20—-30 m:t=-5.54028,df=18,P< 0.001;-10—-20 m:t=-7.87839,df=18,P< 0.001;0—-10m:t=-5.58455,df=18,P< 0.001)。在游憩帶景觀內部靠近邊緣的0—10 m距離上,物種溢出趨勢也明顯較弱,其物種豐富度平均只有5.3,顯著低于景觀內部(P< 0.04);與非游憩帶0—10 m相比,同樣明顯較低(t= -1.40933,df=18,P= 0.17578)。

圖1 游憩帶與非游憩帶的邊緣溢出效應Fig.1 Spillover effects at the edges of the recreation zones and the non-recreation zones
與動物擴散物種不同,風擴散物種在游憩帶和非游憩帶中均產生了明顯的溢出效應(圖1),但游憩帶中風擴散物種的溢出效應強于非游憩帶(t=-1.51186,df=2,P= 0.2697)。非游憩帶中風擴散物種的豐富度在開放空間中的均值為8.4,比景觀內部平均高出13.5%(P< 0.05),且隨著與邊緣距離的增加呈現了明顯的衰減效應。但在游憩帶外部空間,雖然風擴散物種溢出效應較強,但并沒有表現出明顯的空間衰減。在開放空間中,風擴散物種的豐富度均值為8.8,比非游憩帶高出4.8%(P> 0.05),比其內部平均高出17.6%(P< 0.04)。此外,風擴散物種在兩個實驗景觀內部邊緣均表現了明顯的溢出趨勢,尤其在0—10 m的林緣,其豐富度均顯著高于內部20—50 m的水平(P< 0.01)。
無助力擴散物種(包括重力擴散、彈射擴散等無法長距離擴散的物種)在兩個實驗景觀中均只有少量溢出(圖1)。非游憩帶無助力擴散物種在0—-30 m的外部空間平均溢出1.9種,比景觀內部(均值4.0)平均低51%(P< 0.001)。除了在0—-10 m的邊緣有少量溢出(均值3.1),在-10—-30 m的范圍內無助力擴散物種幾乎未見記錄;而游憩帶外部空間,無助力擴散物種豐富度平均只有1.0。即使在外部0—-10 m的距離范圍內同樣較少,在大多數樣方中未見記錄。在內部0—10 m距離上,無助力擴散物種的豐富度同樣較低,與其內部10—50 m相比,差異性顯著(t=22.04541,df=3,P< 0.001)。
動物擴散、風擴散以及無助力擴散3個類群共同決定了兩個實驗區的總體溢出效應(圖1)。結果顯示,總體溢出效應在兩個實驗帶明顯不同。由于動物擴散物種的消極響應,游憩帶總體溢出效應在10—-30 m的距離上均顯著弱于非游憩帶(t=-3.07562,df=4,P< 0.04)。但在10—20 m的景觀內部,游憩帶的物種豐富度水平略高于非游憩帶(P< 0.06)。在非游憩帶,總體溢出效應相對較強,在邊緣0—-10 m的距離上物種豐富度均值達到19.0,顯著高于景觀內部平均水平(t=-11.28726,df=4,P< 0.001);而在景觀內部0—10 m,物種豐富度顯著高于游憩帶(P< 0.04)。

圖2 交通廊道與非交通廊道的邊緣溢出效應Fig.2 Spillover effects at the edges of the traffic corridors and the non-traffic corridors
對廊道邊緣溢出效應的對比結果顯示(圖2),交通廊道中的動物擴散物種和風擴散物種同樣表現了與非交通廊道顯著不同的邊緣溢出效應(動物擴散物種:t=4.72746,df= 2,P< 0.05;風擴散物種:t= -6.54654,df= 2,P< 0.03)。這種差異性主要體現在景觀外部-10—-30 m的距離范圍。在該距離范圍內,交通廊道中的動物擴散物種溢出效應明顯較弱,形成了明顯的空間梯度(P< 0.001)。但在0—-10 m的緣帶,交通廊道與非交通廊道均存在明顯溢出,且未檢測到有顯著差異(P> 0.05)。
盡管風擴散物種在兩種不同的廊道中均有大量溢出(圖2),但交通廊道風擴散物種的溢出更為明顯,尤其在距離林緣-20—-30 m(即靠近道路較近一側)的距離上豐富度均值達到10.4,顯著高于非交通廊道(P< 0.03)。在0—10 m的景觀內部,交通廊道與非交通廊道中風擴散物種豐富度同樣較高。非交通廊道的開放空間中,風擴散物種的溢出數量隨著與景觀邊緣距離的增加逐漸減少。
交通廊道與非交通廊道中無助力擴散物種的溢出效應同樣較弱(圖2),且無顯著差異(t=-0.2116,df= 2,P= 0.85202)。交通廊道的整個外部空間0—-30 m無助力擴散物種豐富度平均只有1.2,在距離林緣較遠的區域,無助力擴散物種未見記錄。而在景觀邊緣內部(0—10 m),交通廊道無助力擴散物種相對較少,但與非交通廊道相比無顯著差異(P> 0.05)。
盡管兩種類型廊道中的動物擴散和風擴散物種的溢出效應存在顯著差異,但對總體溢出效應的檢驗發現,兩者之間并無明顯差異(t=1.04876,df= 2,P= 0.40434)。如圖2顯示,景觀邊緣兩側(0—-10 m和0—10 m)總體豐富度均較高,外部0—-10m的距離上溢出效應明顯。在景觀外部,隨著與邊緣距離的增加,兩個實驗廊道中總體溢出效應均逐漸減弱;而在景觀內部,物種豐富度無顯著差異(P> 0.05)。
3 討論
結果發現,游憩帶與交通廊道均產生了與非游憩帶和非交通廊道明顯不同的邊緣溢出效應,旅游開發可能是導致這些結果的主要原因。
在本實驗景觀中,游憩帶與交通廊道中動物擴散物種的溢出效應均明顯弱于非游憩帶和非交通廊道,這可能來自3種影響機制:首先,旅游開發與游人活動導致的景觀改變可能降低了某些物種的生態連通度,阻礙了動物擴散媒介對其種子的傳播[18]。而且在游憩帶開放空間中修建的大量人工游憩設施等可能也增加了景觀的隔離,干擾了某些小型動物如嚙齒類對某些大型種子的擴散;其次,定向傳播假說[19]認為,動物擴散媒介有助于種子向適宜生境傳播[20]、增加幼苗的更新成功率[21]。然而在游憩帶,旅游開發導致了林緣外部生境的嚴重退化,如土壤硬化、水土流失、細菌繁殖等。這種退化可能影響了動物擴散物種向該區域的傳播,減少了幼苗的更新成活率;第三,旅游開發對景觀邊緣結構的改變也可能對物種擴散產生影響[22-23]。在本研究區中,盡管早期的人類活動已經導致了一定程度的景觀改變,但近些年來旅游開發對景觀結構的改變更為顯著。尤其旅游開發過程中產生了大量具有高對比的硬質邊緣結構,可能增加了林緣內外環境與功能的對比和突變[23-25],影響了景觀內部物種向外部滲透和擴散[24-25]。
此外,當地旅游業的迅速發展使得旅游活動干擾越來越頻繁。野外觀察發現,某些對植物種子具有擴散作用的鳥在取食種實的過程中,明顯受到了游人的各種干擾(如觀賞、打鬧、跑動、喧嘩以及戶外運動等),嚴重影響了其取食時間和取食數量。這可能最終導致種子在該區域傳播機會的減少[26]。而在交通廊道中,大量交通工具的進入也可能對動物的取食行為產生影響。例如,Francis等研究發現,機械噪音會對某些鳥類的行為產生明顯影響,減少它們對植物種子的傳播[27]。
與動物擴散物種不同,風擴散物種在游憩帶和非游憩帶均有較強溢出,而在游憩帶更為明顯。產生這一結果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旅游開發改變了林緣結構,導致了風速和風向的明顯改變,從而更有利于細小種子向開放生境擴散[28];同時,旅游開發產生的開放生境也為外來種子提供了更多的定植空間,尤其增加了風擴散物種入侵的機會[29]。此外,由于風擴散物種的種子通常非常細小,相對于其它大型種子而言更容易附著在游人和車體上,因此游人和交通工具的進入也可能是導致該類群物種增多的原因之一。
交通廊道中風擴散物種產生了比非交通廊道更為顯著的邊緣效應,這證明了景觀連通度對風擴散物種運動的促進作用[8]。然而交通廊道中風擴散物種在距離林緣-30 m的外部空間(即道路邊緣)同樣產生了明顯的溢出,這可能是由于汽車數量以及道路邊緣風速的增加促進了細小種子在該范圍內的運動和定植。
本研究范式中的無助力擴散物種是指具有重力擴散和彈射擴散模式而無法實現長距離擴散的物種。該類群的種子通常較大,不具有動物擴散和風擴散的明顯結構特征,通常只能在幾米的范圍內擴散[9],因此這可能是導致該類群物種在所有實驗區僅有少量溢出的根本原因。該結果也與Brudvig等[8]的研究發現相一致。然而一個顯著結果是,在游憩帶景觀內部0—10 m的范圍內,無助力擴散物種豐富度明顯低于非游憩帶。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該類物種個體數量稀少,在有干擾因子存在的條件下,更容易因漩渦效應而發生本地滅絕[30]。同時,無助力擴散物種大多為動物傳粉,而旅游開發導致的景觀破碎化對動物傳粉媒介同樣能產生隔離效應,減少它們對花粉的傳播,從而影響本地某些小種群的繁殖更新[31];另外,景觀破碎化導致的外來花粉量的減少還可能增加本地種群自交衰敗的可能性[32],最終影響種群的更新[33]。除了隔離效應之外,游人活動也可能通過干擾昆蟲的傳粉行為影響本地種群的傳粉效率,導致繁殖失敗。但該推斷尚無實驗證據,有待進一步觀察和研究。
在本實驗中,總體溢出效應是動物擴散物種、風擴散物種以及無助力擴散物種溢出的綜合結果。雖然廊道的對比結果沒有發現總體溢出效應存在顯著不同,但動物擴散和風擴散兩個群體的顯著差異表明,在總體溢出效應沒有受到明顯影響的情況下,旅游開發同樣可能對某些物種產生影響。這種影響來自于對某些物種運動生態學的不同干擾效應,因此無法通過總體多樣性來反映,而需要從運動生態學加以識別,因此具有一定的潛在性。
4 結論
本研究以種子的擴散模式作為分類依據,研究了旅游景觀中不同擴散方式的植物溢出效應,反映了旅游開發對植物運動生態學產生的潛在影響。該研究表明,在旅游開發實踐中要盡可能保持景觀的完整性和自然性,減少邊緣結構,防止旅游活動對物種擴散等生態過程產生的影響。對于已經破碎化的景觀,要通過各種技術和管理手段增加斑塊之間的連通性以及邊緣的滲透性,盡可能減少對溢出效應的制約和消極影響。尤其對于自然保護區的旅游開發活動更要加強管理,防止破碎化效應以及過度的游憩干擾對物種擴散這種生態過程的影響,這對生物多樣性保護具有重要意義。
由于本研究未對種子雨和種子庫進行監測,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對旅游景觀中溢出效應與種子擴散過程之間關系的深入討論。在未來的研究中將進一步關注旅游開發對種子雨及種子庫的影響,為旅游干擾和植物擴散影響提供更直接的實驗證據。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 Rowley R J. Case studies and reviews. Marine reserves in fisheries management. Aquatic Conservation: Marine and Freshwater Ecosystems, 1994, 4(3): 233- 254.
[2] McClanahan T R, Mangi S. Spillover of exploitable fishes from a marine park and its effect on the adjacent fishery. Ecological Applications, 2000, 10(6): 1792- 1805.
[3] Palumbi S R. Fisheries science: why mothers matter. Nature, 2004, 430(7000): 621- 622.
[4] Nowlis J S, Roberts C M. Fisheries benefits and optimal design of marine reserves. Fishery Bulletin, 1999, 97(3): 604- 616.
[5] Ricketts T H, Daily G C, Ehrlich P R, Michener C D. Economic value of tropical forest to coffee produc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4, 101(34): 12579- 12582.
[6] Ricketts T H. Tropical forest fragments enhance pollinator activity in nearby coffee crops. Conservation Biology, 2004, 18(5): 1262- 1271.
[7] Gell F R, Roberts C M. Benefits beyond boundaries: the fishery effect of marine reserves. TRENDS in Ecology and Evolution, 2003, 18(9): 448- 455.
[8] Brudvig L A, Damschen E I, Tewksbury J J, Haddad N M, Levey D J. Landscape connectivity promotes plant biodiversity spillover into non-target habitat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9, 106(23): 9328- 9332.
[9] Damschen E I, Brudvig L A, Haddad N M, Levey D J, Orrock J L, Tewksbury J J. The movement ecology and dynamics of plant communities in fragmented landscap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8, 105(49): 19078- 19083.
[10] Stearns S C. Life-history tactics: a review of the ideas.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1976, 51(1): 3- 47.
[11] Franzén M, Nilsson S G. Both population size and patch quality affect local extinctions and coloniza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 2010, 277(1678): 79- 85.
[12] Nathan R, Getz W M, Revilla E, Holyoak M, Kadmon R, Saltz D, Smouse P E. A movement ecology paradigm for unifying organismal movement research.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8, 105(49): 19052- 19059.
[13] Levey D J, Bolker B M, Tewksbury J J, Sargent S, Haddad N M. Effects of landscape corridors on seed dispersal by birds. Science, 2005, 309(5731): 146- 148.
[14] Jordano P, Forget P M, Lambert J E, B?hning-Gaese K, Traveset A, Wright S J. Frugivores and seed dispersal: mechanisms and consequences for biodiversity of a key ecological interaction. Biology Letters, 2011, 7(3): 321- 323.
[15] Hale M L, Lurz P W W, Shirley M D F, Rushton S, Fuller R M, Wolff K. Impact of landscape management on the genetic structure of red squirrel populations. Science, 2001, 293(5538): 2246- 2248.
[16] López-Barrera F, Manson R H, González-Espinosa M, Newton A C. Effects of varying forest edge permeability on seed dispersal in a neotropical montane forest. Landscape Ecology, 2007, 22(2): 189- 203.
[17] Van der Pijl L. Principles of Dispersal in Higher Plants. 3rd ed. New York: Springer, 1982: 499- 499.
[18] Rolstad J. Consequences of forest fragmentation for the dynamics of bird populations: conceptual issues and the evidence. Biological Journal of the Linnean Society, 1991, 42(1- 2):149- 163.
[19] Howe H F, Smallwood J. Ecology of seed dispersal.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1982, 13: 201- 228.
[20] Wenny D G. Advantages of seed dispersal: a re-evaluation of directed dispersal. Evolutionary Ecology Research, 2001, 3(1): 51- 74.
[21] Wenny D G, Levey D J. Directed seed dispersal by bellbirds in a tropical cloud fores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998, 95(11): 6204- 6207.
[22] Cadenasso M L, Pickett S T A. Effect of edge structure on theux of species into forest interiors. Conservation Biology, 2001, 15(1): 91- 97.
[23] Ries L, Fletcher R J Jr, Battin J, Sisk T D. Ecological responses to habitat edges: mechanisms, models, and variability explained.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Evolution, and Systematics, 2004, 35: 491- 522.
[24] Cadenasso M L, Pickett S T A, Weathers K C, Jones C G. A framework for a theory of ecological boundaries. BioScience, 2003, 53(8): 750- 758.
[25] López-Barrera F, Newton A. Manson R. Edge effects in a tropical montane forest mosaic: experimental tests of post-dispersal acorn removal. Ecological Research, 2005, 20(1): 31- 40.
[26] 劉炳亮, 蘇金豹, 馬建章. 旅游區游憩活動對鳥類擴散種子的影響. 生態學報, 2017, 37(14): 4786- 4794.
[27] Francis C D, Kleist N J, Ortega C P, Cruz A. Noise pollution alters ecological services: enhanced pollination and disrupted seed dispersal.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012, 279(1793): 2727- 2735.
[28] Damschen E I, Baker D V, Bohrer G, Nathan R, Orrock J L, Turner J R, Brudvig L A, Haddad N M, Levey D J, Tewksbury J J. How fragmentation and corridors affect wind dynamics and seed dispersal in open habitat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4, 111(9): 3484- 3489.
[29] Orrock J L, Danielson B J, Burns M J, Levey D J. Spatial ecology of predator-prey interactions: corridors and patch shape influence seed predation. Ecology, 2003, 84(10): 2589- 2599.
[30] Manne L L, Pimm S L. Beyond eight forms of rarity: which species are threatened and which will be next? Animal Conservation, 2001, 4(3): 221- 229.
[31] Wilcock C, Neiland R. Pollination failure in plants: why it happens and when it matters. Trends in Plant Science, 2002, 7(6): 270- 277.
[32] Groom M J. Allee effects limit population viability of an annual plant. The American Naturalist, 1998, 151(6): 487- 496.
[33] Luck G W, Daily G C. Tropical countryside bird assemblages: richness, composition, and foraging differ by landscape context. Ecological Applications, 2003, 13(1): 235- 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