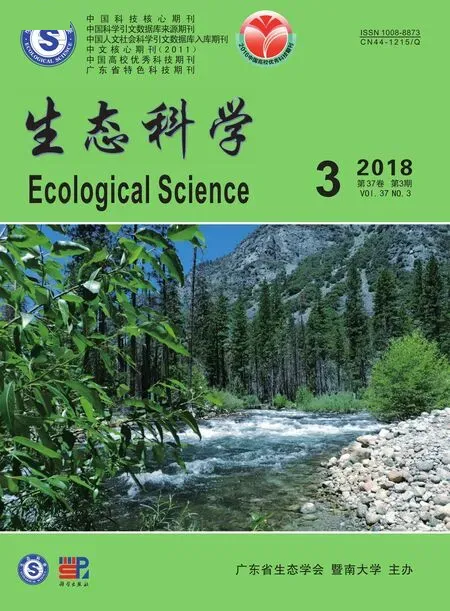青藏高原高寒生態區生態系統脆弱性時空變化及驅動機制分析
郭兵, 孔維華, 姜琳, 范業穩
1. 山東理工大學建筑工程學院, 山東 淄博 255000
2. 華東師范大學地理信息科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 上海 200241
3. 武漢大學測繪遙感信息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 武漢 433079
4. 區域開發與環境響應湖北省重點實驗室, 武漢 430062
5. 東華理工大學江西省數字國土重點實驗室, 南昌 330013
6. 地理國情監測國家測繪地理信息局重點實驗室, 武漢 433079
7. 浙江水利水電學院, 杭州 310018
1 前言
生態系統是構成陸地生態圈的最基本組成單元之一, 是維持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1]。20世紀以來, 氣候變暖狀況日益加劇, 全球氣候與環境發生了極大變化, 物種多樣性喪失、極端天氣事件頻發、沙漠化加劇、兩極冰川融化等正是對生態系統變化的強烈反饋, 極大的威脅了人類的生存和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2]。關于“脆弱生態環境”、“生態系統脆弱性”的研究已引起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目前 IPCC(2010)的定義相對權威, 認為生態系統脆弱性研究內容主要包括生態系統自身變化的評價、生態系統響應變化的敏感性評價、變化對生態系統造成的潛在影響評估和預測以及生態系統對外界脅迫或變化的適應性評價[3]。生態系統脆弱性是生態系統在特定時空尺度相對于外界干擾所具有的敏感反應和自恢復能力, 是自然屬性和人類經濟行為共同作用的結果。中國是世界上脆弱生態類型最多的國家之一, 其中青藏高原高寒生態區則是生態系統脆弱性最為明顯的地區, 主要脆弱生態環境問題包括凍融侵蝕、水力侵蝕、土地沙漠化、鹽漬化、水資源匱乏等[4-5]。生態系統脆弱性的時空差異性是導致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和貧富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 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地區社會的和諧、可持續發展[6-7]。因此開展生態系統脆弱性評價研究,深入剖析生態系統脆弱性的形成原因和驅動機制,為指導生態區保護及生態環境的恢復與治理提供決策依據和技術支持, 有利于實現生態區生態系統完整性的維護和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牢固樹立生態文明觀念、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的必然要求[8-9]。
當前國內外研究學者針對青藏高原高寒生態區的脆弱生態系統開展了大量研究。李佳[10]基于生態-經濟-社會耦合模型, 運用生態旅游雙向責任制度,從生態、社會、經濟三個方向選取指標構建了評價體系, 全面剖析和研究了三江源地區生態系統脆弱性。高江波等基于MODIS數據結合生態系統結構、功能、生境的脆弱性評價指標體系, 評估了西藏高原自然生態系統的脆弱性, 并分析了其空間異質性特征[11]。肖桐等基于凈初級生產力(NPP), 利用IPCC提供的生態系統脆弱性的概念, 探討和分析了三江源地區基于NPP的脆弱性時空變化分布格局[12]。于伯華等分析了青藏高原高寒生態系統形成機制, 從3個層次選取了10個指標構建了脆弱性評價指標體系, 進而對青藏高原生態脆弱性及其區域差異進行了分析和探討[13]。春梅利用景觀指數對玉樹州7個天然草地景觀類型進行了生態脆弱性空間格局對比和分析。盡管不同的專家學者針對不同的生態類型區開展了相關的脆弱性研究, 但是由于各個研究對象的尺度和地域差異顯著, 其評價結果很難對比和推廣[14]。此外, 全球氣候變暖日益加劇, 極端氣候事件頻發, 人類活動對自然生態系統干擾強度也日趨增大, 應高度重視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在生態脆弱性評價中的作用[15]。
本研究通過深入調查青藏高原高寒生態區的生態環境背景特征(凍融侵蝕、鹽漬化、水力侵蝕、干旱等災害嚴重), 引入了極端氣候和災害指數, 構建了青藏高原高寒生態區的生態脆弱性評價體系, 并分析和探討了該地區 2000—2013年的脆弱性時空變化格局及其驅動機制, 為后續的生態脆弱性相關研究提供重要參考。
2 材料與方法
2.1 研究區域
青藏高原高寒生態區包括青藏高原大部(除去柴達木盆地), 橫跨西藏、青海、四川和云南四省(26°N—39°N, 73°E—104°E), 以高寒氣候為主, 年平均氣溫低(-5—12℃), 降水稀少, 主要集中于5月到9月[12]。該生態區水資源量約為5688.61×108 m3,占中國水資源總量的20.23%, 是長江、黃河及恒河等10余條河流的源區。青藏高原水熱時空分布格局差異顯著, 多風、干旱、低氧、寒冷、輻射強以及晝夜溫差大是高原氣候的典型特點, 加上該區大部分地區位于 5000米以上, 凍融侵蝕發育明顯, 鹽湖廣布,鹽漬化嚴重[14]。青藏高原東南部由于地形起伏較大,降水充沛并且集中, 從而導致地區的水力侵蝕狀況較為嚴重。青藏高原的地表覆被類型從東南向西北依次是森林、灌叢、高寒草原、高寒草甸、高寒荒漠, 主要的植被類型有高山松林、高山櫟林、常綠落葉闊葉混交林、針闊混交林等。該地區以草地生態系統為主,占總面積的 50.16%, 其次是荒漠生態系統, 其面積約占37%左右[12]。青藏高原高寒生態區的土壤類型空間分布具有明顯的水平地帶性和垂直地帶性, 主要有沼澤鹽土、草甸鹽土、棕鈣土、栗鈣土、寒漠土等。
2.2 指標介紹
本研究通過對青藏高原高寒生態區生態環境本底特征的實地調查, 結合《國家主體功能區規劃實施方案》、《生態環境狀況評價技術規范(試行)》以及相關研究[14-18], 同時考慮到相關指標獲取的可操作性和關聯性, 本文從水體、氣候、植被、土壤和人文五個方面選取指標構建了研究區評價體系(圖2)。
2.3 數據來源

圖1 研究區概況Fig.1 Location of the study region

圖2 青藏高原高寒生態區脆弱性評價體系Fig.2 Evaluation system of vulnerability in alpine ecological fragile region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表1 指標介紹及生態學意義Tab.1 Evaluation indexes and ecological significance
土地利用遙感監測數據采用中國科學院遙感與數字地球研究所(2000年、2005年、2010年)和國家自然資源和地理空間基礎信息庫項目辦公室(2013年)提供的中國土地利用遙感監測數據集, 空間分辨率為1 km2x1 km2。NPP數據來自MOD17A3產品,該數據集的時空間分辨率分別為1 km和1年, 可以從Level 1 and Atmosphere Archive and Distribution System(LAADS)官方網站免費下(https://lpdaac.usgs.gov/products)。GDP公里格網數據(GDP密度)來源于中國科學院遙感與數字地球研究所(2000年、2005年、2010年)和國家自然資源和地理空間基礎信息庫項目辦公室(2013年), 空間分辨率為1 km。氣象站點數據主要包括20—20時的降水量(0.1 mm)、平均風速(0.1 m·s-1)、日照時數(0.1小時)、日最高氣溫(0.1℃)、日最低氣溫(0.1 ℃)、日平均氣溫(0.1 ℃), 來源于中國氣象共享數據網。1:100萬土壤類型數據,數據格式為 Grid, 由中國科學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制。
2.4 研究方法
2.4.1 綜合指數法
當前針對生態環境脆弱性的研究多采用分級賦權重評價模型[6,10], 該方法對選取的各脆弱性評價因子分等級用于評價, 這種方法適用于大尺度的宏觀研究, 而且如果脆弱性評價因子選擇科學合理的話,結果也是比較理想的。但是考慮到不同的分級方案對最終的脆弱性評價結果的影響較大, 并且分級方案的主觀性很強, 為了避免指標分級過程中人為因素的過多干擾, 本文采取一級指標分級賦權重加權而二級指標歸一化賦權重加權求和兩種評價模型進行綜合研究, 以上兩種評價模型的公式一致, 如下:

其中, EVI(Ecosystem Vulnerability Index)為生態脆弱性指數; Ii為第i個歸一化指標(或分級指標);為第i個指標權重;n為指標個數。
歸一化方法:

其中,Ii為脆弱性評價指標I的歸一化值;Imin為I指標的最小值;Imax為I指標的最大值。Ii越大, 說明脆弱性指標對脆弱性影響越顯著, 脆弱性值越大;反之則越小。
2.4.2 氣候傾向率
氣候趨勢系數主要反映各氣候因子長期趨勢變化的方向和程度, 其計算方法為n個時刻的氣候因子與自然數1, 2, 3, …,n的相關系數[16-17]。其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rxt為趨勢系數絕對值;xi為氣候因子 i;x為氣候因子i的多年平均值;n為時間序列數;t為(n+1)/2.rxt越大則表明相應的氣候因子年際變化越劇烈。
氣象要素的趨勢變化的一次線性方程為:

式中: a1·10成為氣候傾向率, 單位為某要素單位/10a。根據線性回歸理論得:

式中:ρx是要素x的均方差,ρt為數列1, 2, …,n的均方差, 這樣就可以從趨勢系數rxt計算出氣候傾向率。
3 結果與分析
根據青藏高原高寒生態區的自然、人文特征及主導生態環境問題, 結合專家打分法和層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參考國內外相關科研科學研究成果、案例及文獻[3,7,18-20], 在此基礎上, 對每一個判斷矩陣行向量進行幾何平均和歸一化, 計算得到各判斷矩陣中對應每一行指標的權重,然后對各個判斷矩陣進行一致性檢驗, 其各因素判斷矩陣的一致性指標分別為 0.020、0.024、0.018、0.027、0.013, 其相應的一致性比率分別為 0.017、0.020、0.015、0.021、0.009, 其數值均小于 0.1, 表明各判斷矩陣均具有較好的一致性, 進而確定了該地區的一級指標和二級指標的相對權重(表2—6)。
利用 ArcGIS 10.2的柵格計算器, 基于表 2—6中青藏高原高寒生態區脆弱性評價體系中指標權重值, 利用綜合指數法計算生態脆弱性指數(不包括土壤), 根據該指數的數據直方圖分布和標準差結合ArcGIS10.2的 Natural Breaks 工具, 確定該指數分級閾值(表 7), 得到生態脆弱性指數(不包括土壤)的分級結果, 然后結合土壤脆弱性指數分級結果(由于土壤脆弱性計算中水力侵蝕、鹽漬化、凍融侵蝕計算指標的重復性較大, 為了避免指標的重復計算導致的其影響因子權重被擴大, 本研究對土壤指數的二級指標水力侵蝕、鹽漬化、凍融侵蝕的分級結果求最大值進而直接獲取土壤脆弱性分級結果), 進而利用柵格計算器計算獲取了青藏高原高寒生態區生態弱性值(EVI), 最后基于表格 8中的分級標準, 對青藏高原高寒生態區的四期脆弱性值進行了分級。
通過對圖3分析發現, 青藏高原高寒生態區總體上處于中度脆弱狀態: 其中極度脆弱區和重度脆弱區主要分布于噶爾縣中北部、那曲縣大部、格爾木縣、治多縣北部; 中度脆弱區則主要分布于治多縣的南部、瑪沁縣、雅魯藏布江流域的上游; 而輕度和微度脆弱區則主要集中于青藏高原東南部。其中雅魯藏布江河谷地帶區居民多從事農牧業, 對植被破壞較為嚴重, 加之坡度較大, 土壤流失嚴重,滑坡、泥石流等地質災害嚴重, 因此該地區生態系統脆弱性較大。

表2 一級指標權重Tab.2 Index weight of first level

表3 二級指標權重(水體)Tab. 3 Index weight of second level(water)

表4 二級指標權重(植被)Tab.4 Index weight of second level (vegetation)

表5 二級指標權重(氣候)Tab.5 Index weight of second level(climate)

表6 二級指標權重(人文)Tab.6 Index weight of second level(humanity)

表7 一級指標脆弱性分區閾值Tab.7 Thresholds of first level index

表8 生態脆弱性分級Tab.8 Classification of ecological vulnerability
本研究通過對不同級別的脆弱性面積及面積百分比進行統計分析發現(表 9): 近十三年中, 輕度脆弱區面積最大, 面積百分比分別為 45.62%(2000年)、41.84%(2005年)、41.92%(2010年)和37.45(2013);其次為重度脆弱區, 所占面積百分比分別為17.30%(2000年)、18.44%(2005年)、17.05%(2010年)和15.81(2013年), 呈現先增加后減小的趨勢; 微度脆弱區和中度脆弱區面積在近十三年中均呈現先減小后增加的態勢, 2013年面積百分比相比2000年分別增加4.07%和6.95%。極度脆弱區面積則在2000—2005年期間增加 12.09(104) km2, 而在 2005—2010年和2010—2013年面積有一定程度的減小, 分別為7.03(104) km2和7.87(104) km2。總體上, 2000—2005年青藏高原高寒生態區的生態脆弱性狀況加劇,而在2005—2010年和2010—2013年生態系統狀況則表現為一定程度的改善。青藏高原高寒生態區2000、2005、2010和 2013年的平均生態系統脆弱性值分別為3.80、3.93 、3.82和3.81, 因此近十三年該地區總體的生態系統脆弱性表現為先增加后減小的趨勢。

圖3 青藏高原高寒生態區2000-2013年生態脆弱性 (a)2000年; (b)2005年; (c)2010年; (d)2013年Fig.3 Ecological vulnerability of alpine ecological fragile region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in 2000, 2005, 2010, and 2013

表9 青藏高原高寒生態區近十三年不同等級脆弱性面積對比Tab. 9 Area comparisons of different grades of ecosystem vulnerability
4 討論
4.1 自然因素對生態脆弱性變化的影響
(1)海拔
青藏高原高寒生態區的海拔高度落差大(93—8805 m), 平均海拔4000 m以上, 其生態環境具有顯著的垂直地帶性分布, 海拔每升高100 m, 氣溫則降低 0.8—0.9℃。本研究分析了海拔因子對近十三年平均生態系統脆弱性分布格局及變化強度的影響。
圖4(a)顯示青藏高原高寒生態區的生態系統脆弱性平均值隨著海拔的升高增大, 達到5100 m之后脆弱性值增加幅度減小, 原因在于隨著海拔的升高,氣溫降低, 降水減小, 氣候類型由熱帶-山地熱帶-山地亞熱帶-山地寒溫帶-高山寒帶-高山寒冬風化帶-高山冰雪帶, 植被覆蓋類型則依次由山地森林-灌叢草原-山地草原-高寒草甸-高寒草原-高寒荒漠草原-高寒荒漠, 植被覆蓋度依次降低, 生物多樣性減小,生態環境逐漸惡化, 加上海拔較高的羌塘高原地區多冰雹、暴雪、大風、凍融侵蝕嚴重, 因此生態系統脆弱性隨著海拔的升高變大; 而從生態系統脆弱性值的標準差分析, 脆弱性值標準差先隨著海拔的升高而增大, 在3000 m左右達到最大值, 之后則隨著海拔的增加而減小, 原因是東南部多為低海拔地區, 受印度洋、孟加拉灣、太平洋暖濕氣流的影響,降水豐富, 植被茂盛, 植被類型多為熱帶、亞熱帶山地森林等, 人類活動干擾較小, 總體生態系統狀況較好, 因此內部差異性較小。而高海拔地區則主要分布于西部和北部, 氣溫低, 降水少, 地表覆被類型單一, 多高寒草原、高寒荒漠草原、高寒荒漠, 加上該地區凍融侵蝕、鹽漬化、冰雹、暴雪等自然災害嚴重, 生態系統脆弱性普遍較低, 內部差異不明顯。在3000 m左右的海拔帶, 為山地森林-高山灌叢-草原的過渡地帶, 植被覆蓋類型多樣, 降水較多, 加上該地區地形起伏較大, 水力侵蝕嚴重, 人口密集,人類活動干擾強度較大, 因此區內的生態系統脆弱性差異顯著。圖4(b)顯示了青藏高原高寒生態區的生態系統脆弱性變化強度與海拔的相關性, 結果表明:以2000 m、4300 m為分界點, 生態系統脆弱性變化強度的正負值交替變換, 即海拔<2000 m時, 生態系統脆弱性變化強度約等于0, 說明該海拔帶上生態系統脆弱性相對穩定, 與該地區的氣候類型、植被覆蓋類型、低人口密度等因素相關; 2000 m<海拔<4300 m時, 生態系統脆弱性變化強度為負值, 說明該海拔帶上的生態系統脆弱性呈減小趨勢, 這主要受氣候、地形、植被、人類活動影響較大; 海拔>4300 m時, 生態系統脆弱性變化強度為正值, 說明該海拔帶上的生態系統脆弱性呈增加趨勢, 與該地帶的低氣溫、低降水、植被覆蓋類型、凍融侵蝕等相關。生態系統脆弱性變化強度的標準差在2700 m左右的海拔帶上達到最大值, 說明該地區的生態系統脆弱性變化強度空間分布格局復雜多樣, 主要受地形地貌、降水、水力侵蝕、滑坡、泥石流等因素的影響。

圖4 海拔對近十三年平均脆弱性及脆弱性變化強度的影響Fig.4 Relations between altitude and average vulnerability and change intensity
(2)氣溫
為了更深入的分析探討氣溫變化強度對生態系統脆弱性變化的影響, 本節基于氣象站點數據統計和分析了氣溫氣候傾向率與生態系統脆弱性及其變化強度的相關性。圖5(a)表明: 青藏高原高寒生態區的生態系統脆弱性隨著氣溫氣候傾向率的增加而增大, 其中主要原因是20世紀80年代尤其是近十三年來氣溫增加顯著, 增加速率相比 20世紀60年代—80年代有一定程度的增大。氣溫的快速增加一方面加大了地區水分蒸發量, 加上降水和氣溫時空分布差異明顯, 造成半干旱、干旱區的旱災、沙漠化、鹽漬化加重, 另一方面加劇了高寒凍土區的凍融進程, 凍融侵蝕加重。圖5(b)顯示了生態系統脆弱性變化強度與氣溫氣候傾向率的相關性, 結果發現: 當氣溫氣候傾向率<0.24 ℃·10a-1,生態系統脆弱性為減小趨勢, 但是減小的強度逐漸降低, 說明在該區間氣溫的增加對生態系統狀況的改善產生積極的影響, 其原因在于氣溫的增加對植被的光合作用和生長期生長產生影響; 當 0.24℃·10a-1<氣溫氣候傾向率<0.52 ℃·10a-1時, 生態系統脆弱性變化強度為正值并且呈現增加趨勢, 說明氣溫的增加是該地區的生態系統脆弱性加速增大主要誘因, 該階段氣溫的增加通過蒸散比、土壤濕度、干燥度、沙漠化、凍融侵蝕等因素對生態系統產生影響; 當0.52 ℃·10a-1<氣溫氣候傾向率<0.73℃·10a-1時, 生態系統脆弱性變化強度為正值但是呈現增加減小, 說明生態系統脆弱性隨著氣溫增加速度的增大加劇的幅度減小, 該現象與地區生態系統自身本底狀況相關; 氣溫氣候傾向率>0.73℃·10a-1時, 生態系統脆弱性變化強度為負值, 說明生態系統脆弱性隨著氣溫增加速度的增大而減小, 主要原因在于氣溫的上升改變了植被在垂直空間上的分布, 從而使不適宜植被生長的部分高海拔地區的氣候發生改變, 進而改善生態環境狀況。

圖5 年均氣溫氣候傾向率與近十三年平均脆弱性值和脆弱性變化強度的相關性Fig.5 Relations between temperature climate tendency rate and the average vulnerability and change intensity
(3)降水
本節基于氣象站點統計和分析了降水氣候傾向率與生態系統脆弱性及其變化強度的相關性。圖6(a)分析了青藏高原高寒生態區的生態系統脆弱性多年平均值與降水氣候傾向率的相關性, 結果表明: 青藏高原高寒生態區的生態系統脆弱性多年平均值隨著降水氣候傾向率的增加而增大, 其主要原因有兩個,其一是青藏高原當前處于暖濕化狀態, 而氣溫升高速率尤為顯著, 并且該地區降水、氣溫增加的空間分布差異性很大, 因而造成多數地區的蒸散比增大,土壤濕度降低, 不利于植被生長, 其二是高寒地區多冰雹、暴雪, 對于區域生態環境產生一定程度的破壞, 加上快速增加的降水, 加劇了高寒凍土區的凍融侵蝕, 而東南部低海拔地區, 由于地勢起伏較大, 降水多, 且多集中于 5—9月份, 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災害頻發, 因此降水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該地區的水土流失量。圖6(b)顯示了生態系統脆弱性變化強度與降水氣候傾向率的相關性, 結果發現: 當降水氣候傾向率<18 mm·10a-1, 生態系統脆弱性變化強度為負值并且強度減小, 說明生態系統脆弱性呈現減小趨勢; 當18 mm·10a-1<降水氣候傾向率<52 mm·10a-1時, 生態系統脆弱性變化強度為正值且強度增加, 說明生態系統脆弱性呈現增加趨勢; 當52 mm·10a-1<降水氣候傾向率時, 生態系統脆弱性變化強度為正值但強度減小, 說明生態系統脆弱性增加趨勢加劇。青藏高原高寒生態區的降水氣候傾向率與生態系統脆弱性變化強度的相關性格局, 主要原因是總體上降水的增加對生態環境的改善產生積極的影響, 如土壤濕度、植被蓋度、地表水資源, 但是當降水增加速度過快時, 由于青藏高原高寒生態區的降水集中, 多冰雹、暴雪, 對植被、土壤質地都產生破壞, 容易引發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災害, 進一步加劇凍融侵蝕和水力侵蝕, 因此降水增加速度過大對生態環境產生一定的破壞作用。

圖6 年降水氣候傾向率與近十三年平均脆弱性值和脆弱性變化強度的相關性Fig.6 Relations between precipitation climate tendency rate and the average vulnerability and change intensity
4.2 人為因素(人口密度)對生態脆弱性變化的影響
人口密度作為社會經濟指標之一, 對青藏高原高寒生態區的生態系統脆弱性產生較大的影響, 本小節以縣級行政區為統計基本單元統計和分析了兩者之間的相關性, 結果(圖7)發現: 近十三年青藏高原高寒生態區的生態系統脆弱性平均值與人口密度(人·km-2)兩者相關性趨勢變化(曲線 c)可分為兩個階段: 人口密度(人·km-2)<75 和人口密度(人·km-2)>75。在人口密度(人·km-2)<75階段, 變化曲線可分為兩種情況: 曲線a和曲線b。曲線a反映的是生態系統脆弱性隨著人口密度(人·km-2)的增加而減小, 說明區域生態環境的好的地區, 氣候宜人, 水資源豐富,能夠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提供更多資源, 因此人口密集, 人口密度(人·km-2)表現為隨著生態系統脆弱性的減小而增加, 并且曲線 a還表明在青藏高原高寒生態區的生態系統脆弱性較大的地區人口承載能力為 20人·km-2, 超過該閾值, 脆弱性隨之增加; 曲線 b則反映了生態系統脆弱性值隨著人口密度(人·km-2)的增加而增大, 說明了在生態環境較好的地區, 人口數量的過度增加, 會對區域生態環境產生壓力, 進一步對區域生態環境產生一定程度破壞,因此生態系統脆弱性值會隨之增加。在 20<人口密度(人·km-2)<75 階段, 脆弱性基本保持平穩, 在人口密度(人·km-2)>75階段, 脆弱性值隨著人口密度(人·km-2)的增大而增大, 說明快速增長的人口數量超出了自然生態環境的資源承載能力和恢復能力,脆弱性值則隨之而增大, 曲線 b則表明在青藏高原高寒生態區生態環境較好的地區的人口承載力為60—80 人·km-2。
5 結論
本研究在充分考慮青藏高原高寒生態區特殊的自然生態環境背景特征(凍融侵蝕、鹽漬化、水力侵蝕劇烈, 海拔高, 氣候寒冷)的基礎上, 引入極端氣候事件因子和人類活動干擾因子構建了青藏高原高寒生態區的生態系統脆弱性評價體系, 進而對研究區近 13年的生態系統脆弱性時空變化格局及其驅動機制進行了分析和探討。

圖7 近十三年平均人口密度與平均脆弱性值的相關性Fig.7 Relations between population density and the average vulnerability
(1)青藏高原高寒生態區的生態系統脆弱性總體上屬于中度脆弱狀態, 其空間分布格局自東南向西北呈現遞增趨勢。
(2)2000—2013年, 青藏高原高寒生態區總體的生態系統脆弱性表現為先增加后減小的趨勢, 具體表現為: 2000—2005年青藏高原高寒生態區的生態脆弱性狀況加劇, 而2005—2010年和2010—2013年生態系統狀況則表現為一定程度的改善。
(3)生態系統脆弱性時空變化分異格局與地形、氣候(氣溫、降水等)、人口密度存在顯著地相關性。
由于受研究區特殊的地理區位限制, 部分評價指標的反演精度有待進一步提高。此外, 青藏高原高寒生態區的脆弱性時空變化驅動機制分析中需要充分考慮自然和人類活動因子的交互影響。以上不足之處將在后續的研究中進行深入的探討。
[1] 孫武, 侯玉, 張勃. 生態脆弱帶波動性、人口壓力、脆弱度之間的關系[J]. 生態學報, 2000, 20(3): 369-373.
[2] 李鶴, 張平宇, 程葉青. 脆弱性的概念及其評價方法[J].地理科學進展, 2008, 27(2): 18-25.
[3] 徐廣才, 康慕誼, 賀麗娜, 等. 生態脆弱性及其研究進展[J]. 生態學報, 2009, 29(5): 2579-2587.
[4] 孔博, 陶和平, 李愛農, 等. 汶川地震災區生態脆弱性評價研究[J]. 水土保通報, 2010, 30(6): 181-184.
[5] PARSON E A, COREL R W, BARRON E J, et al.Understanding climatic impacts, vulnerabilities, and adapt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building a opacity for assessment [J]. Climate Change, 2003, 57: 9-42.
[6] CHASMAL J D, QUETIER F, LAVOREL S, et al.Including multiple differing stakeholder values into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s of socio-ecological systems [J].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08, 18: 508-520.
[7] 周毅, 李旋旗, 趙景柱. 中國典型生態脆弱帶與貧困相關性分析[J]. 北京理工大學學報, 2008, 28 (3):261-263.
[8] 徐羹慧. 內陸干旱區生態環境系統與氣候系統關系的分析評述[J]. 沙漠與綠洲氣象, 2007, 1(1): 53-56.
[9] 李輝霞, 劉淑珍, 鐘祥浩, 等. 基于 GIS的西藏自治區凍融侵蝕敏感性評價[J]. 中國水土保持, 2005, (7): 44-46.
[10] 李佳. 基于旅游的社會-生態系統脆弱性研究-以三江源為例[J]. 地下水, 2012, 234(2): 210-212.
[11] 春梅. 基于景觀格局的玉樹州天然草地生態脆弱性分析[J]. 安徽農業科學, 2012, 40(15): 8599-8600.
[12] 高江波, 侯文娟, 趙東升, 等. 基于遙感數據的西藏高原自然生態系統脆弱性評估[J]. 地理科學, 2016, 4(2): 112-120.
[13] 肖桐, 王軍邦, 陳卓奇. 三江源地區基于凈初級生產力的草地生態系統脆弱性特征[J]. 資源科學, 2010, 32(2):323-330.
[14] 于伯華,呂昌河. 青藏高原高寒區生態脆弱性評價[J].地理研究, 2011, 30(12): 2290-2296.
[15] 蔣衛國, 陳云浩, 李京, 等. 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帶生態環境的空間格局演變[J]. 自然資源學報, 2005, 20(6): 871 -878.
[16] 劉曉瓊, 劉彥隨, 延軍平, 等. 生態脆弱區多年氣候變化特征分析—以陜西榆林市為例[J]. 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08, 22(1): 54-59.
[17] 周永娟, 王效科, 歐陽志云. 生態系統脆弱性研究[J].生態經濟, 2009, 11: 163-167.
[18] GALLOPIN G C. Linkages between vulnerability,resilience, and adaptive capacity [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06, 16(3): 293-303.
[19] SMIT B, WANDEL J. Adaptation, adaptive capacity and vulnerability [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06,16(3): 282-292.
[20] DUGUY B, ALLOZA J A, BAEZA M J, et al. Modelling the Ecological Vulnerability to Forest Fires in Mediterranean Ecosystems Us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J].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2, 50: 1012-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