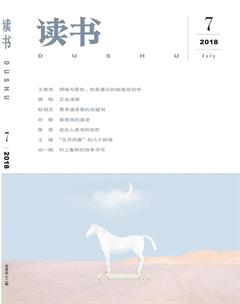“五月風暴 ”的幾個側面
王璞
垃圾堆積在幾乎每棟奧斯芒式公寓樓的門口,引發街巷中的造山運動,惡臭四散。城市停止了運轉,連地鐵也不再通行。如果你的抽水馬桶壞了,對不起,請忍耐。郵政都關門了,更別說銀行和商場。沒地方買糖,沒地方購煙,沒地方聽天氣預報。但這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在有些街區,催淚瓦斯的濃煙還在升騰,哪怕你住在五層也難以幸免。是的,這是一九六八年五月中下旬的法國巴黎。
一九六八年的 “五月風暴 ”已經過去整整五十年。關于這一 “事件 ”,從法國集體記憶的文化工業到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的歷史修辭,人們似乎已經得到了某種 “官方說法 ”。時間、地點和人物越來越確定:先開始說是五月,然后強調只是五月初;先開始說是巴黎,然后強調只是左岸,也許只是拉丁區;主角只有一個:大學生 —“反抗父親又渴望主人的孩子們 ”(拉康說過類似的話)。以致今天的法國人也常會想當然地感嘆:“對啊,書上說一切都是因為男生想獲得進入女生宿舍過夜的權利。”難道,無事生非?的確,催淚瓦斯的濃煙剛剛散去,雷蒙 ·阿隆就用了這樣的詞來形容“五月風暴 ”:“無事 ”(non-événement)。
然而,“五月風暴 ”不是僅僅關于拉丁區,甚至不是僅僅關于巴黎;“五月風暴 ”不光包括五月上旬大學生們在街頭吃到警棍的那幾天,甚至并不特指五月;“五月風暴 ”也不能說是學生運動。這是美國學者克里斯汀 ·羅斯通過《六八 “五月風暴 ”及其后世生命》一書再三強調的:不管索邦校園在整場運動中多么重要,“五月風暴 ”首先是法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總罷工。只是,這一點遭到了刻意的遺忘和涂抹,在所謂 “歷史記憶 ”中日漸模糊。克里斯汀 ·羅斯的研究是新世紀以來關于這一事件的重要論述之一,在接下來的文字中,我想透過她的視角,重訪那場運動的幾個側面,不僅為了五十周年的紀念,更為了歷史感的復活和進一步的爭辯。
一九六八年五月初,當巴黎街頭示威大學生受到警察 “棍擊 ”的消息和畫面傳遍全國,工人們行動了,聲援學生的緊急罷工在五月十三日爆發。罷工迅速從私營領域向公共事業和國家部門蔓延,從巴黎向全國蔓延。約九百萬人停止了工作。當勞動者決定不再參與資本主義的游戲,一切國家機器、所有生活秩序都在剎那間變得像影子一樣徒有輪廓,顯出了內在的虛妄。統治階級迫不及待地要求談判,而總工會(CGT)的官僚們也不知所措。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政府和總工會達成了提高最低工資等協議。工會領導和某些政黨連忙宣布:“勝利了!”但在五月的人民眼中,這不過是勞資之間的老戲碼。他們決定拋棄總工會,乃至踢開傳統左翼政黨。他們的決定很簡單:“罷工繼續 ”,“讓我們繼續斗爭 ”。
全國總罷工,這樣的歷史名詞我們還算熟悉。但今人真的能夠想象總罷工之下日常生活的狀態嗎?不論當年在羅斯教授的課堂上,還是在閱讀她專著的過程中,關于 “五月風暴 ”,我學到的最令人神往的瞬間并不是什么街頭對峙的重大時刻,而是一個生活細節:總罷工的日子里,不論是雪鐵龍汽車廠的工人,還是首都的公務員,人們閱讀 —羅斯注意到,僅在巴黎,五月和六月的書籍銷售就增加了百分之四十。當資本主義驟停,書店成了幸存的 “商業 ”,書籍成了特別緊俏的 “商品 ”。人們閱讀 —關鍵不在于讀什么,而在于本該待在流水線上、收銀臺前的人們開始閱讀。人們閱讀,人們也開始重新學習如何思考,如何行動,如何生活。人們由此質疑著乃至重新定義著社會空間(課堂、車間、會議室、街頭 ……是否應該區隔?)、社會時間(我如何 “浪費 ”這一天?)、社會身份(學生、工人、白領 ……只能各過各的日子?)。正如羅斯所論,不同于 “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 ”的既有革命模式,“五月風暴 ”展示了一種新的反資本主義實踐。
平等及其新空間
事后總有這樣的痛惜:“然而學生和工人還是沒能結合起來。”也總有譏誚的聲音:“他們壓根兒結合不了。”羅斯對 “五月風暴 ”及其后續發展的研究力圖打破這類或左或右的迷思。將學生和工人區隔開來,將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區隔開來,這其實一直是資本主義國家機器在社會空間管理上的基本功。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一日,罷工的苗頭一出,總理蓬皮杜就做出了一個意外決定:在電視講話中宣布立即重新開放被警察控制的索邦大學校園。學生們利用這個機會占領了索邦。當權者都在指責蓬皮杜讓步太大,戴高樂總統 —第五共和國的締造者和君主般的威權英雄,當時正要出訪羅馬尼亞—甚至說這是 “貝當 ”式投降。但蓬皮杜的策略才真是在營救所謂秩序:“學生的事情是一個教育改革問題 ”,工人的事情,另說。他知道學生造反和工人革命結合起來的后果,他希望學生在學校造反,工人在工廠罷工,各搞一套,各自訴求,互不串聯。
“五月風暴 ”中,學生接管了學校,把索邦變成自由議事堂,在拉丁區的周邊筑起了街壘(這是法國革命的傳統)。工人們占領了工廠,管理工廠的一切事務。但是,當學生和工人各自進行著自己的 “占領 ”時,他們的社會空間卻又一次明確了:學生在拉丁區,工人在廠區;學生在思想和辯論的地盤,工人接手了生產的場域。區隔是否反而固化了?羅斯的著作得出了否定答案:“五月的主要理念是思想爭辯和工人斗爭的結合。”她的整本書都在探照一種 “關系性 ”的新主體空間的創造及敞開。
運動中不同人群提出的訴求五花八門,彼此間辯論也無休無止,以至于一位美國觀察家曾說,這是典型的法蘭西革命,沒有統一目標和路線圖,只偏愛 “開放的過程 ”。羅斯則指出,這一開放過程正蘊含著 “五月風暴 ”的統一性。她借用當時參與者的回憶強調,
“五月風暴 ”最根本的激情是 —“平等 ”。這里的平等不再是傳統法權意義上的抽象平等,而是打破一切社會差異 —尤其是社會分工差異 —實行直接民主和進行政治參與的平等。在對平等的追求中,工人和學生其實早已結合在了一起。你能區分出五月初的街頭多少人是學生、多少人是普通市民、多少人是工人?在街頭和警察國家的近身對抗中,所謂的學生運動已然成為取消社會隔斷的新空間。羅斯記述了很多工人的經歷,他們早在五月初就已經是運動的一部分。而罷工開始后,當有些左翼學生前往工廠時,他們得到了完全的接納,不論他們只是想高談理論,還是想 “扎根 ”去當學徒工。羅斯著作的一個重要貢獻在于,她提醒我們注意屢遭忽視的 “五月之后 ”:這種互相接納的政治、這種新關系的創造,綿延于一九六八年以后的社會運動。打破資本主義專業分工和社會空間區隔的平等政治,聽起來是不是就像無政府主義的烏托邦一樣不可思議?但正如老薩特所說: “當所有人都判定這不可思議的時候,它卻的確發生了。”它的真實 “發生 ”乃至綿延究竟表現為怎樣具體的形式和實踐?這也是羅斯所要探尋的。我從她的研究中所得到的重要教誨之一是:要真正了解“五月風暴 ”,不能只聽 “學運領袖 ”和其他弄潮兒事后的一面之詞。他們中好幾位當年風頭無兩,而在退潮期卻紛紛懺悔了自己 “極左 ”的過去,搖身一變為后工業社會的成功人士乃至新自由主義的鼓吹者,又在大眾傳媒上壟斷了關于一九六八年的闡釋權。相反,羅斯引導我們去關注那些社會各界的 “普通 ”參與者,以及沒有留下署名的各類文獻。她尤其聚焦于一種新組織:行動委員會(comités daction)。不同于政黨和各類派性 “小組 ”(groupuscules),這種委員會不僅廣泛成立于學生和工人之中,而且也出現在社區和鄰里之間。
它們在罷工和占領期間負責人們的生活所需,進行政治辯論,安排綱領和文件;它們是直接民主的新形態,既不依靠絕對 “服從 ”的原則,也不遵循 “競選 ”的游戲。在它們之中,群眾積極交匯并形成看似不可能的 “主體性 ”。不少工人在桑西埃(Censier)街區的 “勞動者 /學生行動委員會 ”參與討論、油印材料,法國內務部立刻斥他們為從地獄 “潛入 ”巴黎的 “渣滓 ”;而著名作家杜拉斯和布朗肖所參加的 “作家 /學生 /勞動者行動委員會 ”以聲明回應:“我們都是渣滓。”要研究這樣的組織并不容易。羅斯強調,這些行動委員會大多并沒有主席或書記,也沒有辦公場所和預算,人員來來往往,日程和議題也不固定。但據她考證,有些社區的行動委員會持續了四年之久,遠遠超出了那個春夏之交的時間范圍。而對于 “普通”的親歷者而言,這些委員會留下的記憶比各類鏡頭所捕捉到的 “重要時刻 ”要深切得多。人們在這種新社會關系和政治形態中嚴肅
地改變著身邊的世界,也分享著集體性的快樂。如果從這一 “基層 ”的角度看,那么一九六八年所代表的不是讓 -克勞德 ·卡里耶爾等人所回憶出來的美學烏托邦,不是短暫的激情迸發,不是 “禁止一切禁止 ”(interdire dinterdire)、“快感無障礙 ”(jouir sans entraves)這樣統治街頭的詩性標語;而是再具體、再真實不過的個人和集體,是他們日復一日進行的再具體、再真實不過的創造性工作和 “行動 ”。戴高樂的“面容和嗓音”那么,激進平等的組織形態和生活實踐是否具有可持續性?難道,政權的問題不復存在了?羅斯重視舊政治的解體和新社會關系的有機生成,她站在羅莎 ·盧森堡的革命觀那一邊,但并沒有回避列寧主義之問。而這也是當時很多親歷者最直接的困惑:我們奪取了想象界、象征界,我們奪取了影像和語言,但我們沒有 “奪取政權”。根據列寧主義的原則,“奪權 ”是決定性的政治。必須用有組織的革命暴力砸碎舊有國家機器,因此必須有先鋒政黨去取得和掌握政權。一九六八年法國的局面似乎足以讓人聯想到一九一七年俄國臨時政府和蘇維埃的并存。當年,在列寧看來,資本主義國家和人民群眾組織的 “雙權 ”結構絕非長久之計,事不宜遲,立即奪權。但是,從激進平等和直接民主的角度看,列寧黨的奪權模式不可避免會帶來新的威權、新的國家機器和不平等結構。“五月風暴 ”沒有按照列寧的劇本展開,它的直接民主和集體自組織蘊含著超克列寧主義模式的命題,但并沒有得出答案,仍然表征為歷史的兩難。
五月三十日,戴高樂總統發表了電視講話,那是 “五月 ”和“六月 ”的轉折點。一位五月分子說:“戴高樂說話了 ……節日結束了。”戴高樂的聲音化身為資本主義政權的集結號。在“五月風暴 ”的進程中,戴高樂有過兩次講話。五月十九日他在從羅馬尼亞歸國后有一次講話,態度是 “改革,可以;混亂,不行 ”。他關于舉行全民公決的提議感覺像是形式民主的把戲,很快就淹沒在全國的噓聲中。一時間,一位別具威權的高大領袖,變成似乎一推即倒的空架子。二十九日,戴高樂消失了。他的消失常常被認為是法國現代史上一個重要但又曖昧的節點。后來人們知道,他去了位于聯邦德國的巴登 -巴登軍事基地,和法國駐軍總司令雅克 ·馬蘇將軍接觸。難道他要把坦克開上巴黎街頭?難道他要讓傘兵在塞納河兩岸從天而降?然后他躲進了科隆布的鄉間別墅。三十日,他回到巴黎,發表了極為簡短、只有三分鐘的電視講話,沉穩地決定:自己并不辭職,但立即解散國會并提前進行選舉。同一天,戴高樂的支持者涌上了香榭麗舍大街,右岸的 “熱愛秩序 ”的呼喊聲第一次蓋過了左岸的《國際歌》。形勢起了變化。
羅斯所引用的許多五月回憶都提到了戴高樂開口說話的三分鐘。她所沒有討論的另一則回憶,在我看來,可能更耐人尋味。那就是法國戰后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路易 ·阿爾都塞的記述。他在后來的回憶錄《來日方長》中,花了不少篇幅為自己辯護,當時他接受法國共產黨的審慎態度,不支持青年們的 “幼稚 ”造反。在自辯中,他也提到了戴高樂的講話。他關心的不是戴高樂說了什么,而是戴高樂的 “面容與嗓音 ”。阿爾都塞感覺,當戴高樂那張飽經滄桑的臉、那嚴肅的嗓音出現在電視上和電波中時,資產階級專政就已經贏了。僅僅憑著聽到這個人的聲音,全國的資產階級就足以安下心來。關鍵是它所傳達的政治無意識信號:“放心吧,我還在。”接下來,阿爾都塞就批評,當時青年低估了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無所不在的強大和穩固。雖然法國共產黨問題多多,但必須要有這樣一個黨才能具備抗衡力量。一切又回到先鋒政黨的邏輯。
戴高樂的確是國家機器的完美 “意象 ”。而我們無須是拉康的信徒(他是阿爾都塞長時間的精神分析師)也能體察到,阿爾都塞明顯在戴高樂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銀行家父親。后人常把 “五月風暴 ”簡單化地比喻為一次弒父行動。如果真是這樣,那么,阿爾都塞這樣的老黨員所扮演的角色卻是不斷向青年人呼喊:“只有我才知道父親是多么強大,你們的辦法根本不行!”于是,不僅 “結構主義不上街 ”,作為 “科學 ”的馬克思主義也不上街。在這點上,雅克 ·朗西埃等學生徹底和阿爾都塞分道揚鑣。他們認為,恰恰是這些老師最愛承認資本主義政權的穩固,在反復認出國家之父的同時,又在政黨中尋找父權的替代,跳不出 “權威 ”本身的邏輯。但“五月風暴 ”不僅僅是關于政權,更不是關于 “弒父 ”,它代表了一種不能用既有政黨模式來理解的政治。“節日 ”(它的快樂是嚴肅的)當然會結束,但新的實踐種子不死。
境遇、全球六十年代和再斷代
“最重要的是,行動發生了 ……”薩特的話的確代表了存在主義乃至境遇主義的態度。存在先于本質,在追問運動的 “本質 ”之前,我們首先要意識到,它發生了,它作為境遇展開了。在過去的五十年中,人們對 “五月風暴 ”的“性質 ”的思考陷入了一系列僵硬的二元對立:“戴高樂還是學生?革命還是心理劇?革命還是歇斯底里?事件還是無事生非?革命還是狂歡?嬉戲還是嚴肅?詞語還是行動?奪取語言還是奪取政權?”當然,還有:運動是成功還是失敗?所有這些概念分界線都是羅斯的論述所致力于消解的。激進平等從來不是理念或 “本質 ”,而是實踐。她把 “五月風暴 ”及其后續發展還原為活生生的實踐性境遇,這樣才能在各類歷史書寫的刪改之外發現 “事件 ”的“后世生命 ”。
這也意味著必須重新思考 “五月風暴 ”的歷史意義,尤其是在五十年后的今天,當“全球六十年代 ”日漸遠去,成為一個史學話題的時候,我們是否能在資本主義和反資本主義的 “大歷史 ”中給出那場運動的定位?羅斯的論述包含著從巴黎公社到 “五月風暴 ”若隱若現的線索,這一脈絡似乎暗合了忠實于 “六八精神 ”的法國哲人阿蘭 ·巴迪歐對革命長周期或革命世紀的 “斷代 ”。這一周期意味著無產階級革命的全面展開,而全球六十年代帶來了一場危機、一次飽和、一種主體性的內爆,產生了既有革命模式的內在批判。不過我認為,羅斯會更傾向于朗西埃的思想,而對巴迪歐的斷代有所拒斥。因為從朗西埃的理論來看,革命的歷史敘事往往要求一種角色扮演:誰是歷史的主體?誰是階級基礎?誰是團結對象?誰需要深入誰?誰該接受改造和再教育 ……朗西埃所警惕的是(而羅斯對此多有借重),如此一來,革命主體性或由某個 “主義 ”事先確定或由某種哲學事后追認,從而局限、遮蔽乃至壓抑了平等這一綿延不絕、隨時隨地可能發生的激進實踐。
關于 “全球六十年代 ”,更早的理論言說來自美國馬克思主義者弗雷德里克 ·杰姆遜。在一九八四年的《為六十年代斷代》一文中,杰姆遜試圖把反殖民斗爭、第三世界崛起、后現代主義文化、毛澤東和法國理論高峰連貫起來。很顯然,每一個 “境遇 ”都有非常具體的國別乃至地方性特征,但是六十年代如果可以稱為一個 “年代 ”,就在于一種 “他者的政治 ”:全球人民在他者的斗爭中理解、思考和開啟自己的實踐。“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 ……”這一點在羅斯對 “五月風暴 ”的論述中也相當醒目。沒有第三世界的革命現實,“五月 ”是不可能的:“越南就在我們工廠里 ”,法國青年工人們這樣說。早在一九六七年,關于本國罷工的《我希望,待會兒見》(A bient.t, jespère)和關于越戰的《遠離越南》(Loin du Vietnam)兩部電影是幾乎同時放映的。羅斯認為,從越南反帝斗爭在法國學生、工人中所起到的團結作用來看,我們可以同意薩特的說法,越南是 “五月 ”的根源之一。而且根據她的考察,行動委員會這種形式也可以在法國激進青年所發明的許多“基層越南委員會 ”(Comités Viet-nam“de base”)中找到前身。政治體驗的新熔巖噴發四溢,“法國工人 ”“越南戰士 ”和“赤腳醫生 ”在部分 “六八一代 ”心中凝結為三位一體的意象。
從這樣的全球聯動來斷代 “六十年代 ”,開端和終點很難界定,但有一點可以明確,在一九八四年,杰姆遜已經體察到,那種他者和自我之間革命境遇的關聯性和全球性已經消失。“西方 ”左翼和第三世界抗爭之間的想象性團結也不復存在:“西方 ”見證了 “占有式個人主義 ”的潛行、凱旋和深化;而“解殖 ”之后的第三世界困在全球體系中,面壁于發展主義現實。一九八○年,法國 “人民 ”又一次來到街頭,送葬薩特,似乎包含著時代的告別禮。朗西埃、巴迪歐等 “六八一代 ”中的少數仍在堅持探索,但作為境遇的 “全球六十年代 ”已然消逝。杰姆遜給出這樣的解釋:“經濟決定因素的復歸。”隨著資本主義的自我調整完成,新自由主義 “共識 ”穩下了陣腳,在新政治經濟現實的礁石上,激進的潮水退去。
也就是說,杰姆遜的 “全球六十年代 ”斷代建立在資本本身的全球性之上,既與之對立,又是其鏡像。他所揭示的這種 “終結 ”似乎也預示了那種最常見的 “結論 ”:“五月風暴 ”只是后工業世界的文化或 “生活方式 ”調試過程中的一次震蕩,年輕人反抗了一下 “國家、學校、教會 ”,實現了更徹底的個人性。我們又回到了 —“無事”。據悉,羅斯二00二年書中批判過的 “六八歷史學 ”今年仍然在熱鬧上演。杰姆遜要打開六十年代的豐富性和全球關聯性,但如果從羅斯的視野看去,他的斷代還是體現出過多的 “歷史決定論 ”,過于倚賴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垂直結構。于此,一面是羅斯和朗西埃對激進平等實踐的強調、對歷史敘事權威的拒斥,一面是巴迪歐對 “事件 —主體 ”和“世紀 ”的回溯性忠誠(“我仍然在那里,一直在那里 ”),還有一面是杰姆遜對資本和反抗的總體性斷代 —我的思考仍在三者間搖擺,無法做出評判。
在“五月風暴 ”五十年周年之際,我們或可在幾種思路之間保持張力和辯證,以便嘗試開啟再一次的斷代。如果再斷代是可能的,如果歷史思考和講述是可能的,那么它必然指向我們的現實,一個和過去的別樣實踐、和他者的異路、和“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 ”重新關聯的現實。至少,讓我像羅斯一樣把薩特的話引完:“……既然它發生了,那么它就可能再次發生。”
(Kristin Ross,May68 and Its Afterlive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