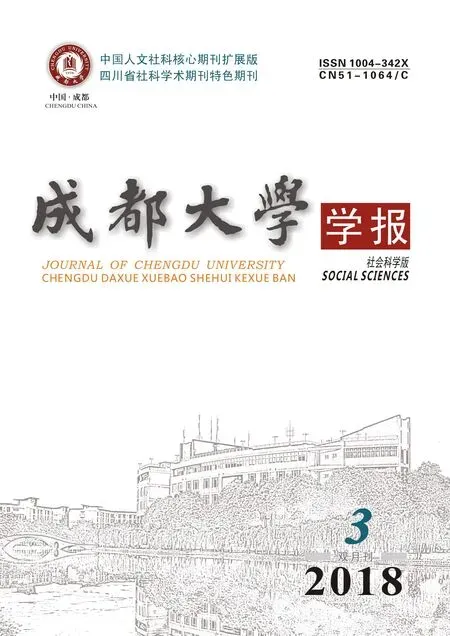論科塔薩爾《指南手冊》中跨體寫作的異質性張力
張博煒
(武漢大學 文學院, 湖北 武漢 430072)
作為拉美文學20世紀60年代“文學爆炸”的領軍人物,同時也被視為博爾赫斯之后拉美文學“幻想派”最重要的代表作家①,胡利奧·科塔薩爾(Julio Cortázar)一直以來都是全世界文學研究者的“寵兒”。而與國外火熱的研究形成反差的是,這種重視并沒有延續到中國的學術界。除了少數西語學者,國內對于拉美文學的研究長期以來只停留在馬爾克斯、博爾赫斯、聶魯達等少數對中國當代文學影響深遠的文學大師身上,而對于同屬于“文學爆炸”代表人物的科塔薩爾、富恩斯特、卡彭鐵爾等作家卻缺乏應有的關注,不僅鮮有討論這些作家創作的專著,就連期刊論文都非常有限——盡管在出版界,科塔薩爾的作品已經大量的得到譯介②。
科塔薩爾在西方國家的火熱顯然不會是空穴來風。與加西亞·馬爾克斯、巴爾加斯·略薩、卡洛斯·富恩特斯并稱20世紀60年代拉丁美洲“文學爆炸”的四大主帥之一的科塔薩爾無論是從數量還是質量上都為拉美文學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據學者統計,這位極其高產的作家一生至少出版了長篇小說四部,短篇小說集八本,詩集二本,散文集三本,詩劇一部,故事、詩歌和隨筆合集二部,各類文章四五十篇[1]3。同時,這些豐富的作品在文體、主題、形式等方面也都做出了多樣而深入的嘗試與探索,大大拓展和豐富了結構現實主義、幻想文學等流派的寫作路徑,推動了拉丁美洲,尤其是阿根廷本土的文學創作,并引領了一大批追隨者。科塔薩爾的長篇名作《跳房子》結構精巧,描寫細膩,令科塔薩爾有“拉丁美洲的喬伊斯”之稱,而他創作的一大批形式豐富,內容奇特的短篇小說,更令他當之無愧地獲得了“短篇小說大師”的盛贊。
科塔薩爾的文學創作具有豐富的內涵,而本文著重討論的是其短篇小說集《克羅諾皮奧與法瑪的故事》的第一部分《指南手冊》。在這一部分中,作者運用“跨體寫作”(Cross-style Writing)的手法創作了六則主題迥異的生活指南(另含一篇導言)。在此,科塔薩爾以一種實用性文體進行了文學文體式的寫作,在打破了傳統文體觀中文學文體與實用性文體的區隔的同時,也塑造了文本與文體在形式、內容、思想等各個層面上的異質性張力,并最終實現了對機械化日常生活經驗的的反思與嘲弄。
一、文體區分與跨體寫作
所謂的跨體寫作,指的是一種跨越文體進行的寫作模式,即利用一種文體書寫常常出現在另一種文體中的內容。這種文體跨越既可以是文學文體內部的交叉,如以小說的方式寫作詩歌,也可能更深一步,直接跨越文學文體與非文學文體的界限。科塔薩爾在《指南手冊》中的跨體寫作正屬于后者,因此在進入文本之前,我們有必要首先對文體區分問題進行一些辨析。
實際上,文學文體與非文學文體/實用文體/科學文體的區分是20世紀西方文學理論核心議題,其本質關系到文學作為一種藝術樣式的自主性應該如何明確。無論是雅柯布森對于符號六因素和詩性自指的論述,或是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陌生化概念,還是英美新批評對于文學特異性和科學文體區分的爭辯均與此有關。
文學和非文學的邊界何在?有論者認為:“文學文體和科學文體實際上沒有明確分界,有各種中介文類,組成一條連續的光譜,詩處于文學性最強的一端”[2]3,這一觀點似乎太過模棱兩可,但實際上卻是文體區分的現狀。然而,文學文體和科學文體的差異始終是無法否認的。新批評認為這種差異來自兩種文體在語言上的差異:文學語言是模糊的、不精確的,科學語言文體則是明晰的、精確的。瑞恰慈(Richards)在《文學批評原理》中特別區分了語言的科學用法和文學用法,并且認定科學語言和文學語言的區分在于前者是“為了一個表述所引起的或真或假的指稱而運用表述”,而后者則是“為了表述所觸發的指稱所產生的感情的態度方面的影響而運用表述”。[3]243在瑞恰慈那里,“指稱性”(referential)是辨別文學文體與科學文體的關鍵,這也與雅柯布森(Jakobson)“詩性(poeticalness)是符號自指”的說法具有內在的一致性。符號學認為,實用/科學語言與文學語言的重要區分在于符碼(code)的強弱差異,符碼問題實際上也與指稱性密切相關:伴隨著強烈的指稱性,實用/科學語言的編碼往往是強制性的,人們能夠做出的解釋幾乎固定;而對于感情性的文學語言而言,編碼則往往沒有明確的判斷標準,解碼過程相對比較寬泛。
無論如何,文體具有“常識”意義上文學與非文學的區分是無可爭辯的事實,讀者對文學文體和實用文體的區分是“自然而然”的事,文體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約定俗成”的問題。讀者在閱讀小說、戲劇、詩歌、散文這些文體時,無需考慮就會將其視為文學作品來進行閱讀,但當他們閱讀說明書、指南、食譜這些實用性文體時,關注點則不會放在作品的文學性上。
文體直接影響的是讀者的接受方式,學者趙毅衡對此清晰地指出:“體裁的最大作用,是指示接收者應當如何解釋眼前的符號文本,體裁的形式特征,本身是個指示符號,指引讀者采用相應的‘注意類型’或‘閱讀態度’”,“體裁看起來像是符號文本的分類,卻更是一套控制文本接受方式的規則……體裁是文本與文化之間的寫法與讀法契約。”[4]139問題是,這樣一種約定俗成的契約是否總是可靠的?一方面,文學文體與非文學文體長期以來存在著互相交織的情況,如果一部作品兼具不同文體的性質,讀者應該選擇哪一種“接受期待”來完成他的閱讀?另一方面,一種文體究竟可以在多大意義上規定和約束文章的內容,當兩種文體的核心性質發生沖突,最終如何才能確定一個文本的文體性質?
在現代主義的文學創作中,這樣的問題并非是文學理論上的假設,而是實實在在的文學批評問題,針對文學內部不同體裁的跨體寫作似乎已經無法滿足作家在形式上探索的欲望,越來越多跨越文學文體與非文學文體的嘗試使得體裁的界限真正變得更加模糊和不確定,同時也對體裁的接受期待產生了挑戰。
英國實驗派詩人、劍橋大學教授J·H·蒲齡恩(Prynne)將實驗報告的語言置入詩歌文體中,即使文本本身的詩性有限,讀者仍然需要按照詩歌的閱讀期待來進行閱讀,這似乎是體裁的強大規定性的體現③;但米洛拉德·帕維奇(Pavic,M)的《哈扎爾詞典》、韓少功的《馬橋詞典》卻不會真的被視作是詞典這樣一種實用性文體,盡管其形式一目了然,但最終體裁的規定性卻讓步給了文本內容,體裁在這里失去了對文本接受方式的控制。
那么,到底是什么使得特定體裁的文本接受方式在這里發生了變化呢?以科塔薩爾的《指南手冊》為例,為什么讀者最終選擇將這一跨體寫作的作品作為文學文本而非實用性文本進行接收?在筆者看來,《指南手冊》之所以能夠突破體裁的規定性,其關鍵是對于實用性文本“單義性”與“實用性”特征的消解:就形式而言,《指南手冊》通過將詩性語言與指稱性語言相糅合,將清晰明確的意義轉變成了模糊不清的意義,由此抵消了文本的單義性;而就內容而言,《指南手冊》則是通過書寫無功利的對象,從根本上抹殺了指南的工具性質,最終取消了文本的實用性。通過文本細讀,下文將針對這兩種不同的消解方式進行更為細致的討論。
二、指南的形式:指稱性語言與詩性語言的糅合
就文體而言,《指南手冊》中的六則指南都屬于實用文體中的“指南”、“說明書”一類。依照語言學家賴斯(Reiss)從功能理論角度對文本類型的劃分,這類文體屬于“信息功能文本”(informative text),也就是以描述物體和事實為主要功能的文本[5]107。這種“描述物體和事實”的功能要求文本必須清楚地傳達某種明確的意義,因此其語言使用必須具有強烈的指稱性,文本語句之間的結構關系也需要側重于邏輯性層面。
換而言之,信息功能文本應當是“單義”的,它要求的是清晰、明確地進行表意,不需要也不允許讀者做出過多的解讀——如果一本說明書讓閱讀者產生了多重意義的理解,它就很難說是“稱職”地完成了“說明”的任務,這正如瑞恰慈所說,“就科學語言而言,指稱方面的一個差異本身就是失敗:沒有達到目的。”[3]244而作為一種跨體寫作,《指南手冊》在形式上首先需要無限接近其戲仿的指南文體,這就要求作者盡可能多地使用信息功能文本中的強指稱性語言,科塔薩爾對此顯然有著充分的自覺,幾乎在每一篇指南中,我們都可以找到這種單義的強指稱性語言。以《上樓梯指南》中的這一段為例:
上樓梯應從抬起位于身體右下方的部分開始,該部分一般會被皮革覆蓋,除個別情況外其大小與臺階面積吻合。該部分(為簡便起見我們將該部分稱作腳)安置在第一級臺階上之后,抬起左邊對應的部分(也稱作腳,但請勿與此前提到的腳相混淆),將其抬至與腳相同的高度,繼續抬升直到將其放置在第二級臺階上,至此,腳在第二級臺階,同時腳在第一級臺階。(最初的幾級臺階通常最為困難,在熟悉了必要的配合后情況將好轉。腳與腳的重名也為說明造成了困難。請特別注意:不要將腳與腳同時抬起。)[6]16
如果舍棄對于“上樓梯”這一動作的前理解,我們幾乎可以把這一段選文視作是運動指南或者健身手冊中的篇章,其中的每一個短句都對應著舉手、抬足等具體的行為動作,具有著極強的指稱性。同時,段落的句子之間也有著強烈的邏輯關系,語句承接關系清晰,意義直接指向外延,這同樣也是指稱性語言的典型特征。除了《上樓梯指南》之外,在《哭泣指南》、《羅馬滅蟻指南》、《三幅名畫的欣賞指南》、《手表上發條指南》等篇章中,作者也都大量使用了類似的指稱性語言,而這些指稱性語言的使用,實際上是為了塑造文本的指南文體的體裁身份,符合指南文體以“解釋說明”為目的的體裁規定性,以“單義性的語言”書寫“實用性的文體”。
然而,不同于真正的信息功能文本,科塔薩爾的《指南手冊》最終仍是一種基于文學創作目的的跨體寫作,作者的文體實驗并非只是為了創作一本毫無技術含量的“工具指南”,他還需要通過其他的方式來突破其戲仿文體的體裁規定性。因此,科塔薩爾在指稱性語言之外又使用了大量的詩性語言,意圖消解實用性文體的單義性。如《手表上發條指南》一文的開篇寫道:
在那深處會有死亡在等待,但無需恐懼。請用一只手握住表。兩根手指拈起發條鑰匙,輕輕回轉,于是新的時期開始,樹木抽枝發芽,船只乘風而去,時間好像扇子漸漸展開自身,從中生出空氣,地上的微風,一個女人的影子,面包的香氣。[6]20
此處的語言顯然不再是“指南”這一實用性文體“應該”使用的語言。在這里,文本的語言不再側重于單義性與指稱性,而是側重復義性與詩性,它是優美的、詩意的,更是模糊的。就符號表意而言,所謂的詩性語言采用的是弱編碼的形式,語言沒有固定的所指,而是以指向自身的方式呈現,它允許并且鼓勵讀者進行多樣化的解讀。不同于指稱性語言與實用性文本這一體裁的合一關系,詩性語言的使用與指南的實用性文體屬性顯然是矛盾的,正如前文所述,實用性文體要求使用清晰與確定的語言,但詩性語言卻是模糊與不確定的,這就使得文本喪失了指稱性,無法傳達明確的意義。換而言之,詩性語言的使用最終消解了實用文體應當具備的單義性特征,語言從內部突破了體裁的規定性。
《指南手冊》因此也就具備了一種語言雜糅與文體沖突的異質性張力:就指稱性語言的使用而言,它仍然是實用文體,體裁的規定性要求讀者在進入文本時要依照實用文體的閱讀期待進行,讀者也會有意識地將其視作實用文體來進行閱讀,并以此理解文本中的指稱性語句;但就詩性語言的使用而言,它所糅合的詩性語句又通過拒絕指稱的方式,不斷打破著實用文體的體裁規定性,努力將讀者拉扯到文學文體的一端,最終造就了搖擺在兩種文體間的狀態。
三、指南的內容:無功利對象對實用性文體的消解
盡管詩性語言通過“化單義為復義”的方式從形式方面消解了文體的實用性特征,但更為極致和徹底的消解實際上來自于《指南手冊》對于書寫對象的選擇。就文體的內容規定性而言,“指南”這一文體通常的書寫對象應當是那些復雜、未知的事物——正因為缺乏足夠的認識,讀者才需要通過“指南”來加深自己的認識、指導自己的行動;另一方面,指南文體的隱含讀者相對也比較明確,每種指南都有著的特定的受眾,如“旅行指南”的隱含讀者是旅人,而“產品使用指南”的隱含讀者則是顧客。這種內容規定性實際上與指南的實用性文體屬性密切相關,指南文體的實用性要求它的內容必須是有用的,換而言之,一篇理想的指南在目標受眾的手中必然可以指導其特定的行動。
然而,科塔薩爾《指南手冊》所選擇的書寫對象卻都是無需指導的行為與事物,而其設想的隱含讀者與實際的讀者也是一種不相匹配的關系。《上樓梯指南》、《哭泣指南》與《手表上發條指南》的隱含讀者是那些不懂得如何上樓梯、如何哭泣和如何給手表上發條的人們,但對于現實生活的讀者而言,這些都是不言自明、無需指導的生活常識,因此任何《指南手冊》的現實讀者都“無法”通過閱讀這些指南來改善他們的現實生活。
換而言之,《指南手冊》實際上書寫的是一種不具備目標受眾的“無用指南”,這種對象的無用性直接從根本上挑戰了實用性文體的體裁規定性:既然是實用性文體,其內容必然應當是實用的,但《指南手冊》的內容卻無法對任何人起到實際的指導作用,沒有人會需要通過閱讀《上樓梯指南》來學習如何上樓梯,也不會有人需要通過閱讀《哭泣指南》來學習如何哭泣。實用性在這里被徹底地拋棄,讀者原來的閱讀期待也就隨之發生改變,他們不再把眼前的文本看做是指南、說明書一類的實用性文本,轉而將文本視作文學文本進行閱讀。
“無用”同時有著更深層次的內涵:從工具理性的角度而言,“無用”的實質即功利性的缺席及現實性的疏離,而根據書寫對象與現實的關系,《指南手冊》中這種“無用的書寫”也大致可以被分為三類不同的主題,即內現實主題、反現實主題與超現實主題:
第一類內現實主題的作品包括《上樓梯指南》《手表上發條指南》《哭泣指南》和《恐懼方式指南及示例》。在這一類作品中,指南的對象都是內化于現實之中,無需人們再加以思考,無論是“上樓梯”和“給手表上發條”這種簡單、瑣碎的無意識動作,還是“哭泣”和“恐懼方式”等純粹直觀的情感體驗,這些行為都已經內化到了日常生活之中,人們不用再通過閱讀指南來進行學習,而作者刻意以說明書的方式對無意識行為進行機械化的書寫,這就構成了對現實的一種反諷。
第二類反現實主題的指南包括《三幅名畫的欣賞指南》。該作針對提香的《神圣之愛與世俗之愛》、拉斐爾的《獨角獸婦人》與荷爾拜因的《英格蘭的亨利八世》三幅名畫進行了美術鑒賞上的指導,詳盡地分析了畫中的筆觸、色彩、意象和內涵。從行文來看,這似乎是最接近實用文體的一則指南,但這一實用性卻無法經受讀者的細讀,在看似可信的文字之下,科塔薩爾實際上是通過戲謔的方式,以顛覆傳統的話語進行一種反現實的美術鑒賞,其所做出的闡釋恰恰是對現實中美術鑒賞方式的違背,因此同樣無法對讀者形成指導作用。
第三類超現實主題的作品包括《羅馬滅蟻指南》。這一指南的內容是“為古羅馬去除蟻患”,由于指南對象在時空和行為上都是超現實的存在,我們可以稱這一類指南為超現實主題。相對之前的兩類文本,《羅馬滅蟻指南》的內容更加接近純粹的幻想,作者在此構想了一種為古羅馬去除蟻患的方式:通過搶先抵達泉源來消滅螞蟻。而這一內容上的超現實性也就決定了這則指南對于現實讀者而言同樣是無用的。
無論是哪一類指南,其書寫對象都與現實生活保持了一定的距離,因此也就不具有功利性。而這種無功利、無實用性的對象顯然與指南的“實用性文體”身份是不相符合的,實用性文體要求寫作對象應當具備功利性,而如果對象不具備功利性,文體自身的實用性也就因此受到了挑戰,同樣,無功利對象所呼喚的也是一種與之匹配的文學文體。因此,對于“實用性文體”與“無功利對象”雙方而言,彼此都是那個意圖取消對方本質性的存在,而作者通過將這兩種互相對立的要素進行整合,也就最終塑造了《指南手冊》中在內容層面上的異質性張力。
文本中指稱性語言與詩性語言的混合已經從形式上對體裁概念發起了挑戰,而對“無功利對象”的書寫又進一步從內容層面上沖擊了“實用性文體”的本質規定性,《指南手冊》實用性文體的體裁身份由此就遭到了徹底的消解,實用性最終宣告缺席。對于藝術創作而言,實用性的缺席本應是一種常態,這是審美的無功利性所決定的;但對《指南手冊》這樣一種以實用性文體進行創作的作品而言,實用性的缺席則是在根本上質問著體裁自身的規定性和文本存在的依據。
應當說明的是,這種矛盾最終并非始終保持著懸置的狀態。盡管讀者們在進入《指南手冊》這一文本時首先看到的是一個實用性文體,但當他們意識到了這一文本的非實用性,他們就開始轉向了文學文體的閱讀方式。科塔薩爾的這一實驗同時證明,即使文體的體裁規定性受到挑戰,讀者仍然會為這一喪失了體裁身份的文本重新找到合適的體裁期待。對于《指南手冊》而言,它最終擺脫了其所戲仿的實用性文體身份,而是以文體實驗的姿態重新回歸到文學文體的位置:讀者們接受和閱讀到的是一個帶有實驗性質的文學文本;而作者也通過摧毀期待的方式改變了讀者對特定體裁的接受方式,重新與文化簽訂了一份“寫法與讀法的契約”。
四、指南的目的:在陌生化中反思日常生活
科塔薩爾的短篇小說創作以幻想小說為主,這與他師承博爾赫斯有關系——科塔薩爾第一部發表的短篇小說,就是經由編輯博爾赫斯之手得以公之于眾。然而科塔薩爾與博爾赫斯的短篇小說創作路徑卻又不盡相同,相比博爾赫斯無邊無際的純幻想文學,科塔薩爾的幻想小說仍有其現實根基所在。正如他本人在訪談中提到的:“我首先獲得的是生活的經驗而不是思想上的經驗”[1]4。科塔薩爾對生活經驗的處理是極其多樣的:在形式上,他嘗試使用各種各樣的文體、敘述結構來完成幻想對生活經驗的加工;在內容上,其創作中既有對生活經驗的扭曲、變形、夸張,也包含了對生活經驗的拒絕、排斥和反諷。
就此而言,科塔薩爾在《指南手冊》中的文體實驗就不僅僅是一種形式層面的探索和嘗試,它同時還有著特定的寫作目的和思想內涵。《指南手冊》的六篇作品中,有超過一半的作品指向的都是內化于現實之中的瑣碎生活,無論是“上樓梯"“給手表上發條”,還是“哭泣”“恐懼”,這些以無意識行為和情感體驗為主題的指南最終指向的是日復一日的“內現實”。“內現實”的生活是日常的、重復的、機械的,是無需說明和解釋的,但科塔薩爾卻刻意使用一種帶有解釋說明性質的文體進行書寫,其實質是通過文學的方式對人們習以為常的事物進行陌生化處理,最終指向對日常生活的反思。
正如什克洛夫斯基被反復引用的名句“那種被稱為藝術的東西的存在,正是為了喚回人對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頭更成其為石頭”[7]6,科塔薩爾在這里也是希望通過文體實驗的方式使讀者重新開始審視和感受無趣的日常生活。這種“喚回人對生活感知”的目的在《指南手冊》的那篇序言中有著清楚的顯現:
日復一日軟化磚塊的任務,在這自稱為世界的粘團塊中開出道路的任務,每天早上碰見面目可憎的平行六面體,懷著狗一般的滿足,滿足于一切照舊,身邊同樣的女人,同樣的鞋子,同樣的牙刷的同樣的味道,對面房子同樣的頹喪,百葉窗上有骯臟的招牌,寫著“比利時酒店”。[6]3
“世界的粘團塊”“面目可憎的平行六邊體”“狗一般的滿足”,科塔薩爾在遣詞造句之中表達的是他對于機械性日常生活的不滿,這種不滿從很大程度上而言構成了他寫作《指南手冊》的初衷和原動力。但需要強調的是,科塔薩爾又不僅僅是希望嘲諷人們對待日常生活的態度,他同時還希望能夠以這種陌生化的方式喚醒讀者關于生活的熱情,他仍然對此懷有希望,并由此認為如果人們還能“感受一只蛾子微乎其微的心跳”,那么就“并非一切都無可挽回”[6]4。
在前文已經引用過的《上樓梯指南》中,科塔薩爾利用指稱性的語言書寫無意識的日常生活,將上樓梯這一無需思考的行為通過肢解動作細節的方式進行陌生化的呈現,使讀者能夠在閱讀時重新審視上樓梯這一動作。上樓梯這一下意識的行為在作家的書寫下變得似乎非常復雜,以致必須閱讀說明書才能學會,而這種文本建構出來的“復雜”與日常經驗進一步碰撞,產生出趣味盎然的閱讀效果,讓讀者能夠以相似的思維方式審視機械化的日常生活。
同樣在《哭泣指南》里,作者不僅認真介紹了“哭泣”這樣一種情感行為,同時還給出了“正確的哭泣方式”。在科塔薩爾筆下,正確的哭泣方式應當“不會有出丑之虞,也不會因為與微笑的粗略相似造成失禮的混淆。常規水平或者普通的哭泣表現為臉部整體收縮以及伴隨著眼淚和鼻涕產生的痙攣聲響,并以兩者收結,因為哭泣在擤鼻涕的時刻告終”[6]6。這種對哭泣的細節性描寫正是使用陌生化的手段將讀者的感知從機械的狀態中喚醒,令讀者能夠通過文本重新認識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行為舉止,審視自己在生活中的姿態。
這種陌生化的書寫方式最終造成的是文本書寫與日常生活之間的緊張關系,并組成了《指南手冊》的最后一組異質性張力關系。生活已經為人們所熟悉,因此“事物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知道它,但對它卻視而不見。因此,關于它,我們說不出什么來”[7]7。但科塔薩爾卻對這種生活經驗做出了大膽的加工和嘲弄,他意圖讓事物擺脫知覺的機械性,喚回讀者對于生活的感受力。這同時也構成了科塔薩爾寫作《指南手冊》的最終目的,無論是對指稱性語言和詩性語言的糅合還是無功利對象的書寫,最后都在拒斥日常這里得到了統一。正如科塔薩爾在序言中所表明的,他希望能夠“拒絕轉動彈子鎖的微妙行為,一切可在其中變形的行為,不讓它以慣常反應的冷漠效率實現”[6]3,而《指南手冊》正是他幫助讀者達到這個目的的一次實踐和一個工具。
《指南手冊》不僅僅只是一場單純的形式游戲,它有著更為明確的寫作內涵,科塔薩爾意圖通過這種跨體寫作實現陌生化的效果,進而喚醒讀者的對于生活細節的感知,實現對日常生活的反抗,引發人們對機械化現代生活的思考。而只有理解了這一點,我們才能真正把握科塔薩爾《指南手冊》這樣一種文體實驗的意義所在。
注釋:
①關于拉美當代小說流派的分類,可參考陳眾議:《拉美當代小說流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年。
②20世紀80年代至今,科塔薩爾在國內已經得到譯介的作品包括:長篇小說《跳房子》《中獎彩票》,短篇小說集《游戲的終結》《動物寓言集》《萬火歸一》《克羅諾皮奧與法瑪的故事》《被占的宅子》《南方高速》,散文集《科塔薩爾論科塔薩爾》,繪本《熊的話》等,同時,在《世界文學》等期刊散見有科塔薩爾的其他一些小說創作。

參考文獻:
[1]朱景冬.科塔薩爾其人[J].外國文學,1994(4):3-5.
[2]趙毅衡.重訪新批評[M].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3.
[3]艾·阿·瑞恰慈.文學批評原理[M].楊自伍,譯.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2.
[4]趙毅衡.符號學[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
[5]李治.紐馬克、賴斯的文本分類及翻譯方法論的比較分析[J].未來與發展,2010(10):106-109.
[6]胡里奧·科塔薩爾.克羅諾皮奧與法瑪的故事[M].范曄,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
[7]維克托·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國形式主義文論選[M].方姍,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