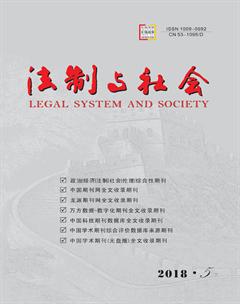刑事既判力制度在中國的適用
摘 要 既判力理論是大陸法系刑事訴訟的基礎理論,其目的是為了解決刑事判決生效后的效力以及程序公正、司法權威等問題,但就中國目前的刑事訴訟法律規范來看,尚未認可既判力制度。本文通過對刑事既判力制度進行梳理,發現在實踐中存在規避既判力制度的現象,并且既判力制度與再審理論存在嚴重沖突,故而試圖探尋刑事既判力制度一系列問題的解決之道。
關鍵詞 刑事既判力 價值基礎 再審程序
作者簡介:李園園,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
中圖分類號:D92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5.254
“實體真實,程序正義”是刑事訴訟制度的價值追求和目的,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確實存在為追求“實事求是”原則而將案件陷入一種馬拉松式反復審理的例子,如念斌一案,這暴露出中國刑事訴訟制度中的巨大漏洞。但刑事既判力在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界卻很少有深入的研究,故本文結合我國實際問題對刑事既判力制度進行探討,以求從既判力的角度剖析、解決相關理論與司法實踐問題。
一、刑事既判力在中國適用中面臨的問題
(一)撤訴規避既判力
在實踐中,檢察院為達到業績考核標準,經常以撤訴的方式規避法院的無罪判決;而通常審判機關也會與檢察機關互通有無,在證據不足或具備其他無罪判決條件的狀況下對其提出撤回起訴的建議。檢察院撤回起訴的行為規避了判決的既判力,使得應當宣布無罪的案件回到尚未起訴的狀態。我國刑訴法對于撤回起訴的規定十分模糊,甚至有些細節,諸如撤訴的時間、條件以及后果都十分不合理,這使得檢察院撤訴具有隨意性和任意性,無法保障被告的基本權利,甚至嚴重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權利。
1.撤訴的時間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242條 和《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456條 的規定,可以看出檢察機關回起訴的時間有兩種,一種是在人民法院作出判決前,人民檢察院只要有規定的情況都可以提出撤訴,第二是在特殊情況下,即在因為補充偵查而延期審理的情況下,檢察院也可以在補充偵查期限內提起撤訴。由以上分析可知,檢察院申請撤訴的時間范圍非常寬泛,囊括了整個審判過程。這樣寬泛的時間維度造就了檢察院撤訴的任意性,一但檢察院申請撤訴,法院審查同意,案件便回歸到尚未提起公訴的狀態,在以后的任意時間點,檢察院都可以再行提起公訴。這顯然侵犯了當事人的基本權利。
2.撤訴的條件
從《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459條第一款 的規定來看,法律似乎對檢察院的撤訴行為作出了明文的條件限制,但對比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5條 和第195條 的第二、三款有關宣告無罪的情況發現,其內容完全重合,也就是說原本應該做出無罪判決的案件,由于檢察院以相同理由做出的撤訴陷入了可能被再次提起訴訟經歷審判的危險境地。
3.撤訴的過程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公訴案件撤回起訴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 第4條規定:“對于人民法院建議人民檢察院撤回起訴或擬作無罪判決的,人民檢察院應當認真審查并與人民法院交換意見。”從這條規定可以看出人民法院可能會在案件符合無罪判決條件的情況下對檢察院提出撤訴建議,或人民法院將要做出無罪判決時會告知檢察院,而檢察院根據“最高檢指導意見”將會與人民法院交換意見。在刑事訴訟中,作為中立審判者的人民法院竟然可以向作為公訴人的檢察院提出撤訴建議,甚至將擬作的判決也與公訴人互通有無,非公開秘密性的“交換意見”,嚴重不符合刑事訴訟兩造對抗裁判中立的訴訟模式,這一系列行為的是否符合程序公正令人懷疑。檢察院撤訴這一行為原本就會使將要做出無罪判決的案件因無法受到終局裁判的效力的保護而陷入危險狀態,而撤訴行為非但沒有受到法院的限制和審查,反而以一種“建議”的形式受到鼓勵,這是十分不合法理的。
4.撤訴的后果
《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459條第三款規定:“對于撤回起訴的案件,沒有新的事實或者新的證據,人民檢察院不得再行起訴。”實踐中,許多檢察院向法院申請撤訴,之后又以“發現新事實新證據”為由再次提起訴訟,但所謂的新事實新證據實際上卻是被告人新的與本案無關的犯罪事實,甚至如念斌案一樣,在沒有未達到法定條件的情況下再次重新立案提起公訴。
(二)再審程序與既判力的矛盾
我國再審案件從2008年至2012年以來每年基本保持在42000件左右 ,其數量的龐大在國際上首屈一指。基于中國的實際,在刑事訴訟中存在著大量的誤判,為 “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等思想提供了成長的土壤,這些觀念又轉而為審判監督程序的構建提供了支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原則幾乎為所有的刑事再審案件提供了理論支持,但不受限制的有錯必糾將導致審判監督程序具有任意性弊端,主要表現為:啟動主體多元、啟動理由寬泛模糊、沒有明確的時效和次數限制、權利保障視角的嚴重缺位 。這些弊端無一不加深著再審程序與刑事既判力之間的矛盾:一旦啟動了審判監督程序就等于將終審判決和其經過的訴訟過程一并否認。一方面,判決已經生效就獲得一種既判力,從而具備了不可改變性以維護司法權威和被告人的權利;另一方面,審判監督程序要求改變已經生效的錯誤判決,以確保個案正義。為避免犧牲其中任何一項目的應當承認裁判的確定力,但在合乎嚴格要件的例外情形,容許救濟程序來排除裁判的確定力。
二、中國問題的解決之道
(一)樹立正確的訴訟觀念
刑事訴訟每一項制度的更新和構建都離不開對于訴訟理論的更新和訴訟觀念的轉變。刑事訴訟不僅是一個訴訟過程,還是一個認識過程,更是一個價值選擇過程。實體真實、個案正義確實刑事訴訟所追求的重要目標,但并不代表諸如保障被告人權、維護司法權威、注重訴訟效益等其他刑事訴訟價值就可以為其讓步。我們應當反思“實事求是”原則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清楚地認識它使得疑罪從無、無罪推定、上訴不加刑、既判力等原則難以有存在的空間。 所以,我們要為“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原則的適用范圍規定一個合理的邊界,在思想上樹立既判力觀念。不僅法律界要有既判力的法律觀念,還要促使我國公民對刑事訴訟有科學的價值認識。
(二)規避既判力問題的解決
基于程序正義的要求,訴訟過程一般不可逆轉,所以訴訟程序對檢察機關撤回公訴的行為應當進行嚴格的限制,通過法律明文規定撤訴的時間范圍、具體條件等;在訴訟過程中,法院應保持客觀中立,不得建議檢察院撤回起訴,更不得與檢察院非公開秘密性的交換意見;撤回起訴的效果應等同于無罪判決,檢察院不得就同一事由向法院再次提起公訴。
(三)調和再審與既判力之沖突
“立法者應當將裁判的確定力與裁判的公正性同時予以關注,對其沖突加以是適當的調節和我平衡。” 但對于平衡其限度的把握并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筆者從擬從中國再審的現狀,提出對中國再審與既判力矛盾的調和方案。
1.提高判決質量
近年來,媒體報道了大量的誤判案件,如 :張氏叔侄案、曾成杰案、念斌案等,再審案件數量之龐大,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中國各級法院發生錯誤生效裁判并不是一個小概率事件,若要調和審判監督程序與既判力構建之間的矛盾,減少再審糾錯的案件數量是必經途徑。因此,提高判決的質量應當作為我們減少誤判案件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通過提高司法工作人員的素養,嚴格貫徹法律,從根源上阻止誤判案件的產生從而減少再審程序的啟動次數。
2.審判監督程序之改革
審判監督程序與既判力制度之間的矛盾并非不可調和,要使二者共融共存就要對審判監督程序重新定位,進行一定的改革。首先要承認終局裁判的既判力和確定力,保持其不可更改性,但卻有事實認定錯誤和法律適用錯誤需要啟動再審程序時,應嚴格限制再審的啟動主體,明確規定合理的再審啟動條件,明文規制再審的啟動時間范圍和次數,并適用“禁止不利于被告的變更”原則。
三、結論
不僅是出于人權保障、訴訟效益以及法律權威等刑訴法價值的考量,既判力的意義還在于,在終局判決具有確定力的情況下,訴訟的各個主體才能真正的對判決結果自行負責,為真正的兩造對抗提供了程序保障。在建設法治社會的進程中,設計出一套符合中國國情的既判力制度并加以適用是刻不容緩的。
我們強調要維護終局裁決的確定力和既判力,但并不否認既判力制度與再審救濟可以相融共通,即將再審程序作為既判力制度的例外,完善審判監督的法律規定,限制再審的啟動主體、條件,允許在有利與被告的情況下進行再審救濟,體現判決一旦做出不輕易改變的性質。可以說再審程序為既判力劃定了發生效力的范圍,二者相互制約,相互平衡。
注釋: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242條規定:“宣告判決前,人民檢察院要求撤回起訴的,人民法院應當審查撤回起訴的理由,作出是否準許的裁定。”
《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456條規定:“法庭宣布延期審理后,人民檢察院應當在補充偵查的期限內提請人民法院恢復法庭審理或者撤回起訴。”
《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459條第一款:“在人民法院宣告判決前,人民檢察院發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撤回起訴:(一)不存在犯罪事實的;(二)犯罪事實并非被告人所為的;(三)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的;(四)證據不足或證據發生變化,不符合起訴條件的;(五)被告人因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不負刑事責任的;(六)法律、司法解釋發生變化導致不應當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七)其他不應當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
《刑事訴訟法》第15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責任,已經追究的,應當撤銷案件,或者不起訴,或者終止審理,或者宣告無罪:(一)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的;(二)犯罪已過追訴時效期限的;(三)經特赦令免除刑罰的;(四)依照刑法告訴才處理的犯罪,沒有告訴或者撤回告訴的;(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 (六)其他法律規定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
《刑事訴訟法》第195條:“在被告人最后陳述后,審判長宣布休庭,合議庭進行評議,根據已經查明的事實、證據和有關的法律規定,分別作出以下判決:(一)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依據法律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有罪判決;(二)依據法律認定被告人無罪的,應當作出無罪判決;(三)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
陳婷.既判力與自我糾錯的矛盾——論兩審終審制度下的審判監督程序.法學博覽.2014(6).
陳瑞華.刑事再審程序研究.政法論壇.2000(6).
熊秋紅.錯判的糾正與再審.環球法律評論.2006(5).
施鵬鵬.刑事既判力理論及其中國化.法學研究.2014(1).
參考文獻:
[1]陳瑞華.刑事訴訟中的重復追訴問題.政法論壇.2002(5).
[2]龍宗智.念斌被再度確定為犯罪嫌疑人問題法理研判.法制與社會.2015(1).
[3]宋英輝、李哲.一事不再理原則研究.中國法學.2004(5).
[4]李哲.刑事既判力相關范疇之比較.比較法研究.2008(3).
[5]李哲.刑事裁判的既判力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6]楊興培.反思與批評:中國刑法的理論與實踐.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7]胡錦光.司法公信力的理論與實踐.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
[8]黃士元.刑事再審制度的價值與構造.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
[9]汪建成.沖突與平衡——刑事程序理論新視角.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10]樊崇義.刑事訴訟法哲學思維.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