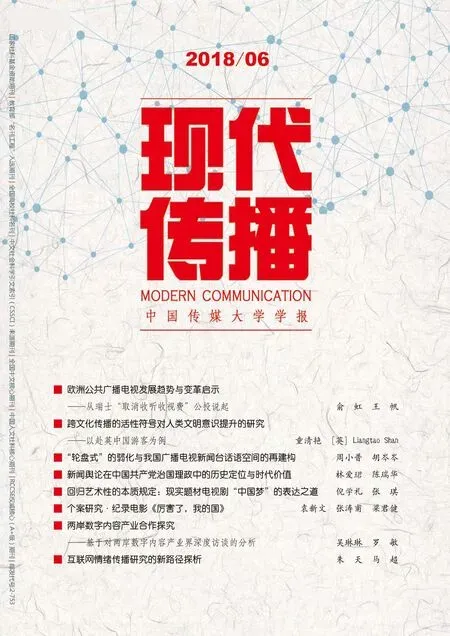新聞UGC生成行為:主體重構與角色辨析*
■ 熊 茵 劉煒心
UGC,即用戶生成內容,泛指以任何形式在網絡上發表的由用戶創作的文字、圖片、音頻、視頻等內容,是Web2.0環境下的網絡信息資源創作與組織的模式。①作為一種強調“人人參與”的互聯網內容生產模式,UGC發軔于20世紀90年代的個人網站,后經歷了論壇、博客、視頻網站、獨立SNS等形式的演進,現正朝微博、微信等移動化、大眾化、融合化的新方向發展,已經成為社交網絡平臺最重要的信息源。②當下環境,UGC理念及其“技術叢”廣泛影響社會各領域,深刻形塑了社會觀念和行為。新聞領域也概莫能外,新聞內容的UGC生成行為逐漸興起,并不斷挑戰傳統的新聞專業生成模式(PGC)。大量普通民眾、各類脫媒機構等開始介入新聞生產傳播活動,新聞傳播主體發生了極為紛繁復雜的身份演變和角色分化,并從根源上導致了包括新聞傳播的價值理念、行為模式、競合態勢等在內的新聞傳播格局變遷。要厘清UGC興起背景下新聞傳播諸多嬗變與迷思,首先要對新聞傳播主體的類型及角色內涵加以辨析。本文將在梳理文獻的基礎上,試圖建構雙維度交叉的分類框架,對新背景下的新聞傳播主體發起較為深入的探討,為“后新聞業”③時代的新聞主體的理論體系略添一二思考。
一、文獻回顧與綜述
新聞傳播主體是指生產新聞與傳播新聞的主體。④它是新聞流程的發起環節,深刻影響新聞傳播過程及其他要素,學界相關研究成果可謂豐碩。結合UGC興起之時代背景,本文對相關性較強的文獻進行歷時地回顧和梳理,并根據研究的階段性側重,將之劃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1.單一視角下的“本體”研究
隨著UGC理念及“技術叢”的興起,越來越多“個人”成為互聯網的主體:他們不僅僅是消費者和用戶,也是更主動的生產者、創造者和建設者。⑤“個人”成為新聞生產與傳播的新生力量。新主體一出現,研究者旋即聚焦“本體”,從多維度勾勒UGC新聞傳播主體的肖像輪廓,闡釋其特質與內涵。此類型研究有以下角度:(1)身份研究:研究者對UGC新聞傳播主體身份的描述不盡相同,如草根記者、公民記者、民間記者、個人媒體、自媒體等,但就UGC新聞主體身份達成的基本共識是:記者身份的社會泛化,即“人人都是記者”。隨著研究的深入,不少學者對主體身份進行細化,例如“草根新聞”(Grassroot Journalism),原指非精英階層的普通公眾創作并傳播的新聞。但后來人們發現,很多所謂的草根新聞作者其實并不是“草根”,而是專家、學者、記者等擁有較高社會地位的人。公民新聞參與的主體,既應包括過去沒有話語權的普通公眾,也應該包括過去有一定話語權的名人。對UGC新聞主體身份的細化研究體現其成分多樣性和參差性等特點。(2)特征研究:謝因·波曼和克里斯·威理斯指出,“參與式新聞”(Participatory Journalism)的傳播主體具有身份的多元化和沖擊話語壟斷的主動性特征,也帶有個體的特色和個性。網民積極參與新聞直播,有強烈的個人化修辭特色,足以突破傳統媒體的“想象共同體”的建構。(3)行為研究:有學者指出,公民在搜集、報道、分析和散布新聞和信息的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且逐漸從簡單的從事相關信息的搜集、匯編工作轉向親赴現場通過各種現通訊設備對事件展開文字和影像報道。胡泳則對民眾的新聞參與行為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概括,其行為包括了新聞評論、草根報道、另類編輯及核查事實等新聞實踐。從主體的行為研究可知,民眾個體積極且深度介入到新聞傳播各環節,有著極為豐富多彩的民眾新聞實踐活動。(4)失范研究:盡管不少研究者篤信“足夠多的眼睛,就可以讓所有問題浮現”⑥,樂見“人人都是記者”局面的形成,然而現實中UGC新聞實踐一再逾矩和失范使研究者不得不駐足反思。有研究者指出,所謂的“公民記者”缺乏基本新聞學的訓練和素養,他們提供的資料也因此缺乏可信性。有些過分熱心的人可能還會制造麻煩。學者林靖和蔡雯也得出類似結論,即普通公民的新聞實踐行為,具有臨時性、隨意性、情緒化等特點,是自發而非自覺進行,缺乏基本新聞素養和專業精神,并不能完全擔負起職業記者進行深入調查和客觀報道的全部工作,因而傳播主體難以信任。
UGC初興階段,研究者從身份特質、實踐內容、行為規范等多個角度開啟對具有新興形態特征的新聞傳播主體研究,這類研究全面立體地勾勒了新興主體的樣態特征,有助于對之進行全面把握和深刻理解。
2.二元視角下的主體及關系研究
UGC理念的激勵和互聯網技術的推動,使以“個人”為基本單位的傳播能量被激活⑦,民眾成為新聞傳播的活躍力量。相形之下,傳統新聞機構在應對來勢洶洶的挑戰中頗有頹勢和疲態,傳統新聞傳播秩序與格局發生逆轉和改變。面對UGC興起后的新形勢,學界跳出“本體”研究的單一視角,對“傳統—新興”二元新聞主體及其力量消長、關系競合等展開了頗有價值的研究。喻國明將互聯網社會中的傳播二元主體定義為“個人”與“機構”,指出互聯網對于這個社會的最大改變,就是將社會構建的基本單位從“機構”降解到了“個人”。當“個人”成為一個權力主體和一個社會傳播構造的基本單位時,它的社會應用和社會把握方式就有很大的不同。⑧克萊·舍基(Clay Shirky)在其論著《人人時代:無組織的組織力量》中提出,“大規模的業余化”(mass amateurization)趨勢正在生成。有無數人在從業余的角度進攻專業人士的堡壘,從軟件、音樂、電影到文學等等都是這樣。以此為標準則可將新聞傳播主體分為傳統職業新聞傳播者和新興的業余新聞傳播者兩大陣營。此外,有研究者以PGC與UGC模式為分水嶺,將新聞傳播主體分為專業者(professionals)與非專業者(no-professionals)。
此外,研究者對UGC興起后長期共存的二元主體間關系及關系轉化進行了更具價值的研究。胡泳(2016)指出,UGC平臺在與PGC(專業內容生產)博弈中逐漸與之結合,“業余的專業化”是未來互聯網內容發展的新趨勢,PUGC或成發展進路。UGC向PGC新聞生產方式的轉向或兩者融合等類似觀點在丁月、蘇慧瑩的文章中亦有體現。
從這一階段研究可知,UGC興起背景下的新聞傳播主體逐漸分裂為兩大相對陣營,無論是“個人”傳播者VS.“機構”傳播者、職業傳播者VS.業余傳播者,還是專業人士VS.非專業人士,二元主體間存在極復雜的博弈與競合關系及生態。“二元”視角下的對比性研究從更深層面上揭示二者新聞主體間關系及各自特點。但彼時的“二元”視角容易走入“非此即彼”的思辨困境,恐使研究者忽略二元之外其他較為隱蔽的新聞主體。
3.三元結構的主體及關系研究
二元視角下的研究不足以窮盡UGC興起背景下極為復雜的新聞傳播主體,有學者逐步觸及二元之外的其他新聞主體的研究。黃志杰首提“脫媒”一說,認為“脫媒”將廣泛存在于傳統媒體和個人自媒體二元主體之外,并舉例中紀委的APP和網站已經成為脫離傳統媒體的“大媒體”。他指出,傳統媒體和民眾自媒體之外,具有“脫媒”特征的新聞傳播主體大量存在,構成新聞傳播三元主體格局態勢。楊保軍教授對此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他明確提出了“脫媒主體”一說:新媒介生態環境中,“三元類型傳播主體”結構已經形成。以往人們更多關注職業新聞主體與民眾個體新聞活動及其關系,對“非職業新聞組織(群體)主體”——“脫媒主體”——卻關注不夠。但事實上,“脫媒主體”是結構新聞傳播新格局的重要力量,它對公共化新聞傳播主體的結構變革、職業新聞傳媒的生存法則、生產方式、傳播原則、功能目標、傳播價值等都造成了結構性的作用和影響。而且,不同“脫媒主體”間的差異性,在新環境中的具體表現也有所不同,與職業新聞主體、民眾個體間有著紛繁復雜的關系。第三類新聞傳播主體介乎傳統范式的新聞媒介組織與新興的“個體”新聞傳播主體兩極之間,他們既不完全恪守新聞的專業理念和職業規范,也非全然像“個體”傳播者般的率性而為、隨心所欲,而是在商業主義、宣傳主義等邏輯框架下開展“泛新聞”生產與傳播,例如黨政機關部門自建的信息發布(如地方政務“兩微一端”)、企業公司自建的營銷媒體平臺(企業服務號、營銷微博號及APP等)、相對獨立的內容型自媒體個人或組織機構等。這類新聞傳播主體不僅數量龐大,組織形態多樣、動機目的復雜,而且其新聞產品的形制與樣態各式各樣、常變常新、不一而足。三元主體結構論是對二元視角的跳脫與超越,它敏銳捕捉到二元之外的其他新聞傳播主體生發和崛起,將研究引入了更新且深的領域。
綜上所述,學界對UGC興起后的“新聞傳播主體”的研究大致經歷了一元“本體研究”、二元視角下的主體及關系研究、三元結構的主體及關系研究的三階段。從研究的發展趨勢看,研究對象不斷豐富、研究視野不斷拓寬、問題意識日趨強烈、研究體系漸趨完整。本研究將在前人基礎上,嘗試搭建新框架,討論UGC興起后極為復雜的新聞傳播主體類型及意涵。
二、“雙維度”交叉框架下的新聞傳播主體類型重構
回顧文獻可知,學界常應用社會學“職業化”或“專業性”為標準來劃分新聞傳播主體的類型、闡釋角色內涵。然而從研究效果上看,由于將“職業化”等同“專業性”而進行簡單而含糊的劃分,主體研究仍有不少籠統模糊、不盡其義之處。鑒于類型研究的邏輯起點在于擇定嚴謹清晰的分類框架,因此,本文將先對新聞傳播主體的“職業化”和“專業性”的進行維度及向度上的界定與厘清,以便清晰地建構主體類型。
維度一:以利己為立場的“職業化”。《現代漢語詞典》對“職業”的解釋是“個人在社會中所從事的作為主要生活來源的工作”;“職業”英文表達為“vocation”,《韋氏國際英語大辭典》的解釋是:一個人通常為了報酬而經常受雇用的工作。據此,“職業化”是指將某一行為固化為獲取生活來源的謀生手段之過程,是受利益驅動的過程。就新聞傳播主體的“職業化”來看,其內涵是指主體以新聞生產傳播活動作為謀求生存之手段,追逐利益是其壓倒性的首要特征。新聞傳播主體的職業化程度越高,工作狀態的標準化、制度化程度越高,新聞生產與傳播的行動效率也越高,以此來達成其獲利最大化。“職業化”程度之高低可用以考量新聞傳播主體開展活動是否以“利己”為前提、以利益實現為倚重,其行動多遵循資本邏輯或政治邏輯。
維度二:以利他為立場的“專業性”。專業性是伴隨某行業的規模化、正規化和自治化逐漸生成的,是行業獨有的核心話語權。學界對“專業性”內涵的基本共識包括:基于深奧理論基礎上的專業技術,以區別于僅滿足實用技巧的工匠型專才;以公共服務為宗旨,其活動有別于追逐私利的商業或營業,其根本價值是為公眾服務的精神;形成某種具有資格認定、紀律懲戒和身份保障等一套規章制度的自治性團體,以區別一般的行業。⑨對新聞傳播主體的專業性研究多見于新聞專業主義的相關討論當中。鑒于中西政治體制、文化傳統等的迥然不同,符合我國具體國情和語境的新聞專業主義標準和主體專業性的具體內涵還有待廓清和完善,因此本文所討論之主體“專業性”側重于在不同語境被共同強調的部分,即操作技能和表現手段上的專業水準以及實踐中的專業倫理。⑩從“專業性”維度考量主體的新聞生產與傳播活動是否具有知識及操作層面的專業水準和規范倫理,且是否以“利他”為前提、以社會服務為倚重,其新聞行為遵循媒介邏輯。
從上述分析可知,“職業化”和“專業性”是行業發展進程中一體兩面,不可分割。但兩者邊界清晰,有時甚至是對沖相斥。19世紀美國黃色報刊時期,眾人皆以新聞生產為“職業”,其職業化程度不可謂不高,但全行業倫理道德、行業操守之混亂,其專業程度之低,恰成反比。因此,新聞傳播主體以職業化標準或專業性為原則開展新聞實踐活動,以其倚重不同、起意目的各異,最后呈現的傳播效果和社會影響也將大相徑庭。
倘若以“職業化”和“專業性”的維度對主體類型進行平行劃分,簡單分為“職業”和“非職業”主體、“專業”和“非專業”主體,與之前研究并無二異。本研究認為,主體的“職業化”和“專業性”處于復雜交織纏繞之中。傳統媒體時代,傳播主體的“職業化”與“專業性”之間多存在單一性正向關聯,“專才專崗”的基本邏輯,即一般情況下,新聞專業人士能從事新聞職業崗位,反之則難。有學者形象地指出,彼時所謂記者,大致是這么一個形象:受過新聞教育,受雇于某個傳統新聞機構,恪守新聞業的行為準則。這一描述實際上清楚表明了傳統媒體時代記者的“職業化”與“專業性”高度合一的身份特征。隨著互聯網發展,尤其是在UGC理念及“技術叢”興起之后,新聞傳播者的“職業化”與“專業性”的特征顯現出復雜的反向交織關聯,即原有“專才專崗”的局面被“大規模業余化”的泛職業化趨勢打破,大量非專業人士嘗試跨界開展職業化活動;相應的,專業人士也得以跳出職業框架,率性而為、隨心所欲地開展別樣的行動。就新聞傳播而言,UGC推動了兩類交叉特征的新興主體生成:一類是新聞專業人士掙脫原有職業框架,開展職業色彩較弱的、追求專業水準和理想的新聞傳播活動(例如不少新聞專業人士脫離媒介組織后開展同人新聞、獨立新聞、眾籌新聞等活動);另一類如非新聞專業人士(機構)開展以立場維護和利益追逐為倚重的職業化新聞傳播活動(例如政府、企事業、組織機構甚至民眾個體等開展的新聞活動)。這兩類新聞傳播主體的“職業化”和“專業性”程度均介乎于傳統職業新聞傳播主體和民眾新聞傳播主體兩極之間,他們生產與傳播的新聞既與絕大多數“率性而為”的民眾新聞不一樣,也與絕大多數“專心致志”的職業新聞有所不同。他們當中既有超越傳統范式的新聞創新與改進,也有各懷動機的新聞失范和逾矩,他們的傳播行為和新聞形制參差多態、極為復雜,新聞傳播的效果也不一而足,對原有的新聞傳播秩序帶來巨大的沖擊和挑戰。因此,對此二類新興的新聞傳播主體應有更多研究關注。
綜上所述,“職業化”和“專業性”是對新聞主體不同維度的特征描述,“職業化”觀照市場、追逐利益,而“專業性”則超越利益、堅守水準與規范。在漫長的傳統新聞業時代,兩者特性多呈現秩序井然的正向關聯。然而在UGC驅動下,“大規模業余化”到來,社會化工具清除了公眾表達的原有障礙,從而打破了大眾傳媒特有的瓶頸。以前專業媒體人員從事的種種工作被廣泛地業余化。非新聞專業人士(機構)開展職業化新聞傳播活動、新聞專業人士也可以進行非職業化新聞傳播活動,“職業化”和“專業性”兩者特性在新聞傳播主體身上交錯和角力。倘若從上述基本概念和邏輯關聯出發,紛紜復雜的新聞主體類型和角色內涵似乎逐漸清朗起來。
三、四類新聞傳播主體的角色內涵辨析
本文以“職業化”與“專業性”程度強弱作為分類標準且進行交叉關聯,將UGC興起背景下的新聞傳播主體分為四大類型,即堅持傳統范式、居于主流地位的新聞傳播主體,“訴說沖動”型民眾傳播者,“利益偏向”型新聞傳播主體,“創新突破”型新聞傳播主體。四類型中,前二者為傳統新聞業時代的二元主體,后二者為UGC興起背景下的新興傳播主體。從研究來看,UGC興起后新聞傳播的四元主體格局初現(如圖1所示)。

圖1 雙維度交叉框架下新聞傳播主體類型示意圖
四類新聞傳播主體扮演不同的“傳者角色”,深刻辨析其角色內涵有助于加深對當下“人人參與”新聞傳播的新秩序與新格局的認知與理解。
角色類型一:“傳統范式”的新聞傳播主體。從現代報業誕生以來,以報紙、廣播、電視為主要媒介形態的新聞事業得以大規模高速發展,新聞媒介組織也逐漸形成了一套以平衡“專業規范”和“商業利益”為路徑依賴的新聞范式。新聞媒介組織在特定利益訴求的前提下,開展規模化、組織化新聞生產與傳播活動,并在長期實踐中形成一套新聞知識理念體系以及操作規范等,鑄就所謂新聞的“專業性”。此后,通過兼顧“職業化”和“專業性”的平衡,新聞媒介組織達成利益實現與專業權威樹立的雙贏,并最終確立了其社會話語“中心”地位。在傳統范式長期而深刻的影響下,新聞媒介組織機構是民眾“共識”中認同的新聞傳播“正宗”,出自于他們的產品也才是民眾所認可的權威、可信、規范的新聞,他們形塑了新聞傳播的價值理念和行為規范,造就了各類新聞報道的基本固定的樣貌和格式。進入UGC興起的時代,秉持傳統范式理念的新聞媒介組織依然存在,依舊是新聞傳播格局中的重要力量,也供給大量較高品質的新聞。但技術賦權推動其他新聞主體的不斷興起壯大,傳統新聞媒介組織機構的話語中心地位受到沖擊和挑戰,呈現頹勢和疲態。為應對當前嚴峻現實,傳統新聞媒介組織也在紛紛找尋出路、融合轉型,試圖重新回歸傳播主導地位。
角色類型二:“訴說沖動”的新聞傳播主體。“訴說沖動”是人類本能之一。本能之下,人人都是自然的新聞活動者,這與有無新聞意識、有無新聞觀念、有無新聞業、有無媒介技術或者技術有多高明先進沒有關系。從本能意義上看,民眾都是此類新聞傳播主體,他們既無需新聞專業背景,也不會以此謀利,他們生產與傳播信息的初始動因僅僅是有一種無意識的“訴說的沖動”,并且從中獲得非功利性的“自我滿足”:表現出自己消息靈通、見多識廣、熟悉行情(沉醉于“最先知道”的虛榮)。其次,“在場”優勢是民眾開展“本能”新聞傳播的重要促因。無處不在的民眾是事件發生的最早的現場見證者,他們能比專業記者更及時、更真實生動地呈現新聞現場。尤其在偶發性或突發性事件中,第一時間“在場”往往成為民眾傳播新聞的重要優勢。8·16天津港爆炸事件中,普通網民的直播式文字描述、圖片、小視頻等成為事件初期階段重要的新聞來源。當然,由于缺乏專業素養和職業動因,僅基于“訴說沖動”的民眾新聞多為淺表層面的動態消息、現場新聞等,且有碎片化、情緒化等諸多不足,甚至基本的新聞要素模糊不全,新聞表達語焉不詳,此類新聞數量雖多但總體質量不高。但民眾訴說沖動下的生產與傳播的新聞也并非全無可取。除了上文所述的時效性、現場感等優勢之外,從宏觀上看,協同自組織機制一旦啟動,訴說沖動下的民眾將依然可能發揮群體優勢,多方漸次發掘信息,最終還原事實真相。
角色類型三:“利益偏向”型新聞傳播主體。得益于UGC技術與平臺的興起與普及,非新聞專業背景的組織或群體個人逐漸被賦予了開展職業化新聞實踐的可能性。典型如楊保軍教授所指“脫媒主體”就屬此類型。“脫媒主體”描述的是曾經主要依賴新聞媒介機構實現新聞傳播需求,但借助當下UGC技術和平臺自建媒體實現新聞的自主生產與傳播的組織或群體,例如政府、企事業單位等的官方網站、“兩微一端”等傳播平臺。從新聞行為專業規范化程度來看,這類新聞傳播主體由于其本身就是相對獨立的利益組織或利益群體的一部分,必然有自身的傳播立場和傾向,它本質上追求的是宣傳效果、廣告效果、公關效果,因而,它骨子里奉行的乃是宣傳傳播、廣告傳播、公關傳播的觀念,它采用的更多的是偏向宣傳、廣告、公關的手段和方法,他們期望的也是自身組織內部、群體內部的認同以及受傳對象對“脫媒主體”所根源的組織或群體的認同。甚至在一些極端情況下,雖然各個機構都自建媒體,但是他們并不以公共利益為首要考慮,他們發布很多信息,但必然有他們不愿意、沒有動力發布的信息,他們也必然會發布一些假信息。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互聯網技術公司為拓展其商業版圖,逐漸向新聞業進軍,其本身也成為傳統范式之外的強大新聞傳播力量。例如,臉譜網(Facebook)通過“即時文匯”(Instant Article)、“通告”(Notify)和“訊號”(Signal)等三大應用軟件(App),構建了基于社交媒體平臺的新聞產品矩陣,從新聞的生產、分發、運營等層面重塑新聞格局。國內情況亦是如此,典型如社交媒體巨頭騰訊及旗下新聞產品和以算法推薦見長的“今日頭條”等,對傳統新聞產生巨大沖擊。有學者對此憂心,指出對于一家由極客主導的互聯網公司而言,它很難履行告知的責任——即幫助公眾了解什么才是最重要、最值得關注的公共事務。這些責任原本屬于傳統媒體,在經歷了近百年的爭議和嘗試后,奉行專業主義和職業倫理已經成為全球新聞界的共識。但科技公司用“算法邏輯”和“資本邏輯”取代“媒體邏輯”后,勢必徹底顛覆關于新聞價值、專業主義和職業倫理的共識。
“利益偏向”型新聞傳播主體其新聞專業性較弱、有的甚至可以拋開新聞專業性,以維護利益或實現目的為基本前提開展新聞活動。由于“專業性”讓位于“職業化”,這類主體生產與傳播的新聞產品及傳播行為帶有或隱或顯的立場或利益的偏向色彩。無論是對黨政機關或公司企業的自建媒體平臺、還是從技術公司創立的新聞聚合平臺上的新聞加以審視,不難發現其在框架選擇、報道平衡、中立表達等操作方面與新聞專業規范相去甚遠。
角色類型四:“創新突破”型新聞傳播主體。UGC為專業人士提供了跳出職業框架之外的可能,成就了他們“別樣”的新聞實踐創新。由于受到職業規制所限,不少供職于新聞機構的專業人士常無法達成表達上的自我滿足和自我實現。他們或于工作之余,或索性脫離體制,在微博、微信等自媒體平臺上開展有別于“職業狀態”的新聞活動,成就了大量既有相當專業水準、且樣態新奇的新聞報道。“創新突破”型新聞傳播主體的新聞報道的特點和優勢集中體現在新聞表達上的“合法偏離”與新聞報道策略上的“邊緣突破”。“合法偏離”源自修辭學,通常認為語體系統有效度或規范度,在這個“度”內的語言表述都是規范的、合法的。偏離這種規范度的,有正面的,向上的,精彩的,有魅力的“突破”;也有負面的,向下的,有礙于表達理解的“語病”。“合法偏離”產生話語實踐的張力,給語言表達帶來新的生命力。“創新突破”類主體脫離新聞敘事表達的職業約束,在保證基本事實準確和主軸意義不偏離的前提下,在新聞修辭上進行了“合法偏離”的多種創新嘗試。例如曾供職傳統媒體、后創辦自媒體“米糕新聞日記”創始人胡亞平談及新聞表達創新時,闡釋以下觀點:第一視角的代入是我傾向于微信公眾號寫作的原因,我對于純客觀的事實報道已經十分厭倦,而且對于假借專家之口說一些不痛不癢的觀點感到厭倦。我希望通過個人的體驗和感受,與人分享對事件的看法,分享細節、分享真實的體驗,這是一般新聞做不到的。這是更有溫度的敘事方式和傳播方式。自媒體“有槽”的創始人詹涓也表達同樣的觀點:我們是有意想要做私人化表述,拉近與讀者之間的距離。傳統媒體的新聞敘事是要盡可能抹去作者的意見和存在感,以此來體現客觀、中立。但我們關注的角度、采寫的方式都決定了不可能像傳統報道那樣板正。新聞修辭上的“合法偏離”為受眾帶來新鮮的閱讀體驗,大大提升新聞的傳播效果。曾引發“魏則西”事件的輿論熱潮的微信公眾號“有槽”在文章《一個死在百度和部隊醫院之手的年輕人》的結尾寫道:“我是無神論者,但在這件事情上我期待有報應,我希望涉事的所有人,包括醫療監管官員、百度的人、醫院的人、康新的人、柯萊遜的人,夜里能聽到魏則西和其他受害者的哭聲。”這句話出現在“有槽”的一篇“調查報道”中,但其具有強烈抒情和明確觀點表達的話語風格是對傳統新聞報道規范的“偏離”,但這句話成了微博上轉引率極高的一句話,它激起了讀者的強烈共鳴,客觀上對文章的傳播起了積極助推的作用。此外,“創新突破”型主體擅用“邊緣突破”式報道策略。作為體制外的新聞生產傳播主體,不僅沒有新聞生產傳播的優先權,還受到了新聞管理部門的規制管理(例如網信辦頒布關于“時政新聞”的排他性采寫規定等),他們通常多在非中心類新聞題材、或對中心類題材的邊緣信息、邊緣角度進行切入報道,使新聞報道完成從“邊緣”逼近“中心”的進路,引發民眾關注和媒介組織介入、最終實現新聞的社會使命和功能。
四、余論:互鑒融合中的理念回歸
在UGC理念普及及相關技術賦權下,自由多元的新聞生產與傳播活動得以大規模展開。新聞行為的“職業化”和“專業性”高度合一的傳統模式被打破后,四類新聞主體逐漸生成并結構成新聞傳播新圖景。雖然有各自側重的新聞題材和擅長的新聞類型,但四類主體在新聞話語權及其他相關利益上持續展開激烈競爭博弈。從發展進路上看,四類主體都在互鑒所長中補齊短板,將對方的優勢因素結構性嵌入、融合發展,力圖提升自身的傳播效果。“傳統范式”的新聞傳播主體不斷吸納“民眾”優勢,例如積極采用無處不在、無時不刻的民眾信源和素材,從民眾對新聞的評論和反饋中捕捉新選題、調整后續報道方向,甚至主動開設民眾主導的“參與式新聞”類的頻道或欄目。例如《人民日報》官方微博正在逐步開展汲取“民眾”優勢的轉型嘗試,在準確核實的基礎上直接轉發推送民眾或非媒機構的新聞類信息,小編“親民”地參與網友討論和評論從中獲得新聞線索和素材補充等。“創新突破”型新聞傳播主體則正朝著“內容創業”的職業規范發生轉變,他們不斷調整從心所欲的新聞傳播態度,逐漸將新聞活動當成職業或事業來悉心經營。隨著UGC平臺的廣告推送、內容打賞、流量變現等機制不斷完善,“創新突破”型主體的職業化轉向日趨明顯。“利益偏向”型新聞傳播主體逐漸認清新聞本質及基本規律,在加強新聞專業性的前提下,巧妙合理運用新聞框架,開展春風化雨、行之有效的認知建構;“訴說沖動”型的民眾則從最初只因“第一時間在場”優勢與便利,無意識開展新聞活動,發展到后來有意識、積極尋找新聞線索,能動地開展報道策劃、深入新聞現場、搜集新聞素材和數據,生產出有一定原創度的新聞信息,并借此為利器發聲、爭鳴和維權,其新聞生產傳播行為發生了向“職業化”和“專業性”雙重轉向和提升。從事公民新聞生產的早期代表人物周曙光最初表示:“我之前不知道自己那種行為叫公民記者行為。我就想去看看到底發生了什么?湊熱鬧而已。”然而,他這種“湊熱鬧”式的無意識新聞活動很快就演進為利益驅動下的類職業化新聞行為,他說:“當然,公民記者也能做成商業項目,公民記者的報道能產生社會效應,社會效應能產生商業效應。”四類主體都進行積極自我審視,互鑒優長,在優勢融合中不斷提升新聞的生產力和傳播效果。在激烈競合之中,各類新聞主體逐漸回歸一種“平衡”的新聞操作理念,即唯有調和“職業化”和“專業性”身份角色沖突,平衡專業主義、商業主義和宣傳主義之間的關系是其生存發展的重要邏輯。
注釋:
① 趙翔宇、范哲、朱慶華:《用戶生成內容(UGC)概念解析及研究進展》,《中國圖書館學報》,2012年第5期。
② 楊善林、王佳佳、代寶等:《在線社交網絡用戶行為研究現狀與展望》,《中國科學院院刊》,2015年第2期。
⑤ Shayne Bowman,Chris Willis,歐陽俊杰:《參與式新聞的興起》,《中華文化論壇》,2009年第S1期。
⑥ 原文為:Given Enough Eyeballs,All Bugs are Shallow.開放源代碼運動的主要領導者埃里克·雷蒙(Eric Steven Raymond)的名言。
⑦ 喻國明、張超、李珊等:《“個人被激活”的時代:互聯網邏輯下傳播生態的重構——關于“互聯網是一種高維媒介觀點”的延伸探討》,《現代傳播》,2015年第5期。
⑧ 喻國明:《關系賦權范式下的傳媒影響力再造》,《新聞與寫作》,2016年第7期。
⑨ 劉思達:《職業自主性與國家干預——西方職業社會學研究評述》,《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1期。
⑩ 芮必峰:《描述乎·規范乎——新聞專業主義之于我國新聞傳播實踐》,《新聞與傳播研究》,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