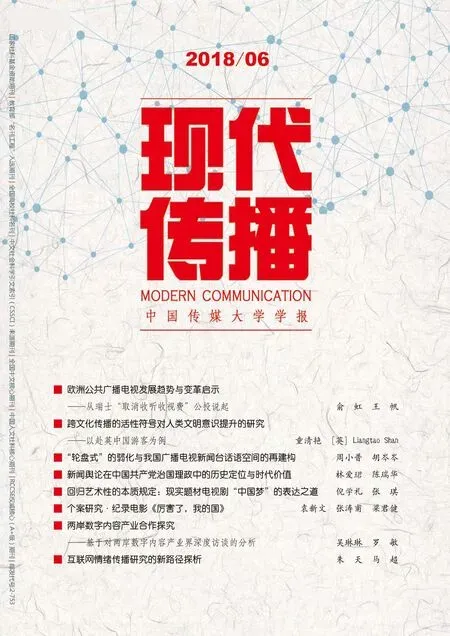中國傳媒市場結構的變遷、模型及優化*
■ 易旭明 倪 琳
市場結構作為產業組織經濟學核心概念之一,旨在揭示特定產業市場競爭與壟斷格局、企業生產效率以及資源配置效率,已成為現代政府實施產業規制、調控產業發展的一個關鍵指標。當前中國傳統媒體產業效率較低,且面臨著媒體融合和產業融合新業態的沖擊,市場結構整合與優化的問題十分迫切。作為傳統媒體代表的電視與作為新興媒體代表的互聯網,兩者在中國傳媒產業史上產業規模最大、規模經濟效應最強,因此本文通過聚焦其產業增長與市場結構變遷,試圖揭示中國傳媒市場結構變遷的主要特征及其深層原因,構建中國本土傳媒市場結構變遷模型,思考媒體融合環境下中國傳媒市場結構的優化路徑。
一、傳媒市場結構研究評述
市場結構指的是市場中企業關系的特征和形式,更具體地說是指公司規模分布狀況。經濟學文獻常將市場結構分為完全競爭、完全壟斷、寡頭壟斷、壟斷競爭四種基本類型。結構和行為、績效是反映市場競爭與壟斷關系的三個指標,主流經濟學假設認為很多時候結構是關鍵影響因素,有的學派則顛覆了這種因果關系,認為結構是效率的結果,所以對學術爭論的把握也取決于現實條件和行業特征①。市場結構通常包括賣者和買者數量、準入壁壘、成本結構、產品差異化、一體化等要素,受政府規制、反壟斷等公共政策影響②,其中決定市場結構最主要的三個因素是市場份額、大公司集中度和進入壁壘③。
縱觀經濟學史,市場結構及其經濟效率是經濟學家討論的核心問題之一,因為競爭與壟斷是財富生產與分配的關鍵,探究競爭與壟斷、政府干預與市場調控對經濟效率的影響也就成為經濟研究的核心領域。這也是研究傳媒產業市場結構及其優化的理論基礎。經濟學核心理念認為,競爭是大多數現代市場的驅動力,壟斷則會破壞競爭帶來的良好結果④。總體而言,推崇競爭、反對壟斷是經濟學的一個基本理念,也是政府用反壟斷法干預市場結構的理論基礎;但是規模經濟也有利于經濟效率的提高和整體福利的改善。尤其是在數字化科技條件下,現代工業和傳媒信息產業的規模經濟效應更是顯著提升,世紀之交世界各國放松規制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優化競爭、提升產業規模經濟和國際競爭力。
傳媒市場結構之所以重要,不僅因為它關乎經濟效率,還因為它關乎傳媒社會功能的實現。隨著傳媒規制放松引發傳媒并購和集中現象,傳媒市場結構也成為國外傳媒經濟研究熱點之一。市場結構的集中度關涉西方發達傳媒產業政策的敏感神經,正如大衛·揚所論,市場結構對塑造傳媒行為和內容起著關鍵作用,新的傳媒技術導致規模經濟與傳媒產權重組也將對市場結構產生更加復雜而重要的影響。⑤
中國傳媒產業市場結構文獻也不少,尤其是傳統媒體市場結構及其經濟效率研究。王禮生認為電視產業屬于壟斷競爭型市場結構⑥,王威將電視廣告市場結構與報業比較,認為中國報業是壟斷競爭型,而電視市場屬于寡頭壟斷型。⑦陶喜紅認為中國電視市場結構屬于寡占Ⅲ或Ⅳ型結構,相對其它較分散競爭的紙質與廣播傳媒,電視與互聯網傳媒市場結構同屬壟斷程度較高類型。⑧易旭明則認為中國電視市場結構競爭活力和規模效應“雙低”,全國市場、區域市場結構分別屬于“核-粒模型”和“單向-層級壟斷”結構。⑨有的研究并未直接使用“市場結構”概念,但同樣指向中國傳媒產業“條塊分割、畫地為牢”“市場分割破碎”和文化產業“行政切割”的市場結構弊端,傳媒事業、產業混合的實踐中也出現了社會公益逐漸抽離的現象。
綜上所述,市場結構的確是優化配置資源、提高經濟效率、實施產業政策的核心樞紐。各國傳媒市場結構都涉及政治和經濟雙重目標,中國傳媒市場結構更是因雙重目標而對經濟效率標準有所偏離。但是現有文獻對中國傳媒市場結構的研究多停留在宏觀定性分析層面,有部分定量分析但未深入研究其變遷規律、理論模型,對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市場結構變遷趨勢比較研究則更少。
二、“M型”電視媒體市場結構變遷及成因
如果說市場結構能夠體現市場競爭壟斷格局和經濟效率,那么從市場結構的歷史變遷中則可發現政策要素與技術要素對市場結構發生作用的規律,從而利于采取合適的規制政策優化市場結構。因為決定市場結構最主要的三個因素是市場份額、集中度和進入壁壘,且有學者認為經常需要描述的市場結構只有CRn指標——即市場前n家廠商的集中度系數,其中最常用的指標是CR4,由此可見市場集中度系數對衡量市場結構的重要性。所以,本文研究市場結構變遷首先是研究市場集中度變遷,再探究集中度變遷中市場壁壘變遷的特征和影響。
本文主要是運用廣告收入統計市場集中度的指標,因為廣告是傳統電視臺最重要的收入來源,互聯網作為媒體對傳統電視的經營競爭首先也是體現在廣告方面。本文統計的1992年至2016年我國電視市場廣告收入總額及集中度CR1、CR4、CR8系數如表1所示;將表1集中度系數轉換成曲線圖,則形成圖1。
從圖1中,我們可以發現中國電視市場集中度變遷軌跡呈顯著“M型”特征,即集中度系數升降幅度較大并且反復曲折波動,拐點顯著。具體考察“M型”集中度曲線波動原因,我們發現在曲線拐點期都有重大調控政策出臺,這些重大政策分別是:(1)1995年停批新臺政策,提高準入壁壘帶來集中度回升。1983年底
表1 中國電視廣告市場規模與市場集中度變遷(1992-2016)

表1 中國電視廣告市場規模與市場集中度變遷(1992-2016)
年份廣告總額(億元)CR1CR4CR8199220.5523.84(央視)40.4449.97199329.4421.98(央視)37.1647.55199444.7621.65(央視)35.8644.12199564.9830.78(央視)44.8154.09199690.7938.67(央視)53.4662.001997114.4136.48(央視)53.5164.491998135.6430.03(央視)42.6449.581999156.1530.19(央視)42.6949.862000168.9131.67(央視)45.7053.722001179.3730.11(央視)53.9665.822002231.0327.63(央視)46.3355.482003255.0429.52(央視)47.3857.012004291.5427.44(央視)45.8355.082005355.2924.26(央視)41.8153.462006404.0222.94(央視)39.9553.432007442.9522.58(央視)40.2953.932008501.5032.10(央視)50.0462.952009536.2030.03(央視)47.4358.492010679.8327.71(央視)45.4155.272011897.9225.39(央視)44.7258.7620121132.2723.76(央視)38.9550.3620131101.1023.24(央視)40.2551.0620141278.5021.27(央視)35.8646.5320151146.69———20161239.00———

圖1 中國電視廣告市場集中度變化曲線(1992-2014)
“四級辦臺”政策后基層電視臺猛增、違規節目“亂播濫放”損害精神文明,從1994年開始廣電部開始停止批建縣級電視臺,1995年全面停止批臺,于是1995年市場集中度CR4系數比上年提高了8.95個百分點。(2)1996年底以《關于加強新聞出版廣播電視業管理的通知》為標志的“治散治濫”政策降低了退出壁壘,撤銷違規臺或者合并合法臺,廣播電視播出機構迅速由6937座下降到2216座,導致市場集中度上升。但1997年-1998年的省級臺主頻道“上星”政策則降低了全國覆蓋電視市場準入壁壘,增加了競爭主體,又成為市場集中度轉而下降的作用力。(3)2001年《關于廣播電影電視集團化發展試行工作的原則意見》為標志的集團化政策掀起了區域內無線電視臺和有線電視臺合并、廣播影視集團化改革高潮,這一政策降低了退出壁壘,推動市場集中度CR4系數升至峰值53.86%。但由于跨區域重組的政策壁壘高聳,使上海、北京等優勢電視臺在集團化后很難大幅擴張,加之湖南等上星頻道競爭激烈,市場集中度無法持續上升轉而降低。(4)政策賦予央視2008年奧運會的壟斷報道權也形成了市場準入壁壘,促成了集中度上升至階段性高點。2009年國務院《文化產業振興規劃》、國家廣電總局《〈關于認真做好廣播電視制播分離改革的意見〉的通知》推動的“制播分離”政策則變相降低了準入壁壘,使原先缺乏競爭優勢的電視臺更容易購買優質節目;加之劣勢電視臺退出政策缺失、市場資源難以優化配置,集中度便持續下降。曲折波動的M型市場結構變遷軌跡由此形成。
可見,中國電視市場結構是一個顯著的“政策市”,行政壁壘對過山車式的“M型”集中度變遷軌跡起著基礎性乃至決定性作用。提高傳媒規模效應、“做大做強”始終是中國電視傳媒政策目標之一,但是幾次整體集中度上升和優勢機構規模上升都是短期政策干預推動所致而非市場競爭演化的結果。只要現有按行政級別和區劃配置資源的電視市場壁壘存在,則從M型市場結構變遷軌跡可以預見未來電視市場集中度會呈持續下降的趨勢。
三、“U型”互聯網媒體市場結構變遷及其成因
一般認為中國互聯網媒體始于1995年,商業互聯網新聞始于1998年,傳統媒體網絡化高潮是1999年,2003年中國網絡媒體影響全面形成。為了發展中國信息產業并利用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中國對互聯網產業采取了相對電視產業低得多的準入退出壁壘,由此形成互聯網媒體市場經營主體數量巨大、產業規模和傳播影響力增長迅猛的發展態勢,市場結構及其競爭、壟斷特征也與電視媒體完全不同。本文統計了從1999年至2016年中國互聯網媒體廣告總額及市場集中度變遷數據,如表2所示。將表2轉換為圖2,我們可以發現中國互聯網媒體廣告市場集中度變遷大至呈平緩“U型”軌跡,即集中度系數先降后升,除一個拐點外并未出現反復升降轉折。歷史上市場集中度最低點是2007年(CR4系數為42.4%),曲線起點2001年和終點2015年CR4系數分別為71.4%和69%,高點和低點之間集中度單調遞減或遞增。
表2 中國互聯網媒體廣告總額及市場集中度變遷(1999-2016)

表2 中國互聯網媒體廣告總額及市場集中度變遷(1999-2016)
年份廣告總額(億元)CR1CR419990.9—20003.5——20014.136.59(新浪)71.6120024.936.37(新浪)71.32200310.829.8(新浪)66.5200423.425.2(新浪)63.3200541.718.0(新浪)47.3200660.515.7(新浪)46.6200710616.5(百度)42.4200817018.8(百度)44.42009207.421.5(百度)47.42010337.124.3(百度)49.92011537.728.3(百度)57.12012773.129.5(百度)62.82013110028.9(百度)63.92014154031.9(百度)65.620152184.531.7(百度)6920162902.729.37(阿里)—

圖2 中國互聯網媒體廣告市場
這種U型市場集中度變遷軌跡,體現了特定技術條件下市場作用主導、政策影響居次的競爭演化特征:(1)產業導入期:市場需求小、集中度高且緩慢下降。早期互聯網用戶和廣告需求都很小,互聯網企業數量較少、能夠獲得廣告收入的就更少,因此市場集中度數值系數較高,但集中度隨市場培育和競爭者增加而逐步降低。(2)產業成長期:市場迅速擴張、競爭者準入及其業務創新活躍,集中度迅速下降。2003年是中國互聯網用戶和廣告需求大幅上升的重要節點,需求增長進而引致更多供給,從而帶來市場集中度加速下降——2003年廣告需求同比增長120.41%、網站數量增長61.75%,市場集中度CR4系數則下降了4.82個百分點。激烈競爭中的互聯網創新也是市場集中度下降的原因,2005年集中度CR4系數同比下降16個百分點,原因之一就是門戶網站廣告份額大幅下降,而廣告新模式——搜索廣告市場份額迅速增長,富媒體廣告創新也是稀釋原有模式市場份額的因素之一。(3)產業成熟期:規模效應、競爭與重組及部分政策等因素推動市場集中度上升。互聯網廣告市場集中度CR4系數在2008年開始上升、2011年大幅提高7.2個百分點,都伴隨著競爭加劇、優勝劣汰、業務創新、重組并購等一系列市場行為,互聯網媒體市場結構已經演變成為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顯著的寡頭壟斷結構,市場集中度進一步上升。(4)產業蛻變期:優勢企業市場地位突出和激烈競爭并存,市場集中提高和創新活躍并存。一般產業在成熟期后通常進入衰退期或者蛻變期,衰退產業會因市場縮小導致集中度提高,但互聯網媒體產業顯然不是衰退,而是在市場擴張和創新蛻變中提高集中度——2015年中國互聯網廣告集中度CR4系數已經高達69%。騰訊、阿里、百度等優勢企業規模效應顯著,但其市場份額差距不懸殊、競爭激烈、創新頻繁;自由進出的中小互聯網媒體亦在活躍的競爭和創新中尋求商機,市場可謂接近兼具規模和競爭效率的“有效競爭”結構。
綜上,中國互聯網媒體市場結構及其變遷軌跡與電視市場截然不同,這種結構不是政府干預的結果,而是在準入退出壁壘較低的條件下,企業充分應用互聯網技術的規模經濟效應,在激烈的市場競爭、并購重組中逐步演化而成。未來互聯網媒體寡頭壟斷市場結構和高集中度水平因其內在的經濟效率或許很難改變,僅有可能變數在于具體寡頭及其排序在競爭中微調。
四、市場壁壘與市場集中度的關系模型
M型電視市場結構變遷與U型互聯網媒體市場結構變遷軌跡在中國語境下出現,表面上是不同產業各自發展,其深層次是技術規模行政壁壘導致市場壁壘的形成,從而作用于市場集中度的不同表現。“U”型市場集中度軌跡更能夠體現市場自由運作下競爭效應與規模效應的經濟效率,盡管政府仍有不少關于內容規制的政策出臺,但的確很少像傳統媒體那樣通過大規模行政壁壘干預互聯網媒體經營和市場份額的政策,所以互聯網媒體市場集中度未出現市場集中度驟升驟降的現象。互聯網廣告份額首位企業經歷了門戶網站新浪網、搜索引擎百度、電商網站阿里的變遷也進而說明,U型市場結構變遷是較低市場壁壘下市場充分競爭、重組的結果,也體現了激烈競爭中互聯網業務、模式和技術創新的效率。相比之下,市場壁壘較高的電視市場結構,始終是處于行政壟斷地位的央視一家獨大。可見市場壁壘對于中國傳媒市場結構的形成發揮著決定性作用。
所謂市場壁壘包括準入壁壘和退出壁壘,準入壁壘即企業進入某一市場時所遇到的困難和障礙,它在決定競爭企業數量和規模分布上起著“中樞”作用;退出壁壘則指市場在位企業虧損時退出市場的成本。西方傳媒產業研究多關注準入壁壘,如美國學者諾姆的經典模型就如此,其核心討論的是進入壁壘與市場集中度之間的關系,如表3所示。該模型認為,傳媒進入壁壘高低影響市場集中度的升降、傳媒產業規模經濟特征影響總體市場集中度震蕩軸(即中位水平)走勢,準入壁壘高則市場集中度高,規模經濟強則市場集中度高,如果壁壘高、規模效應弱則會出現先升后降的倒U型軌跡,如果壁壘低、規模效應強則會出現先降后升的U型軌跡:

表3 規模經濟和準入壁壘對市場集中度趨勢變化的影響
應該說這個關系模型對美國市場競爭條件下的傳媒集中度變遷具有較強解釋力,對中國媒體市場也有一定解釋力。但是中國傳媒市場壁壘與市場集中度之間的作用關系更為復雜,有些中國傳媒市場結構現象表3無法解釋,這是因為中國傳媒市場結構中存在退出壁壘缺失的問題。由于經營低效而破產或者被兼并在美國是不言自明的事,退出壁壘影響未被充分考慮。但是,中國本土傳媒市場壁壘與市場集中度的關系模型則必須增加退出壁壘變量,并綜合規模經濟壁壘和準入壁壘變量:

表4 中國傳媒準入退出壁壘、規模經濟壁壘對市場集中度的影響模型
表4模型顯示,準入壁壘升高、退出壁壘降低是中國電視市場集中度上升的動因,反之則是市場集中度降低的動因。如“集團化”、奧運報道權壟斷等政策就屬于行政準入壁壘提高,“治散治濫”就屬于行政退出壁壘降低,這些政策都導致了市場集中度提高;“四級辦臺”“省級頻道上星”等政策則是行政準入壁壘降低,導致了市場集中度降低。在中國互聯網傳媒市場,較低的準入壁壘、并購壁壘加上互聯網規模經濟效應提升,形成了U型集中度變遷軌跡。
從市場集中度模型和變遷的曲線形態甚至可以洞察未來市場結構趨勢。由于退出壁壘的缺失,在位電視臺即便虧損也不能退出市場,優勢電視臺即便有規模優勢也很難充分發揮,電視市場結構M型軌跡的未端指向是一個不斷朝下的趨勢,市場集中度會持續降低。互聯網媒體市場則不同,它的退出壁壘較低——一旦虧損往往就可以選擇退出,并購行為也容易進行從而導致市場集中度能夠保持高位。在互聯網平臺規模效應不斷提高的技術條件下,未來中國互聯網媒體市場結構屬于U型曲線中規模經濟壁壘上升、行政準入和退出壁壘下降的情形,市場集中度CR4值將定位在拋物線的最高區域。
五、對中國傳媒市場結構優化的思考
基于對中國傳媒市場結構(包括市場集中度和市場壁壘等要素)變遷原因、關系模型的深入分析,本文認為M型的市場結構軌跡是我國傳統媒體按行政區劃主導資源配置條件下,數次通過“政府之手”提高電視機構規模、卻又無法阻止市場集中度和規模效應持續下降的震蕩型趨勢;U型市場結構軌跡則是在“市場之手”作用下競爭整合、優勝劣汰而形成的經濟高效的拋物線。這兩種市場結構變遷應該如何評價?從產業經濟學的角度,對于M型的市場結構變遷趨勢不難發現其弊端,優化方向是激活市場競爭、提升規模效應、適度提高集中度并促進有效競爭市場結構形成。對U型的互聯網市場結構軌跡則可能會出現兩種評價:一種是贊賞它成為均衡競爭活力與規模效應的最佳詮釋者;另一種是謹慎審視其壟斷特性對整體經濟效率和社會效益的不良影響。雖然認識到M型的電視市場結構很難朝U型互聯網市場結構優化,兩者之間具有不可通約性,但基于一定的現實條件,我們也可以嘗試從比較的視角對中國傳媒市場結構優化展開建設性思考。
1.電視市場結構優化過程中引入退出機制
對中國電視產業市場集中度變遷軌跡及其成因、模型分析表明,中國電視產業要建立有效競爭市場結構面臨著高聳的政策性市場壁壘障礙:退出壁壘保護了低效電視臺生存、阻礙了相對高效電視機構擴張和規模效應實現;進入壁壘削弱了競爭活力、阻礙了潛在高效和創新機構進入市場。從歷史和現實來看,規模小、效率低的基層電視臺難以退出市場原因大致有三:(1)中央和地方宣傳需要、保證輿論導向需要是低效電視機構存在的根本原因;(2)地方公共文化傳播和娛樂市場需要依然存在;(3)現實中很敏感的問題是員工安置和資產處置困難。因此推動中國基層電視臺(也包括部分省級電視臺乃至中央電視臺的頻道)退出市場的思路在于:第一,行政推動低效電視臺或頻道退出市場,但須安排必要的電視播出時段并拓展各種新媒體渠道,確保中央政策宣傳和輿論導向需要、滿足地方黨政工作宣傳需要;第二,主動剝離低效“可經營性節目”生產部門,推動其參與市場競爭并與高效市場機構實施重組整合;第三,通過各種手段合理安置電視臺或頻道退出后的員工,充分利用設備資產。當然,這只是中國兩千多家電視臺中的低效資源退出市場、優化市場結構的原則性思路,如何實現平穩過渡,其中還充滿著多種可能性。
2.促進互聯網媒體市場的可競爭性與社會效益
評價中國互聯網媒體市場結構,我們也需要基于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率的雙重維度。從經濟效率維度看,其市場結構以及“U型”變遷軌跡較好體現了市場競爭和技術的效率,且規模效應強、新進入者多、創新活躍,較好體現了有效競爭的理念。但是,占據寡頭地位的優勢互聯網企業亦有可能利用壟斷地位來排斥競爭、損害全行業經濟效率。當然,互聯網行業規模效應強,市場集中度高可謂國際普遍現象。美國互聯網廣告市場集中度亦是逐年遞增,2016年第二季度集中度CR10系數達到74%,與中國同期CR10系數78.6%非常接近。對此各國往往是針對性地規制壟斷行為、促進競爭,充分發揮“可競爭性理論”所強調的自由準入來保持競爭性、提高績效,而非直接分拆企業來降低市場集中度。所以中國互聯網媒體市場結構優化的理論方向,在于保持寬松行政壁壘、培育競爭力量,并有效規制壟斷行為、減輕經濟壁壘阻礙競爭的不良影響。在互聯網的傳媒屬性和社會影響越來越強時,我們還需要從社會效益維度審視互聯網媒體市場結構。2015年中國互聯網媒體廣告市場集中度CR6系數已達74.3%,按照著名經濟學家植草益的標準這已屬于“極高寡占型”市場結構。并且某些市場——如即時通信、搜索引擎等市場——集中度則更高,如2015年第四季度中國搜索引擎市場百度就占據了85.54%的份額,壟斷機構對公眾利益的潛在威脅不容小覷,“魏則西事件”即是例證之一。所以,從社會效益維度來審視互聯網媒體寡頭壟斷市場結構,亦需通過法治手段規制其不良經營行為。
3.作為結構優化路徑的媒介融合規制
數字技術和互聯網技術在傳媒行業已經無處不在,真正“傳統”的主要是混合事業產業功能的傳媒機構和有待創新的規制政策。對受眾而言,各種媒體形態都是平等競爭的選項,所以對傳媒機構來說跨媒體融合也勢在必行。媒體融合表層是技術、產品、市場的融合,深層卻是組織結構、傳媒理念和規范標準的融合。媒介融合本身就可以是一種市場結構優化的過程,融合必然導致各種傳媒機構在各個領域進入退出、優化布局,但中國媒介融合的重心更多在于通過調整行政壁壘來激活國有媒體機構的再造:(1)整合重組:打破產權壁壘推進非新聞類國有媒體與民營媒體進行適當重組整合、優化內部激勵約束機制,國有產權比重可以根據導向安全和經營需要靈活掌握,從而在淘汰低效國有傳媒機構同時擴大傳媒規模,這也是在當下民營媒體已經占據了互聯網媒體市場絕對優勢的環境下較為可行的融合發展路徑;(2)激活競爭:進一步激活包括新聞在內的國有媒體之間競爭,既包括媒體內部競爭,也包括國有媒體之間效率考核競爭,還可以要求國有媒體安排適當比例產品進行社會采購、公平競爭;(3)統一規制:根據社會影響和公共利益原則對國有、民營媒體內容實施統一標準的社會規制,也對承擔公共服務的內容實行統一扶持,這既是規范傳媒社會價值的需要,也是推進傳媒公平競爭和建立有效傳播體系的需要。
注釋:
①③ [美]威廉·G·謝潑德、喬安娜·M·謝潑德:《產業組織經濟學》,張志奇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1、83頁。
② F.M.Scherer,David Ross.IndustrialMarketStructureandEconomicPerformance(ThirdEdition).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90.p.5.
④ [荷]亨利·W.狄雍、[美]威廉·G.謝潑德:《產業組織理論先驅——競爭與壟斷力量形成和發展的軌跡》,蒲艷、張志奇譯,經濟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
⑤ David P.T.Young.ModelingMediaMarkets:HowImportantisMarketStructure?The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13(1).pp.27-44.
⑥ 王禮生:《中國電視業市場結構實證分析》,《系統工程》,2007年第5期。
⑦ 王威:《我國媒介廣告市場集中度分析》,《國際新聞界》,2007年第4期。
⑧ 參見陶喜紅:《中國傳媒產業市場結構演變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
⑨ 易旭明:《有效競爭視域下中國電視市場結構再考察》,《現代傳播》,201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