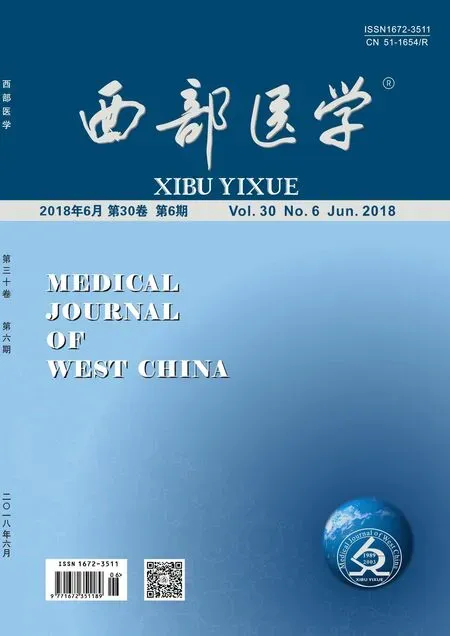丙戊酸鈉聯(lián)合拉莫三嗪對原發(fā)性癲癇患者 外周血細(xì)胞因子與療效的影響*
王紅梅 吳建平 譚華
(1.內(nèi)江市第二人民醫(yī)院神經(jīng)內(nèi)科,四川 內(nèi)江 641100 2.西南醫(yī)科大學(xué)神經(jīng)內(nèi)科,四川 瀘州 646000)
癲癇是一種由于大腦中神經(jīng)細(xì)胞處于異常狀態(tài)放電而引起的突發(fā)的、短時的腦部功能紊亂神經(jīng)系統(tǒng)綜合征,其發(fā)病原因多樣,發(fā)病機(jī)理復(fù)雜[1]。癲癇癥狀突發(fā)、相對嚴(yán)重,而根治又極為不易,不僅會對患者造成生理上的傷害,更會造成周圍人群的恐慌,給患者造成很大的心理傷害,對患者的正常生活帶來極大的困擾[2-3]。目前在中國有將近一千萬癲癇患者,是僅次于頭痛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常發(fā)病[4]。在癲癇的發(fā)病機(jī)制中,免疫機(jī)制越發(fā)引起人們的關(guān)注,其中細(xì)胞因子TNF-α、IFN- γ、IL-2、IL-10、IL-4、IL-6、 IL-17A、IL-23、IL-1β等被認(rèn)為與癲癇的發(fā)病密切相關(guān),其外周血水平可以作為癲癇控制情況的指標(biāo)。目前癲癇的治療主要以藥物治療為主[5]。但部分患者單一用藥效果不顯著,現(xiàn)聯(lián)合用藥越發(fā)受到關(guān)注,有研究發(fā)現(xiàn)丙戊酸鈉與拉莫三嗪聯(lián)用治療小兒原發(fā)性癲癇可以提高療效,減少不良反應(yīng)[6]。本研究對收治的150例原發(fā)性癲痛患者進(jìn)行前瞻性隨訪研究,觀察丙戊酸鈉聯(lián)合拉莫三嗪治療成人癲癇的療效、安全性及對相關(guān)細(xì)胞因子的影響,現(xiàn)將結(jié)果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納入2014年3月~2016年3月于本院神經(jīng)內(nèi)科就診的原發(fā)性癲癇(各種類型)成人病例150例,隨機(jī)分成對照組(丙戊酸鈉)和觀察組(丙戊酸鈉+拉莫三嗪),每組各75例,對照組中男33 人,女42 人;年齡19~72歲,平均(38.5±11.6)歲;病程1~20年,平均(9.8±2.4)年;全身性發(fā)作47例,部分性發(fā)作28例。觀察組中男32 人,女43 人;年齡17~70歲,平均(36.7±10.8)歲;病程3~22年,平均(9.5±2.6)年;全身性發(fā)作51例,部分性發(fā)作24例。兩組患者一般資料及病程等情況對比差異無統(tǒng)計學(xué)意義(P>0.05)。取得醫(yī)院倫理委員會的批準(zhǔn)和患者同意。
1.2 納入與排除標(biāo)準(zhǔn) 納入標(biāo)準(zhǔn) ①年齡18~65歲,根據(jù)ILAE(1989)診斷標(biāo)準(zhǔn)確診為原發(fā)性癲癇(各種類型)。②就診前3個月癲癇發(fā)作頻次≥3次。③規(guī)范化腦電圖結(jié)果顯示有發(fā)作狀癲癇放電行為。④核磁共振結(jié)果顯示無腦部結(jié)構(gòu)性病變。⑤患者心、肺、肝、腎功能及血液系統(tǒng)無明顯疾病。⑥患者知情同意。排除標(biāo)準(zhǔn):①并發(fā)心、腦血管、肝、腎和血液系統(tǒng)等較重疾病。 ②并發(fā)有其他腦部病變。③有精神病史,或妊娠及哺乳期患者。
1.3 治療方法 對照組:采用丙戊酸鈉口服治療。丙戊酸鈉(商品名稱:丙戊酸鈉片,規(guī)格:0.2g×100片,批準(zhǔn)文號:國藥準(zhǔn)字H19983059,生產(chǎn)企業(yè):山東仁和堂藥業(yè)有限公司)口服,開始劑量每日10~20mg/kg,視患者適應(yīng)情況酌量加,每日劑量不超過1000mg。觀察組: 采用丙戊酸鈉聯(lián)合拉莫三嗪用藥,丙戊酸鈉用量與單藥組一致,拉莫三嗪(商品名稱:拉莫三嗪分散片(立雅),規(guī)格:50mg×56片,批準(zhǔn)文號:H20110590,生產(chǎn)企業(yè):Actavis hf.(冰島))。初始劑量25mg,二周加到50mg,加至維持劑量100~200mg/d。兩組均治療6個月。
1.4 療效指標(biāo) ①觀察兩組患者腦電圖(electroencephalogram,EEG)情況,包括好轉(zhuǎn)時間及癲癇放電例數(shù)情況。②觀察兩組患者3個月內(nèi)和6個月內(nèi)發(fā)作次數(shù)。③6個月時填寫SES自尊量表[7],記錄得分情況,得分越高患者心理自尊狀況越好。④計算臨床療效總有效率:控制:治療后臨床癥狀變輕,各種類型癲癇發(fā)作次數(shù)降低≥95% ;有效:治療后臨床癥狀消減,發(fā)作次數(shù)降低≥50%;無效:患治療后臨床癥狀無變化,發(fā)作次數(shù)降低≤50% 。⑤外周血TNF-α、IFN- γ、IL-2、IL-10、IL-4、IL-6、 IL-17A、IL-23、IL-1β:空腹?fàn)顟B(tài)下采集靜脈血液,用ELISA法測量治療前和治療6個月時兩組患者的外周血TNF-α、IFN- γ、IL-2、IL-10、IL-4、IL-6、 IL-17A、IL-23、IL-1β水平。⑥記錄兩組患者不良反應(yīng)出現(xiàn)的狀況,如食欲減退、頭昏嗜睡、惡心反胃及出現(xiàn)皮疹[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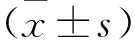
2 結(jié)果
2.1 兩組患者腦電圖結(jié)果比較 觀察組患者治療后EEG 好轉(zhuǎn)的時間與對照組比較差異有統(tǒng)計學(xué)意義(P<0.05);觀察組放電消失比例與對照組比較,差異有統(tǒng)計學(xué)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兩組患者腦電圖結(jié)果對比 Table 1 Comparison of EEG results in the two groups
注:與對照組比較,①P<0.05
2.2 兩組患者發(fā)作次數(shù)及自尊量表SES得分比較 兩組患者在治療之前發(fā)作頻次無顯著差異(P>0.05),治療后發(fā)作次數(shù)均有下降,其中三個月發(fā)作頻次觀察組顯著低于對照組(P<0.05),6個月平均發(fā)作頻次觀察組顯著低于對照組(P<0.05);SES分?jǐn)?shù)觀察組顯著高于對照組(P<0.05),說明觀察組心理自尊情況好于對照組,見表2。
2.3 兩組患者外周血TNF-α、IL-2IFN-γ、IL-10、IL-4、IL-b、IL-17A、IL-23、IL-1β水平比較 兩組患者治療6個月后 TNF-α、IFN- γ、IL-2、IL-6、 IL-17A水平均比治療前均顯著降低(P均<0.05);而且觀察組的 TNF-α、IFN- γ、IL-2、IL-6、 IL-17A水平顯著低于對照組(P均<0.05),但兩組IL-10、IL-4、IL-23和IL-1β治療前后無顯著差異(P均>0.05),見表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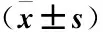
表2 兩組患者發(fā)作頻次及SES 得分 Table 2 Relapse frequency and SES score in the two group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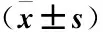
表3 兩組患者TNF-α、IFN- γ、IL-2、IL-10、IL-4、IL-6、 IL-17A、IL-23、IL-1β水平對比 Table 3 Comparison of TNF-α, IFN- γ, IL-2, IL-10, IL-4, IL-6, IL-17A, IL-23 and IL-1βlevels

組別n時間IL-6(pg/mL)IL-17A(pg/mL)IL-23(pg/mL)IL-1β(pg/mL)觀察組75治療前519.73±36.555.32±1.784.63±1.89127.53±19.56治療后428.74±19.35①②1.42±1.08①②4.17±1.57120.87±18.84對照組75治療前537.73±28.875.86±1.554.89±1.78134.38±20.49治療后478.24±21.622.78±1.544.35±1.69118.74±19.48
注:與治療前相比較,①P<0.05;與對照組比較,②P<0.05
2.4 兩組患者治療療效比較 兩組患者在治療后,觀察組癥狀得到控制的比例明顯高于對照組(P<0.05),有效率兩組差異無統(tǒng)計學(xué)意義(P>0.05),無效率觀察組顯著低于對照組(P<0.05),總有效率方面,觀察組明顯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tǒng)計學(xué)意義(P<0.05),見表4。
2.5 兩組患者不良反應(yīng)率比較 觀察組不良反應(yīng)顯著低于對照組(P<0.05),故聯(lián)合用藥不良反應(yīng)小于單用丙戊酸鈉,見表5。

表4 臨床有效率對比[n(×10-2 )] Table 4 Comparison of clinical efficiency
注:與對照組比較,①P<0.05;與對照組比較,②P>0.05

表5 不良反應(yīng)出現(xiàn)率對比[n(×10-2 )] Table 5 Comparison of adverse reaction rate
注:與對照組比較,①P<0.05
3 討論
癲癇是大腦神經(jīng)細(xì)胞突然發(fā)生不正常放電而導(dǎo)致的短期大腦功能紊亂[10]。按病因分原發(fā)性和繼發(fā)性兩種,除遺傳因素外無明顯病因的稱為原發(fā)性癲癇[11]。如不及時救治會導(dǎo)致腦部神經(jīng)細(xì)胞突觸鏈接因異常放電造成的器質(zhì)性改變,影響患者的運動、意識、認(rèn)知甚至記憶能力,嚴(yán)重?fù)p害患者的生理和心理健康[12-13]。癲癇及時治療后,大多數(shù)的患者病情能夠得到長期有效的控制,但仍有少數(shù)患者療效不理想,飽受疾病癥狀的困擾。臨床上治療癲癇方式多樣,首選方式為藥物治療。為避免藥物相互作用兼顧經(jīng)濟(jì)性和安全性,臨床醫(yī)學(xué)上多將單一藥物作為治療癲癇的主要手段,但由于某些患者使用單一藥物病情無法得到有效控制,因此聯(lián)合使用藥物成為一種日益受到重視的方案[14-15]。
丙戊酸鈉作為治療癲癇的常用藥,通過抑制γ-氨基丁酸轉(zhuǎn)氨酶等的活性,提高此類氨基酸的濃度起到阻遏Na+、Ca2+流入細(xì)胞膜的作用,從而抑制神經(jīng)突觸的異常放電以達(dá)到治療的目標(biāo)。其療效明確,價格便宜,不良反應(yīng)較少,被廣泛運用于抗癲癇治療。拉莫三嗪是一種Na+離子通道阻遏劑,同時抑制谷氨酸的釋放,是一種新批準(zhǔn)臨床應(yīng)用的抗癲癇藥物,主要在人體肝臟中通過糖苷化后進(jìn)行一系列的代謝[16-17]。丙戊酸鈉一方面是高效的糖苷化酶抑制物,通過與拉莫三嗪競爭結(jié)合葡糖醛酸的方式阻滯其肝臟代謝,延長其半衰期;另一方面丙戊酸鈉有著90%左右的血漿蛋白絡(luò)合率,能夠阻滯拉莫三嗪與血清蛋白的絡(luò)合,提高其血液游離態(tài)濃度[18]。因此從藥理學(xué)和藥物動力學(xué)角度兩者的聯(lián)合用藥時沒有藥物相互沖突,而且會提高血液中的有效濃度,縮短藥效發(fā)揮時間,可快速抑制腦神經(jīng)非正常放電,具有更高效的抗癲癇的作用。在本研究中,觀察組患者治療后EEG好轉(zhuǎn)用時顯著早于對照組。觀察組放電消失比例明顯高于對照組;觀察組3個月時和6個月時平均發(fā)作頻次顯著低于對照組同時SES自尊得分觀察組明顯高于對照組;而且觀察組的療效總有效率顯著高于對照組,不良反應(yīng)出現(xiàn)明顯低于對照組。提示聯(lián)合使用丙戊酸鈉和拉莫三嗪,兩者的藥效發(fā)生協(xié)同作用;同時拉莫三嗪采用逐漸加量的方式給藥,當(dāng)血液藥物濃度提高時,通過監(jiān)測病人的臨床反應(yīng)而減少藥物使用量,有效減少了攝取藥物量,從而減小了患者對藥物發(fā)生不良反應(yīng)的機(jī)率。
細(xì)胞因子TNF-α、IFN- γ、IL-2、IL-10、IL-4、IL-6、 IL-17A、IL-23、IL-1β被認(rèn)為與癲癇的發(fā)病密切相關(guān)。其中TNF-α一方面是巨噬細(xì)胞產(chǎn)生的炎癥指標(biāo)因子,其水平高低反映炎癥的程度,另一方面能夠興奮神經(jīng)細(xì)胞和損傷血腦屏障,誘發(fā)癲癇發(fā)生,并使炎癥因子進(jìn)入神經(jīng)系統(tǒng),加劇炎癥和癲癇的發(fā)生[19]。IFN- γ具有促進(jìn)血管內(nèi)皮細(xì)胞HLA-DR抗原表達(dá)的作用,通過免疫介導(dǎo)的病理過程導(dǎo)致血腦屏障的損傷,進(jìn)而影響到腦部神經(jīng)元,使其更容易受到興奮因子的影響。研究發(fā)在IFN- γ缺失的實驗大鼠致癲癇實驗中,其具有更低的易感性,同時癲癇癥狀明顯減輕。提示治療后IFN- γ高表達(dá)預(yù)后療效較差[20]。IL-2是一種Th1細(xì)胞合成分泌的糖蛋白,在機(jī)體免疫調(diào)節(jié)中起作用,同時也是一種神經(jīng)遞質(zhì)類似物,能夠提高神經(jīng)元內(nèi)Ca2+濃度,興奮神經(jīng)元,誘發(fā)癲癇[21]。IL-10、 IL-4均由Th2細(xì)胞分泌,其作為細(xì)胞因子合成抑制因子,可以抑制促炎介質(zhì)的合成,可能對癲癇的發(fā)作有抑制作用[22]。IL-6作為中樞神經(jīng)系統(tǒng)免疫反應(yīng)因子,在癲癇發(fā)作初期會急劇升高,在發(fā)作間隙也普遍高于正常人[23]。現(xiàn)在還沒有直接證據(jù)證明IL-17A參與癲癇的發(fā)作,但是其與多種變性及免疫反應(yīng)相關(guān),IL-23則與IL-17A協(xié)同作用[24]。IL-1β在神經(jīng)系統(tǒng)疾病中均有不同程度升高,其明顯促進(jìn)腦損傷的病情加重,其通過抑制CABA通路,阻遏抑制性遞質(zhì)發(fā)揮作用,促進(jìn)疾病進(jìn)展[25]。在本研究中,兩組患者治療6個月后 TNF-α、IFN- γ、IL-2、IL-6、 IL-17A水平均比治療前顯著降低,而觀察組的 TNF-α、IFN- γ、IL-2、IL-6、 IL-17A水平顯著低于對照組,但兩組IL-10、IL-4、IL-23和IL-1β治療前后無顯著差異,其原因可能是經(jīng)過治療后,由此導(dǎo)致的對神經(jīng)、血管、肝腎等的損害降低,炎癥反應(yīng)得到抑制,免疫系統(tǒng)過激狀態(tài)得到改善,提示丙戊酸鈉和拉莫三嗪聯(lián)合使用能夠更好地降低 TNF-α、IFN- γ、IL-2、IL-6、 IL-17A水平。
4 結(jié)論
本文資料顯示,丙戊酸鈉和拉莫三嗪聯(lián)合使用治療原發(fā)性癲癇能夠更好的降低患者血清TNF-α、IL-2水平,改善患者的腦部異常放電情況,對癲癇的臨床療效良好,不良反應(yīng)少,可在臨床推廣應(yīng)用。
【參考文獻(xiàn)】
[1]秦曉云, 竇長武, 張占普,等. 動態(tài)腦電圖監(jiān)測癲癇患者的臨床意義[J]. 西部醫(yī)學(xué), 2016, 28(3):358-360.
[2]周東, 鄢波. 早期識別和手術(shù)治療促進(jìn)顳葉內(nèi)側(cè)癲癇預(yù)后[J]. 西部醫(yī)學(xué), 2015, 27(6):801-801.
[3]Schulz J, Beicher A, Mayer G,etal. Counseling and social work for persons with epilepsy: observational study on demand and issues in Hessen, Germany[J]. Epilepsy & Behavior E & B, 2013, 28(3):358-362.
[4]譚啟富, 陳謙學(xué). 積極穩(wěn)妥地開展癲癇的外科治療[J]. 臨床外科雜志, 2015(6):410-411.
[5]江志, 楊理明, 寧澤淑,等. 丙戊酸鈉單藥治療新診斷兒童全面性癲癇失敗原因分析[J]. 中國神經(jīng)精神疾病雜志, 2016, 42(8):560-563.
[6]張華. 拉莫三嗪聯(lián)合丙戊酸鈉治療難治性癲癇部分性發(fā)作的臨床研究[J]. 中國臨床藥理學(xué)雜志, 2016, 32(12):1085-1087.
[7]周玉珍, 李留芝. 基于跨理論模型干預(yù)對癲癇患兒自尊水平的影響[J]. 中國實用護(hù)理雜志, 2016, 32(17):1310-1314..
[8]Jang H W, Kim S W, Cho Y J,etal. GWAS identifies two susceptibility loci for lamotrigine-induced skin rash in patients with epilepsy[J]. Epilepsy Research, 2015, 115:88-94.
[9]Na H E, Min F L, Shi Y W,etal. Clinical features and risk predictors of skin rashes induced by carbamazepine and lamotrigine[J]. Journal of Practical Medicine, 2016,32(22):3760-3764.
[10] 汪珊, 丁瑤, Zhong Irene Wang,等. 單光子發(fā)射計算機(jī)斷層成像術(shù)減影成像和磁共振融合技術(shù)用于癲癇致癇灶定位的研究進(jìn)展[J]. 中華神經(jīng)科雜志, 2014, 47(4):263-265.
[11] 王婧婧, 趙衛(wèi), 孫學(xué)進(jìn). 原發(fā)性癲癇的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進(jìn)展[J]. 中國醫(yī)學(xué)影像學(xué)雜志, 2016, 24(9):714-716.
[12] 王偉秀, 陳霞, 李榮品,等. 癲癇患兒海馬急性損傷的MRI表現(xiàn)[J]. 中國醫(yī)學(xué)影像學(xué)雜志, 2015, 23(8):573-577.
[13] 陳彤, 郭亮. MR功能成像在癲癇認(rèn)知功能方面的應(yīng)用進(jìn)展[J]. 磁共振成像, 2015(7):540-543.
[14] 賈妮. 拉莫三嗪聯(lián)合丙戊酸鈉治療小兒癲癇的臨床研究[J]. 中國臨床藥理學(xué)雜志, 2016, 32(14):1293-1295.
[15] 張華. 拉莫三嗪聯(lián)合丙戊酸鈉治療難治性癲癇部分性發(fā)作的臨床研究[J]. 中國臨床藥理學(xué)雜志, 2016, 32(12):1085-1087.
[16] 史道華, 鄧婕, 連秋燕. 血漿蛋白含量與丙戊酸游離藥物濃度的相關(guān)性[J]. 中國臨床藥理學(xué)雜志, 2014, 30(3):188-189.
[17] 尚德為, 溫預(yù)關(guān), 王占璋. 拉莫三嗪個體化給藥臨床藥師指引[J]. 今日藥學(xué), 2016(4):217-224.
[18] 鄭冰, 魏曉霞, 張明芳. 丙戊酸鈉的血藥濃度監(jiān)測和合理用藥探討[J]. 海峽藥學(xué), 2015, 27(11):252-254.
[19] Saghazadeh A, Gharedaghi M, Meysamie A,etal. Proinflammatory and anti-inflammatory cytokines in febrile seizures and epilepsy: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Reviews in the Neurosciences, 2014, 25(2):281.
[20] Saghazadeh A, Gharedaghi M, Meysamie A,etal. febrile seizure, epilepsy[J]. Reviews in the Neurosciences, 2014, 25(2):281-305.
[21] de Vries E E, Van d M B, Braun K P,etal. Inflammatory mediators in human epilepsy: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 2016, 63:177-190.
[22] Godukhin O V, Levin S G, Parnyshkova E Y. The effects of interleukin-10 on the development of epileptiform activity in the hippocampus induced by transient hypoxia, bicuculline, and electrical kindling[J]. Neuroscience & Behavioral Physiology, 2009, 39(7):625-631.
[23] Hulkkonen J, Koskikallio E, Rainesalo S,etal. The balance of inhibitory and excitatory cytokines is differently regulated in vivo and in vitro among therapy resistant epilepsy patients[J].Epilepsy Res, 2004, 59 (2-3):199-205
[24] Nakae S, Nambu A, Sudo K,etal. Suppression of immune induction of collagen-induced arthritis in IL-17-deficient mice[J].J Immunol, 2003, 171(11):6173-6177.
[25] Hu S, Sheng W S, Ehrlich L C,etal. Cytokine effects on glutamate uptake by human astrocytes[J]. Neuroimmunomodulation, 2000, 7 (3):153-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