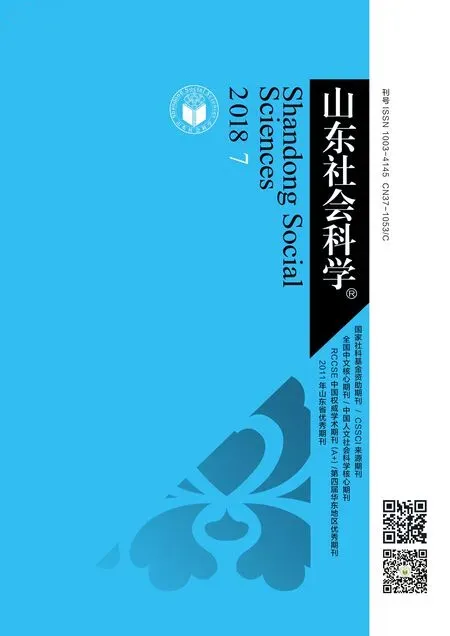社會(huì)變遷中的婚姻制度
——基于1950—1954年新會(huì)司法檔案的研究
梁文生
(電子科技大學(xué)中山學(xué)院,廣東 中山 528402)
一、導(dǎo)言
婚姻制度是重要的社會(huì)制度,其變化與社會(huì)變遷息息相關(guān)。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頒布第一部法律《婚姻法》*此處所說(shuō)的法律是指狹義上的法律,即以“法”命名的規(guī)范,解放初期存在大量行政法規(guī)和規(guī)范性文件。,此后,婚姻家庭發(fā)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實(shí)乃中國(guó)歷史上鮮見(jiàn)。這不僅僅是制度的改變,而且將人們從陳舊婚姻觀念的桎梏中解放出來(lái),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等原則無(wú)形中改變了中國(guó)傳統(tǒng)社會(huì)結(jié)構(gòu)。本文著重分析解放初期婚姻司法案件的特征和類(lèi)型,整體考察婚姻制度在社會(huì)轉(zhuǎn)型期的變化原因。
關(guān)于中國(guó)解放初期婚姻制度的轉(zhuǎn)型,目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此領(lǐng)域早期研究成果要數(shù)楊慶堃(C.K.Yang)的《中國(guó)的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家庭和鄉(xiāng)村》*C.K.Yang. Chinese Communist Society:The Family and The Village.The M.I.T Press,1965.,它研究中國(guó)解放初期婚姻家庭和鄉(xiāng)村狀況的變化,材料主要源自報(bào)刊,更多著墨于解放前婚姻家庭制度的介紹和分析,并進(jìn)行理論解釋。此書(shū)為后來(lái)者提供了一個(gè)較為完整的理論框架。2000年美國(guó)學(xué)者迪亞蒙特(NeilJ.Diamant)以《家庭革命:1949—1968年中國(guó)城鄉(xiāng)政治、情愛(ài)和離婚》延續(xù)此領(lǐng)域研究*Neil J.Diamant. Revolutionizing the Family: politics, love, and divorce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 1949-1968.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該書(shū)以北京、上海和云南三地民政局有關(guān)解放初期的離婚數(shù)據(jù)為研究對(duì)象而進(jìn)行分析,填補(bǔ)了運(yùn)用定量方法研究中國(guó)解放初期婚姻家庭制度的空白,然而,書(shū)中數(shù)據(jù)的完備性值得懷疑,不無(wú)以偏概全之嫌。
國(guó)內(nèi)對(duì)此問(wèn)題的研究,除了報(bào)紙報(bào)道和教科書(shū)介紹之外,諸多研究把重點(diǎn)放在1950年《婚姻法》的宣傳和實(shí)施方面,材料更多的是報(bào)道、文件、政策等文獻(xiàn)。*如周由強(qiáng):《當(dāng)代中國(guó)婚姻法治的變遷(1949—2003)》,中共中央黨校博士論文,2004年;葛世濤:《新婚姻法與建國(guó)初期婦女婚姻家庭研究》,廣西師范大學(xué)碩士論文,2006年;郭俊:《建國(guó)初期貫徹婚姻法運(yùn)動(dòng)研究》山東輕工業(yè)學(xué)院碩士論文,2012年;王群:《建國(guó)初期山東省宣傳貫徹婚姻法研究》,山東師范大學(xué)碩士論文,2014年;閆麗云:《變革中的沖突與較量——20世紀(jì)50年代陜西婚姻制度改革研究》,西北大學(xué)碩士論文,2015年;韓軍強(qiáng):《婚姻法與建國(guó)初期婚姻制度改革研究——以四川省為中心的探討(1950—1956)》,四川師范大學(xué)碩士論文,2009年;唐曉敏:《從〈人民日?qǐng)?bào)〉的宣傳報(bào)道看〈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婚姻法〉的宣傳和貫徹(1950—1953)》,湘潭大學(xué)碩士論文,2014年等等,不一而足。而采取實(shí)證材料特別是司法檔案進(jìn)行研究的,有朱穎的《解放初期的婚姻訴訟研究——以永修縣人民法院的判決為例》(江西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碩士論文,2010年)、《法律、民意、政策:建國(guó)初期婚姻訴訟審判的依據(jù)——以江西省永修縣人民法院的判決為例》(《南昌航空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1年第1期),王雅丹的《建國(guó)初期郎岱縣婚姻制度變革——以當(dāng)?shù)鼗橐雠袥Q書(shū)為例(1950—1957年)》(貴州民族大學(xué)碩士論文,2016年)。這些利用司法檔案的研究側(cè)重對(duì)部分裁判文書(shū)的分析,從而提出實(shí)體法和程序法的問(wèn)題,但是法院的司法檔案是否完備,整體上對(duì)社會(huì)變遷有何影響,其研究可謂付之闕如,最大原因可能在于搜集史料困難。本研究以廣東省新會(huì)縣人民法院1950—1954年的婚姻案件為對(duì)象,從史料來(lái)說(shuō)無(wú)意將研究擴(kuò)大至全國(guó)范圍,也無(wú)意把結(jié)果說(shuō)成具有普適性。因此,解放初期新會(huì)縣的地方經(jīng)驗(yàn),在全國(guó)而言只是冰山一角,未足窺全貌。
新會(huì)是廣東歷史文化名城(現(xiàn)為江門(mén)市一個(gè)轄區(qū)),地處中國(guó)南部沿岸,珠江三角洲中西部。新會(huì)因宋元崖門(mén)海戰(zhàn)而載入史冊(cè),更因是陳白沙和梁?jiǎn)⒊实囟劽谑馈U驗(yàn)樾聲?huì)縣并非默默無(wú)聞之地,稱(chēng)其為華南地區(qū)的代表也不為過(guò),所以本文研究新會(huì)法院的司法檔案,也是一個(gè)恰當(dāng)選擇。新會(huì)法院保存大量民國(guó)時(shí)期司法檔案,以及自解放以來(lái)完整的民事司法檔案。本文僅擷取1950—1954年婚姻糾紛司法檔案為研究對(duì)象,其余時(shí)間段的相關(guān)檔案以資參考。同時(shí),主要運(yùn)用定量分析方法進(jìn)行案例研究。有關(guān)解放初期司法檔案的研究實(shí)屬不多,本文可取之處首要在于材料的新穎性。
關(guān)于制度變遷的理論,可以概分為和諧學(xué)派和沖突學(xué)派兩大陣營(yíng)。和諧學(xué)派認(rèn)為制度自長(zhǎng)自發(fā)地向好的方面發(fā)展,而沖突學(xué)派則認(rèn)為社會(huì)沖突才促使制度變遷,并且可能得出壞制度。然而無(wú)論如何,政治和權(quán)力在制度變遷中起著重要作用*唐世平:《制度變遷的廣義理論》,沈文松譯,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6年版,第60-67頁(yè)。。1949年,中國(guó)新舊政權(quán)過(guò)渡涉及社會(huì)制度變遷。司法機(jī)構(gòu)采取“舊瓶裝新酒”的改造,保留原有“設(shè)備”和“組織”兩塊物質(zhì)形體,宣布取消舊“規(guī)范”和“象征設(shè)備”,再注入符合新政權(quán)意識(shí)形態(tài)的新規(guī)范。*[美]費(fèi)正清:《偉大的中國(guó)革命:1800—1985》,劉尊棋譯,世界知識(shí)出版社2000年版,第330頁(yè)。國(guó)家制定新法律,設(shè)立新制度,并運(yùn)用權(quán)力迅速推行制度轉(zhuǎn)型。1950年《婚姻法》制定的婚姻制度,正是社會(huì)急劇變遷時(shí)期制度轉(zhuǎn)型的樣本。新舊制度轉(zhuǎn)型之際,涌現(xiàn)大量婚姻糾紛,該法規(guī)定行政離婚和訴訟離婚兩種方式。1951—1985年新會(huì)行政離婚才406對(duì),812人*新會(huì)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huì)編:《新會(huì)縣志》,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8頁(yè)。。其時(shí),新會(huì)縣人口約50萬(wàn),行政離婚人數(shù)不多,訴訟離婚才是主要途徑,這正是本文研究的對(duì)象。
二、婚姻制度轉(zhuǎn)型的社會(huì)表征
(一)解放前后婚姻案件數(shù)量的變化
以1950—1954年新會(huì)法院婚姻案件為研究對(duì)象,原因是這五年頗能突出體現(xiàn)制度轉(zhuǎn)型的過(guò)程和特點(diǎn)。但是,此期間與前后時(shí)間具有連續(xù)性,并且社會(huì)發(fā)展有前因后果的關(guān)系,因此,本文將新會(huì)法院民國(guó)時(shí)期和1955—1959年的婚姻糾紛判例作為參照數(shù)據(jù)。*民國(guó)司法檔案現(xiàn)已由新會(huì)區(qū)人民法院移交檔案局保管,解放初期司法檔案仍然存放在法院檔案室。本文所說(shuō)的婚姻案件與離婚案件有緊密聯(lián)系又略有區(qū)別。離婚案件包括離婚、脫離夫妾關(guān)系、脫離同居關(guān)系、解除婚約等解除婚姻關(guān)系的民事案件,以及通奸、籍婚騙財(cái)、重婚、虐待、破壞家庭等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譬如通奸案件,在對(duì)通奸行為進(jìn)行刑事處理同時(shí),也對(duì)婚姻關(guān)系作出處理。而婚姻案件除了包括離婚案件外,還有圍繞婚姻主題產(chǎn)生的請(qǐng)求結(jié)婚、確認(rèn)婚姻關(guān)系等案。因此,婚姻案件數(shù)量略高于離婚案件,但兩者互用也不會(huì)產(chǎn)生重大誤差。
楊慶堃指出,直至1950年施行《婚姻法》,中國(guó)的婚姻家庭制度才發(fā)生根本變化*C.K.Yang.The Chinese Family i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in Chinese Communist Society:The Family and The Village,The M.I.T Press,1965,p.18.。這一重大變化的指標(biāo)之一就是離婚率。盡管離婚數(shù)據(jù)是一堆冷冰冰的數(shù)字,但往往能夠說(shuō)明問(wèn)題。為了考察1950年《婚姻法》的社會(huì)影響,先來(lái)比較新會(huì)縣解放前后離婚率的變化(見(jiàn)表1)*新會(huì)縣民國(guó)時(shí)期的離婚數(shù)據(jù),根據(jù)現(xiàn)存民國(guó)檔案目錄整理而成。1950—1959年離婚案件數(shù)據(jù),參見(jiàn)新會(huì)縣法院志編纂委員會(huì):《新會(huì)縣法院志(2012)》,內(nèi)部刊物,2013年版,第295-296頁(yè)。。
從表1可見(jiàn),中華民國(guó)時(shí)期新會(huì)縣婚姻案件極少,離婚案件更是屈指可數(shù)。1937年到1945年,新會(huì)縣地方法院每年審理的民事案件少則數(shù)十宗,多則273宗。其中,離婚案件數(shù)分布在0—3范圍內(nèi),1941年、1942年和1944年甚至沒(méi)有離婚案件。1937年到1945年恰好是抗日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百姓遭逢離亂,自無(wú)暇顧及

表1 新會(huì)法院歷年婚姻案件數(shù)據(jù)表
家務(wù)事,另外法院機(jī)構(gòu)的運(yùn)作也受到影響,因此這段時(shí)間民事案件較少。1946—1949年,抗日戰(zhàn)爭(zhēng)勝利,國(guó)民黨政權(quán)管治步入正軌,百姓生活逐步穩(wěn)定,這時(shí)期民事案件總數(shù)陡然猛升。1946—1948年分別為661、745、570宗。1949年因?yàn)閲?guó)內(nèi)解放戰(zhàn)爭(zhēng)的爆發(fā),所以民事案件總數(shù)降為231宗。從民事總數(shù)來(lái)看,這個(gè)時(shí)期民事案件總量較多,甚至比解放后的案件數(shù)量還要多。然而,其中的離婚案件仍然維持在低水平。綜觀中華民國(guó)時(shí)期,不管民事案件總量如何變化,離婚案件數(shù)量一直很低,甚至好幾年的數(shù)字為零,比率最高為6.38%。
相比之下,解放初期新會(huì)縣離婚案件數(shù)量卻大幅攀升。1950—1959年的民事案件總數(shù)量分布在146—738之間,與1946—1949年分布在231—745之間的情形相近。也就是說(shuō),新會(huì)縣民事案件總量在解放前后變化不大。但是,離婚案件數(shù)量變化很大。1950年新會(huì)縣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95宗,1951年115宗,1952年已升到405宗,1953年達(dá)到頂峰558宗。此后幾年均維持在147—333宗之間,占民事案件總數(shù)的比率保持在70%—90%。1950年離婚案件數(shù)較少,原因在于新會(huì)縣人民法院于1950年5月才成立,受理案件的時(shí)間較短。另外,1950年5月《婚姻法》才實(shí)施。其后三年,離婚案件節(jié)節(jié)攀升,1953年數(shù)量達(dá)到最高。這可以理解為事物發(fā)展需要一個(gè)緩沖過(guò)程,普羅大眾逐漸接受《婚姻法》的理念,并知道國(guó)家通過(guò)司法制度保障離婚的順利進(jìn)行,從而導(dǎo)致離婚訴訟激增。另一個(gè)重要原因,1950—1952年中國(guó)政府忙于應(yīng)付朝鮮戰(zhàn)爭(zhēng)事務(wù),無(wú)暇顧及《婚姻法》的宣傳。1953年政府大力宣傳《婚姻法》,開(kāi)展貫徹婚姻法運(yùn)動(dòng)月活動(dòng),深入到農(nóng)村基層*張成潔、莫宏偉:《新中國(guó)第一部〈婚姻法〉宣傳與貫徹運(yùn)動(dòng)述論》,《河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 2008 年第1期。。因此,新會(huì)縣離婚案件在1953年達(dá)到最高峰,可能是宣傳效應(yīng)的結(jié)果。1954—1959年民事案件總量下降,是因?yàn)樨?cái)產(chǎn)型的糾紛減少,但由于離婚案件保持穩(wěn)定態(tài)勢(shì),比率也就越來(lái)越高。從離婚案件總體而言,除了1950年和1951年的離婚數(shù)量占民事案件總數(shù)的22.51%和34.64%之外,1952—1959年比率達(dá)61.21%—94.23%。
新會(huì)的離婚案件數(shù)量在解放前后形成一個(gè)明顯分水嶺。解放前后,新會(huì)法院的民事案件總量變化不大,但是離婚案件數(shù)量變化卻有天淵之別。唯一解釋是新政權(quán)推行新婚姻法的結(jié)果。1950年婚姻法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解放思想,并且從制度安排上,使廣大民眾能夠順利解決婚姻糾紛。解放前的社會(huì)為何壓制離婚?新社會(huì)又通過(guò)怎樣的機(jī)制改變舊婚姻家庭制度?下文接著分析。
(二)從城市到鄉(xiāng)村
中國(guó)幅員遼闊,農(nóng)村土地及人口是其葷葷之大者,費(fèi)孝通稱(chēng)之為“鄉(xiāng)土中國(guó)”。新會(huì)縣鄉(xiāng)土特性突出,農(nóng)村的土地和人口占據(jù)重要地位,而且傳統(tǒng)觀念在農(nóng)村民眾中根深蒂固。另外,華南地區(qū)宗族組織較強(qiáng),自然村實(shí)際上是一個(gè)以血統(tǒng)關(guān)系為紐帶而組成的家族,居民相互之間有著或親或疏的血緣關(guān)系。這種“單個(gè)宗族社區(qū)”模式,在東南地區(qū)大規(guī)模存在*[美]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國(guó)東南的宗族組織》,劉曉春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頁(yè)。。新會(huì)縣的情形亦復(fù)如是。要改變中國(guó)現(xiàn)狀,必須改變農(nóng)村基本形態(tài),要改變農(nóng)村基本形態(tài),則要改變強(qiáng)大的宗族家庭結(jié)構(gòu)。
在城市和鄉(xiāng)村貫徹落實(shí)婚姻法,所遇到的困難程度不同。城市人口受到較好的教育,信息流通快速,容易接受新觀念和新制度,因此,婚姻法能夠在城市迅速展開(kāi)。相反,農(nóng)村人口受教育程度低,信息不暢,傳統(tǒng)觀念牢固,接受新婚姻觀念和制度相對(duì)緩慢,甚至產(chǎn)生對(duì)抗情緒和行為。其實(shí),中華民國(guó)的婚姻法也提倡一夫一妻、婚姻自由原則,但是除了城市上層階層接受之外*C.K.Yang.The Chinese Family i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in Chinese Communist Society:The Family and The Village,The M.I.T Press,1965,p.29-31.,未能得到切實(shí)執(zhí)行。直到解放前夕,中國(guó)社會(huì)主要存在三種婚姻形態(tài):一是在全國(guó)城鄉(xiāng)特別是農(nóng)村占絕對(duì)主導(dǎo)地位,以強(qiáng)迫包辦、男尊女卑為主要特征的封建婚姻制度。這是新婚姻法堅(jiān)決摧毀的婚姻模式。二是主要分布在城鎮(zhèn)的形式上提倡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的改良婚姻制度,即中華民國(guó)婚姻法取得的成果。三是各解放區(qū)實(shí)行的、倡導(dǎo)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的新民主主義婚姻制度。這是解放初期要向全國(guó)推廣和深化的婚姻模式。*王思梅:《新中國(guó)第一部〈婚姻法〉的頒布與實(shí)施》,《黨的文獻(xiàn)》2010年第3期。
新會(huì)縣內(nèi)稱(chēng)得上城市的唯有縣城,余下者是星羅棋布的村落,諸多村落聚集處形成墟鎮(zhèn)。因此,要促使新會(huì)縣婚姻家庭發(fā)生重大轉(zhuǎn)變,必須將婚姻法深入農(nóng)村,改變農(nóng)村的家庭結(jié)構(gòu),特別是削弱宗族力量。當(dāng)然,新會(huì)是著名僑鄉(xiāng),外出人口較多。諸多農(nóng)民出身的人口當(dāng)中,不僅華僑眾多,而且遍布各地城市從事各行各業(yè)者甚眾。這些城市聚居者,與農(nóng)村有割不斷的聯(lián)系,成為城鄉(xiāng)合一的人口。為此,判斷離婚當(dāng)事人屬于城市或農(nóng)村,筆者劃分為三類(lèi):一是當(dāng)事人完全是城市居民,被歸入城市類(lèi)型;二是當(dāng)事人一人或兩人屬于城鄉(xiāng)合一人口,或一方是城市居民,另一方是農(nóng)村人員,被歸入城鄉(xiāng)類(lèi)型;三是當(dāng)事人均為農(nóng)村人員,被歸類(lèi)為農(nóng)村類(lèi)型。以此劃分標(biāo)準(zhǔn)標(biāo)示離婚案件的地域歸屬,得出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見(jiàn)表2)。*表2中總計(jì)數(shù)據(jù)略少于表1中的離婚案件數(shù),因少數(shù)案件當(dāng)事人信息不詳而不能作出歸類(lèi),未納入統(tǒng)計(jì),但差距不大,不影響分析結(jié)論。

表2 1950—1954年新會(huì)法院離婚案件地域來(lái)源統(tǒng)計(jì)表
表2數(shù)據(jù)表明,1950年新會(huì)縣人民法院審理的離婚案件中,城市類(lèi)型案件41宗,占了一半;城鄉(xiāng)類(lèi)型和農(nóng)村類(lèi)型相加為42宗,又占一半。1951年的案件分布與1950年相仿,仍然是城市類(lèi)型占半。但是,從1952年開(kāi)始,農(nóng)村類(lèi)型案件占大多數(shù),如果加上城鄉(xiāng)類(lèi)型,約占總數(shù)三分之二。1953年,農(nóng)村類(lèi)型和城鄉(xiāng)類(lèi)型之和,上升至占年總數(shù)的五分之四,至1954年更升到約九成。從1950—1954年案件地域類(lèi)型的變化,可以看出城市類(lèi)型案件所占比重越來(lái)越低,而農(nóng)村類(lèi)型案件的比重卻與之相反。
從案件地域來(lái)源看,1950—1954年新會(huì)縣離婚案件呈現(xiàn)出由城市類(lèi)型逐步向農(nóng)村類(lèi)型轉(zhuǎn)移重心的特征。這可以說(shuō)明婚姻案件在解放初期突增的原因。因?yàn)檗r(nóng)村人口居多,當(dāng)農(nóng)村人員自由離婚時(shí),自然導(dǎo)致離婚案件激增。另一方面,這個(gè)特征也說(shuō)明新婚姻法的執(zhí)行逐步由城市深入農(nóng)村基層,是改變傳統(tǒng)婚姻制度的重要體現(xiàn)。
(三) 解放了的女性
由三綱倫常千年來(lái)塑造的男權(quán)社會(huì),女性處于附屬地位。男性離婚遠(yuǎn)比女性容易。傳統(tǒng)社會(huì)中,男性一紙休書(shū)便可打發(fā)妻子,即使與發(fā)妻不睦,男性可以通過(guò)娶妾方式另結(jié)新歡,而無(wú)須離婚。更深一層而言,男性掌握家庭經(jīng)濟(jì)大權(quán),利用經(jīng)濟(jì)手段控制女性的離婚與否。女性提出離婚訴訟少之又少,除男權(quán)至上的傳統(tǒng)觀念影響之外,還有國(guó)家婚姻制度、司法制度沒(méi)有給予切實(shí)的法治保障等原因,最后是受經(jīng)濟(jì)因素制約。無(wú)怪乎楊慶堃說(shuō),解放前婚姻家庭的穩(wěn)定性,是以廣大婦女犧牲自己為代價(jià)的*C.K.Yang.The Chinese Family i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in Chinese Communist Society:The Family and The Village,The M.I.T Press,1965,p.67.。
1950年婚姻法貫徹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等原則,主要體現(xiàn)在女性地位的提高,讓廣大婦女打破傳統(tǒng)束縛,自由提出離婚訴訟。因此,1950—1954年新會(huì)縣婚姻案件中,原告性別是判斷男女地位轉(zhuǎn)變的重要指標(biāo)。新會(huì)縣人口性別構(gòu)成在民國(guó)至解放初期,女性多于男性,1941年,男性與女性比例為85.94%(以女性100為標(biāo)準(zhǔn)),1949年為79.15%,1959年為87.57%。如此推算,1950—1954年間新會(huì)縣男性人口是女性人口的八成左右*新會(huì)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huì)編:《新會(huì)縣志》,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頁(yè)。。

表3 1950—1954年新會(huì)縣婚姻案件的當(dāng)事人分類(lèi)*表中有些少數(shù)案件是機(jī)關(guān)起訴或處理的,原告既不是女性也不是男性,因此,女性起訴案件和男性起訴案件數(shù)之和并不一定等于案件總數(shù)。
誰(shuí)先提出訴訟是法律意識(shí)的直接體現(xiàn),也是明確自身法律地位的行為。從表3數(shù)據(jù)可見(jiàn),女性原告提起訴訟的案件占婚姻案件絕大比重,1950—1954年共1105宗,占婚姻案件總數(shù)1514的72.99%。與之相對(duì)應(yīng),男性原告的案件整體比率24.31%。女性主動(dòng)起訴的,約占四分之三,遠(yuǎn)超男性起訴的數(shù)量。數(shù)據(jù)說(shuō)明女性不僅提高法律意識(shí),而且通過(guò)實(shí)際法律行為保障自己合法權(quán)益。
當(dāng)然,考察女性地位提高,還需進(jìn)一步研究女性提起婚姻訴訟案件的相關(guān)特點(diǎn)。據(jù)上分析,1950年婚姻法的貫徹落實(shí),經(jīng)歷從城市走向農(nóng)村的發(fā)展進(jìn)程,那么,哪些地域的女性先提起婚姻訴訟?是城市還是農(nóng)村居多?可從表4中的數(shù)據(jù)進(jìn)一步分析。
整體數(shù)據(jù)顯示,絕大部分女性訴訟者來(lái)自農(nóng)村,而不是城市。1950年和1951年,提起婚姻訴訟的女性更多來(lái)自城市,1952—1954年,大量農(nóng)村和城鄉(xiāng)女性紛紛提起婚姻訴訟。這種數(shù)據(jù)變化和上述分析情況相一致。另一方面,來(lái)自農(nóng)村的男性提起訴訟的案件逐年增加,也與農(nóng)村逐漸接受婚姻法的情況相符。

表4 1950—1954年新會(huì)法院婚姻案件中原告地域的分類(lèi)*表中有的案件不能統(tǒng)計(jì)出地域來(lái)源,譬如有的案件是移送其他法院,或者簡(jiǎn)單處理案件而沒(méi)有記錄當(dāng)事人的地域來(lái)源,所以城市、城鄉(xiāng)、農(nóng)村三類(lèi)案件數(shù)之和不一定等于案件總數(shù)。
其次,關(guān)于當(dāng)事人年齡問(wèn)題,數(shù)據(jù)表明,女性原告年齡最多集中在21—30歲,為551人,占女性原告總數(shù)60.5%;其次是31—40歲,為261人,占女性原告總數(shù)28.7%;小于20歲或大于40歲的女性相對(duì)較少(見(jiàn)表5)。前兩個(gè)年齡段人數(shù)相加,相當(dāng)于總數(shù)九成。與之相比,男性原告年齡也多在21—40歲,而41歲以上的男性原告人數(shù)比例則比女性的要高。從男女年齡差別來(lái)看,是可以得到合理解釋的,因?yàn)槟行阅挲g一般比女性的略高。另外,兩者多數(shù)集中在20—40歲之間,原因之一是此年齡段者更容易接受新思想,并且從性情而言,這類(lèi)人尚屬容易激動(dòng)的青年,在婚姻關(guān)系中容易激化矛盾而提起離婚。當(dāng)然,這種解釋是一般原因,實(shí)際婚姻糾紛存在各種各樣原因。
最后,在女性提起婚姻訴訟的案件中,審判結(jié)果更多以離婚為主,判決不離婚的較少。相比之下,在男性提起婚姻訴訟案件中,判決離婚的比女性起訴的案件要低,而判決不離婚則要高。據(jù)統(tǒng)計(jì),第一,女性起訴的案件中,撤訴與和好的案件數(shù)占比12.12%。男性起訴的案件中,撤訴與和好占比15.26%。兩者差別不大。第二,女性起訴案件中,判決離婚和調(diào)解離婚的案件,占女性起訴案件總數(shù)70.86%。而男性起訴案件中,判決離婚和調(diào)解離婚的案件,占62.77%,比女性起訴案件少將近一成。第三,兩者最大區(qū)別點(diǎn)在于判決不離婚方面,女性案件為17宗,占1.54%,而男性案件38宗,占10.33%,后者比率高出近一成。

表5 1950—1954年新會(huì)縣提起婚姻訴訟主體的年齡段
兩者為何有此差別?首先,關(guān)于離婚率的問(wèn)題,男性起訴的婚姻案件類(lèi)型更多是涉及日常生活糾紛,而女性起訴的案件側(cè)重于社會(huì)制度造成的糾紛,因此,女性起訴案件被判離婚的機(jī)率更高。其次,當(dāng)兩性以同樣理由起訴離婚,如果一方不同意離婚,那么男性起訴的案件被判決不離婚的機(jī)率更高。因此,從審判結(jié)果來(lái)看,女性更容易離婚,而男性離婚相對(duì)受到一定限制。這應(yīng)該與傳統(tǒng)社會(huì)中男性占主導(dǎo)地位有關(guān),即使在新政權(quán)建立初期,女性仍然處于弱勢(shì)地位,新婚姻法更側(cè)重于婦女權(quán)益的保護(hù)。這同樣說(shuō)明,解放了的女性社會(huì)地位正逐漸提升,符合“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原則的發(fā)展趨勢(shì)。
三、婚姻糾紛類(lèi)型分析
從1950—1954年新會(huì)法院婚姻案件來(lái)看,產(chǎn)生的原因形形式式,筆者將其劃分三大類(lèi)型:常識(shí)型案件、社會(huì)制度型案件和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型案件。
(一)常識(shí)型
常識(shí)型案件是指根據(jù)普通人常識(shí)來(lái)判斷,可以作出相近結(jié)論的案件類(lèi)型。這種常識(shí)通常不會(huì)因社會(huì)變動(dòng)而發(fā)生重大改變,因此,常識(shí)型案件的處理在不同國(guó)家或不同社會(huì)均有相似之規(guī)定。
最為常見(jiàn)的常識(shí)型案件是因生理缺陷而導(dǎo)致的離婚糾紛。生育是婚姻建立家庭的基本功能之一。男性或女性身體缺陷而喪失生育能力,可導(dǎo)致離婚糾紛。譬如1953年鄭某年訴李某彩離婚一案,兩人1949年結(jié)婚,因女方是石女而離婚。又如1954年李某訴梁某離婚一案,女方李某18歲嫁給梁某之后,發(fā)現(xiàn)梁某染上梅毒喪失性功能而起訴,雙方調(diào)解離婚。另外常見(jiàn)的生理缺陷是弱智、精神病或傳染病。因生理缺陷不能實(shí)現(xiàn)生育功能,所以雙方提起離婚訴訟是合理的常識(shí)。
另外,配偶一方下落不明,或因其他原因而不能共同生活,從而發(fā)生糾紛,是常見(jiàn)的常識(shí)型案件之一。夫妻在共同生活中培養(yǎng)感情,養(yǎng)育子女,如果長(zhǎng)時(shí)期分居,不利家庭組織的正常運(yùn)作。因此,此類(lèi)案件通常做出解除婚姻關(guān)系的處理。這也是大眾認(rèn)知的常識(shí)之一。在研究數(shù)據(jù)中,1951—1954年男性因配偶下落不明提起離婚的,分別有2、10、6、2宗,共20宗。這些一方下落不明的情形大多數(shù)因社會(huì)變動(dòng)而造成。譬如,1952年馮男訴李女離婚一案,雙方均是農(nóng)民,1929年結(jié)婚,曾育一子夭折,1937年抗日戰(zhàn)爭(zhēng)開(kāi)始,因?yàn)樯罾щy,男方當(dāng)兵謀生,女方自動(dòng)離鄉(xiāng)找生活,解放后男方回鄉(xiāng)發(fā)覺(jué)女方下落不明,故而訴請(qǐng)離婚。女性因?qū)Ψ较侣洳幻鞫鹪V離婚的案件,也不在少數(shù),1952年14宗,1953年18宗,1954年11宗。另外,如果以?xún)傻胤志訛橛商崞痣x婚,要視分居原因和時(shí)間長(zhǎng)短作出不同裁判結(jié)果。一般而言,如果分居時(shí)間不長(zhǎng),男方提出離婚的,多半被判決不離婚。不管結(jié)果怎樣,這些常識(shí)型案件,男女起訴的機(jī)會(huì)均等。
在研究案件中,尚有一類(lèi)常識(shí)型案件,乃因配偶不忠提起的離婚糾紛。婚姻基于愛(ài)情,愛(ài)情基于忠誠(chéng),此乃人類(lèi)情感之通識(shí)。因?yàn)橥樘崞痣x婚糾紛,要視原告請(qǐng)求而定,如果強(qiáng)烈要求離婚的,一般會(huì)被判決離婚。男性因此起訴的案件比女性起訴的要多。
常識(shí)型案件還有因性格不合而起訴離婚的,但是性格不合很難做出量化認(rèn)定,因此,無(wú)論男女哪一方起訴,被判不離婚的機(jī)會(huì)均等。相反,因時(shí)代原因而出現(xiàn)的常識(shí)型案件,更能賺取人們同情,做出離婚判決而不致產(chǎn)生異議。例如,1954年馮某(女)訴葉某(男)離婚一案,兩人1939年結(jié)婚,生育兩個(gè)兒子,抗日期間被告葉某在廣西銻礦工作,當(dāng)日軍占領(lǐng)礦廠時(shí),跳樓逃走摔傷,導(dǎo)致間歇性精神病,無(wú)法工作。解放后,原告馮某長(zhǎng)期在廣州經(jīng)商,遂起訴至法院要求與被告離婚,以判決離婚結(jié)案。
從研究案件中可見(jiàn),男性起訴的案件更多屬于常識(shí)型案件,所以離婚率頗高。然而,女性起訴案件的離婚率更高,原因在于女性起訴的案件類(lèi)型,除了屬于常識(shí)型案件之外,更多是社會(huì)制度型案件和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型案件。
(二)社會(huì)制度型
社會(huì)制度型案件是指因?yàn)樯鐣?huì)制度變化而導(dǎo)致的婚姻糾紛。譬如,中國(guó)傳統(tǒng)社會(huì)妾侍制度一直存在。1950年《婚姻法》明確一夫一妻制,廢除納妾制度。兩個(gè)社會(huì)制度的變化產(chǎn)生許多解除夫妾關(guān)系的離婚案件。
因此,在研究案件中,脫離夫妾關(guān)系糾紛是最突出的社會(huì)制度型案件,這也體現(xiàn)社會(huì)轉(zhuǎn)型過(guò)程中突然出現(xiàn)的斷裂。脫離夫妾關(guān)系的訴訟熱潮由新制度促致,并由其他社會(huì)制度的改革支持而推波助瀾。與廢除納妾制度相關(guān)的離婚糾紛是重婚案件。男性在解放前納妾不違法,但在解放后納妾是法律禁止的,其行為構(gòu)成重婚。因此,1950—1954年因婚姻制度的改變而出現(xiàn)許多重婚訴訟。脫離夫妾關(guān)系與重婚訴訟均是由新舊社會(huì)婚姻制度的沖突而導(dǎo)致。其中,脫離夫妾關(guān)系案件數(shù)在婚姻案件中占一定比重(見(jiàn)表6)。研究數(shù)據(jù)表明,男性起訴脫離夫妾關(guān)系的案件僅有1宗,余下均為女性起訴,共計(jì)120宗,占女性起訴案件總數(shù)10.86%。由此可見(jiàn),因社會(huì)制度變動(dòng)導(dǎo)致的婚姻糾紛不在少數(shù),并且對(duì)女性影響更大。

表6 1950—1954年新會(huì)縣女性起訴脫離夫妾關(guān)系案件統(tǒng)計(jì)表
脫離同居關(guān)系也是社會(huì)制度型案件之一。解放前,人們對(duì)同居、納妾之事習(xí)以為常。甚至乎結(jié)婚之方式,既可向政府登記成立,也可以舉行婚禮形式得以成立。因此,同居關(guān)系容易過(guò)渡為正式婚姻。但是,1950年《婚姻法》明確規(guī)定婚姻的成立以登記為準(zhǔn)。沒(méi)有登記而共同生活的,只屬于同居關(guān)系,不能像婚姻一樣得到法律正式保護(hù)。同居生活而發(fā)生糾紛因而歸入婚姻糾紛范疇。同居雙方同意結(jié)婚的,可以補(bǔ)辦登記手續(xù)結(jié)為夫妻。不同意結(jié)婚,則由法院解除同居關(guān)系,財(cái)產(chǎn)和子女參照離婚條件予以處理。例如,1951年戴女訴李男脫離同居關(guān)系糾紛一案,兩人1945年同居生活,生育一子,因生活矛盾訴至法院,經(jīng)法院調(diào)解雙方解除同居關(guān)系,兒子由女方負(fù)責(zé)撫養(yǎng)。同居關(guān)系既非結(jié)婚,又非納妾,故而在處理此類(lèi)案件時(shí),有時(shí)以脫離同居關(guān)系為案由,有時(shí)則以脫離姘居關(guān)系為案由。這也說(shuō)明同居關(guān)系在時(shí)人看來(lái)是一種非正式和非法的關(guān)系。事實(shí)上,這種因社會(huì)制度造成的社會(huì)關(guān)系一直處于社會(huì)邊緣地帶。即使時(shí)至日后,同居關(guān)系要么保持非法同居關(guān)系的惡名,要么演變?yōu)槭聦?shí)婚姻。直到1994年《婚姻法》才明確規(guī)定,非經(jīng)婚姻登記的同居關(guān)系,法律不予調(diào)整。換言之,既不承認(rèn)事實(shí)婚姻,也不處理同居關(guān)系,將其放任在私人領(lǐng)域。
另一類(lèi)常見(jiàn)的社會(huì)制度型案件是婚約糾紛。婚約或訂婚,指通常依照民間習(xí)俗在結(jié)婚前訂立婚書(shū)、交換禮物、或立媒妁人等協(xié)議。《唐律疏議》規(guī)定婚約具有法律效力,特別是已交付禮金的,雙方不得違反,否則刑罰處置。訂婚傳統(tǒng)在解放前依然流行,基本上被視為具有婚姻效力的環(huán)節(jié)。1950年《婚姻法》沒(méi)有規(guī)定婚約的效力。1950年6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huì)有關(guān)婚姻法施行的若干問(wèn)題與解答》說(shuō)明:訂婚不是結(jié)婚的必要手續(xù)。任何包辦強(qiáng)迫的訂婚,一律無(wú)效。男女自愿訂婚者,聽(tīng)其訂婚。訂婚的最低年齡,男為19歲,女為17歲。一方面自愿取消訂婚者,得通知對(duì)方取消之。1953年3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huì)有關(guān)婚姻問(wèn)題的解答》兩次重申,訂婚不是結(jié)婚的必要手續(xù)。男女自愿訂婚者,聽(tīng)其訂婚,但別人不得強(qiáng)迫包辦。在這一解釋中刪去訂婚年齡的內(nèi)容。*張希坡:《中國(guó)婚姻立法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2頁(yè)。兩個(gè)解釋明確訂婚沒(méi)有法律效力,乃個(gè)人自愿行為。當(dāng)然,從解釋的變化和司法實(shí)踐來(lái)看,訂婚是傳統(tǒng)習(xí)俗之一,要立即改變之并非易事,因此,新舊制度的沖突遂產(chǎn)生婚姻糾紛。在研究案件中,解除婚約的案件在1952年有8宗,1953年4宗,1954年2宗,共計(jì)14宗。其中,女性起訴解除婚約的9宗,男性起訴的5宗;來(lái)自城市的8宗,來(lái)自農(nóng)村的6宗。關(guān)于解除婚約糾紛案件的處理分兩種情況,一是普通民眾的婚約糾紛,應(yīng)一律予以解除,如果一方要求返還禮金的,可判處予以沒(méi)收上繳國(guó)庫(kù)。另一種情況是關(guān)于軍人婚約的,1952年7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內(nèi)務(wù)部、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huì)總政治部聯(lián)合發(fā)布《關(guān)于軍人婚姻問(wèn)題座談紀(jì)要》,確立非軍人提出取消婚約的,須以軍人一方同意的原則。*張希坡:《中國(guó)婚姻立法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2頁(yè)。這兩種處理情況,在研究案件當(dāng)中均有判例。關(guān)于第一種情況的案件,如1952年原告馮女訴被告聶男解除婚約一案,兩人由父母包辦于1951年訂婚,男方交付禮金給女方家庭,原告以不了解被告不愿意結(jié)婚為由,起訴要求解除婚約,被告則要求女方返還禮金。法院判決解除雙方婚約,沒(méi)收男方交付的禮金,上繳國(guó)家。當(dāng)然,某些同類(lèi)案件中,如果禮金較重,法院會(huì)判決返還部分禮金,再?zèng)]收其中一部分。關(guān)于軍人婚約的處理情況,國(guó)家是出于保護(hù)軍婚,維護(hù)社會(huì)穩(wěn)定為目的,從而對(duì)婚約做出變通處理。通過(guò)法律明確規(guī)定訂婚沒(méi)有法律效力,再加上沒(méi)收禮金這種具有懲罰性質(zhì)措施,訂婚制度逐漸消亡。
較之于常識(shí)型案件的發(fā)生更多關(guān)系到人的因素,社會(huì)制度型案件關(guān)系到人的因素較少,更多是社會(huì)外部以合法律性形式加諸人身。簡(jiǎn)單地說(shuō),國(guó)家控制的因素更強(qiáng)。1950年《婚姻法》強(qiáng)調(diào)一夫一妻、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沖擊著傳統(tǒng)社會(huì)一夫多妾、夫權(quán)嚴(yán)重的婚姻制度,從而導(dǎo)致大量社會(huì)制度型案件的出現(xiàn)。在此類(lèi)型案件中,對(duì)女性的保護(hù)力度大于男性。女性起訴的婚姻案件更多屬于社會(huì)制度型案件。
(三)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型
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型案件指由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固有形態(tài)或者社會(huì)結(jié)構(gòu)變化,導(dǎo)致糾紛產(chǎn)生的案件。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猶如建筑物的框架,是支撐著整幢房屋的支柱,一般指一個(gè)國(guó)家或地區(qū)內(nèi)擁有一定資源、機(jī)會(huì)的社會(huì)成員所組成的方式及其相互關(guān)系,如人口結(jié)構(gòu)、家庭結(jié)構(gòu)、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社會(huì)階層結(jié)構(gòu)等表現(xiàn)形式。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分為制度結(jié)構(gòu)和觀念結(jié)構(gòu)。制度結(jié)構(gòu)是制度相互之間形成的相對(duì)穩(wěn)定的形態(tài),它可以通過(guò)制度變遷發(fā)生變化。觀念結(jié)構(gòu)則深植于人的思想觀念之中,并非朝夕之間可以發(fā)生大轉(zhuǎn)變。
筆者從家庭結(jié)構(gòu)、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和社會(huì)階層結(jié)構(gòu)三方面分析研究對(duì)象。其中,家庭結(jié)構(gòu)更傾向于觀念結(jié)構(gòu),而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和社會(huì)階層結(jié)構(gòu)則屬于制度結(jié)構(gòu)范疇。
首先是由家庭結(jié)構(gòu)導(dǎo)致的婚姻糾紛。傳統(tǒng)家庭中重男輕女觀念一直存在,即使新政權(quán)建立,也不輕易消除。新舊政權(quán)更替伴隨著新舊觀念的較量。新政權(quán)大力提倡“破四舊”,即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fēng)俗、舊習(xí)慣,但是收效甚微。因?yàn)樗呐f是文化系統(tǒng)的一部分。依照涂爾干所說(shuō)的“分工—功能—習(xí)慣—規(guī)范”公式,*[法] 埃米爾·涂爾干:《社會(huì)分工論》,渠東譯,三聯(lián)書(shū)店2000年版,第326-330頁(yè)。文化經(jīng)長(zhǎng)時(shí)間積淀而成,是民眾的集體意識(shí),并且文化觀念與社會(huì)功能相適應(yīng)。這種集體意識(shí)和適應(yīng)性并非一朝一夕能被改變或根除。因此,觀念結(jié)構(gòu)的轉(zhuǎn)變需要一個(gè)漫長(zhǎng)過(guò)程。
男權(quán)主導(dǎo)的家庭結(jié)構(gòu)使“絕大多數(shù)婦女投入奴隸生活的深淵”,因虐待而提起的離婚訴訟,在家庭結(jié)構(gòu)型案件中最為突出。從1950年司法機(jī)關(guān)受理的婚姻案件看,以婦女要求解除不合理婚姻關(guān)系為主,其中因包辦、強(qiáng)迫、買(mǎi)賣(mài)婚姻,虐待婦女,重婚,通奸以及遺棄等糾紛占三分之二以上。*羅瓊、段永強(qiáng):《羅瓊訪談錄》,中國(guó)婦女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103頁(yè)。1950—1954年新會(huì)縣女性因虐待原因而起訴的婚姻案件134宗,占女性起訴的婚姻案件12.13%;因毆打而起訴的案件88宗,占女性起訴的婚姻案件7.96%;上述兩類(lèi)案件共計(jì)222宗,占比20.09%(見(jiàn)表7)。由此可見(jiàn)是比較常見(jiàn)和突出的案件類(lèi)型。
家庭結(jié)構(gòu)型案件是新舊觀念沖突的具體表現(xiàn)。如1952年李某申請(qǐng)與庶母結(jié)婚一案,李某父親死亡,家庭被評(píng)為貧農(nóng)成分,他與父親第三妾相戀,向政府和法院申請(qǐng)批準(zhǔn)兩人結(jié)婚,經(jīng)調(diào)查,區(qū)政府批準(zhǔn)兩人登記結(jié)婚。庶母子相戀在傳統(tǒng)觀念里被視為大逆不道、違背倫理的事情。但是,為了提倡婚姻自由原則,并且廢除納妾制度,兩人終成眷屬。此案不僅反映觀念的改變,而且反映家庭結(jié)構(gòu)正在變化。

表7 1950—1954年新會(huì)縣女性因虐待、毆打而起訴的婚姻案件
其次是由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導(dǎo)致的婚姻糾紛。經(jīng)濟(jì)條件是婚姻家庭的重要組織部分,因經(jīng)濟(jì)問(wèn)題導(dǎo)致婚姻糾紛常常發(fā)生。然而,這里所說(shuō)的由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導(dǎo)致的案件,并不僅是具體個(gè)案,是指因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發(fā)生變化而改變大部分人的經(jīng)濟(jì)水平,從而推動(dòng)或保障離婚的自由發(fā)生。1950—1953年的土改運(yùn)動(dòng),打擊地主,按人口分配田地,使廣大婦女得到經(jīng)濟(jì)保障,容易擺脫男性或家庭束縛,她們得以行使離婚自由權(quán)。在大部分離婚案件中,女性都拿到自己應(yīng)得的土地和房屋。婚姻自由離不開(kāi)經(jīng)濟(jì)保障,也表明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的變化與離婚之間存在密切關(guān)系。
最后是因社會(huì)階層結(jié)構(gòu)導(dǎo)致的婚姻糾紛。與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型案件的原理相同,社會(huì)階層結(jié)構(gòu)的變化也與離婚存在密切關(guān)系。解放初期,新政權(quán)提倡人人平等的人民民主專(zhuān)政政策,采取嚴(yán)厲打擊土豪劣紳措施,消滅剝削階層,使中國(guó)社會(huì)階層又形成一個(gè)平型社會(huì)。正是社會(huì)階層結(jié)構(gòu)的變化,加上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的支持,導(dǎo)致許多與舊階層劃分界線(xiàn)的離婚案件出現(xiàn)。這也是改變男女地位的社會(huì)運(yùn)動(dòng)之一。
四、小結(jié):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
從上述分析中不難看出,常識(shí)型案件每個(gè)時(shí)代都存在,但是,社會(huì)制度型和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型案件則因時(shí)因地制宜,只有在社會(huì)變遷合適條件下才大量迸發(fā)。從后兩者的內(nèi)容來(lái)看,它們折射婚姻家庭領(lǐng)域從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的轉(zhuǎn)變。
在社會(huì)制度型和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型案件當(dāng)中,既有看得見(jiàn)的因制度變化所致的案件和因家庭結(jié)構(gòu)中男權(quán)觀念所致的案件,也有許多看不見(jiàn)的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和階層結(jié)構(gòu)變動(dòng)而造成的案件。無(wú)論是可見(jiàn)和不可見(jiàn)的案件,它們主要從兩個(gè)方面顯現(xiàn)出來(lái),一是從社會(huì)制度方面,希望把婚姻制度從傳統(tǒng)型轉(zhuǎn)變?yōu)楝F(xiàn)代型,如消除妾侍制。二是從社會(huì)觀念方面,希望把傳統(tǒng)觀念轉(zhuǎn)變?yōu)楝F(xiàn)代觀念,如把男尊女卑思想轉(zhuǎn)變?yōu)槟信降扔^念。這兩方面的轉(zhuǎn)變可以改變社會(huì)潛在結(jié)構(gòu),譬如把男權(quán)主導(dǎo)的傳統(tǒng)型結(jié)構(gòu)改變?yōu)槟信降鹊默F(xiàn)代型結(jié)構(gòu)。由此,以社會(huì)制度和社會(huì)觀念為標(biāo)準(zhǔn),可以將婚姻領(lǐng)域劃分Ⅰ、Ⅱ、Ⅲ、Ⅳ區(qū)域(見(jiàn)圖1)。

圖1 婚姻案件類(lèi)型解釋圖
第Ⅰ區(qū)代表著傳統(tǒng)社會(huì)制度和傳統(tǒng)社會(huì)觀念相一致的領(lǐng)域,第Ⅱ區(qū)代表傳統(tǒng)社會(huì)觀念和現(xiàn)代制度相沖突的領(lǐng)域,第Ⅲ區(qū)代表現(xiàn)代社會(huì)制度和現(xiàn)代社會(huì)觀念相一致的領(lǐng)域,第Ⅳ區(qū)代表傳統(tǒng)社會(huì)制度和現(xiàn)代社會(huì)觀念相沖突的領(lǐng)域。常識(shí)型案件均可能在四個(gè)區(qū)域中產(chǎn)生。但是,因?yàn)樵诘冖窈偷冖髤^(qū)社會(huì)觀念和社會(huì)制度相一致,所以社會(huì)制度型案件和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型案件不發(fā)生在這兩大領(lǐng)域。相反,第Ⅱ區(qū)和第Ⅳ是社會(huì)制度和社會(huì)觀念相沖突的區(qū)域,因此,它們是社會(huì)制度型案件和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型案件發(fā)生的領(lǐng)域。
社會(huì)制度和社會(huì)觀念兩大標(biāo)準(zhǔn)的沖突,產(chǎn)生四種沖突形態(tài):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社會(huì)制度之間的沖突、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社會(huì)觀念的沖突、傳統(tǒng)社會(huì)制度與現(xiàn)代社會(huì)觀念的沖突、傳統(tǒng)社會(huì)觀念與現(xiàn)代社會(huì)制度的沖突。
綜觀1950—1954年新會(huì)縣人民法院婚姻案件,除了基本的常識(shí)型案件之外,更多的是社會(huì)制度型和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型案件,它們以社會(huì)制度和社會(huì)觀念相沖突的方式產(chǎn)生糾紛。從這個(gè)原理出發(fā),我們就可以解釋上述幾個(gè)問(wèn)題。
首先是回答解放前后新會(huì)縣婚姻案件數(shù)量差距懸殊的問(wèn)題。按道理來(lái)講,解放前應(yīng)該有一定數(shù)量的離婚案件,因?yàn)槌WR(shí)型案件任何時(shí)候都存在,但是為什么新會(huì)縣民國(guó)時(shí)期極少甚至沒(méi)有離婚案件?原因之一是傳統(tǒng)社會(huì)觀念壓抑離婚,導(dǎo)致大家形成了寧愿啞忍也不欲離婚的集體心理。原因之二是傳統(tǒng)社會(huì)制度造成男女無(wú)須離婚,即可有離婚之事實(shí)。國(guó)家沒(méi)有強(qiáng)制登記制度,婚姻當(dāng)事人婚姻狀態(tài)可以自行解決。男性通過(guò)納妾另結(jié)新歡,沒(méi)必要與發(fā)妻對(duì)簿公堂;而婦女在沒(méi)有必要的情況下,要么忍受丈夫的虐待,要么離開(kāi)家庭自尋生活,也不需要國(guó)家和他人干預(yù)。與之相反,解放后新會(huì)縣的離婚訴訟數(shù)量急劇上升,同樣可以從社會(huì)觀念和社會(huì)制度這兩個(gè)標(biāo)準(zhǔn)進(jìn)行解釋。在社會(huì)觀念方面,新婚姻法大力宣傳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新觀念,號(hào)召?gòu)V大人民勇敢起訴解除不幸婚姻,因此促使離婚數(shù)量大幅上升。社會(huì)制度設(shè)定置相應(yīng)措施,讓廣大民眾能夠迅速解決婚姻糾紛。解放后國(guó)家強(qiáng)制推行婚姻登記制度,沒(méi)有登記的婚姻不被承認(rèn)。在解放前已存在離婚事實(shí)的夫妻,為了再娶或承認(rèn)現(xiàn)有婚姻,紛紛提起離婚訴訟。更不用說(shuō),除常識(shí)型案件之外,社會(huì)制度型和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型案件大量發(fā)生,更推高婚姻訴訟數(shù)量。
其次是回答在新會(huì)縣婚姻訴訟中,為什么女性起訴的案件數(shù)量比男性起訴的要高得多。對(duì)于常識(shí)型案件來(lái)說(shuō),男女起訴的機(jī)率相當(dāng),兩者的案件數(shù)量差距不大。但是,對(duì)于社會(huì)制度型和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型案件來(lái)說(shuō),女性起訴的案件占了其中絕大部分,男性起訴的案件沒(méi)有或者極少。原因是傳統(tǒng)社會(huì)壓制女性地位,而新婚姻法提倡男女平等原則,無(wú)疑是從觀念上和制度上解放了女性,讓女性通過(guò)法律途徑維護(hù)自身權(quán)利。因此,女性起訴的案件數(shù)量遠(yuǎn)大于男性起訴的案件數(shù)量。
從傳統(tǒng)走向現(xiàn)代,不是坐直通車(chē),而是曲折而漫長(zhǎng)的道路。特別是社會(huì)制度、社會(huì)觀念和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的轉(zhuǎn)變并非一蹴而就,需要?dú)v經(jīng)漫長(zhǎng)的時(shí)間。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既涉及社會(huì)觀念,又涉及社會(huì)制度,更涉及到社會(huì)結(jié)構(gòu),要實(shí)現(xiàn)理想目標(biāo),尚需時(shí)日。新會(huì)縣人民法院婚姻案件的特征僅僅揭示了社會(huì)變遷中婚姻制度的一個(gè)面相,其深層變遷機(jī)制還需另文探討。
- 山東社會(huì)科學(xué)的其它文章
- 人類(lèi)文明形態(tài)變革的哲學(xué)表征
——“人類(lèi)文明形態(tài)變革與哲學(xué)理念創(chuàng)新”國(guó)際學(xué)術(shù)研討綜述 - 跨文化對(duì)話(huà)融合的新突破
——《劉若愚跨文化詩(shī)學(xué)思想研究》評(píng)介 - 地方立法起草過(guò)程中部門(mén)協(xié)調(diào)問(wèn)題探析
- 鄉(xiāng)村公共服務(wù)供給側(cè)改革視域下村級(jí)組織運(yùn)轉(zhuǎn)經(jīng)費(fèi)保障政策研究
- 網(wǎng)絡(luò)嵌入、社會(huì)責(zé)任與品牌價(jià)值
——基于制造業(yè)企業(yè)經(jīng)驗(yàn)數(shù)據(jù)的實(shí)證研究 - 大運(yùn)河沿線(xiàn)區(qū)域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jí)路徑及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