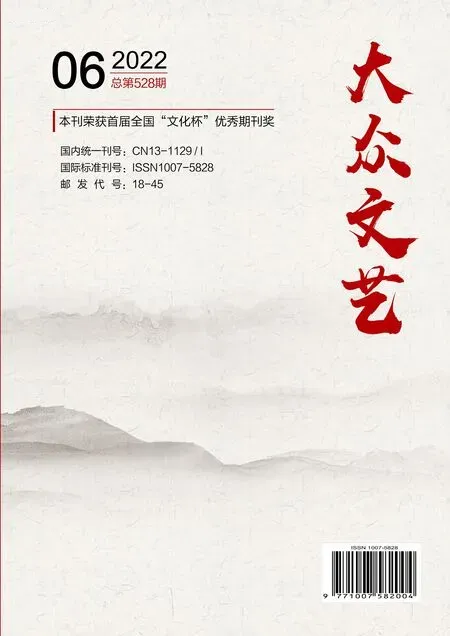抗戰散文中的貴州形象解析
(興義民族師范學院 562400)
“七七”事變后,全國各界人民抗日救亡運動情緒高漲。救亡圖強成為了文學創作的主流。1938年3月,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漢口成立,隨即在昆明、桂林、貴陽等地建立分會。1939年,貴陽開售《文藝戰線》《中國青年》等延安進步刊物,從而帶動和促進了貴州文學的發展,大批報刊如雨后春筍般崛地而起,如《中央日報》(貴陽版)、《抗建》相繼創刊。隨著抗戰不斷深入,文人或路過或暫住在貴州,留下了一大批文學作品,如茅盾、巴金、老舍、沈從文、謝冰瑩、沙汀、艾蕪、熊佛西、劉北祀等,來自不同地域的作家帶著異域文化近距離的感受并體認這一城市,將中國文學中曾經默默無聞的“貴州”形象進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集中呈現。
而抗戰時期的貴州,具有特殊的歷史氛圍和文化環境,一方面,它地處西南,在歷史上屬于“流放”之地,“荒蕪”“野蠻”成為歷代文人的集體無意識。但是另一方面,抗日戰爭的爆發,一大批文人涌入貴州,將五四新文化新思想帶入這片未開化之地,對其舊的文化傳統形成較大的沖擊,這種新舊文化的相互聯系和沖突,無論是于貴州這一城市還是文人都讓其帶有了非常明顯的時代特征。正如美國學者理查德·利罕在他的《文學中的城市》中所談到的關于城市和文學文本之間的關系,他們的深刻的聯系決定了對城市的一種閱讀就是另一種方式的文本閱讀,而文本中的城市像我們呈現的文化歷史等,既豐富了城市本身,同時也豐富了對城市進行文學想象的描述方式。
一、自然貴州——山國水鄉
在中國傳統文學中,以山水比德始于孔子,他將“繪事”與藝、德、仁、道等相結合,開創了山水比德的先河。在《論語·雍也》中提出“智者樂水,仁者樂山”這一言論,體現了山水、仁智的內在同一性。山有其博大高深,其蘊含著正直,他拔地而起的簡潔彰顯著瀟灑從容,他的滄桑,見證著他的偉岸、蒼穹和持之以恒。在抗日戰爭時期這一特殊的語境下,當全國大部分城市都淪陷后,文人們攜家帶口的逃亡和家仇國恨,讓他們在歷史大潮中肩負起了巨大的歷史使命。而此時的貴州一時間成為了文人們眼中的焦點,“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的獨特的貴州“山形”在文本中得以多重方式呈現。一方面,由于受到“山”的場域的影響,審美主體將主觀意念投射在“山”這一客體上,從而使“山”意象既具有自然的屬性,又帶有了精神性的特點。另一方面,從客觀上來看,“山”本是一種自然存在,但是由于在空間上的拔地而起和巍峨雄偉的外形,在時間上的亙古不變,使它成為了文人們的心靈棲息和精神寄托之所。
感受了“廣袤平原”的文人們,初入貴州,最具視覺沖擊力的是那雄偉奇壯的高山,“貴陽位于萬山之中,峰巒環繞……因為山多水少,所以號稱‘山國’”沙鷗也持有相同的觀感,沒到貴陽城之前“飽覽了無窮的山色”,一路上的高山讓作者以為至少還是會有平地的,但是:“到了這山國中的貴陽城,還是四望皆山!”對于外來入黔的文人來說,在他們的意識里,既然是作為省會的城市,大抵應該是平原。而令人意外的是唯一較平的地方貴陽,用來作了省會,“但是,也還是在山谷里。”
山所呈現的印象,首先是“奇險”。張恨水途徑貴州,對貴州高山之險是深有體會的:盤山公路是不足為奇的,但是此處的盤山路趨勢“屈曲而上”,而車是穿懸崖而過,下面是草木青隱,深遠無底,在僅容兩車并行的道上盤旋而上,霧又重,小孩們驚呼“入半天云上”。無論是從湖南入黔還是從昆明、桂林入黔,貴州的高山險路都給人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特別是著名的二十四道拐,“在高山上共轉二十四次彎之多。”這種時上時下,循環住復,著實“令人目跳心驚”。李長之經過二十四道拐時,覺其“讓人驚絕”。而它的險是因其結構的“奇特”,這像之字一樣的路,汽車在上面爬行,一共連著二十四次。而這的確是不能不讓人“膽戰心驚”。雖說奇險的二十四道拐讓人膽戰心驚,但面對“高”“大”的山峰所得到的力量的美,卻使作者得到了一種情感的疏導,在這種山國的旅行,“是久居北方那種大平原的人所想象不到的”。緊接著作者用三個你決想不到來形容審美對象的獨特,你“決想不到世界上會有‘沒有平地’的地方”,光這一點來說,這于一直住在平原的作者來說,已經是不可思議的一點了,但是,“你決想不到整日走,始終是在山里;”“你決想不到所見的完全是山嵐青巖,而沒有曠野。”而就是這種刻骨銘心的不可思議,給了觀者不一樣的感覺,“就是這種山色,讓人忘了汽車顛簸之苦,讓人忘了時常要幫著推動汽車之勞,讓人忘了憩在那極其狹小的小旅店中的不舒服。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作者隨著對貴州不斷的解讀,其情感也發生了變化,從最開始接觸到山時的“膽戰心驚”到三個你絕想不到,到最后連用三個“讓人忘了”來表達這樣一種力量之美對人心靈的凈化,并引導人的情感宣泄。
山有厚重,水無常勢,在大自然中,山和水因其外形秉性不同而構成了兩種風格迥異的形式,成為了中國文學中常見的兩種意象。貴州雖是“山多水少”,但是在抗戰時期,他卻成為了文人們的“水鄉江南”,這和“花溪”是不無關系的。于巴金來說,花溪是他們的媒人,1944年的5月8日,他和相戀了八年的愛人蕭珊在美麗花溪旁一個名為“花溪小憩”的賓館里情定終生,而花溪也見證了他們海枯石爛的愛情。“我們感到寧靜的幸福。四周沒有一聲人語”在貴陽這段日子,巴金寫出了被司馬長風認為是“現代小說典范”的《憩園》,而他在貴陽中醫院住院期間所發生的事情,也成為了他《第四病室》的寫作素材。
在不少文人眼里,抗戰時期的花溪就是世外桃源:有連綿不斷的青山,有一望無際的稻田,還有一條穿鎮而過的小河。當地人民自耕自食,“滿田野的女人”唱著山歌,輕松而愜意。而文人們對貴州花溪“江南”式的追求也在大量作品中表現了出來:“山水幽靜,儼然西子風光。”“西南何及江南秀?自是花溪獨得名。”“春來休憶江南好,綠染花溪聊勝無。”這樣一個曾經荒蕪貧窮的貴州,在抗戰時期成為了多少顛沛流離文人的夢里水鄉,一個精神的憩息之所。
如果說山之“奇險”水之“靜美”是貴州的外在形態的表征,那么,其“雄”“壯”則是其內在的精神表征。文人們未入黔之前,大抵有一個概念上的貴州。主要來源于文學史對它的描述和旁人對其的概說。如“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兩銀。”應該是較為深入人心的貴州形象了。在行將入黔之前,施蟄存就被朋友告知“公路險峻,土匪猖撅”,因此“余不覺惴惴,頗悔不由漢乘飛機矣。”剛進入貴州境內時,感覺終日行走于崇山峻嶺之間,曲折迂回,突在山之巔 ,突在谷之底,“險峨之狀,心目交栗”。而這種往還回旋,極限體驗,讓他“直疑在夢寐中矣。”一路深入貴州,經大盤山時,由于車陷入泥中,無法挪動,光靠車上四人是無計可施了,在這“人幽谷,出沒萬山中”的地方,“遙望對山有人家”,約半小時就邀來了二三十人,將車開出。其時,心存感激之情不溢言表,友人的告誡也被拋于腦后了,黔路上的諸多事情,改變了作者的看法,淳樸的山民,奇險的道路當是給作者最大的印象。行走在滇黔桂路上的同濟,在他的《千山萬嶺我歸來》一文中,通過對貴州山地文化的體認、感悟,從最初的認為貴州是一個“貧瘠不毛之地,荒涼無足觀”的地方,進而發現“花溪一走,乃發現了崇山峻嶺的雄放當中,更有清瑩嫵媚的隱伏。碧樹,青山,流泉,綠野。有一個字可以形容——“秀”!花溪風景之“秀”可與江南任何名勝爭衡。”故“愈覺中國之可愛”,而群山雄傲之下,頓覺“天之高,地之厚,中國之大,中國人之必定大有為!”
二、人文貴州
可以說貴州既是一幅絢麗的風景畫,同時也是一幅奇異的風俗畫。作為少數民族地區的貴州,自然有自己獨特的民風民俗,最讓外地文人好奇的是衣飾。在參加趕集的時候,林冰看到“光怪離陸”的服裝感覺是“洋洋大觀”:戴土耳其式的帽子的女苗民們……他們大多下身圍一摺子短裙,走起路來左右擺動,“怪好看的”。在荒涼多山的貴州行走時,數小時見不到人家,而衣著奇特的眾多的苗民同樣引起了施蟄存的注意“男子裹頭巾,突出于顱額間,如承盤;女子御黑色斜領衣,褶裥短裙,仿佛漢代裝束。”同濟也覺得苗民的衣飾“紅綠斑斕,大有西班牙村女之風。”
雖說如前所述的雄壯秀美的山水強化了文人的家國形象,也勾起了他們濃厚的思鄉之情,但是沿途所見的貴州高原地域原始的生活方式,極度的貧窮和落后卻讓他們觸目驚心。作家黑子從廣西入黔,看到的廣西鄉間的民房較為整潔,當地的老百姓雖苦,但是衣著至少還是樸素的,但是到了貴州就不同了,由于境內都是高山,交通非常不便,故“因之人民多故步自封,老死不相往來。”交易市場非常原始,鄉親們帶來自己平日所中的一些農作物,在趕集的時候換取一些食鹽布匹之類的,“其交易實質不脫‘物物交換’”但是在這種質樸和忠實背后,文人們也看到了少數民族地區的落后與愚昧,“人民直不知衛生為何物.且智識程度異常低落。作事毫無秩序,與新生活相去甚遠。”而“‘窮’!‘塞’!‘愚’!”成為了他們共有的特點,
貴州發展的滯后帶來了文化傷痛,但其淳樸的性格卻給很多文化名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未到貴陽之前,熊佛西一直在猶豫,覺得“貴陽不是我們來的地方,即使來了也使我們有寂寞之感”然而,到了貴陽,由于好客熱情的朋友,“這里不但不使我們寂寞,而且使我們有在此長住的愿望。”。貴陽給謝冰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我找到了這么多熱情的朋友,是的,有了你們,我才有留戀,才對貴陽發生特別的好感。”李長之由昆明經貴陽到重慶,最后到成都,一路行走,感到“貴州人很富有情感,很喜歡朋友。同時也很機敏,而常有風趣”。
雖說很多文人們從沒有想過會踏上貴州這片荒蕪貧瘠的高原之地,不管是處于自愿還是由于逃亡。但是,在抗日戰爭這一特殊語境下,文人們在救亡圖強這一主導思想引領下,在這片未開化土地上奉行著五四新文化所標榜的啟蒙主題,同時,貴州雄壯氣魄的山地文化也在精神上也反哺了流離失所的他們,而他們對貴州的體認和書寫,完成了對貴州這一形象的重新建構。
參考文獻:
[1]理查德·利罕.吳子楓譯.文學中的城市·知識與文化中的歷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0.
[2]千里.黔靈游記.黔靈[J],1945.7.
[3]沙鷗.貴陽一瞥.旅行雜志[J],1938.12.
[4]李長之.西南紀行[A].施康強.征程與歸程[M].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5]張恨水.東行小簡[A].施康強.征程與歸程[M].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6]陳志雄.湘黔滇旅行記[A].施康強.征程與歸程[M].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7]巴金.關于第四病室[A].創作回憶錄[M].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1.
[8]巴金.憩園[M].廣州:花城出版社,2010.11
[9]蘇利.花溪.中央日報[N],1939.7.4.
[10]胡騎.東西南北話貴陽. 貴州日報[N],1945.11.18.
[11]同濟.千山萬嶺我歸來[A].施康強.征程與歸程[M].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12]施蟄存.西行日記[A].施康強.征程與歸程[M].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13]林冰.西南公路[A].施康強.征程與歸程[M].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14]黑子.花溪游春[A].貴州日報[N],1945.3.23.
[15]熊佛西.貴陽三月[A].貴州日報[N],1945.8.16.
[16]謝冰瑩.寄自烏江[A].中央日報[N],1943.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