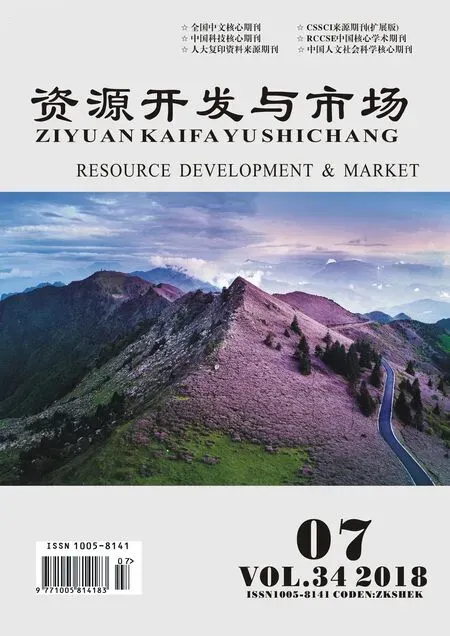經濟增長對霧霾污染影響的門檻效應研究
——基于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的分析
,b
(重慶工商大學 a.長江上游經濟研究中心;b.經濟學院 重慶 400067)
1 引言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GDP由1978年的3679億元增長到2017年的827122億元,增長了近223.82倍。在經濟取得快速發展的同時我國環境狀況卻在不斷惡化,2013年爆發了52年以來史上最為嚴重的霧霾天氣,霧霾波及25個省份100多個大中型城市,直到現在霧霾污染仍然是人們心中揮之不去的陰影。以PM2.5為首的霧霾污染嚴重威脅著人類的健康和環境問題。根據我國空氣質量在線監測分析平臺的數據可知,2016年符合PM2.5年均濃度二級標準的只有云南省、內蒙古自治區、廣東省、海南省、福建省、西藏自治區、貴州省、青海省和黑龍江省9個省級地區,沒有一個省市的PM2.5年均濃度符合一級標準,超過2/3的省市PM2.5年均濃度都沒有達到二級標準,霧霾污染現狀不容樂觀。
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推進綠色發展,持續實施大氣污染的防治行動,打贏藍天保衛戰。“十三五”規劃綱要指出應以提高環境質量為核心,加大生態環境保護力度,大力推進污染物達標排放以及總量減排,深入實施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因此,揭示經濟增長對PM2.5濃度的影響機制并測算其影響程度,對我國政府更有效地制定相關政策和措施,降低PM2.5濃度與治理大氣污染具有重要的意義。
2 文獻綜述
有關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相關的研究上。Grossman、Krueger[1]提出了著名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理論,即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之間呈倒“U”型關系,為經濟增長和環境污染之間關系的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較多學者的研究證實了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之間存在倒“U”型曲線。高宏霞等[2]認為二氧化硫和廢氣排放量與人均GDP之間的關系符合EKC假說;鄭麗琳、朱啟貴[3]認為經濟增長和碳排放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倒“U”型關系;李小勝等[4]認為工業廢水排放與人均收入之間呈現出倒“U”型關系。也有學者對此得出了相反或其他結論,王飛成、郭其友[5]認為我國西部地區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呈現“N”型關系;王敏、黃瀅[6]研究發現我國城市大氣污染(PM10、SO2、NO2)與城市人均收入之間存在“U”型關系。隨著經濟增長,它與環境質量之間呈現出倒“U”型、“U”型或“N”型等關系,然而這種趨勢的形成是受經濟發展水平、技術水平和對外開放水平等多種因素共同影響的結果,需要在不同變量下對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的關系進行分段研究。
綜上所述,現有的研究存在以下兩個方面的不足:①較多的文獻討論的是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的倒“U”型、“U”型或“N”型等關系,少有研究說明經濟增長對環境污染、碳排放等的影響程度,忽視了經濟增長對環境質量的影響會與其他相關變量的不同階段有關。②多數研究探討的是城鎮化、對外開放等對環境污染影響的門檻效應,缺乏經濟增長對我國霧霾污染PM2.5影響的門檻效應研究。基于已有的研究,本文對以下兩個方面進行研究:一是基于面板門檻模型,根據數據自身特點內生地對數據進行分組,通過數據自動識別確定門檻值,解決門檻條件設定過于主觀和一般線性模型解釋力較弱的問題。二是研究經濟增長對我國霧霾污染PM2.5濃度存在的非線性影響,豐富我國經濟增長對環境質量影響的研究。
3 模型設定與指標選擇
3.1 STIRPAT模型
Ehrlich、Holden[16,17]提出了IPAT模型,該模型為I=PAT。該模型被廣泛用于評價人口(P)、社會富裕程度(A)、技術水平(T)對環境壓力(I)的影響,后來Waggoner等[18]將技術進步(T)分解成T和每單位產出消耗(C)的ImPACT形式。IPAT模型和ImPACT模型存在著較大的局限性,模型只滿足驅動因素單調、同比例的變化,被解釋變量對解釋變量的彈性恒等于1。Dietz、ROSA[19]將IPAT模型進行了相關拓展,建立了隨機形式的STIRPAT模型,彌補了環境壓力與每個影響因素之間成等比例變化的不足,方程表示為:
I=αPβ1Aβ2Tβ3ε
(1)
式中,I、P、A、T與I=PAT模型中變量表示的含義一致;α表示模型的系數;β1、β2和β3表示待估計的參數;ε為誤差項。隨機形式的STIRPAT模型是一個包含多變量的非線性模型,可應用于研究各個影響因素對環境壓力的非等比例變化的影響。對模型(1)兩邊分別取對數,模型表示為:
lnI=lnα+β1lnP+β2lnA+β3lnT+lnε
(2)
基于隨機形式擴展的STIRPAT模型允許納入更多相關的影響因素來分析其對環境壓力的影響。本文引入產業結構、能源消費結構和對外開放水平三個影響因素,對模型(2)進行擴展,模型調整為:
lnpmit=lnα+β1lnpiit+β2lneiit+β3lnindit+β4lnesit+β5lnopenit+β6lnpgdpit+εit
(3)
3.2 門檻模型
所謂門檻效應是指在門檻變量的不同階段下,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所產生的階段性影響程度。基于Hansen[8]提出的系統內生分組的非線性回歸方法——面板門檻回歸方法,在假設存在單門檻的基礎上,考察經濟增長對霧霾污染的影響是否存在經濟發展水平、人口密度、能源強度和對外開放水平的門檻效應。模型(3)沒有涉及到經濟發展水平等變量的門檻效應,結合門檻模型,本文設立的單一門檻和雙門檻具體模型表示為:
lnpmit=lnα+β1lnpiit+β2lneiit+β3lnindit+β4lnesit+β5lnopenit+λ1lnpgdpitI(qit≤θ)+λ2lnpgdpitI(qit>θ)+εit
(4)
lnpmit=lnα+β1lniit+β2lneiit+β3lnindit+β4lnesit+β5lnopenit+λ1lnpgdpitI(qit≤θ1)+λ2I(θ1
(5)
式中,pmit為被解釋變量,表示i省市t年的PM2.5年均濃度;qit表示門檻變量,用經濟發展水平(lnpgdp)、人口密度(lnpi)、能源強度(lnei)和對外開放水平(lnopen)表示;θ表示估計的門檻值;β1—β5為控制變量系數;λ1、λ2、λ3表示不同區間核心解釋變量的系數;I(*)為指標函數;εit為隨機擾動項。
Hansen認為門檻變量可作為某個解釋變量,也可作為獨立的解釋變量,所以在選取其中一個變量為門檻變量時,其他三個門檻變量仍然可作為控制變量。即當經濟發展水平為門檻變量時,人口密度、能源強度、產業結構、能源消費結構和對外開放水平為控制變量,其他依此類推。
3.3 變量選取與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2001—2015年我國30個省份(未包括香港與澳門特別行政區、臺灣省和西藏自治區)的面板數據,被解釋變量為PM2.5年均濃度,核心解釋變量為經濟增長,門檻變量為經濟發展水平、人口密度、能源強度和對外開放水平。
因變量——PM2.5年均濃度:本文選取PM2.5年均濃度作為環境壓力指標,用來表征大氣環境的質量,霧霾污染均指PM2.5年均濃度。PM2.5已成為我國現階段霧霾污染的主要來源,大量的研究證明顆粒越小對人體健康的危害越大,細顆粒物能飄到較遠的地方,因此影響范圍較大,同時PM2.5與人類壽命的縮短在統計學中具有較高的相關性。本文使用各省份PM2.5年均濃度來表示霧霾污染程度(ug/m3),使研究更具有針對性。相比其他環境要素,PM2.5年均濃度的外溢性較強,解決了本文的內生性問題。
核心解釋變量——經濟增長(pgdp):經濟發展是造成污染最主要的因素之一。經濟總量越大,消耗的資源越多,產生的污染物也越多。我國大多數省份現階段還處在高能耗、高排放和高污染的發展階段。本文主要探討經濟增長在不同門檻變量下對霧霾污染的影響程度,社會富裕程度(A)即經濟發展水平用人均GDP表示。為了剔除物價的影響,各省份的人均GDP都是以2000年為基期所計算的實際人均GDP(元/人)。
門檻變量與控制變量:①人口密度(pi)。P為人口規模,考慮到各省市人口規模和行政區域面積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異,直接用總人口數指標不具有科學上的可比性,所以采用人口密度指標pi表示(人/km2)。②技術水平(ei)。T為技術水平,本文使用能源強度表示技術水平。即各省份的能源消費總量與GDP的比值,用ei表示(t標準煤/萬元)。③產業結構(ind)。第三產業比第二產業清潔,本文試圖考察第三產業比重的提升是否有利于降低霧霾污染,用第三產業值占GDP比重表示(%)。④能源消費結構(es)。不同的能源消費結構會影響到經濟增長的能源消費基礎,不同的能源消費所產生的污染程度會有所不同,本文使用煤炭消費總量占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表示能源消費結構(%)。⑤對外開放水平(open)。對外開放水平對環境影響存在不同的研究結論,一些學者研究表明對外開放造成了“污染天堂”,而另一些學者研究表明對外開放帶來了“污染光環”效應。本文試圖考察對外開放水平對霧霾污染的影響,使用年末登記的外商投資總額占GDP比重來表示對外開放水平(%)。
本文選取PM2.5年均濃度來衡量霧霾污染的程度,PM2.5數據(2001—2012年)來源于哥倫比亞大學國際地球科學信息網絡中心和巴特爾研究所。國內對PM2.5的測度較晚,主要從2013年年底之后才開始進行監測,本文2013年的數據通過指數平滑法處理所得,2014—2015年各省市PM2.5的年均濃度數據來源于《中國空氣質量在線監測分析平臺》,通過每月的PM2.5濃度加總求平均得到PM2.5的年均濃度值。本文采用的其他數據來源于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以及各省市統計年鑒。各變量的相關系數矩陣見表1,實證部分通過軟件Stata15.0完成。

表1 變量間的相關系數矩陣
基于擴展的STIRPAT模型,本文對所有變量取對數,各個變量取對數不會改變數據的性質和相關關系,可消除異方差使數據更加平穩。首先應對各變量之間的相關性進行檢驗,以檢驗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各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檢驗見表1。由表1可知,兩個變量之間相關系數的絕對值最高為0.7296,都沒有超過0.8。且方差膨脹因子的均值為2.37,最大的方差膨脹因子為3.43,遠低于10,各變量之間的多重共線性不大,核心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的變化對被解釋變量不會產生較大的重復性影響。
4 實證結果分析
4.1 變量的平穩性與協整檢驗
在時間序列中,各變量的不平穩性可能會引起偽回歸現象,各變量的不平穩性在面板數據中同樣也會出現偽回歸現象。門檻回歸模型要求各變量(尤其是門檻變量)必須為平穩變量,因此在門檻模型回歸前需要對各個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處于對檢驗結果的穩健性考慮,本文使用相同面板單位根檢驗的LLC檢驗和不同面板單位根檢驗的Fisher-ADF檢驗。非平穩數據存在同階單整可進行協整檢驗,若變量間有協整關系存在,說明方程的回歸殘差是平穩的,仍可在此基礎上直接對原方程進行回歸,此時的回歸結果是較精確的。面板數據的時序較短,本文的協整檢驗使用Kao檢驗。各截面時序的單位根檢驗和協整檢驗見表2。從表2可知,水平序列中少數變量的LLC檢驗和Fisher-ADF拒絕原假設,即存在單位根。在一階差分序列的檢驗中,7個變量的LLC檢驗和Fisher-ADF檢驗均通過了1%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一階差分的數據不存在單位根現象,為平穩數據,所有變量為一階單整過程。Kao檢驗發現,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說明各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各變量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

表2 變量的平穩性和協整檢驗
注:***、**、*分別表示通過1%、5%、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括號內的數值為對應的P值。
4.2 門檻效應檢驗
如果進行門檻效應分析,首先應檢驗以不同變量為門檻變量時是否存在顯著的門檻效應。門檻效應包括存在單門檻效應、雙重門檻效應和三個門檻效應的假設檢驗,單門檻效應、雙重門檻效應和三個門檻效應的原假設分別為不存在單個門檻值、不存在兩個門檻值和不存在三個門檻值,備擇假設存在單個門檻值、存在兩個門檻值和存在三個門檻值。首先應進行是否存在單門檻效應檢驗,如果不存在單個門檻效應則不需使用門檻回歸分析;如果存在單門檻效應則應繼續進行雙門檻效應檢驗。接受雙門檻效應原假設則只需要進行單門檻效應分析,拒絕雙門檻效應原假設則需進行三個門檻效應檢驗,三個門檻效應檢驗如果接受原假設說明只需要進行雙門檻效應分析,拒絕三個門檻效應原假設說明應進行三個門檻效應分析。
根據其假設條件對方程進行估計,利用軟件Stata15.0通過Bootstrap(自舉法)300次反復抽樣得到具體的F值和P值,確定各門檻變量的門檻值以及門檻個數。具體的門檻效應檢驗結果見表3。當門檻變量分別為經濟發展水平、人口密度和對外開放水平時,單門檻效應的檢驗分別在10%、1%和5%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了原假設,雙門檻效應檢驗均未通過至少10%顯著性水平的檢驗,說明以這三個變量為門檻變量時經濟增長對霧霾污染的影響存在顯著的單門檻效應。當門檻變量為能源強度時,單門檻效應和雙門檻效應的檢驗分別通過了10%和5%顯著性水平的檢驗,三個門檻值檢驗并沒有通過10%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以能源強度為門檻變量時經濟增長對霧霾污染的影響存在顯著的雙門檻效應。

表3 各變量的門檻效應檢驗
注:*、**、***分別表示通過10%、5%、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
4.3 門檻模型估計與分析
利用表3對門檻效應的檢驗,得到各變量的門檻值之后,分別估計以經濟發展水平、人口密度、能源強度和對外開放水平為門檻變量的門檻效應模型,進一步分析這些門檻變量在經濟增長中對霧霾污染效應產生的門檻作用,具體的回歸結果見表4。
以經濟發展水平為門檻變量時,經濟增長對我國霧霾污染的影響存在顯著的單門檻效應。當人均GDP低于15463元時,經濟增長每增加1%會引起霧霾污染濃度增加0.0288%;當人均GDP高于15463元時,經濟增長每增加1%會引起霧霾污染濃度增加0.0571%,經濟增長對霧霾污染的影響都沒有通過至少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經濟增長對霧霾污染的正向影響在跨過門檻值之后增大,呈現出“階梯式”上升特征。在其他控制變量不變的情況下,經濟增長加劇了霧霾污染,這與我國現階段高投入、高能耗和高污染的經濟發展模式密切相關。

表4 門檻模型估計結果
注:*、**、***分別表示通過10%、5%、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
以人口密度為門檻變量時,經濟增長對我國霧霾污染的影響存在顯著的單門檻效應。當人口密度低于81人/km2時,經濟增長每增加1%會引起霧霾污染濃度增加0.7594%;當人口密度高于81人/km2時,經濟增長每增加1%會引起霧霾污染濃度減少0.0130%,跨過門檻值后經濟增長對霧霾污染的影響未通過至少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以人口密度為門檻變量時,經濟增長對霧霾污染的正向影響在跨過門檻值后變為負向影響,呈倒“U”型關系。
以能源強度為門檻變量時,經濟增長對我國霧霾污的影響存在顯著的雙門檻效應。當能源強度低于0.653t/萬元時,經濟增長每增加1%會引起霧霾污染濃度增加0.1573%;當能源強度跨過第一道門檻且低于3.348t/萬元時,經濟增長每增加1%會引起霧霾污染濃度增加0.1941%;當能源強度跨過第二道門檻值3.348t/萬元時,經濟增長每增加1%會引起霧霾污染濃度增加0.2583%。以能源強度為門檻變量時,經濟增長對霧霾污染的影響呈現出“階梯式”增長特征,說明在其他控制變量一樣的情況下,技術進步有利于降低霧霾污染。
以對外開放水平為門檻變量時,經濟增長對我國霧霾污染的影響存在顯著的單門檻效應。當對外開放水平低于門檻值12.966%時,經濟增長每增加1%會引起霧霾污染濃度增加0.3054%;當對外開放水平高于門檻值12.966%時,經濟增長每增加1%會引起霧霾污染濃度增加0.2635%。在對外開放水平跨過門檻時,經濟增長對霧霾污染的正向影響減弱。
從各門檻模型的估計結果可知,無論以哪個變量作為門檻變量,人口密度與霧霾污染之間都呈現出正向關系,人口密度增加不同程度地會加劇霧霾污染,人口密度越大的地區對機動車輛和住房等的需求也越大,由此帶來更多的能源消費,生活消費的增加將產生更多的生活垃圾。能源強度與霧霾污染呈現出負向關系,即技術水平提升會降低霧霾污染,技術水平的提升可提高投入產出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同時能降低生產和生活中的污染排放。不同的門檻變量下,第三產業占比對霧霾污染的影響方向不同,且都沒有通過至少10%顯著性水平的檢驗。能源消費結構與霧霾污染呈現出正向關系,即煤炭消費占比的提升會加劇霧霾污染。2016年我國煤炭消費比重高達65%左右,過高的煤炭消費占比會釋放大量的氮氧化物、二氧化硫和顆粒物等,是構成霧霾污染PM2.5的元兇。對外開放水平與霧霾污染呈現出負向關系,對外開放水平的提升有利于降低霧霾污染,說明外商投資存在“污染光環”效應,不存在“污染天堂”現象。無論以哪一個變量作為門檻變量,經濟增長基本都與霧霾污染呈現出正相關關系,經濟不斷增長,資源消耗越多,產生的污染物也不斷增加。社會經濟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環境問題,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環境質量卻不斷惡化,經濟增長模式仍然是傳統的資源要素驅動模式,因此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迫在眉睫。
5 結論與建議
本文以2001—2015年我國30個省市的面板數據為樣本,基于STIRPAT模型和面板門檻模型,以經濟發展水平、人口密度、能源強度和對外開放水平為門檻變量,實證分析了經濟增長對我國霧霾污染影響的門檻效應。研究結論為:①經濟增長對我國霧霾污染的影響存在著顯著的門檻效應。以經濟發展水平、人口密度和對外開放水平為門檻變量時,經濟增長對我國霧霾污染的影響存在著顯著的單門檻效應;以能源強度為門檻變量時,經濟增長對我國霧霾污染的影響存在著顯著的雙門檻效應。②以經濟發展水平和能源強度為門檻變量時,經濟發展對霧霾污染的正向影響在跨過門檻值后增大,呈現出“階梯式”增長特征;以人口密度為門檻變量時,經濟增長對霧霾污染的正向影響在跨過門檻值后變為負向影響,呈現出倒“U”型關系;以對外開放水平為門檻變量時,經濟增長對霧霾污染的正向影響在跨過門檻值后減弱。③不同的門檻變量下,人口密度和能源消費結構與我國霧霾污染呈現出正相關關系,能源強度和對外開放水平與我國霧霾污染呈現出負相關關系,產業結構對我國霧霾污染的影響在不同的門檻變量下其作用不同且不顯著。
建議:①加快推進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我國現階段經濟增長方式仍然是傳統資源要素驅動模式,應加快經濟發展由資源要素驅動模式不斷向技術創新驅動模式的突破與轉變,使經濟發展由傳統模式向低碳產業經濟轉型。實證結果表明,經濟增長對霧霾污染的影響基本都呈現出正向作用,經濟發展不能只注重量的提升,更要注重質的提升,治理霧霾污染任重而道遠。②合理調控人口密度。在人口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要防止人口過快集聚,對人口密度過快集聚和較大的地區應進行合理的分流與布局,提高對生活垃圾的處理速度,實現人口密度增加通過提高公共交通分擔率與資源使用率等途徑緩解霧霾污染。③不斷提升科學技術水平。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治理霧霾污染必須依靠科技的力量。加大對科學研發的投入,提升技術水平,提高治理環境污染的能力,加快產、學、研結合,加快推廣新裝備、新技術的使用,實現科學技術在生產和生活中的廣泛應用。④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加大產業結構調整,積極進行產業結構升級。加快第三產業的發展,首先應控制高能耗、高污染和高排放產業的發展,淘汰落后產能,鼓勵產業實行清潔生產,制定并實施有效的綠色環保產業扶持政策,建立起低碳和清潔的產業結構體系。⑤優化能源消費結構。應逐步降低煤炭消費比重,加強水電、天然氣、太陽能、風能等替代性能源的使用,積極開發可再生能源和清潔能源,增加清潔能源的供給,促進能源體系多元化發展。通過稅費政策抑制煤炭過度消費,逐步推進減煤換煤,加大北方地區的“煤改氣”、“煤改電”。⑥合理優化外商投資。一如既往地吸引優秀外資,吸引外資不僅要看經濟效應,更要看環保效應,大力引進高附加值、低排放和低污染的外商投資項目,不斷優化外商投資結構,加大對外商投資的甄別,提高外商投資準入的質量評價標準,將霧霾污染作為新的污染指標納入到甄別優質外資的評價分析中,促進“引資”、“引智”與“引技”的有機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