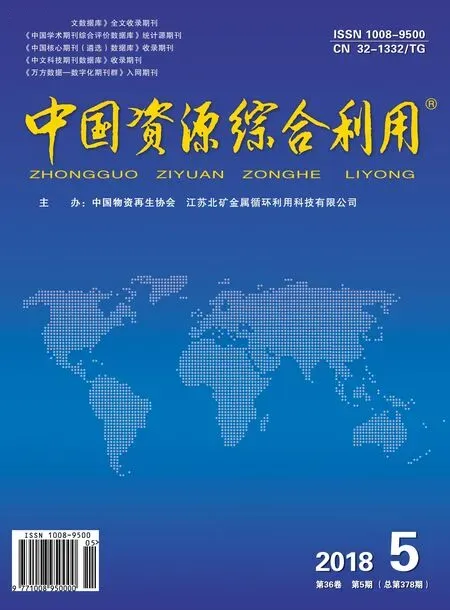陜西省土地利用碳排放總量及其效率分析
金 雯
(南京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南京 210095)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碳排放引起的全球氣候變暖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主要包括土地利用直接碳排放和間接碳排放兩種類型。土地利用類型的轉變或保持引起的碳排放屬于土地利用直接碳排放,前者如砍伐森林、圍湖造田、建設用地面積變化等;后者如農田耕作、養分投入、種植制度改變等,主要是由土地經營管理方式轉變所驅動的碳排放[1]。土地利用間接碳排放是碳排放最主要的來源,也是各土地類型上承載的人為活動引起的碳排放,如化石能源消耗、農業活動、工業過程、廢棄物、人類和動物呼吸等。
本文所研究的排放效率是指將土地開發利用和碳排放情況均納入效率評價的范疇,在投入一定量的土地、資金、能源、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之后,除經濟效益產出之外,還伴隨碳排放對環境有影響的非期望產出,引入SBM效率評價模型,計算城市土地利用過程中由要素資源投入、經濟期望產出、碳排放非期望產出之間構成的綜合效率。效率值越高,表明土地利用中資源配置越合理,經濟產出和碳排放之間的關系也越和諧。這不再僅僅是用簡單的碳排放總量、碳排放強度指標來衡量一個地區的碳排放情況,土地利用碳排放效率分析更能反映出一個城市在經濟發展中碳排放的權利以及在生態環境保護中減少碳排放的責任。鑒于此,本文以陜西省為例,在估算土地利用產生的碳排放總量基礎上,基于投入產出的角度進行碳排放效率測算,并對碳排放無效城市進行低碳優化,以期進一步完善現有土地利用碳排放的相關研究。
1 研究區概況
陜西省位于我國西北部,地處東經105°29′~111°15′、北緯31°42′~39°35′。全省縱跨黃河、長江兩大流域,是新亞歐大陸橋和中國西北、西南、華北、華中之間的門戶,具有承東啟西、連接西部的區位之便。全省土地面積20.56萬km2,下設10個省轄市和楊凌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示范區,2014年末常住人口3 775萬,GDP總值為17 640.84億元,比上年增長8.9%,居全國第15位。由于自然環境、資源基礎和發展條件等差異,陜西省形成了以北山、秦嶺為界的特色鮮明的三大片區,即陜北、關中和陜南地區。近年來,由于陜西省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大量農用地、非農用地轉為城市建設用地,對陜西省生態環境及低碳土地利用帶來了嚴重的影響[2]。
2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2.1 數據來源
土地利用數據來源于陜西省國土資源廳編制的《陜西省土地利用現狀數據集》(1999-2015),主要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建設用地4類;測算耕地、建設用地碳排放量所需的數據以及社會經濟數據來源于《陜西統計年鑒》(1999-2015)、相關國土資源局網站及統計局網站等,其中經濟類數據按2005年價格折算。
2.2 研究方法
2.2.1各類用地碳排放(吸收)量測算方法
本文主要研究耕地和建設用地的碳排放、林地和草地的碳吸收,引入如下碳排放的估算公式[3]:

式中,C為碳排放量(t);Si為第i種土地類型的面積(hm2);Ki為第i種土地類型碳排放(吸收)系數(t/hm2),吸收為負,其中耕地、林地和草地的碳排放系數分別為0.497 0 t/hm2、-0.581 0 t/hm2、-0.021 0 t/hm2。
對于建設用地,本文采用陜西省整體單位GDP能耗數值來近似代替二、三產業的單位GDP能耗數值,這在一定程度上會造成陜西省建設用地碳排放總量被低估,但有利于更清楚認識到建設用地的碳源作用[4]。引入如下計算公式:

式中,Ej為建設用地碳排放量(t);GDP′為二、三產業產值(萬元);H為單位GDP能耗(標準煤/萬元);K為煤炭消耗碳排放系數,K=0.747 6 t(C)/t。
2.2.2碳排放效率測算方法
碳排放效率測算的模型主要有基于全要素生產率的DEA(CCR和BCC)、SBM模型及基于隨機前沿分析的SFA模型等。本文將在已有文獻的基礎上,采用SBM模型來避免DEA模型的測算偏差問題,基于建設用地擴張帶來的不同時期的投入產出數據,將碳排放納入非期望產出最終采用SBM模型[5]。其公式如下:

2.2.3指標選取
本文將資本、勞動力、土地利用納入投入指標,建設用地投入帶來的土地經濟收益產出即單位碳排放放量實現GDP增加值作為期望產出,碳排放這個“壞”的產出作為非期望產出[6]。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具體統計情況如表2所示。

表1 指標體系

表2 指標統計表
3 結果與分析
3.1 碳排放時序特征分析
根據前文所述的碳排放核算清單,測算陜西省2005-2014年土地利用碳排放總量,如圖1所示。結果顯示,2014年陜西省土地利用碳排放總量較2005年增加了9 510.30萬t,增長率為268.17%,年均增長約951萬t,年均增長率為10.37%。其中,建設用地碳排放量較2005年增加了9 304.46萬t,年均增加930.45萬t,年均增長率為8.78%,可見建設用地碳排放是影響碳排放總量的主要因素。從圖1可知,從2009年開始,建設用地碳排放量呈現出明顯快速增長趨勢,這與陜西省的快速城鎮化、舊城改造以及城市大面積擴展的背景相符。總之,陜西省土地利用碳排放量在當前及未來一段時間內呈現出明顯的增加趨勢,土地低碳利用的壓力較大。
為了便于比較分析陜西省各區域土地利用碳排放的差異,將陜西省按空間劃分為:關中、陜南和陜北三大區域,各區域碳排放量的測算結果如圖2所示。

圖1 2005-2014年陜西省耕地、林地、草地及建設用地的碳排放量

圖2 2005-2014年陜西省關中、陜北、陜南地區碳排放量
圖2顯示,研究期內關中、陜北、陜南土地利用碳排放量均逐年增加,年均增長率分別為7.30%、13.46%、22.56%,陜南碳排放量的增加速度明顯高于關中和陜北,這是因為在研究期后期,陜南土地利用的碳匯優勢逐年縮小。2005-2014年,陜西省三大區域碳排放格局的差異與自身的土地利用特點和二三產業比重密切相關,因此三大區域碳排放總量呈現出關中最大、陜北次之、陜南最小的分布格局。
3.2 碳排放效率分析
基于前文給出的SBM非導向模型,運用MaxDEA軟件對2014年陜西省各市(區)的土地利用碳排放總效率、技術效率、規模效率進行測算,如表3所示[7]。其中,總效率(綜合技術效率)綜合評價了陜西省土地利用中所有資源配置、要素投入實現產出的效率高低;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揭示了在給定的要素投入條件下,土地開發利用所能實現的相對最大化產出;規模效率揭示了在技術水平不變的前提下,陜西省土地實現已有產出的相對最小化投入[8]。
在15個DMU中,僅漢中、安康、商洛3個城市為總效率有效單位,主要集中在土地利用強度較低、土地總產出不高欠發達的陜南地區;相對而言,經濟較發達的關中、陜北地區大部分城市總效率偏低,但碳排放總效率最低的為銅川市,主要表現為經濟產出不足并伴隨著過高的地均碳排放。就整體而言,陜西省碳排放效率值較低。
究其原因分析,技術效率無效是碳排放總效率無效的原因之一。技術無效表明在現有的技術水平上,投入資源的使用是無效的從而造成了資源浪費[9]。從土地利用碳排放的角度解釋,技術無效是因為在規模報酬影響下,各類資源、資金、勞動力等要素投入不僅伴隨產生了大量碳排放而且還沒有實現經濟效益產出最大化。西安、楊凌、咸陽、漢中、安康、商洛以及陜西省整體為技術效率有效,其余城市、地區為技術效率無效。7個技術有效DMU中存在3個總效率有效,技術效率有效在地域上分布比總效率有效分布更廣泛。同時,所有無效城市的技術效率均大于總效率,這表明除了技術效率無效造成總效率無效之外,與技術效率同時存在的規模效率也制約著碳排放總效率的高低。具體到土地利用差異上,西安、楊凌、咸陽土地利用高產出地區在總效率無效的基礎上實現了技術效率有效,這表明基于規模報酬可變規律,這些地區在現有建設用地利用管理水平下,社會經濟要素的投入能夠實現單位碳排放帶來的GDP增加值最大。其余土地利用低效產出區與總效率特征保持一致。

表3 DMU
對陜西省各城市進行碳排放規模效率分析,規模效率是由于地區規模因素影響的生產效率,規模過大或過小都將導致平均投入的增加,因此可以通過規模效率來判斷研究區域是否處在最適規模。漢中、安康、商洛為規模效率有效單位,在分布上與總效率有效一致,即總效率無效的地區,其單位規模效率一定無效。相比較于技術效率,實現規模效率有效要更加困難。陜西省土地利用碳排放規模效率有效的單位為技術效率有效的一半,在規模效率下結合規模報酬區間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漢中、安康、商洛處在規模報酬不變階段,即為總效率有效的3個城市。寶雞、關中地區、西安、渭南、楊凌、咸陽、陜南地區以及陜西省整體處在規模報酬遞減階段,可以通過控制建設用地碳排放量的增長或者縮小碳排放規模來提高這些地區的碳排放規模效率。銅川、延安、陜北地區、榆林處在規模報酬遞增階段,相比規模報酬不變與遞減地區,處在規模報酬遞增階段的地區較少,因此可以通過擴大土地利用碳排放規模來有效改善這些地區的規模效率。
4 土地利用碳排放效率低碳優化
4.1 土地利用碳排放低碳優化結果
本文將“碳排放效率的相對有效”(效率值為1)定義為實現了土地的低碳利用,低碳優化則用來解決碳排放總效率無效城市存在的投入冗余與產出不足問題。固定規模報酬下的SBM模型將同時給出各地區實現碳排放總效率有效時的投入產出改進值,如表4所示[10]。投入冗余表明,同總效率有效的陜南三市相比,在產出保持不變的前提下,該地區可以減少要素投入量;期望產出不足表明,在投入保持不變的前提下,單位碳排放實現GDP增加值可增加量;非期望產出冗余表明,在投入保持不變的前提下,可以減少的碳排放量[11]。
4.2 土地利用碳排放低碳優化對策
由表4可知,作為參照改進的地區為陜南的3個城市,碳排放總效率相對有效的城市要素投入與產出不需做優化,其他無效城市則需在土地、資本和勞動等要素投入不變的情況下,增加經濟產出的同時減少碳排放;或是在保持產出不變的情況下差別化地減少要素投入,以實現資源的有效利用和最優配置。關中地區人力資源和技術力量相對雄厚,制造業發展良好,是陜西省最為重要的經濟社會重點發展區域;其所包含的6個城市地均固定資產投資減少幅度均較大,這可能是由于重復建設現象嚴重,因此要減少相關的固定資產投資額[12]。同時,R&D(Rearch and Development)經費也需要減少投入,這說明R&D經費的投入并沒有帶來高效率的產出轉化,因此關中地區需要建立相關的績效考核制度,以求實現技術效率的提高,降低單位二、三產業產值的碳排放量,尤其像銅川、寶雞、延安等城市,技術效率不足是造成總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西安、銅川等城市人口相對密集,可控制農村勞動力對本城市轉移并鼓勵農村勞動力向外省輸出,在控制勞動力數量的基礎上努力提高勞動力的素質,培養高新技術人才。同時,政府應大力發展環保產業,推廣大型環保節能裝備,提倡資源綜合循環利用和清潔能源的使用,制定有效引導支持低碳綠色發展的激勵和配套政策。

表4 2014年陜西省城市土地利用投入產出改進值
陜北地區能源化工業發展迅速,生態環境相對脆弱,因此陜北地區應該繼續實施退耕還林、還草政策,在鞏固現有耕地、林地和發揮碳匯作用的基礎上,鼓勵種植碳吸收能力較強的樹種并培育優勢樹種種植,建立低碳經濟林區。從減少碳源的角度來看,其所包含的延安、榆林兩城市應該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強化節能減排;陜北地區太陽能、風能資源豐富,因此應該加快太陽能、風能、水能等新能源的開發并進行產業化發展,同時加強生態環境的保護和治理工作。
陜南地區在陜西省內相對而言生態環境優越,水力資源富集,在本研究的效率測算中也是相對有效,應繼續加強生態建設,在發揮現有碳匯優勢下進一步挖掘其碳匯潛力,加快水力資源的梯級開發,努力發展綠色產業。
5 結論
本文以陜西省15個城市、地區(含陜西省整體)為研究對象,計算了陜西省2005-2014年土地利用總體碳排放量,并基于投入-產出角度構建了SBM模型,估算了2014年各城市、地區土地利用的碳排放總效率、技術效率與規模效率,并對總效率小于1的碳排放無效城市、地區給出了優化方案,得出如下研究結論。
2005-2014年,陜西省的碳排放總量呈現總體增長的趨勢。其中,建設用地碳排放是影響碳排放總量增長的重要因素,三大區域碳排放量呈現出關中最大、陜北次之、陜南最小的格局。整體而言,陜西省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碳排放量還將持續增加,區域內土地低碳利用的壓力較大。
2014年,陜西省整體碳排放效率值較低。其中經濟相對較發達的關中、陜北地區碳排放總效率無效,碳排放效率最低的為銅川市;土地利用強度較低、土地總產出不高的陜南地區三個城市碳排放總效率有效。西安、楊凌、咸陽、漢中、安康、商洛以及陜西省整體為技術效率有效,其余城市、地區為技術效率無效。漢中、安康、商洛為規模效率有效單位,在分布上與總效率有效一致。
為實現陜西省土地低碳利用,陜南地區需繼續加強生態環境建設,發揮碳匯作用。關中和陜北地區則需采取措施、制定相應的政策,減少投入強度及非期望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