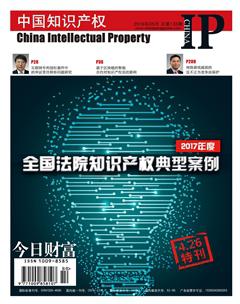網絡游戲畫面的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
吳子芳
筆者之前就網絡游戲畫面的《著作權法》《商標法》等知識產權專門法的保護已撰文探討,在《反不正當競爭法》部分未展開。寫下本文題目的時候,筆者有些猶豫,該提“網絡游戲畫面權利人如何制止不正當競爭行為”,還是直接如題談“保護”1。為了使本文標題看起來精煉簡潔,筆者仍以本文題目撰文就網絡游戲畫面的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問題進行梳理。
筆者曾在《網絡游戲畫面的知識產權保護》一文中,就網絡游戲畫面可受《著作權法》《商標法》等專門知識產權法保護的情形進行了梳理。實踐中,網絡游戲權利人對于網絡游戲畫面的保護訴求是多多益善,很多人將《反不正當競爭法》看成是知識產權法的兜底法、補充法,凡是認為對方游戲中出現了己方知識產權的影子,拿不準或納不進知識產權專門法保護的時候,第一想到的就是《反不正當競爭法》。
網絡游戲畫面主要由聲音、線條、色彩、圖案、動畫特效等視聽元素組成,除了畫面整體可能構成一個獨立的類電影作品外,分割游戲畫面的結果就是游戲畫面被分成眾多美術作品、文字作品、音樂作品或商標,以及無法獲得專有權利保護的元素。《反不正當競爭法》要關注的正是這些無法獲得專有權利保護的元素,并制止他人惡意模仿抄襲。
事實上,由于《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專門法律已經對現行法定的專有權利給予了保護,留給《反不正當競爭法》適用的空間相對有限。
涉及網絡游戲畫面的不正當競爭類型化行為常見情形
我國1993年12月1日起施行的《反不正當競爭法》類型化條款中,網絡游戲畫面可能涉及的不正當競爭行為類型包括:
第五條仿冒。其中常見的主張是第(二)項仿冒他人知名商品特有名稱、包裝、裝潢。
第九條虛假宣傳。大多發生在被告游戲的啟動畫面中存在引人誤解的宣傳內容,如“**游戲口袋版”“***電視劇同名手游”。
2018年1月1日起施行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對類型化條款進行了較大調整,網絡游戲畫面可能涉及的不正當競爭行為類型包括:
第六條混淆。其中第(一)項擅自使用與他人有一定影響的商品名稱、包裝、裝潢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標識,第(三)項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響的域名主體部分、網站名稱、網頁等,第(四)項其他足以引人誤認為是他人商品或者與他人存在特定聯系的混淆行為。需要注意的是,新法已經將舊法仿冒條款“知名商品”中的“知名”改為“有一定影響”,而且“知名”也不再限定“商品”,而是限定商品名稱、包裝、裝潢等被混淆對象。
第八條虛假宣傳。第一款基本保留了舊法中對虛假宣傳的規定,第二款在立法解釋的時候主要提及是為制止惡意刷單行為。涉及網絡游戲畫面的虛假宣傳糾紛中,是否會出現類似于惡意刷單的行為,筆者認為目前就有限的案例下結論還為時過早。
第十二條互聯網專條。第一款經營者利用網絡從事生產經營活動應當遵守反法的各項規定,該款可以認為是規范網絡經營者的原則性條款。第二款所列舉的各項行為都以使用技術措施為前提,在涉及網絡游戲畫面的不正當競爭案件中,只有被告使用了相關技術措施,才可能適用第二款項下的各項規定。
以上類型化條款的列舉可見,新舊反不正當競爭法中可適用于網絡游戲畫面的類型化不正當競爭行為條款,主要為制止混淆(仿冒)特有標識、作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
第一,制止混淆。制止混淆的對象是特有商業標識。能起到區分商品和服務來源作用的商業標識,可視為未注冊商標。在網絡游戲畫面中,此類標識即使不是注冊商標,一般也是在游戲畫面中反復出現或在每次啟動游戲時出現的標識,在游戲玩家中具有很強的識別度。網絡游戲有一定影響的名稱比較容易理解,網絡游戲有一定影響的包裝、裝潢的認定在實踐中會出現很多爭議。由于網絡游戲作為一種在線無形產品和服務,是否存在傳統商品的包裝、裝潢就有爭議。著名的“王老吉”“加多寶”案中,大家所關注的是紅罐涼茶包裝裝潢該歸誰所有,但對 “紅罐”為主體的訴爭對象是否應該作為包裝裝潢并無爭議。“爐石”案中,原告主張爐石標識、單個戰斗場地界面、382張卡牌都構成其知名游戲特有裝潢,但法院認為這些畫面內容是“游戲運行過程中才能逐漸展示給相關公眾的”,由于原告游戲向中國公眾開放距被告游戲僅早兩日,因此,原告游戲中的這些畫面內容無法“為相關公眾所普遍知曉,更難以具備區別商品來源的功能”。另外,也有一些案件中法院認為包括游戲地圖等畫面內容屬于游戲本身的組成部分,而非游戲包裝或裝潢,從對象屬性上直接給予否定。當然,也有一些案件中法院將游戲APP圖標認定為該游戲的裝潢,筆者贊同此種認定。游戲APP圖標一般情況脫離于游戲本身,其指示來源的識別作用更強,該圖標或者能以美術作品尋求著作權法保護,或者以游戲裝潢來制止他人惡意模仿。
第二,制止虛假宣傳。虛假宣傳是網絡游戲案件中常見的原告訴求,大部分案件中原告總能找到一些被告有意搭便車、做比較、突出強調被告游戲特色的不實宣傳。當然,針對網絡游戲畫面中的虛假宣傳內容,這種情形則不多見。由于網絡游戲畫面本身主要用于向玩家提供可玩的游戲內容、展示游戲進程,其中的部分畫面或畫面元素明顯用于宣傳推廣或廣而告之作用的較少。
同時,筆者注意到,法院在一些案件中對被告未經許可使用原告的商業標識認定為構成虛假宣傳。比如在“斗魚”案中,二審判決認定:“本案基于涉案賽事知名度高、影響力大,公眾知曉涉案賽事由火貓TV舉辦并獨家轉播,上訴人未經授權許可直播涉案賽事,卻在直播頁面采用標明火貓TV、MarsTV標識之引人誤解的方式,足以造成相關公眾產生上訴人系涉案賽事合作方或者上訴人直播已獲授權等誤解,從而誤認為上訴人的直播行為來源正當合法,以致會吸引更多觀眾和流量,損害被上訴人的合法權益,構成虛假宣傳”2。由于舊法仿冒條款針對的被仿冒對象較為有限,如果按新法,有一定影響的商業標識都是可被禁止混淆的對象。該案中的被告行為是否可以直接適用第六條禁止混淆條款,而無需再用虛假宣傳條款?筆者認為可以直接適用禁止混淆條款,而無需再用虛假宣傳條款。
涉及網絡游戲畫面的適用原則條款的不正當競爭行為
很多網絡游戲侵權案件中,原告分割主張網絡游戲畫面中的部分內容時,該如何選擇法律適用并不清楚,可能出于擔心僅主張《著作權法》等專門法無法獲得支持,就采用討巧的策略同時主張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但對照《反不正當競爭法》有限的類型化條款又不十分確定,轉而尋求適用原則條款。
往往這種情形時,雙方的爭議會非常大。李琛教授在2017年度AIPPI中國分會版權熱點論壇的發言談及“應對著作權新問題的解釋方法”中,就“爭議過大時的謹慎處理”一節提到:“如果爭議大到無法判斷立法取向的話,可以選擇一個方向,但要慎重。比如說像有些侵權本身爭議很大的時候,至少能夠推斷出當事人對自己行為的惡性程度認識的不是很清楚,因此判處巨額的損害賠償可能就不是很妥當。爭議極大時的另一個處理原則是,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優于司法賦權。如果法律上認識得不太清楚,那么歸入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意味著僅僅只是個案的判斷,但是如果很明確地去賦予一個法律所沒有規定的權利,那這個影響就超越個案而具有普遍性了。”
筆者非常贊同李琛教授的觀點,《反不正當競爭法》的適用僅代表個案判斷,如果無法歸入專有權范圍進行規制,但被告行為的惡意非常明顯,有必要制止以保護原告的合法權益,并維護市場秩序的時候,法院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就再正常不過,也是給予原告訴求以正當合法解決路徑的表現。所以,筆者并不贊同一些學者談及法院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言必稱過度適用原則條款、“從一般條款向原則條款逃逸”等的觀點。
如上文分析,涉及網絡游戲畫面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可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類型化條款的情形非常有限,難以解決實踐中層出不窮、類型多樣的惡意搭便車行為。比如,《大武俠物語》案3中,被告游戲使用了金庸武俠小說中的多個人物名稱,在難以適用《著作權法》規制時,法院最終支持了原告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進行規制。
目前,網絡游戲權利人對于被告游戲抄襲模仿的訴求,已經從簡單的角色形象、對話文字、配樂等顯而易見的知識產權專有權控制對象,延伸到游戲規則、地圖架構、積分設計等更為抽象、隱蔽,且非顯而易見甚至是非可視化的對象。對此,筆者認為,需要分清楚“模仿自由”和“不正當競爭”的界限,“模仿是學習和創新的基礎,自由模仿就是自由競爭,但一些危害競爭的過度模仿,則需要以不正當競爭進行遏制。自由競爭或者自由模仿是原則,構成不正當競爭是例外”4。如果僅是積分規則相同,一般會認為屬于自由競爭的范疇,就像國航給用戶按里程積分,南航也會給用戶按里程積分,二者僅是積分規則相同并不會損害市場競爭秩序,沒有經營者可以為自己創設的簡單積分規則要求獲得壟斷的權利。
當然,如果除了積分規則外,其他的游戲畫面元素也能讓玩家明顯感受到兩款游戲存在相同或關聯之處,明顯體現出在后游戲有意“山寨”模仿的情節,那么通過《反不正當競爭法》加以制止亦是該法應有之功能。需要強調的是,在適用該法原則條款的時候,一定要突出強調被告行為具有主觀惡意,且這種惡意一定有明確的證據給予證實。
由于現行《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十二條原則條款的第一款在對網絡不正當競爭行為進行規制時,已經具備了舊法第二條原則條款的作用,因此,此后網絡游戲畫面所涉及的非類型化不正當競爭行為,可能會更多適用互聯網專條的第一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