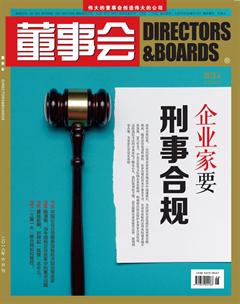未雨綢繆,遠離刑事陷阱
葉曉華
中國企業家面臨的刑事法律風險,范圍之廣,種類之多,情況之復雜,引發世人關注。在我們討論如何防范和管理這些刑事法律風險之前,還是先普及一下那些容易被忽略的且在書本輕易學不到的企業刑事法律風險的基礎知識。
書本學不到的“基礎知識”
企業家很多時候,會在稀里糊涂之中為下屬直接導致的犯罪行為承擔刑事責任。如果不了解企業中的哪些事可能涉及刑事法律風險,想當然地簽了不該簽的字,或是下了不該下的命令,就有可能將自己置于危險的處境。例如重大安全事故罪,如果企業家不懂專業又不深入了解情況,在下屬請示在有安全之虞、但工期緊急、是否強令有關人員違規作業時,表示同意,則一旦出現重大安全事故,企業家就會惹上無妄之災。
單位犯罪。除了人,單位也會犯罪。對于單位犯罪的懲罰,一般是兩罰制,既罰單位,也罰個人。對個人的懲罰一般是追究對單位犯罪行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所以企業家千萬不要認為讓其他人去實施單位犯罪行為就可以逃脫罪責。
企業家沒有違法犯罪不等于沒有刑事法律風險,不等于不會承擔刑事法律風險的后果。當企業家被誣陷或是疑似有違法犯罪行為,但實際上沒有違法犯罪的情況下,盡管最后企業家可能被無罪釋放,但是企業這時可能已經跨了,企業家該坐的牢也坐了,就算有國家賠償,國家還能給你的早餐賠出鮑魚錢嗎?沒有犯罪行為,卻在實際上承擔了刑事法律風險的后果,這樣的事在實踐中屢見不鮮,劉曉慶偷稅漏稅案就是典型一例。劉曉慶被舉報偷稅漏稅,檢察院最后認定其個人并沒有犯罪,犯罪的是她的公司,因此沒有起訴劉曉慶,但劉曉慶卻在獄中待了422天,出獄之后,個人聲譽一落千丈,事業也落入低谷;直到今天,人們提及此案都使用了劉曉慶偷稅漏稅的字樣,這樣的刑事法律風險的后果劉曉慶一直都在承擔,無法擺脫。所以,企業在防范和管理刑事法律風險的時候,不能忽視這種情況的存在。事實上,惡意的刑事犯罪的舉報,毀掉的企業和企業家絕不是一個小數字。
同樣的犯罪行為,如果是單位犯罪,所受懲罰要輕得多。例如個人犯受賄罪的,最重可以判處死刑,但根據刑法第387條規定:“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情節嚴重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由此可見,在單位犯受賄罪的情況下,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判處的刑罰遠輕于個人犯受賄罪的情況。
刑事法律風險是可以管理的
現在我們可以開始討論如何防范和管理企業刑事法律風險了。
首先要解決的是態度問題,對中國企業家而言,這個問題尤其重要。在刑事法律風險爆發之前,很少企業家會真正關心這個問題,爆發之后又誠惶誠恐,這樣的態度顯然無法實現對企業刑事法律風險進行科學的有效的管理。要端正態度,靠他人的說教用處不大,只有企業家自己深刻體會到企業刑事法律風險一旦爆發,對企業家自身以及企業的危害有多大,才有可能真正端正態度,重視企業刑事法律風險的事前預防工作。在這種態度下,一切企業刑事法律風險防范和管理的工作才會變得有意義。
其次,要相信企業是可以對刑事法律風險進行有效管理的。很多企業家擔心,有些法律風險識別出來了,但卻無法避免,徒增煩惱,與其這樣,還不如不識別,圖個心情愉快。但問題是,法律風險還沒有被識別出來,你怎么知道就不能防范和管理?你可能會說,有些你已經知道的刑事法律風險就是無法避免,但問題是,你不知道如何防范,你怎么知道專家就不知道如何防范和管理?事實上,很多解決的方法和方案遠遠出乎你的意料。例如,在看似潛規則橫行的行業中,遵紀守法并不一定總是吃虧,使用管理的方法我們完全有可能繞開刑事陷阱,并取得競爭的優勢。
再次,即便因為種種原因,企業無法做到完全地遵紀守法,無法去阻止刑事法律風險的發生,那也一定要搞清楚哪些刑事法律風險會給企業和企業家帶來重大的或是無法承受的后果。就算死,也不能死的不明不白不是?何況不能阻止法律風險的發生,不等于不能采取積極的應對措施,降低法律風險爆發后的不利后果。
值得一提的是,刑事法律風險防范與法律風險管理是兩個概念,前者更多地是就罪論罪,更多地使用法律方法來解決刑事法律風險的預防問題,而后者是用管理的手段來解決企業面臨的刑事法律風險。例如紫金礦業的污染環境犯罪,前者提出的建議可能是不顧成本地要求對有毒污水做無害化處理,后者的做法則可能是優化商業模式,用新的方法替換容易導致污染的黃金提煉工藝等,一勞永逸地解決懸在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兩者的區別還在于,后者還會區分企業刑事法律風險輕重緩急,并在此基礎上,對企業刑事法律風險防控資源進行分配等等。從廣義上說,刑事法律風險防范是刑事法律風險管理的一部分。
因企制宜打造有效防控體系
態度和認識問題解決了,那么應該如何建立企業刑事法律風險防控與管理體系,實現對其有效的管理呢?
其一,系統地識別是有效管理的基礎。企業刑事犯罪的罪名看起來有限,對犯罪行為的界定,理論上也很清晰,然而一旦具體到具體企業的具體犯罪行為,其中的變數就會大大增加,罪與非罪的界線也會變得模糊。僅僅靠律師或是法務人員的經驗,未能識別潛在重大刑事法律風險行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此必須要有結構化的識別模型,將這種遺漏的可能性盡可能地降低。
識別中應當注意很多犯罪行為都有明顯的行業屬性和企業自身特點,例如中介服務企業不太可能犯重大安全事故罪,但煤炭生產企業犯該罪的可能性就很大,有些罪名只有上市公司高管才可能觸犯,有些罪名只有國企高管才可能被追究刑責。因此,不深入企業,不了解企業在實踐中是如何經營管理的,很多潛在的重大刑事法律風險就無法被識別。
識別的內容還應該包括犯罪的動機。同樣是犯罪,民企老板犯罪與單位犯罪大都是為了企業的利益,但國企高管或是民企的職業經理人犯罪可能就不是。所以,只知道在企業的某個領域可能會有犯罪,不知道為什么要犯罪,企業就很難采取真正有效的防控和管理措施應對刑事法律風險。
其二,準確地評估是有效管理的前提。企業刑事法律風險的后果可能不僅僅是刑法中規定的內容,其引發的間接法律后果可能更加嚴重。例如身為實際控制人的民營企業家被抓坐牢,很可能意味著企業從此一蹶不振,因為他們對企業而言不可或缺。如果只是職業經理人被抓,企業受到的影響可能只是暫時的,再找一個就是。所以在評估一個刑事法律風險對企業的影響時,要將刑法規定的懲罰與企業的實際情況聯系起來,才能得到準確的答案。
其三,科學地評價是提出法律意見和管理建議的基礎依據。僅僅對企業具體刑事法律風險作出準確地評價還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將這種評估與企業整體的目標和發展戰略聯系起來,我們才能夠對每一個企業刑事法律風險對企業的最終影響作出科學地評價,才能在此基礎上針對性地提出每一個企業刑事法律風險的法律意見和管理建議。
第四,科學合理地制定行之有效的防控和管理計劃是企業刑事法律風險管理體系最終的落腳點。對每一個刑事法律風險的科學地評價以及相應的法律意見和管理建議,可以讓我們在分清企業所有被識別出來的刑事法律風險輕重緩急的同時,估算防控和管理企業刑事法律風險的成本和代價,從而為科學合理地制定防控和管理計劃,合理分配企業資源的打下堅實的基礎,最終實現對企業刑事法律風險的有效防控和管理。
總結說來,建立這樣的防控體系,要求根據企業的實際情況,從企業經營管理的業務流程入手,系統全面地識別、評估、評價企業刑事法律風險,建立動態的企業刑事法律風險數據庫,并與具體的崗位聯系起來,對其中的每一項刑事法律風險都要給出明確的法律意見和管理建議,并在上述工作的基礎上,制定企業刑事法律風險的防控和管理計劃。
警惕企業法律風險新動向
建立了上述企業刑事法律風險防范與管理體系,不等于萬事大吉,企業還應該隨時關注企業刑事法律風險的動向,尤其是那些與自己的企業以及企業所在行業密切相關的刑事法律風險。近年來,值得關注的企業法律風險動向主要有:
創新領域的刑事法律風險。在創新受到鼓勵的年代,違法創新成為所謂商業模式創新的主要來源之一。
2012年5月案發的北京巨鑫聯盈科貿有限公司非法集資案就是典型一例,2014年8月6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朱梓君等13人,非法吸收4萬余人26億余元存款案依法作出一審判決。法院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判處朱梓君等13名被告人2年6個月至10年不等有期徒刑,并處10萬至50萬元不等罰金。該案與一般非法集資案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是以銷售商品、“聯合加盟方案”為依托,通過“返利模式”,即讓消費者參與銷售分配為主要賣點,經由網絡、推介會等途徑,拉會員加盟收取加盟費。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一般是指未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承諾在一定期限內還本付息的行為。返利銷售法律上是允許的,盡管這一返利模式與合法商家通常所采模式不同,但與典型的“還本付息”型吸收公眾存款仍存明顯差異。因此,該公司法人代表朱梓君在庭審中提出,公司在經營過程中存在實際銷售行為,其“返利模式”與直接基于本金給付高息的非法集資不同,其行為性質屬創新投資模式,不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然而朱梓君等最終還是被判有罪,其原因在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做了較為寬泛的解釋,“借用合法經營的形式吸收資金”、“承諾在一定期限內以貨幣、實物、股權等方式……給付回報”(不限于“還本付息”)等行為方式都可以被解釋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這導致任何未經批準面向不特定公眾融資的“創新”都可能面臨巨大刑事風險。
這一案例,起碼提醒了企業家一個明白無誤的道理,搞商業模式創新,必須去評估這種創新是否有法律風險,如果創新帶來的收益小于其帶來的法律風險成本,甚至帶來刑事法律風險,那么,這種創新就是一種偽創新。
環境犯罪:越勒越緊的緊箍咒。
我國1997年修改的刑法中首次規定了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但被真正追究刑事責任的企業家并不多。近年來,隨著國家環境政策的收緊,對環境犯罪的打擊力度空前加大。
這不僅僅表現在201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中,取消原"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罪名,改為"污染環境罪"。觸發本罪不再要求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嚴重后果,只要嚴重污染環境就可成立此罪。
同時表現在對污染環境罪的追究力度空前加大,被追究刑責的企業家接二連三,就在前不久輝豐股份連續發布公告稱公司董事、副總經歷季自華,子公司華通化學法定代表人、董事長、公司副總經理奚圣虎,子公司江蘇科菲特生化技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朱光華相續被指控犯污染環境罪被公安部門采取措施。這樣密集的追責,傳遞的信息非常明確:必須嚴格遵守環保法律法規,不能再去玩內部成本外部化的游戲,或是繼續漠視企業對環境污染,否則后果自負!
安全領域的刑事法律風險爆發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不論是安全生產領域還是食品安全領域,國家對安全領域犯罪的打擊從來就沒有手軟過,但是這些年來,因安全領域的犯罪被刑拘判刑的企業家卻明顯增加,個中原因在于隨著新媒體的發展,特別是微信等自媒體的廣泛應用,一旦企業出事,企圖掩蓋事實控制局面的可能性幾乎為零,企業家和其企業被追究刑責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這樣的犯罪不再會有僥幸的存在,這一新的動向也在告誡企業家對安全領域的刑事法律風險一定要給予充分的重視。
老賴入刑的僵尸條款復活。
比環境犯罪入刑更早,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早在1979年的刑法中就有規定,但被追究此罪的企業家很少很少,這一條款基本上相當于僵尸條款,即便在執行難成為中國司法痼疾的時候也很少被執行。新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條同1979年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條相比,作了重大修改,即不再以是否用“暴力、威脅方法阻礙依法執行公務”為必要條件。只要當事人有執行能力,而拒不執行,且情節嚴重的,即可依本罪處罰。2018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自訴案件受理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首次允許當事人通過自訴的方式要求人民法院追究此罪,這一通知意味著老賴入刑的僵尸條款將徹底復活。考慮到中國法院判決裁定的自覺履行率很低,企業家因此可能導致的犯罪估計將大幅上升。
企業刑事法律風險的家長里短,是是非非,如何防控,如何管理,如何實現風險控制與企業發展的雙贏,不是一篇文章可以解決的。但我相信,不論企業刑事法律風險防范和管理的能力有多高,遵紀守法永遠是最好的選擇。
世事變遷,草莽不再英雄,只有尊重法律和規則,認真對待無處不在的刑事法律風險,識別、評估、評價,并有效防控、管理這些法律風險,企業家才能擺脫草莽的氣息,像紳士一樣,去玩財富大冒險的游戲,確保自己和企業在刑事陷阱密布的市場中游刃有余,為企業基業長青筑下最基礎的一道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