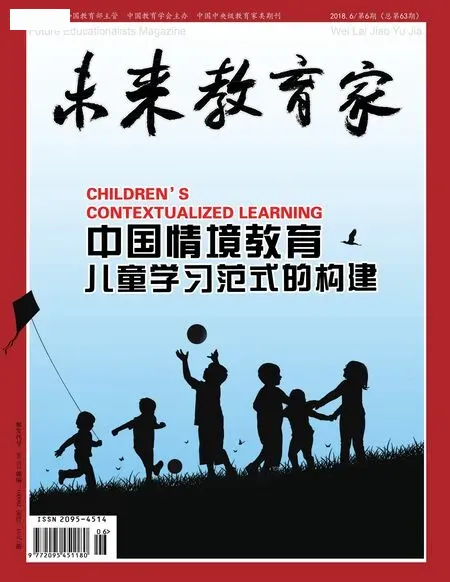聽到孩子

專欄 教育十八拍
欄主 李茂
LI MAO
學校創新研究者和咨詢顧問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碩士,多年教育媒體與譯介經歷,研究領域包括教育哲學、教育設計、學校變革、課程研發、教師成長等
著作(譯著):
《在與眾不同的教室里:8位美國當代名師的精神檔案》《每個孩子都愛學:美國KIPP學校的奇跡》
《今天怎樣管學生:西方優秀教師的教育藝術》
《可復制的教育創新——改變世界的重要力量》
在中部某省一所鄉村學校的開放活動中,我被貼滿了孩子們畫作的幾個展板所吸引。我主動與站在展板前面準備向來訪者作介紹的一位看上去四五年級的女孩聊起來。我問這里面有沒有她的畫,她很高興地指出了她的畫作,其中一幅荷花真的畫得棒極了。于是,我跟她有了以下對話。
A:小朋友,這幅畫你最喜歡什么地方?
B:(指著有花蕊的地方),我最喜歡這朵花。
A:為什么呢?
B:因為我最喜歡月季。
A:月季?但你畫的好像是荷花啊?
B:我畫的時候想象它是月季。
A:是嗎?
B:老師說,可以照著畫,也可以想象著畫。我畫的時候就想象它是月季。
A:哦,那你很喜歡月季吧。是你們家種了月季,還是在哪里看到過月季呢?
B:是我哥哥家的月季。
A:哥哥在哪里呢?
B:哥哥在廣州。
A:哦。哥哥是在上學還是在工作呢?
B:哥哥在上學。
A:那是你爸爸或媽媽在廣州嗎?
B:哥哥跟表姐住一起。……我沒有爸爸。
……
對于這突如其來的答案,我完全沒有心理準備。我趕緊給了她我能給出的最真誠的鼓勵和贊美,并把她遞給我的一張反饋表格填寫完畢,交還給她。看著她依然陽光的臉龐,我才略微放心地跟她說了再見,挪步到旁邊的展板。
真的沒想到一幅畫的背后,藏著孩子內心深處最難以覺察的情感。那位讓他們在語文課上畫畫的老師,讓他們想象著畫的老師,真的很了不起,他無意中幫助孩子實現了一次自我情感的表達,這樣的表達原本可以無人知曉。
這次活動之前,我跟學校老師商量,我們可不可以把這一天變成孩子們跟成年人的一次交流機會。這是一所只有一百來個學生的鄉村小學。學校就在村子里,雖然談不上多么偏僻,但孩子們很缺乏與外面世界的交流。既然那一天會從全國各地來很多參觀者,為什么不可以把這些來訪者變成孩子們的一個資源呢?
于是,學校不僅安排了學生在展板前面負責講解,還特意設計了反饋單,讓他們以此為媒介,與來訪客人有更深入的對話。此外,還做了另一個安排,讓一個小分隊的學生主動采訪來賓,有負責向來賓提問的,還有負責用pad記錄影像的。所以,在活動現場,我們可以看到在不大的校園的好多處地方,來賓跟學生一起熱烈交談的情景。
在后來研討的時候,不少來賓說,沒想到這所村小的學生這么自信,表達能力很強。其實,很難說這是因為學校此前在這方面有什么特別的培養,更多僅僅是因為孩子們有一個機會把他們的自信和表達能力展現出來。或許他們的自信和表達能力與城里的孩子相比還是有一定差距,但看來并沒有我們想象中那么弱。當然,關鍵的不是一個強與弱的評價,而是孩子們獲得了一次難得的機會。
孩子們需要與成年人真正對話與交流的機會。不只是課堂上關于知識和學科的問答,而是真正走進對方、了解對方、關切對方的對話和交流。如果他沒有被走進過,沒有被真正了解和關切過,或者,沒有人讓他走進過,沒有讓他有機會去了解和關切過,那么,他的情感與內心世界,該如何生長呢?
教師們每天走進學校,很長時間跟孩子們同處一室,但很多時候只是“看見”孩子,而沒有真正“看到”,只是“聽見”孩子,而沒有真正“聽到”。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為孩子們創造更多這樣的機會呢?不是所有鄉村學校都有機會被這樣“走進”,對于這所學校來說,這樣的活動也非常態。我們可不可以主動地為孩子們辦一些開放日,專門為他們的各種作品和表演請來觀眾,觀眾們不僅僅觀看,還要近距離地跟孩子們聊一聊,真正聽聽他們是怎么想的,讓他們有機會對一個陌生人開口說話,哪怕只是練一下膽量也好。
我們可不可以把家長會做得像一個節日,讓走進校園里的爸爸媽媽、爺爺奶奶都來為孩子們的進步和作品喝彩。同樣,要安排出專門的時間,讓孩子與成年人有更多的對話與交流。孩子們是家長會的主角,他們自己來匯報,自己來講述,他們自信地接受提問,自信地對跟前的成年人說,“叔叔/阿姨,能向您提幾個問題嗎”。
在那天的活動現場,那位給我介紹的畫荷花的小姑娘,一直在操場的一邊等著來訪者走過來。天氣比較熱,但還不至于一刻都不能在太陽下待。但很多人都在一旁的陰涼處站著,顯得操場的另一邊格外冷清。那時候我真希望走過去的老師能更多一些。是的,你會感到很曬,但想到有機會為這些鄉村孩子送上你溫暖的目光和贊許的話語,你一定會感到,這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