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路癡的“找路”人生
Tera Kir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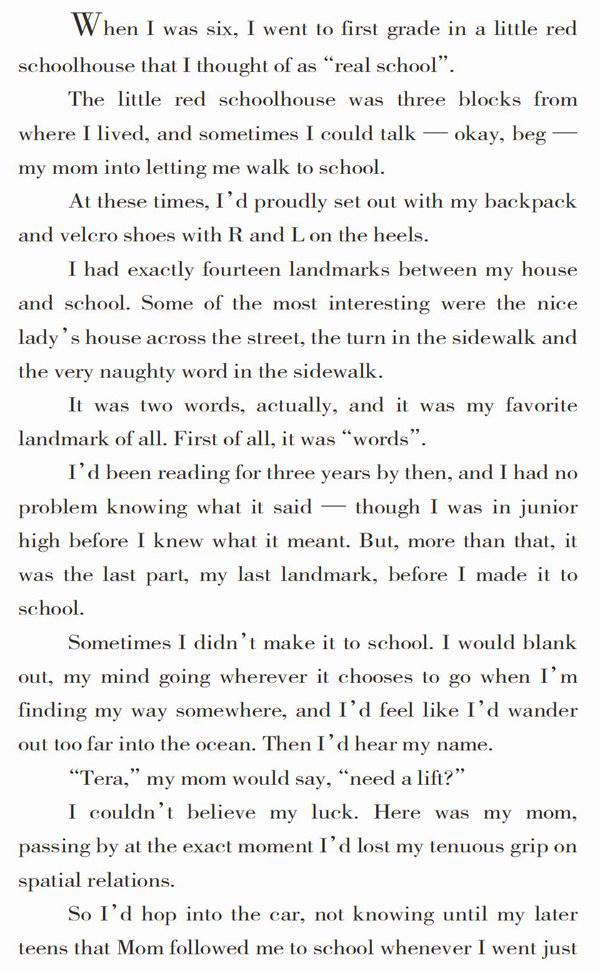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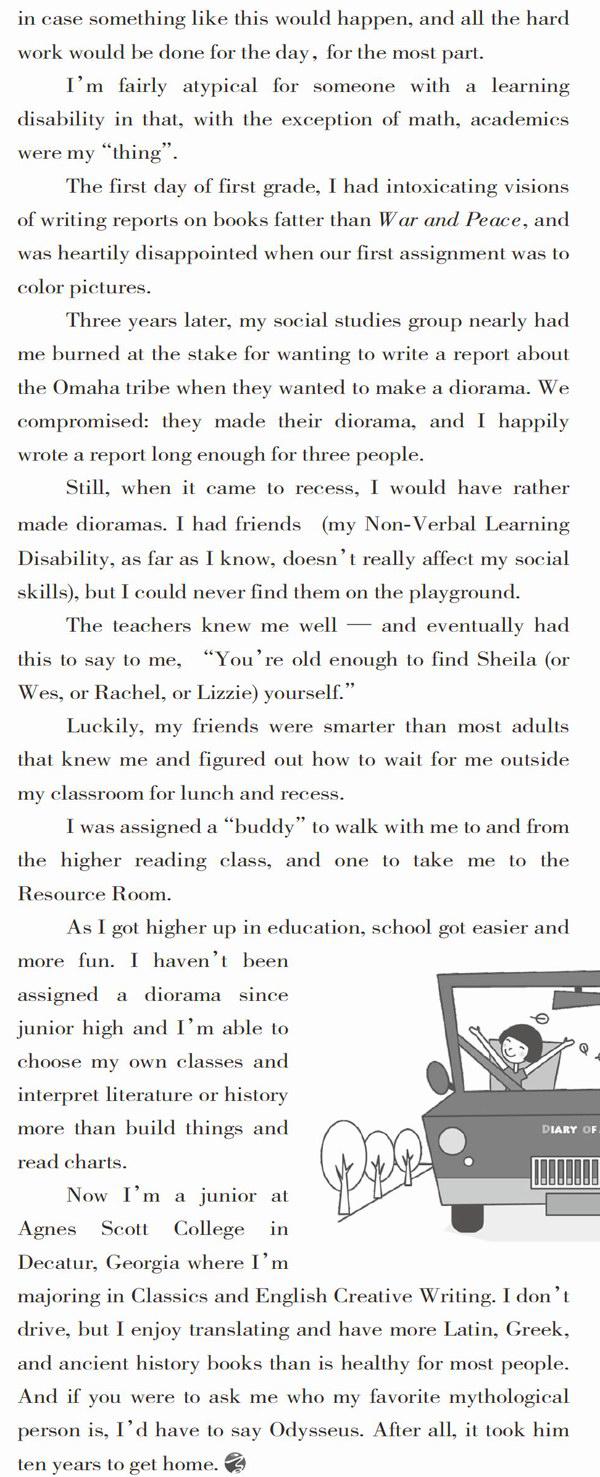
六歲的時候,我去一個很小的紅色校舍里上一年級,我覺得那是所“真正的學校”。
那個紅色的小校舍和我住的地方隔著三個街區。有時候,我會說服——好吧,是央求——媽媽讓我走路去上學。
在那些日子里,我會驕傲地背著雙肩包出發,腳上穿著一雙魔術貼童鞋,鞋跟上還標記著“左”和“右”(編注:作者是一個非語言學習障礙患者,這類人群在語言上有優勢.但可能在視覺空間和社交技巧上有障礙)。
在家和學校之間,我有不多不少14個地標。其中最有趣的幾個是:街道對面的好心太太家,人行道的拐彎處以及路邊人行道上出現的那個非常不文明的詞語。
實際上,那是兩個單詞,是我最喜歡的地標。首先,那可是“詞語”呀。
那時我已經學習閱讀三年了,認出這兩個詞毫不費力——盡管我在上初中后才了解它的意思。但是,更重要的是,那是這段路的最后一截,是我上學路上的最后一個地標。
有時候,我沒能走到學校。我的大腦會一片空白,當我在某個地方找路的時候,我的思緒卻隨心所欲地飄蕩,我會覺得自己游蕩得太遠了,到了汪洋大海里。接著,我就會聽到有人叫我。
“特拉,”我的媽媽會說,“需要載你一程嗎?”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運氣竟然這么好。媽媽就在這里,就在我失去對空間關系的微弱把握時,她恰好從這里經過。
于是我會跳上媽媽的車,然后一天中所有的困難部分就完成了,多數時候是如此。直到十幾歲時,我才知道,媽媽在我每次步行去學校的時候都會跟著我,以防類似的事情發生。
我差不多是一個非典型的學習障礙患者,因為除了數學,學術都是我的“菜”。
一年級的第一天,我還興奮地幻想著能為比《戰爭與和平》還要厚的書寫寫讀書報告,所以得知我們的第一個作業是給圖片涂色時,我打心眼里感到失望。
三年以后,我的社會學習小組差點兒嚴厲地懲罰我,因為我想寫一個有關奧馬哈部落的報告,而他們想做一個立體模型。我們各讓了一步:他們做他們的立體模型,我開心地寫了一份報告,字數足夠三個人的作業要求了。
不過,課間休息時,我寧愿去做立體模型也不想出去。我有朋友(據我所知,我的非語言學習障礙并不會真的影響我的社交能力),但我在操場上從來找不到他們。
老師們非常了解我,最后他們對我說:“你都這么大了,可以自己去找希拉(或韋斯,或蕾切爾,或莉齊)了。”
幸運的是,我的朋友們比多數認識我的成年人都要聰明,他們知道要怎么在教室外面等著我一起去吃午飯或度過課間休息時間。
我被分配給了一位“哥們兒”,他和我一起走路去上高級閱讀課,下課后一起回來。還有一個哥們兒會帶我去資源教室。
隨著年級的增長,上學變得更容易也更有趣了。自初中起,老師就再沒給我留過立體模型的作業,而我也可以自己選課,自己論述文學或歷史,而不是建構東西或去看圖表。
現在,我是位于喬治亞州迪凱特的阿格尼斯斯科特學院大三的學生了。我在這里主修古典文學和英語創意寫作。我不開車,但是,我享受翻譯,比多數人閱讀更多有關拉丁語、希臘語和古代歷史的書籍。如果你問我最喜歡的神話人物是誰,我一定會說是奧德修斯。畢竟,他用了十年時間才回到家里。
- 高中生·青春勵志的其它文章
- 未來的房屋有“大腦”
- 美麗的舞者
- 野黃菊
- 春雨
- 游蘇仙嶺記
- 相思是一條永不枯竭的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