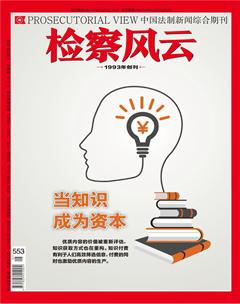為中國(guó)科學(xué)修史
徐恩丹
單是為了一句“中國(guó)古代無科學(xué)”,就值得撰寫一部《中國(guó)科學(xué)史》。然而《中國(guó)科學(xué)史》的意義,絕不僅僅是要滿足阿Q式的虛榮。歷史上,帝國(guó)主義征服一個(gè)民族,從思想匕首先要做的,就是消滅那個(gè)民族的歷史意識(shí)。社會(huì)愈是發(fā)展,人們愈是想較多地知道自己的歷史。
《中國(guó)科學(xué)史》
作者:李申
出版: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
雖然有人主張,凡是確切的知識(shí)都是科學(xué)。但是我們只能說這是屬于科學(xué)領(lǐng)域的知識(shí),卻不能說這是人類科學(xué)活動(dòng)的開始。單是確切的知識(shí),不單早期的人類具有,就是一些高級(jí)動(dòng)物也有,而不僅是本能。然而這些知識(shí),都是動(dòng)物在謀生過程中,人類在他們的生產(chǎn)和生活實(shí)踐中所不自覺地獲得的,是謀生,或生產(chǎn)和生活活動(dòng)的副產(chǎn)物。沒有這些知識(shí),不僅人類,許多稍微高級(jí)一點(diǎn)的動(dòng)物,也無法生存。這些知識(shí)的正確性,是促進(jìn)人類把探討知識(shí)本身作為重要事業(yè)的前提。人和動(dòng)物的區(qū)別,就是無論動(dòng)物如何聰明,都不可能專門把獲取知識(shí)作為自己的一項(xiàng)事業(yè)。但是當(dāng)人類意識(shí)到知識(shí)價(jià)值的時(shí)候,就會(huì)分出一些人來,專門,或主要從事知識(shí)的生產(chǎn)。直到今天,人們的生產(chǎn)和生活,幾乎都要謀求在確切知識(shí),也就是科學(xué)知識(shí)的指導(dǎo)下進(jìn)行,才覺得放心。科學(xué)知識(shí)的生產(chǎn)和應(yīng)用狀況,已經(jīng)成為一個(gè)國(guó)家富強(qiáng)與否和文明程度的標(biāo)志。因此,我們也只把自覺從事的以獲取知識(shí)為目的的活動(dòng)稱為科學(xué)活動(dòng),并且把這個(gè)自覺獲得知識(shí)活動(dòng)的始點(diǎn)作為科學(xué)的始點(diǎn)。
自覺獲取知識(shí)的活動(dòng),在不同領(lǐng)域的表現(xiàn)是不一樣的。在天文學(xué)領(lǐng)域,樹起一根標(biāo)桿去測(cè)量日影長(zhǎng)短變化,甚至在未樹標(biāo)桿之前,注意觀測(cè)日月星的出沒狀況并且記錄它們,這就是天文學(xué)的開始。在醫(yī)學(xué)領(lǐng)域,認(rèn)真觀測(cè)疾病的狀況,自覺尋求治療的方法和藥物,就是醫(yī)學(xué)的開始。在農(nóng)業(yè)領(lǐng)域,探討增產(chǎn)的方法,也應(yīng)該是農(nóng)業(yè)科學(xué)的開始。在數(shù)學(xué)領(lǐng)域,能夠從具體事物中抽象出數(shù)字并自覺探討數(shù)字之間的關(guān)系,也就是數(shù)學(xué)的開始。因此,像我國(guó)典籍《山海經(jīng)》中記載日月出入的位置,《夏小正》中記載中星出沒的時(shí)間,甚至神農(nóng)嘗百草的傳說,后稷教民稼穡,都應(yīng)視為我國(guó)先民科學(xué)活動(dòng)的開端。這些開端具體在什么時(shí)代,當(dāng)時(shí)是什么樣的情況?今天已經(jīng)很難知曉了'然而我們的先民很早就自覺地從事專門生產(chǎn)知識(shí)的活動(dòng),則是確定無疑的。這些活動(dòng)的成果,以不同方式,記載在我們的古籍當(dāng)中。這些記載,就是我們這部中國(guó)科學(xué)史的基本資料。
科學(xué)是人類自覺認(rèn)識(shí)世界、獲取知識(shí)的活動(dòng),和哲學(xué)、宗教都不一樣。哲學(xué)是一個(gè)個(gè)獨(dú)立的思想體系構(gòu)成的世界,體系之間的界限,要遠(yuǎn)大于體系之間的聯(lián)系。宗教的世界里,更是一個(gè)個(gè)獨(dú)立的“王國(guó)”。愈到后來,“王國(guó)”之間就不僅是界限,而且是排斥甚至敵對(duì)。科學(xué)則不是一個(gè)個(gè)獨(dú)立的思想體系,而是一個(gè)不斷發(fā)展的過程,是人類為了更好的生活因而追求更多的知識(shí)、并且對(duì)知識(shí)不斷發(fā)展和改進(jìn)的活動(dòng)。這樣的活動(dòng),是人類生存和發(fā)展的必要組成部分。如果因?yàn)槟承﹤ゴ笕宋锏拿侄箍茖W(xué)之間有所區(qū)別,那也不是獨(dú)立的體系,而是科學(xué)本身發(fā)展的階段,一個(gè)分支。哲學(xué)和宗教體系一個(gè)個(gè)都獨(dú)立于社會(huì)生活之上,人們也根據(jù)自己的狀況決定對(duì)它們的態(tài)度:需要,還是不需要?而未必就影響自己的生產(chǎn)和生活。但人們,無論是個(gè)人還是群體,都不能離開科學(xué),否則就要墮入愚昧和落后。因此,哲學(xué)體系在歷史上不斷變更,宗教體系也不斷更替,都有自己的誕生和滅亡。誕生的,將來也要滅亡。但科學(xué),可以說有誕生,從人類自覺追求知識(shí)開始;卻不會(huì)有滅亡。因?yàn)槿祟惔嬖谝惶欤托枰R(shí),需要知識(shí)的更新。
但是對(duì)于中國(guó)科學(xué)來說,卻有自己的終點(diǎn),這就是隨著西方近代科學(xué)的傳入,中國(guó)科學(xué)的支流逐漸融入人類科學(xué)的主流。具體在什么時(shí)候,不易確定。各個(gè)領(lǐng)域也不一樣。在天文學(xué)領(lǐng)域,以清代國(guó)家采用湯若望等人所制訂的歷法為標(biāo)志,中國(guó)古代天文學(xué)就走到了盡頭,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其他領(lǐng)域,則要到鴉片戰(zhàn)爭(zhēng)以后,才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tái)。也有的門類,比如中國(guó)醫(yī)學(xué),仍然在盡著自己的使命。我們之所以說傳統(tǒng)醫(yī)學(xué),也就是中醫(yī)也有終點(diǎn),只是說它的理論已經(jīng)不是在傳統(tǒng)的道路上繼續(xù)發(fā)展。進(jìn)一步發(fā)展的道路,是融入近現(xiàn)代的世界醫(yī)學(xué)。
金丹術(shù)與中國(guó)科學(xué)
從秦始皇尋不死藥,到唐代皇帝、士大夫們紛紛服用金丹,中國(guó)古人付出了慘痛的代價(jià),經(jīng)歷了近千年的嚴(yán)重爭(zhēng)論,唐末至宋初,整個(gè)社會(huì)的整體,終于認(rèn)識(shí)到,人的身體不可能吸取黃金、還丹所謂“不敗朽”的性質(zhì),不可能借助這些“外物”來加固自己的生命。相反,倒足以嚴(yán)重傷害健康和生命。然而和人類所犯的一切錯(cuò)誤一樣,這些活動(dòng)還是給后人留下了一些有益的東西,也是不幸中的安慰。
首先引起關(guān)注的,自然是中國(guó)人引以為自豪的四大發(fā)明之一,火藥的發(fā)明。
據(jù)唐代李復(fù)言《續(xù)玄怪錄》,周隋之際有個(gè)叫杜子春的人,曾經(jīng)見到道士的丹房“紫焰穿屋上,大火起四合,屋室俱焚”。(《太平廣記》卷16)這應(yīng)當(dāng)是一次火藥爆炸,而不僅僅是失火。后來的《諸家神品丹法》所引《孫真人丹經(jīng)》內(nèi)“伏火硫黃法”,中唐或唐宋之際成書的《真元妙道要略》中也有關(guān)于硫黃、雄黃、硝石和蜂蜜合燒會(huì)發(fā)生劇烈火災(zāi)的記載。對(duì)于硝石不可與硫黃等一起燒煉,也有警告。這些材料,雖然時(shí)代未必確實(shí),但大體可以相信,隋唐時(shí)代,煉丹術(shù)士們已經(jīng)知道硝石、硫黃等一起燒煉會(huì)發(fā)生劇烈燃燒。甚至還可以把術(shù)士們對(duì)此事的了解再往前推。煉丹使術(shù)士們了解到硫黃、硝石等藥物的性質(zhì),為火藥的發(fā)明做了準(zhǔn)備。
然而在煉丹術(shù)士們看來,這是他們的失誤。他們對(duì)待這種失誤的態(tài)度,是尋找一種辦法,去消除這種失誤。所以唐宋時(shí)期的丹書,才有許多“伏火法”或者伏制硫黃等易燃藥物的方法。如同一個(gè)魔術(shù)師僅僅知道兩種氣體混合會(huì)發(fā)生爆炸,而不能說是氧氣、氫氣的發(fā)現(xiàn)者一樣,這些煉丹術(shù)士們,更難說是火藥的發(fā)明者。因此,宋初曾公亮《武經(jīng)總要》中的“火藥法”,應(yīng)當(dāng)認(rèn)為是火藥發(fā)明的標(biāo)志性事件。其配方有兩種,都有十多味藥,可知配方已經(jīng)相當(dāng)成熟。其發(fā)明的時(shí)間,可能要大大早于其公布的時(shí)間。其中的“炭末”等配料,未必和煉丹有關(guān)。因此,火藥的發(fā)明和煉丹有多大關(guān)系?值得研究。
其二是對(duì)金石藥的認(rèn)識(shí)。除了終于認(rèn)識(shí)到金石藥的毒性,知道它們不可能使人長(zhǎng)生不死是最重要的成果之外,為了煉丹藥,唐代出現(xiàn)了一些專以認(rèn)識(shí)煉丹藥物為目的的著作。梅彪的《石藥爾雅》,列出了煉丹用藥和藥方的隱名、別名,以便人們識(shí)別。從認(rèn)識(shí)丹藥性質(zhì)的角度看問題,有一定的科學(xué)價(jià)值。
丹藥雖然不能使人長(zhǎng)生不死,但對(duì)人體有某種醫(yī)療的作用。古代醫(yī)藥書中也常有零星的記載。當(dāng)代張覺人著《中國(guó)煉丹術(shù)與丹藥》,介紹了140余種丹藥及其作用。可算是煉丹術(shù)留給后人有用的遺產(chǎn),
據(jù)《黃帝九鼎神丹經(jīng)》,煉丹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用丹煉成黃金。經(jīng)過煉丹術(shù)士們長(zhǎng)期的實(shí)踐,終于還是煉成外表類似黃金的物質(zhì)。唐代的煉丹術(shù)士們能夠清楚地辨別自然黃金和人工煉制的藥金,并且發(fā)現(xiàn)了鑒別的方法,這就是放在火焰上燒:“若燒火其上,當(dāng)有五色氣。試之果然。”(《舊唐書·孟詵傳》)這種方法,被稱為火焰鑒別法。孟詵是孫思邈的弟子,《舊唐書》本傳說他“少好方術(shù)”。因此,他提供的方法,當(dāng)是方士們常用的方法。
用火焰鑒別金屬,是唐代以前很久就知道的方法。《周禮·考工記》:
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后可鑄也。
后世所謂“爐火純青”,就是指爐火完全變?yōu)榍嗌@是冶煉成功的標(biāo)志。唐代主動(dòng)用火焰鑒別真金和藥金,是火焰鑒別法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
煉丹術(shù)士留給后人的重要思想遺產(chǎn)之一,就是提供了物質(zhì)不滅的范例。
據(jù)葛洪《抱樸子內(nèi)篇》所載的丹方,所用的藥物動(dòng)輒數(shù)十甚至上百斤。唐代的丹方,則僅以斤、兩,甚至少到分。分量的減少,標(biāo)志著煉丹技術(shù)的進(jìn)步和精細(xì)。精細(xì)的煉丹術(shù)使術(shù)士們發(fā)現(xiàn),燒煉前后,藥物的總量不變。
宋代張載提出“氣有聚散而無生滅”,王夫之注解道,一車薪柴燒成灰燼,一部分變成了煙和火焰,并沒有消滅。一鍋飯菜,如合蓋嚴(yán)密,濕熱之氣就不會(huì)跑掉。汞容易揮發(fā),但終究要回歸大地。因此,氣只有聚散,而沒有生滅。
張載曾“出入佛老”,對(duì)道教有深刻的研究。王夫之以汞為例,并且以為合蓋嚴(yán)密,則濕熱之氣不會(huì)散失,都可以看到煉丹過程為防止汞鉛的揮發(fā)而嚴(yán)密封固的影子。因此,“氣有聚散而無生滅”,可以說是中國(guó)古典式的物質(zhì)不滅定律。而為這個(gè)定律提供根據(jù)的,有煉丹術(shù)士的貢獻(xiàn)。
魯迅先生說過,煤的形成,當(dāng)初用了大量的木頭,結(jié)果卻只有—小塊。論及煉丹術(shù)與中國(guó)科學(xué),更是感到用“木”太多,而成就的“煤”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