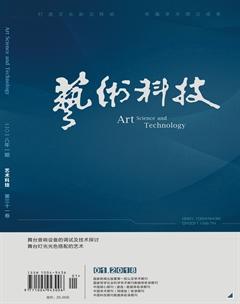淺談中國戲曲表演特色
鞏嬌澆
摘 要:中國戲曲的表演特色是以建立在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和獨特的東方審美觀基礎上的。它以東方文化詩化的虛擬性、程式性、綜合性為表現手段,在演員的“表演”上找功夫,表演哲理認為,“藝術的真實一定不是生活的真實,生活是藝術的來源而藝術是生活的升華不是照搬”。中國戲曲是以“唱、念、做、打”的四功及“手、眼、身、法、步”五法等為表現手法塑造角色,藝術化地根據不同的人物性格、年齡、性別、身份分為生(小生、須生、老生、文武老生)、旦(小旦、閨門旦、正旦、老旦、武旦)、凈(大凈、二凈)、丑(大丑、小丑)等行當幫助演員塑造角色。
關鍵詞:中國戲曲;表演;特色
“唱、念、做、打”是中國戲曲表演的四種藝術手段,唱指歌唱,念指具有音樂性的念白,二者互為補充,構成歌舞化的戲曲表演藝術兩大要素之一的“歌”。做指舞蹈化的形體動作,打指武術和翻跌的技藝,二者相互結合,構成歌舞化的戲曲表演藝術兩大要素之一的“舞”。
基本功之一:“唱”。學習唱功的第一步是喊嗓、吊嗓,擴大音域、音量,鍛煉歌喉的耐力和音色,還要分別字音的四聲陰陽、尖團清濁、五音四呼,練習咬字、歸韻、噴口、潤腔等技巧。當演員掌握了這一切時,更重要的則是善于運用聲樂技巧來表現人物的性格、感情與精神狀態。幾百年來,戲曲美學中一直有傳聲與傳情的分歧,有的演員側重音色和唱腔旋律的美,講究唱出韻味;有的演員則著重中氣充沛、字正腔圓,主張首先要唱出感情。卓越的演員大都把傳聲與傳情結合起來,通過聲樂的藝術感染力,表現劇中人的心曲。戲曲的唱,從來不是穿插在戲里的獨立的聲樂表演,而是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之一。一些優秀劇目,安排唱段是根據劇情的需要,人物性格、思想、情緒發展的需要。通過優美的音樂形象來豐富和加強文學形象,訴諸觀眾的聽覺感官,正像做和打通過優美的舞蹈形象訴諸觀眾的視覺感官一樣。因而戲曲的唱,演員的技巧和修養都是決定藝術創造得失、高下的重要因素。對同一劇目的同一角色,由于演員的體驗、理解不同,也由于唱腔唱法不同,逐漸形成了演唱上各種意趣不同的藝術風格。不同的劇種,對唱的運用也有所不同。有的唱得多,動輒三、五十句,甚至超過百句。有的唱得較少,在劇中人動情的時刻才設置大段的唱腔。唱得多的劇種,往往以唱代念,或介乎唱與念之間,潤腔較少。唱得少的劇種大都在聲樂藝術上刻意求工,對行腔度曲進行高度的提煉。從戲曲發展的過程來看,唱腔的伴奏是由簡到繁的。唱作為主要藝術手段之一,它不是單獨運用的,而是和念、做、打等藝術手段有機結合,融為一體,為塑造人物服務。
基本功之二:“念”。念白與唱相互配合、補充,是表達人物思想感情的重要藝術手段。戲曲演員從小練基本功,念白也是必修課目之一。掌握了口齒、力度、亮度等要領之后,還須結合具體劇目,根據人物的特點和情節的開展,妥善處理輕重、緩急、抑揚、頓挫的節奏變化,達到既能悅耳動聽,又能語氣傳神的藝術境界。戲曲念白大體上可分為兩大類:一種是韻律化的“韻白”,一種是以各自方言為基礎、接近于生活語言的“散白”,如黃梅戲的安慶語、蘇劇的吳語、京劇的京白等。無論韻白或散白,都不是普通生活語言,而是經過藝術提煉的語言,近乎朗誦體,具有節奏感和音樂性,念起來鏗鏘悅耳。唯其念白也是音樂語言,在傳統劇目中,唱和念才相互協調,而無鑿枘之感。
基本功之三:“做”。做功泛指表演技巧,一般又特指舞蹈化的形體動作,是戲曲有別于其他表演藝術的主要標志之一。戲曲演員從小練就腰、腿、手、臂、頭、頸的各種基本功之后,還須悉心揣摩戲情戲理、人物特征,才能把戲演好。演員在創造角色時,手、眼、身、步各有多種程式,髯口、翎子、甩發、水袖各有多種技法,靈活運用這些程式化的舞蹈語匯,以突出人物性格上、年齡上、身份上的特點,并使自己塑造的藝術形象更增光輝。比如在各種步法中,狼狽掙扎時走跪步,少女在歡樂時甩著辮梢走碎步,就不僅是純技術性的表演,而能起到渲染氣氛和描繪情態的作用。同樣是翎子功,用在不同人物身上,有的表現英武,有的表現輕佻,有的表現急躁,有的表現憤怒。在髯口功中,彈須、理髯、甩髯口……各具特點的內涵與表象。卓越的演員表演時既有內心的體驗,又能通過外形加以表現,內外交融,得心應手,而不流于形式。
基本功之四:“打”。打功是戲曲形體動作的另一重要組成部分,它是傳統武術的舞蹈化,是生活中格斗場面的高度藝術提煉。一般分為“把子功”“毯子功”兩大類。凡用古代刀槍劍戟等兵器(習稱“刀槍把子”)對打或獨舞的,稱把子功。在毯子上翻滾跌撲的技藝,稱毯子功。演員從小練武功,需要付出艱苦的勞動。戲曲的做和打,也從來不是穿插在戲里的獨立的舞蹈表演。毯子功的一些項目,單獨地看,近乎雜技;把子功的一些套數,單獨地看,類似武術。但連貫起來,組合在戲里,卻成為具有豐富表現力的舞蹈語言,能夠出人、出情、出戲。一節開打結束時,雙方亮相,不僅勝敗判斷,而且分出了正反。戰勝者要下場,顯示了神采飛揚的風貌;武二花連摔錁子,狼狽相畢露;竄毛表示下水,跺泥體現沉穩;馬童的小翻,襯托了主帥的氣勢。某些戲里的倒扎虎、云里翻,則突現精神失常者的瘋癲迷亂,等等。當這些技術功底與情節相結合時,就有助于刻畫人物、闡釋劇情,并使觀眾得到藝術享受。
中國戲曲表演觀念是虛擬的,它以和觀眾達成默契的程式表演為依托,詩化、傳神地完成了劇本故事空間表現與轉換,把舞臺有限的空間和時間當作不固定的、自由的、流動的空間與時間。在中國戲曲中,說它是這里,它就是這里;說它是那里,它就是那里。千里路之長,說它走完,它就幾步走完。進門到屋內路很短,人物內心需要可以無限拉長。一個圓場十萬八千里;幾聲更鼓,夜盡天明,自由而富有彈性,舞臺空間與時間的含義完全由創作者與演員予以假定,達到了空間和時間景物隨著演員表演而變化,啟發了觀眾心中的時空美感與景物美感。觀眾也表示接受與贊同,受到了人們的喜愛。
參考文獻:
[1] 曾繁仁.中國古代生命論美學的舞臺呈現——試論中國戲曲所包含的生態生命論美學意蘊[J].山東社會科學,2013(05):2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