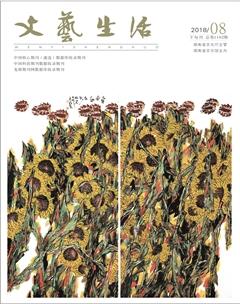以心靈來體驗客觀的真實
柏潔

摘要:具象雕塑是當代雕塑發展中的一個重要表現形式,似乎在當下有愈演愈烈的趨勢,而“超現實”理念作為雕塑創作的表現手法之一,得益于“以心靈來體驗客觀的真實”為觀點的發端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超現實主義”文學藝術運動,它的觀念精髓對藝術發展影響深遠,已成為廣泛使用的代名詞。本文作者也從事雕塑創作,希望探尋在創作實踐中,發掘“超現實”理念給予的更多的意義與內涵。
關鍵詞:具象雕塑;“超現實”理念;創作
中圖分類號:J3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8)24-0188-03
“藝術之始,雕塑為先。”這是梁思成先生在東北大學教授中國雕塑史課程時說過的一句話。現在的“雕塑”一詞也只是藝術發展眾多形式詞匯中的其中之一。追溯人類文明之初,藝術之始,“雕塑”無所謂雕塑藝術品,更多的是以一種實用性更強并帶有裝飾意味的實物存在;在當時,它的功用遠遠超過了它的藝術價值。雕塑藝術在發展了幾千年的悠久歷史長河中,一直以一種具體的,形象的實體藝術形式歷經著滄桑,述說著人類社會文明的發展。
一、中國當代雕塑發展之路
中國有自己濃厚的、獨特的“孔孟哲學”、“儒道思想”,藝術受其影響,多追尋講究“氣韻”、“神韻”一類不易捕捉和言說的“感覺”。因此,中國傳統雕塑中的“寫實”也有別于西方雕塑傳統意義上的“寫實”。換句話說,就是比例、結構、解剖并不是傳統雕塑中看重的。表象不是主體,通過表象傳達的精神才是最主要的。這也在大量的中國傳統宗教、陵墓雕塑中能看出,這個時候的雕塑是具象的,目的、主題也是很明確的。它更像是一種手段,帶給人們更多的是一種神圣、敬畏之意,予人一種遙遠的距離感。
正如孫振華先生所說,“如果說當代中國畫常為沉重的傳統包袱所累,那么當代中國雕塑則有一種無根的煩惱。”中國傳統雕塑的功用性讓其隨著封建帝國的衰落而沒落,精湛技藝也只流傳于部分民間藝術中。由于傳統雕塑一直被看作“皂隸之事”,長久以來也沒有形成較為系統的理論體系。因此,當傳統雕塑被“終結”之后,也就是當代雕塑“重生”之時,只是此時新興的背景和時代已發生了變化。新的體系和觀念接踵而至,讓重生后的“雕塑”應接不暇又興奮不已,開始了全新的詮釋和發展。
孫振華先生在談到當代雕塑轉型時這樣說:“過去的雕塑,面對的是一個儀式化的社會,一個被理想主義光環籠罩的社會,一個宏大敘事社會……在這種社會中,雕塑的空間感、體積感、儀式感;和它的紀念性、永久性以及單純、靜穆的品質,與它在美學上是非常吻合和匹配的。
而中國當代雕塑的核心問題是走向世俗社會。
這個基本走向給當代雕塑所帶來的變化是:以解構、顛覆、調侃、反諷、挪用等方式,消解雕塑在內容上,乃至在形式上的“正經”。它使雕塑的莊嚴和肅穆變得輕松好玩;使甜美的抒情變得粗糙怪異;使曾經高蹈的雕塑開始表現身體的欲望和感性的要求;使曾經是諸神的殿堂,開始轉變成為一個凡夫俗子的世界;使雕塑由過去最典型,最富于“孕育性的頃刻”轉變為一個日常的、普通的生活細節……
在全新的時代背景下,可能要求“雕塑”需要思考的就更多了。當主題慢慢往現實生活及人類本身轉移的同時,雕塑所想表現的情感或是想傳遞的可能比表面的要更豐富。
這樣的轉變應該是好的。這樣的轉型拉近了雕塑藝術與人群的距離。藝術本身就來源于生活,創造與被創造都離不開人類智慧,自然最終也會回到人類本身。
在中國當代雕塑的發展過程中,雕塑家們不輕易放過任何一種可能性,為體現雕塑當代性,對各種材料的嘗試,理論、形式的研究、模仿、創造,以及對傳統的提煉融合再創造。成果也是豐厚驚人的,創造出了一條屬于中國自己的當代雕塑發展之路。逐步沖擊著、淡化著人們對中國傳統造像一直以來存在的一些偏見以及大眾片面的對雕塑概念的認知。
二、“超現實”理念概念
西方藝術思潮的發展無疑優先于我們,有著清晰的脈絡和理論觀點值得我們借鑒與學習。中國當代雕塑的發展是迅速的,在接納著各種藝術思潮帶來的觀念及沖擊的同時,結合中國當代雕塑發展的實際,找到可以溝通的可能性;雕塑家們用自己的方式探索和展現著對主觀或客觀世界的思考;在眾多的藝術思潮和理論中,試圖找到適合自己的那一個“點”,發展深究下去。
藝術常被人們說是“來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這個“高”的意思我認為應該就是一種變相的“超現實”的比喻。“超現實”理念在當代具象雕塑創作中體現較多,作為一種觀念或是一種表現手法。希望表達一種來源于生活,而又無法在現實生活中實現的存在狀態。如澳大利亞雕塑家Ron Mueck的具象人物雕塑,通過改變雕塑人物的尺寸并配以高超的寫實技藝來實現一種仿佛的“真實存在”。雖然展現的對象都是生活中正常的人群但因為尺寸與平常相差迥異而帶給觀者強烈的視覺沖擊力及感染力。又如雕塑家焦興濤有一系列以“物”為原型的具象雕塑,廢棄的包裝箱、被倒空后癟癟的牛奶盒,牙膏盒,揉作一團的口香糖紙,疊在一塊的用過的一次性紙杯,各種色彩的垃圾袋,那些被揉作一團、失去了固定形狀的物品在現實生活中渺小到微不足道,被他改變尺寸并裝置化改造后,讓人們不得不重新認識到這些“物”的存在。就如達利那塊柔軟扭曲了正常形態的掛鐘,長出抽屜的女人體等等。
那么,何為“超現實”?“超現實”作為一種觀念在不同的藝術領域有著不同的表現方式,誠然此“超現實”非彼“超現實”的概念,就需要先了解發端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由一群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法國青年發起的“超現實主義”文學藝術運動。他們目睹了戰爭的荒謬殘酷與破壞,舊的信念失去了魅力,需要有一種新的理想來代替。超現實主義就是他們在探索道路上的嘗試。發起者布雷頓認為,超現實主義并不是理性,教條式的藝術理論,超現實主義是一種觀點,企圖發現揭示比真實世界背后更為真實的意義,一種“自動書寫”無意識的純精神行動。布雷頓找到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學說,為超現實主義找到了堅實的理論依據,并以此作為他終身堅持的“以心靈來體驗客觀的真實”的觀點。弗洛伊德的意識、前意識、潛意識的精神層次理論就像是為在戰爭中飽受精神與身體摧殘的藝術家們找到了“光明”的宣泄情感渠道,找到了自幻想世界返回現實的途徑。“我們其實是生活在夢幻之中,而并不是在夢境中尋找我們的生命”——這樣的超現實主義藝術定義,為參與超現實主義運動的藝術家們提供了創作的源泉。超現實主義是社會文化發展到了一定時期的產物,是當時的社會背景導致藝術家們只能用自己夢幻中想象里的事物來反映當時被殘酷破壞掉的美好。
雖然“超現實主義”作為一種文學思潮的運動并沒有維持多長時間,但作為一種美學觀點,其影響卻十分深遠。對之后出現的,諸如抽象表現主義、波普藝術、行為藝術、行動主義、觀念藝術等藝術運動的思維演變無疑起了深遠的影響,為當代藝術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源泉。后來繪畫與雕塑形式的介入,無疑是為布雷頓的超現實主義觀念帶來了更鮮活的印象與色彩,更為大眾所熟知與了解。
其實,作為繪畫或雕塑藝術創作不可能完全達到布雷頓所說的“自動主義”,更多的是一種與超現實主義核心思想的關系,表現他們對現實的疑問與另一些可能。例如馬格利特,他的繪畫以具象、冷靜、理性、純粹的畫面呈現。他認為,生活的經驗較之物品與名稱,含義,功能之間的關系要更為可靠,畫家的責任便是為了組合現實而提出新的方法和疑問,因為世界是處在持續的改變中,沒有任何事物是常態不變的。他的繪畫是經過了嚴格而具有邏輯性的思考過程,來尋找日常生活中的非尋常現象,從這一點來說,馬格利特與布雷頓的“自動書寫”觀點便不相一致;雖然他亦否認他創作的來源是夢境,但他將生活中之物非尋常組合形成的一種可能的存在,以及他的觀念繪畫中所反映出來的對固有的和已定次序的現實的疑問,挑釁,和超現實主義運動的目標又是緊密相關的。鬼才達利是最后加入超現實主義的成員,也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藝術家之一,他的作品所反映的夢幻與真實,不論是在視覺的強度上,豐富的想象力以及尖銳的諷刺,殘酷的表現都將超現實主義的觀念以具象非理性的意象鮮活的呈現出來,也因為達利的加入為超現實主義帶來了更多活力,并為大眾所注目。
雖然達利的個人主義行為史上褒貶不一,但他對超現實主義美學的貢獻,以及諸多杰出的作品給以后現代藝術的發展所帶來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可以說影響深遠。
三、“超現實”理念給予我的啟發
筆者的一件作品《遙遠的幸福》(如圖1所示)創作之初就是看到達利的作品《圣東尼奧的誘惑》而得來的靈感,畫面前方直立著嘶吼的馬,讓畫面的動感強烈,加長了纖細如竹竿的動物腿,高聳入云間的高度和前方人物的比例讓人有一種強烈的壓迫感和畫面感。《遙遠的幸福》想表現的是中國傳統封建婚姻的題材,坐在一頭驢上蒙著蓋頭就將自己嫁到一個未知的世界需要多大的勇氣,為加強新娘心里的那種忐忑和不安,加長變細后的驢的腿為我找到了那種高度和心理暗示,嘶吼的驢仿佛是一種情緒的宣泄,靜止的人物和行走嘶吼的驢形成一種對比。
作品《蛻離》(如圖2所示)是另一件以封建時代的女性為表現題材的雕塑。主體是一套清末民初時期的女性服飾與鞋,服飾本身沒有情感血肉,穿上它的人物才會賦予這樣的標識。那樣的時代對女性是不公平的,太多道德觀念束縛著,更是有所謂的“三寸金蓮”裹小腳這樣對身心造成嚴重創傷的習俗,因此我創作的只是服飾,人物已蛻離出這件服飾或是那個時代的束縛,可以自由的翱翔云端,這也是為何設計底座為一朵云的造型之意,以增加其唯美的“超現實”感。
選擇用“具象”雕塑的形式來進行雕塑題材創作是因為我認為這是雕塑應有的形態,用一種具體的形體,結合材料反映對應的時代是雕塑從傳統到當代所給出的概念,盡管如今的雕塑已融入很多新型材料、元素,甚至改變了固有的三維形態。但那只是范圍,并沒有改變雕塑職能及本質。就如雕塑家焦興濤所言:“如果我們把藝術作品看做一個客觀的、與現實并行的存在的話,那么相對于我們思考的抽象性,無論它具有什么樣的形態和形式,他都是“具體”并且是“具象的”。
找到超現實理念,就如為自己創作找到一個可以帶入的切入點。這樣的理解和運用可能是片面的,膚淺的,但確是有效的。用超現實的說法或許也是一種試著逃避現實的表現,就如現實已然很殘酷,就讓想象的世界美麗、奇幻一些。“超現實”是一種手段,可以宣泄情感、期許未知、放眼整個空間宇宙,讓思緒無限遐想。當下的人們有著對周圍新事物的好奇和恐懼,也有著對未來世界發展的消極憂慮,這種感覺個人自身的渺小和心靈的脆弱或許有著比戰爭的殘酷更虛幻,更琢磨不定的不安影響。因此,事實上,在現代文化藝術背景中,“超現實”本身已成為一種表現語言,“以至于今天任何的藝術、文學、電影作品,只要他是解體的、幻覺的或是不連貫的,均可能被歸為‘超現實”。找到超現實理念,正如布雷頓所說,那是一個得到啟示的瞬間,“在這一瞬間里,人們解決了夢幻和現實之間的矛盾和對立。”
四、具象雕塑創作的一些感悟
當下是一個全球化信息傳遞快速、便捷的時代。藝術形式多元化,相互交融貫通,當代雕塑的定義與界限已越來越模糊,不僅融入了聲、光、電、影像等現代科技,還融合各種新型材料進行研究開發,似乎現如今的雕塑藝術已不再是傳統寫實功底和技法最為考究的時代。在當下的雕塑創作中,“寫實或具象”已只是其中之一的創作形式,大眾的審美也不僅僅局限于傳統純寫實手法的藝術品,“甚至,一個孤立的雕塑作品已經很難再激起我們的驚喜。”這就使得如今的雕塑創作愈難,愈具有挑戰性,“作品面貌上的可識別性變得不再重要,作品背后的復雜的關系和指涉才是核心。”
那么,當代具象雕塑創作應如何創新?如何運用時代優勢發揮最大的功用?
在如今的具象雕塑創作中,大致有這樣一種模式,即“觀念+技巧”,意思是,有一個不錯的相關主題及形式(說法),配以相當細膩精致的技巧。這更像是一種“中西合璧”的解讀,既有民族性也具備得益于西方傳統寫實功底培養的技法。其實,只要是“用心”作出來的作品,何種形式,用了何種方法或材料,都只是手段,只要那樣的作品是打動人的、精彩的、能讓人與之產生共鳴的都是成功的。
五、結語
藝術創作的魅力在于可以用不同手法來表達內心或客觀世界,無論是對事物一時的感悟或是長久的思考而來的心得體會,或是想表達的對事物的態度等,可以是抒發個人情緒,也可以是站在一個很宏觀的角度表達“大愛”。在進行個人創作時,可以是很放松的,很投入,很專注,亦或是疑惑的、迷茫的,矛盾的。在這個很多技能可以被科技或機器器械取代的時代,不能被取代的是我們的大腦、我們的思想。這就要求我們需要時刻更新知識與技術而不被時代所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