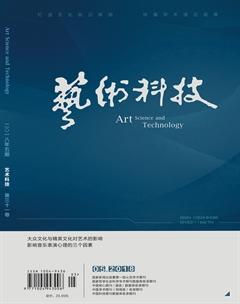花鼓燈字詞考釋
摘 要:花鼓燈的名稱源于何時、由何人命名、其用意如何均無史料佐證。本文僅從現(xiàn)有名稱“花鼓燈”及相關字詞作分析,剖析其文化內涵,通過探索,得到“蘭花”“鼓架子”“玩燈”等精神指向。
關鍵詞:花鼓燈;祭祀;蘭花;鼓架子;玩燈
作為漢民族樂舞典型代表的花鼓燈早在2004年就成功位列文化部公布的40個中國民族民間文化遺產(chǎn)保護試點工程中,成為安徽省唯一入選的項目。2006年,花鼓燈又被列為第一批中國非物資文化遺產(chǎn)保護重點研究項目之一。
何謂花鼓燈?官方文獻及民間藝人說法不一。藝人們的質樸解釋是:蘭花和鼓架子在玩燈。藝人們的直白陳述,是從藝過程中通過感官直接獲取的,從字面上解釋“花鼓燈”不無道理,但筆者認為,在原生態(tài)花鼓燈中每個字詞都有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蘊。
“花鼓燈”一詞最早源于何時,暫無資料顯示,只到清代才有“花鼓燈”一詞的記載。《蕉軒隨錄》云:“鳳陽鄉(xiāng)俗每值燈節(jié)前后,數(shù)日率以花鼓燈為戲。”《鳳臺縣志》中也有記載:“花鼓燈歷史悠久,宋代就流傳在淮河流域的鳳臺、懷遠一帶。”由于史料均出自清代,只能說明最遲在清代已經(jīng)將這種樂舞命名為“花鼓燈”。當然“花鼓燈”一詞出自何人之口也無法考證,把此種樂舞命名為“花鼓燈”的初始用意也無法探究了。本文從“蘭花和鼓架子在玩燈”的相關詞語作一考釋,試為文化研究與探討。
考釋1:蘭花
蘭花是蚌埠一帶花鼓燈的女主角。“花”字從古至今多作為美麗動人女性的指代,明艷動人的女性也多被比作各種名花。
蘭,《說文解字》曰:“(蘭)香艸也。從艸闌聲。落干切。”《左傳》曰:“蘭有國香。說者謂似澤蘭也。”蘭花品類繁多,摘取映合四季的四種蘭花,則有草蘭(即春蘭)、蕙蘭(即夏蘭)、建蘭(即秋蘭)和寒蘭。
筆者認為花鼓燈中的“蘭花”一詞多半取意于春蘭。春蘭又名草蘭,花期在農歷2~3月,期間有“春風”節(jié)令。而花鼓燈中的“燈”字和“鼓”字,器形、七星之柄遙指升至地平線的“大火”,此時節(jié)令仍是春風,花有圖騰、祭祀之意,涂山廟會是“春祭”,再加上春蘭花期中包含“春風”,花鼓燈意義指向應該著重“鼓舞春風”。
考釋2:鼓架子
女主角為“蘭花”,名稱雅且富于韻味,男主角“鼓架子”,名稱俗且直白。鼓架子,字面解釋為“支起鼓的架子”。而花鼓燈中持鼓人是鑼鼓樂的演奏者,被稱為“鼓架子”的男演員是不持“鼓”的,是舞蹈演員。持鼓的不是鼓架子,不持鼓的卻稱為鼓架子,筆者試從花鼓燈的祭祀功能找到原因。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對“鐙”的解釋為:“(鐙)錠也。祭統(tǒng)曰。夫人薦豆執(zhí)校。執(zhí)醴授之執(zhí)鐙。注曰。校、豆中央直者也。鐙、豆下跗也。執(zhí)醴者以豆授夫人。執(zhí)其下跗。夫人受之。執(zhí)其中央直者。按跗、說文作柎。闌足也。鐙有柎。則無足曰鐙之說未可信。豆之遺制爲今俗用燈盞。……生民傳曰。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登薦大羹。箋云。祀天用瓦豆。陶器質也。然則瓦登用於祭天。廟中之鐙。笵金爲之。故其字從金。”
其意為:祭祀祖先或神靈時盛裝供品的器皿就是“豆”,豆是木質的。注曰:“鐙、豆下跗也。”校、豆中央直者也。支起鼓的鼓座在古籍中被稱為“跗”。“鼓跗”即鼓架子是也。
《說文解字》曰:“凡器之足皆曰柎。”擺放器具的架子是比較堅實的,因此在花鼓燈中稱男演員為“鼓架子”。在“雙墩遺址”的刻畫符號中,可以尋到“柎”的影跡。
《紫幢軒詩集》曰:“都人扮傀儡(儺戲)腰鼓而唱,謂之打花鼓。”在沒有配備專職鼓師的情況下,藝人持鼓表演或演唱,表演的藝人即為“跗”——鼓架子。花鼓燈的鼓架子的名稱由此而來。
當樂舞分離后,鼓由專人打擊,原先持鼓的藝人們雖然棄鼓而舞,其稱謂仍沿用“鼓架子”的稱號。應劭《風俗演義》云:在古代,“鼓乃春分之意”。顯見“鼓架子”與“蘭花”的名稱也與花鼓燈在上巳日的“春祭”有聯(lián)系,以上諸多史料說明,無論是花、蘭花、鼓、鼓架子還是燈(火與社火)等演職人員和手持道具都與祭祀有關,也是花鼓燈被創(chuàng)造的原因且一直延續(xù)至今最主要的社會職能。
考釋3:玩燈
花鼓燈的表演在藝人的口中謂之“玩燈”。何謂“玩燈”,玩,本義是以手玩弄,泛指通過獲得非直接利益來娛樂自身。出自東漢·許慎《說文》:“玩,弄也。”一語道出了花鼓燈后世衍生的自娛特性,這種自娛性建立在祭祀先靈和勞動時的心靈釋放和情感宣泄的基礎上。
“游戲是人在勞動中逐漸把自己力量的實際使用看作一種快樂。”[1]玩,就是一種游戲,就是一種快樂,就是一種無拘泥、無限制的心靈釋放,就是拋開一切思緒的羈絆追求的自由與享受。
“家中沒有一畝地,十冬臘月沒寒衣,身受寒冷腹受饑,周天要飯奔東西,圍麻包,披狗皮,晚上蓋個破蓑衣。”“早就想把禹王拜,揭不開鍋我懶得動彈。”“鑼鼓聲一響,腳底版發(fā)癢。”“鑼鼓一打頭對頭,玩燈的都是光蛋猴,一無銀錢買燈草,二無銀錢買燈油,玩燈只靠月亮頭。”①上述燈歌在描述生活苦難時是以玩笑的口吻作出的詼諧幽默的敘述。
生活或生命的苦難需要一種更強烈、更集中的動來宣泄它、緩解它。這就是“玩燈人”的心理狀態(tài)。而這種心理狀態(tài)與舞蹈這一活動的出現(xiàn)動機又極其相似,“原始舞是一種劇烈的、緊張的、疲勞性的動,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體會到最高限度的生命情調”。[2]玩燈人的行為也印證了花鼓燈這一活動的“動機”。
著名的藝術史家威廉·留布克說:“在原始民族那里,藝術作品帶有自然的必要性的印記,而在文明民族那里,它們則滲透著精神的意識。”玩燈人在印證這“必要性的印記”的同時,又增添了一抹現(xiàn)代的精神意識。
注釋:①以上燈歌均摘錄于《花鼓燈歌選》蚌埠藝術研究所,1990。
參考文獻:
[1] 斯圖加特.倫理學[M].商務印務館,1886.
[2] 聞一多選集[M].開明書店,1951.
作者簡介:胡琬羚(1990—),女,安徽蚌埠人,群文系列助理館員,研究方向:舞蹈編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