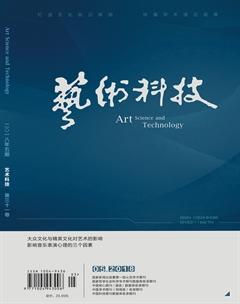三個看起來“形而上”的“玩具”
曹耀元
摘 要:每次提到“玩具”,無論日常生活里的還是學(xué)術(shù)研究中的,大都聚焦在玩具本身或是玩具的功能上。現(xiàn)在我們看到的玩具都是被設(shè)計出來的,但是筆者在生活中觀察到的小孩子都是自然而然開始玩的,任何東西,甚至一根筷子都可以被孩子賦予獨特的意義而成為一個下午的“玩具”,玩是不需要設(shè)計的。在現(xiàn)實生活中,玩具“注入了成人世界的期待”,玩具變成了一種媒介,連接了父母與孩子;玩具就像一雙眼睛,注視著每個家庭的成長。
關(guān)鍵詞:玩具;媒介;親子關(guān)系
1 兒歌是用來唱的玩具
在說玩具之前,筆者想先說說兒歌。兒歌不是一個小話題,中國社會學(xué)奠基人孫本文先生、朱自清先生都研究過兒歌。兒歌材料豐富,其中充滿了好奇、流連、沉思、無語……和玩具一樣,兒歌也分有很多種類,根據(jù)社會學(xué)家鄭也夫先生的研究主要有五類:
第一類:數(shù)數(shù)的兒歌。數(shù)數(shù)為框架的兒歌數(shù)量極大,數(shù)數(shù)的兒歌很可能是兒童最早接觸的歌謠,但是在兒童之間唱誦這類兒歌并不多,主要還是母親帶著孩子的時候唱誦的。
第二類:描述身體特征的兒歌。這類型的兒歌數(shù)量僅次于數(shù)數(shù)的兒歌,是以身體器官或身體特征為基礎(chǔ)的歌謠。如果說數(shù)數(shù)的兒歌只需模仿,那么身體器官的兒歌開發(fā)了想象和比喻,多數(shù)都很切近,直指功能。
第三類:顛倒兒歌。顛倒歌是兒歌中流行的品種。各地的反語歌不計其數(shù),小孩兒們大概都唱過反語歌,被它極致的荒誕吸引,可能也是因為它的荒誕全在表面上,吸引力是短促的。
第四類:斗嘴。兒童生活中少不了博弈,博弈中少不了斗嘴,而文化的作用在于讓我們擺脫孤立無援,站在前人的肩上,一張嘴就能一套一套的,要在吵架的時候不落下風(fēng),也共同托舉出語言的樂子和生活的味道。
第五類:連鎖兒歌。連鎖兒歌大概是其中最流行,也最富有魅力的。這類兒歌被研究者孫介凡先生叫作“連鎖”,朱自清稱它為“接麻”。接麻兒歌的精妙處在于,人們不拘泥于同一個字,常常只要同個聲音就行了,甚至故意不取同音只取諧音,并且接的時候不一定是上句的最后一個字,接上句第一、第二個字都行,這就導(dǎo)致了總是出其不意,荒誕不經(jīng)。
兒童喜歡什么樣的兒歌?第一是有趣,第二可能還是有趣。兒童還沒有進(jìn)入工作領(lǐng)地,還沒有接受各種各樣的誘惑,尤其是在兒歌興起的那個時代,成年人還不會為了子女贏在起跑線上,強迫他們識字、算數(shù)、背唐詩、學(xué)外語,兒童可以率真地跟著天性走,可以率真地玩。玩是不需要設(shè)計的,不需要引領(lǐng)教導(dǎo)的,甚至具體的玩具也是可有可無的,孩子們隨時可以開始玩——看到街上一堆沙子就亢奮不已,能玩上一天;一份報紙或雜志,我們能切割成小方塊,孩子們可以做許許多多幾何形狀,這張紙就事實上變成了一個幾何實驗室。通過折疊,他們可以制作出扇翅膀的小鳥、會彈跳的青蛙、孔雀或者扇尾魚。這些就是幾何學(xué)的實踐,而無須過多的言辭。同樣,學(xué)會了走路的孩子湊到一起,就有了捉迷藏、跳房子;能跑步的孩子湊到一起,就有了官兵捉賊、木頭人。
兒歌是兒童創(chuàng)造的嗎?肯定不是,至少絕大多數(shù)兒歌是大人創(chuàng)造的,兒童還沒這個能力。既然和其他作品一樣,是大人制造的,為什么兒歌卓爾不群呢?筆者想是因為兒童參與了,不是說他們唱誦過,而是兒童雖然沒有創(chuàng)作,卻有選擇權(quán)。曾經(jīng)有過的兒歌一定比留下來的要多得多,兒童們用他們的唱誦投了票,喜歡的他們一唱再唱,不喜歡的不會主動張嘴。于是億萬兒童以他們的情趣,以他們的真誠完成了選擇,引導(dǎo)了兒歌創(chuàng)造者的風(fēng)格方向。從這個意義上說,兒歌就是兒童用來唱的玩具。
2 玩具的媒介意義
回到玩具,玩具是兒童創(chuàng)造的嗎?如果拋開那些“街上看到的一堆沙子”之類的東西,站在現(xiàn)代的角度上看,玩具當(dāng)然不是兒童創(chuàng)造的。“玩具電動火車和洋娃娃是成年人記憶中永恒不變的經(jīng)典,但事實上它們是20世紀(jì)早期育兒觀的產(chǎn)物。……人們認(rèn)為,建筑組裝玩具是在傳授給男孩子們將來成為工程師和科學(xué)家的夢想。這一玩具出現(xiàn)在大多數(shù)的成年美國人都相信存在著一個無限技術(shù)進(jìn)步世界的時期。”玩具就像一種溝通成人世界與兒童世界的媒介,傳遞著雙方的信息。
媒介指的是一種存在形式,即作為信息交流的載體。根據(jù)以麥克盧漢為代表的媒介環(huán)境學(xué)家的觀點,媒介本身的存在改變了人類認(rèn)知世界、感受世界和以行為影響世界的方式,其呈現(xiàn)給我們什么樣的世界,我們就會傾向于感知到什么樣的世界,這就是媒介對我們的生存的世界的“定義”。任何一種媒介報道所形成的外在于我們的環(huán)境并不是真實客觀的社會環(huán)境,而只是介于我們“內(nèi)心主觀世界”與“客觀社會環(huán)境”之間的“中介”的環(huán)境,具體表現(xiàn)為人對于“客觀世界”的信息進(jìn)行篩選之后所呈現(xiàn)的東西。以電子閱讀器為例,電子閱讀器因其自身的媒介特性(電子、熒幕等)使得它傾向于引導(dǎo)讀者(或者說它就是被這樣設(shè)計的)以一種“正常的”方式:一行一行、一面一面的方式來進(jìn)行閱讀。由于這樣的特性,以Kindle為代表的電子閱讀器天然“拒絕”以兒童為代表的消費群體對圖書的特殊“期待”——一種受到好奇心和探索欲的驅(qū)使——提前翻閱后面的內(nèi)容以及對書本本身把玩的沖動,并同時塑造他們的閱讀習(xí)慣。因此,媒介是有態(tài)度的,是有價值傾向的。
現(xiàn)代商人在挑選玩具時,要考慮多個因素,包括玩具的過去銷售數(shù)據(jù)、市場趨勢預(yù)測和社交媒體熱度等。零售商會選中一些電影或電視節(jié)目的播放時間,推出相應(yīng)的許可銷售玩具來促進(jìn)銷量,再對價格進(jìn)行結(jié)算,確保玩具的定價能夠吸引消費者。西爾斯(Sears)的首席營銷官Kelly Cook說:“我們使用相當(dāng)多的算法來統(tǒng)計預(yù)測玩具的價格點。”除了統(tǒng)計、數(shù)據(jù)以外,商店還會讓買家(也就是家長們)預(yù)測孩子們是否喜歡這款玩具、喜歡玩具的哪些特性,哪些玩具創(chuàng)新會吸引他們等。一件玩具從設(shè)計、生產(chǎn)到銷售,每個環(huán)節(jié)的考慮都蘊含了設(shè)計者的態(tài)度和想法,一件件玩具仿佛自然而然地背負(fù)起傳遞成人世界價值觀的使命。這時,玩具也成了一種廣泛存在于成人之間、成人與孩子之間以及孩子之間的交流媒介,發(fā)揮著其獨特的作用。
3 玩具的理性與天性
在商業(yè)世界里,零售商在他們的網(wǎng)站和廣告中推廣玩具;玩具清單也在社交媒體、新聞報道、博客等媒介上得到了廣泛的傳播。這些產(chǎn)品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出現(xiàn)的次數(shù)越多,人們就越有可能看到它們,然后建立起人們對產(chǎn)品的意識。但這些都是成人世界、商業(yè)世界中被理性設(shè)計出來的“玩具”。上文提到,在孩子的天性里,“玩是不需要設(shè)計的,不需要引領(lǐng)教導(dǎo)的,甚至具體的玩具也是可有可無的”。理性和天性之間仿佛再次“針鋒相對”。
《小玩意:玩具與美國人童年世界的變遷》里提道:“玩耍是孩子的工作,而玩具就是他們的工具。”但是筆者認(rèn)為玩不是工作,玩是自發(fā)和自愿的。像過家家之類的玩法好像是在模擬日常的工作,但是動作會故意做得很夸張,一看就知道是在玩。玩更像一種試錯式的學(xué)習(xí),通過玩,能讓孩子們快速獲得反饋、積累經(jīng)驗,提高應(yīng)對意外局面的能力。上文已經(jīng)論證過,玩具不一定非得多么高端復(fù)雜,一根小木棍也可以玩,關(guān)鍵是想玩,有玩具可玩。從這個角度上說,玩具的確是玩的工具,但也就是工具而已。
4 使用工具的人
心理學(xué)家很早就把小孩跟大人的關(guān)系分成三類,判斷關(guān)系最簡單的辦法是做個幼兒園接送測試。假設(shè)實驗者是一個媽媽,早上把孩子送到幼兒園,下班再接回來,看孩子的反應(yīng),就能判斷出他和實驗者之間的類型。
安全型的孩子在媽媽離開的時候會表現(xiàn)出依依不舍,但之后就接受了;而去接他的時候,孩子會非常高興。
回避型的孩子看起來總是無所謂,但是有心理學(xué)家后來做過測試,發(fā)現(xiàn)回避型孩子每次離開家長和見到家長的時候,心跳都在劇烈加速——孩子實際上有強烈的感情變化,但是因為跟家長關(guān)系很疏遠(yuǎn),他克制了自己的感情。
焦慮型的孩子則表現(xiàn)得無論什么時候都極度地需要愛。
三種關(guān)系會導(dǎo)向不同的成長路徑,需要關(guān)注的不僅僅是這個分類,更重要的是統(tǒng)計表明:孩子是哪種類型取決于家長。
玩具只是一個工具,真正重要的是父母與孩子之間圍繞玩具產(chǎn)生的互動。因為互動的背后展現(xiàn)出父母的為人,而父母的為人決定了與孩子之間的關(guān)系,乃至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孩子會成為什么樣的人。父母應(yīng)該明白,孩子不是“私有財產(chǎn)”,家長對孩子是一種關(guān)系,而不是工作。如果家長本人知識豐富充滿自信,跟孩子的關(guān)系很親密,孩子就會有安全感,就愿意去模仿學(xué)習(xí)。
要讓孩子聽話,取得孩子的信任,首先要知道和他的關(guān)系,其次要捫心自問,最后圍繞一個個“小玩意”自然地與孩子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