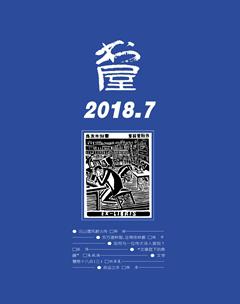李煜《虞美人》與蘇軾《念奴嬌》
李雅坤
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與蘇軾的《念奴嬌·赤壁懷古》,都被譽為千古名篇,兩首詞的開頭都很精彩。
《虞美人·春花秋月》以設問句“春花秋月何時了”開句,如晴天驚雷,劈空而下,具有驚天動地的力量。春花秋月是大自然的永遠存在,但在作者的一句“何時了”中便有了非同尋常的意義:宇宙的永恒與人生的短暫,往昔的熱鬧與今朝的落寞,現實的無奈與前途的未卜,都在這句驚心動魄的設問中噴薄而出。所以這首詞一開篇,就在震撼人心中讓人過目不忘。《念奴嬌·赤壁懷古》的開頭是:“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這樣的句子一開始就把讀者引向了高山之巔,那種壯闊的胸襟與挺拔的氣勢,都是“一覽眾山小”的。如此氣貫長虹的吟唱,真是非蘇東坡莫屬。
然而,如果說“春花秋月何時了”承載的是無盡的宇宙人生思緒,從而將讀者引往廣闊的天地感懷與深邃的哲學思考;那么“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則以鼓動人心的力量,在歷史的長河中揚起了傳統文化的風帆。“風流人物”永遠是中國人揮之不去的情結。但是,“風流人物”必然地譜寫了歷史,卻并不必然地推動了歷史的進步與發展。于是,所謂“千古風流人物”,不過是漫長的農業文明社會里沉浮的帝王將相,歷史卻在這些“風流人物”的叱咤風云中長期停滯不前。然這種情懷深得后人的同情和理解,每個懷有建功立業志向的人都會從這首詞中得到精神振拔和思想共鳴。
《虞美人》接下來的是:“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這幾句語言雖平鋪直敘,卻很動情,也很動人。既是對前邊設問句的應答,也是對設問句含有意義的深化。“又東風”的“又”字用得恰到好處,在一唱三嘆中為“何時了”增光添彩。“故國不堪回首”是人間的變化,“月明中”是永恒的存在;“雕欄玉砌應猶在”是不變的江山;“只是朱顏改”,是國祚的變遷。正是在這種對比的吟唱中,增強了《虞美人》起伏跌宕的節奏,伴隨著節奏,全篇的情調愈發激昂出感人的藝術力量。
而《念奴嬌》的中篇:“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人道是”乃普通的懷古句子,起承上啟下的作用。“亂石穿空”則頗顯一番壯觀的氣象,讀者在身臨其境中勃發的那種凜然的情緒,那種風發的意氣,那種沖天的壯懷,都是不言而喻的。正是在大自然的陶醉中,詩人涵蓋乾坤的感慨出現了:“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蘇軾是詩人,也是政治家,唯其那“割不斷、理還亂”的政治志懷的縈繞不去,才使他面對如畫的江山,想到了“風流人物”指點江山,想到了“多少豪杰”馳騁沙場,于是,觸景生情地“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年輕有為的周瑜偕同美人妻子,怎能不“雄姿英發”呢?英雄加美人,是中國文化里最絕妙的搭配!
然而接下來的敘述,卻是《念奴嬌》的敗筆了:“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眾所周知,赤壁之戰通常被另說為“火燒赤壁”,周瑜的部隊是以火攻取勝的。也就是說,曹操數十萬大軍葬送在赤壁的一片火海中。可以想象,那場面不僅驚心動魄,也讓人毛骨悚然。而置身現場的周郎卻一副“羽扇綸巾”的淡定樣子,在“談笑間”看著不計其數的敵軍“檣櫓灰飛煙滅”中葬身火海,這是一個統帥的鎮定自如,還是一個將軍的冷酷無情?如果說詞中“羽扇綸巾”前的句子唱出了詩人的豪情,唱出了詩人高尚的審美情操,展現的是一幅壯美的圖景。那么,其后的“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不啻為在這幅壯美的圖景外,又用鮮紅的人血涂抹了一幅慘不忍睹的殺戮場景,在這一恐怖的場景里,站著一個談笑風生的“風流人物”。這樣猙獰的形象、這樣慘不忍睹的場景把先前的審美風光都攪得煙消云散了。“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的真實意義不可否認,但不是所有的真實都可以進入文學創作的。當詩人帶著無比贊賞的心態再現赤壁大戰的血腥場面的時候,詩人的詠嘆已沒有了審美的意義,致使開句的那份豪情也蒙上了灰暗的冷色。不是不可以描繪戰爭的血腥與殘酷,問題在于作者是帶著批判的眼光,還是懷著欣賞的心態。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血肉橫飛的赤壁大戰,在蘇軾的生花妙筆下竟成了映襯“雄姿英發”的背景。可以看出蘇軾在這首《念奴嬌》中感懷的不是赤壁承載的那些發人深省的歷史,而是“一將功成萬骨枯”的“風流人物”。《念奴嬌》承載著這樣的文化心理,謂其“千古名篇”,便成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
下面看看這兩首詞的不同結尾:
《虞美人》的結尾是:“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誠然,這里的愁不乏作者淪為階下囚中的無奈與悲苦。然而通觀全篇可以看出,從那句劈空而下的“春花秋月何時了”開始,到“小樓昨夜又東風”,到“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到“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字里行間洋溢著詩人對世間變與不變的傾心關注,對宇宙永恒與瞬間的深切感懷。命運的悲嘆與宇宙的詠嘆是那么天衣無縫地交融在《虞美人》的主旋律中。于是“問君能有幾多愁”中的“愁”,就不僅僅是作者“天上人間”后對囚徒生活的哀怨,更含有寄瞬間于永恒中的悵然。正是這種不可名狀的悵然,把個人的情緒帶入了天地的襟懷中,從而豐富并升華了“一江春水向東流”的哲理意義。
《念奴嬌》的結尾是:“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蘇軾幾乎一輩子都沒有遇到成為“風流人物”的機會,終生處在壯志未酬的“人生如夢”中。難怪他“故國神游”時只能用“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這樣自嘲的語言表達自己與“風流人物”無緣的無奈了。所以面對江上的明月時,只好灑一杯濁酒,不知是祭奠人生的短暫,還是祭奠上蒼的永恒?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與“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都是千古名句。看上去不分軒輊,各有千秋。然而兩者的審美思想卻各異其趣,給人以不同價值的審美感受:如果說“大江東去”是一種飽覽世事滄桑、緬懷“風流人物”的壯懷,從而在躊躇滿志的讀者那里引起強烈的思想共鳴;那么,“問君能有幾多愁”則是洞悉人間無盡苦難后的理性閃光,照亮了所有人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