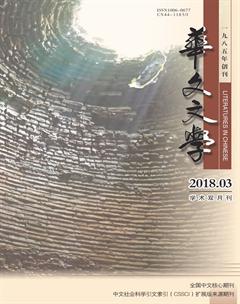劉再復印象記
摘要:這是林崗所寫的劉再復印象記。文章夾敘夾議,既講述兩人亦師亦友的深情厚誼,又描摹出劉再復既浪跡天涯又在象牙塔中的文學家形象。
關鍵詞:劉再復;印象記;文學;林崗
中圖分類號:I0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677(2018)3-0013-04
一
屈指算來我與再復相識也已經有三十四五年了。還是上個世紀80年代初的事情,那時他在學部即后來的社科院工作已有將近20個年頭,我則是大學畢業分配到文學所的新丁。他從院部《新建設》回文學所落在魯迅研究室,我在近代室,正好斜對面。我寫了篇魯迅的論文刊在《魯迅研究》。他看到了,我們碰面的時候他夸我寫得不錯。那是我的初作,受到夸獎當然很高興。后來他又相約有空可以到他在勁松小區的家聊天。一來二往,我們就相熟了。他是我學問的前輩、師長,也是我完全信任、任情交流的好朋友。那時我們非常喜歡到他家談天說地,切磋學問。他的母親我叫奶奶,勤勞又慈祥,炒得一手極美味的福建年糕招待我們,每有聊天暢論古今東西的時候,都使我這樣的晚輩后生得到精神和物質的雙豐收。對我來說,這當然是極其難得的再學習、再摸索的機緣,獲益良多。他后來當了文學所所長,我也從來沒有叫過他“劉所長”,估計叫出來他也覺得怪異,人前背后都是叫再復。他待我們這些晚輩,平易親切,毫無官樣子。就這樣,我們一起切磋,一起寫書,走過了有點兒激動人心的80年代。
我從這段亦師亦友的情誼中收獲最大的就是為他對文學真摯的喜愛所感染,再復是我見過的視文學為生命最為真誠的人。他對文學的熱情和喜愛仿佛與生俱來,文學是他的血液,文學是他的生命。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社會劇烈變遷,改革開放帶來很多從未有過的機會,我也萌生過“出走”的念頭,可是每一次見他,跟他交談,都為他對文學孜孜不倦的熱情所感動,甚至在被突如其來的命運沖擊得有點兒“喪魂失魄”的八九十年代之交,也是如此。我還記得他平淡的話:文學很清苦,但長久一點吧。我本來對文學的認知就很淺,也不是自愿選擇讀文學系的。要論對文學的忠誠度,與再復相比,那真不知相差到哪兒去了。要不是從他對文學火一樣的熱情得到堅持的力量,我今天大概會在不知道的什么地方“弄潮”吧,或者大富大貴,或者身陷囹圄,總之不會有平靜思考的安寧和幸運。每想到這一點我就對人生大起大落但不屈不撓的再復心生感激,人生的良師益友就是這個意思吧。
往大一點說,文革結束撥亂反正的歲月,中國當代文壇有劉再復一馬當先探索理論批評的新出路,也是中國當代文學的幸運。在我看來,文學由于它的性質和在社會的位置,它是很容易迷失的。有點像格林童話那個千叮囑萬叮囑還是行差踏錯的小紅帽,難免受外在的誘惑而迷失在本來的路上。她的美和光彩讓她天真爛漫,不識路途的艱難,不識世道的兇險,同時也令居心叵測的大灰狼垂誕三尺。小紅帽的天真天然地是需要守護的,文學也是如此。我們在歷史上看到,有時候是有意,有時候是無意;或者愿望良好,又或者別有用心,各種社會力量都來插上一杠子,利用文學。于是文學的領域,一面是作家創作,一面也是批評。好的批評就是守護文學。批評雖然也做不到盡善盡美,但至少讓作家和讀者知曉文學本來的路在那里。倫勃朗畫過一幅傳世的名作《夜巡》,那位站在畫面中間的隊長神情警醒,目光堅毅,透出了守衛新興城市的民兵們盡職盡責的神彩。劉再復在我的心目中就是這樣一位為了文學勇敢而孜孜不倦的守夜人。
他所做的事業濃縮成一句話就是守護文學。他看到文學在他生活時代有這樣那樣的迷失、偏差,他覺得自己有義務有責任說出真相,說出值得追求的文學理想是什么。他的話有人聽的時候,發生巨大的社會影響,對當代文壇起了好的作用。有人聽的時候他固然站出來了,即有磨難也不在乎,但我想他不是為了那些社會影響而說的,他是出自對真知的領悟。眾所周知,他后來到了海外,他的話少人聽了,社會影響似若有若無之間。這時候他也沒有遁跡山林,從此沉默。這不是他的性格。他不在乎身在何處,不在乎似有若無,照說不誤。他針對文壇說的話前后有所不同,但那不是他的文學立場和文學理想的改變,而是社會的情形改變,是文學從政治的迷失走到市場的迷失,他守夜人的角色始終如一。文學熱鬧的時候他守護文學,文學冷清的時候他也守護文學,他是中國文壇過去數十年來最為重要而又最為本色的文學的守夜人。
二
晚清以降,中國多災多難,較早時期的改良救亡都無起色,于是文學從古代閑雅的角色逐漸走到社會變革的前臺。從晚清至民國的早期,諸般武藝都用盡了也未能起國家民族于危難之境,先覺者要文學出來為民族的兩肋插刀,這也無可厚非。人畢竟是先要生存才有發展。然而這個形成于嚴峻環境的文學傳統卻日漸隨著現代革命的進展凝固下來,變得僵硬起來。左聯晚期到抗戰,由批評家胡風與諸般人的爭論就顯露端倪。建國后革命這架龐大的國家機器就更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軌道運轉,它馱著文學,文學在它的背上也動彈不得。60年代氣氛還比較寬松的時候,也有些批評家想松一松綁,喘一口氣。比如提出“廣闊道路論”、“寫中間人物論”、“文學是人學”等,其實這些都只是期望小松小綁,在厚厚的泥土覆蓋下透個小孔吸口氣而已,可是后來的事實證明,這是不允許的。
劉再復接受教育成長的文學氣氛,一面是創作的束縛和禁錮,另一面也是視野廣闊,可以飽讀古今中外的優秀文學。后者給他提供日后思想的源泉和養分,前者很自然成了他日夜思索,力圖突破的問題。在嚴重變質鈣化的文學傳統變本加厲進行各種“大批判”的文革時期,他恰在風暴漩渦的中心中國社科院。我曾經很多次聽他講文革中匪夷所思的耳聞目睹,有些傷慘而不那么血腥的細節已經寫在他的散文和師友回憶紀事里了,但還有一些血淋淋的真事他沒有寫,我在這里也難以記述。我覺得,能從過去的血淚和教訓中汲取,是他對文學的思索邁前一步邁深一步邁早一步的關鍵。文革的荒謬,是非顛倒,看似與文學的思索沒有直接的關聯,但兩者隱秘而深刻的關聯被他看到了。這也揭示多少是共通的現象,人都是從個人經驗通往更大的世界,然后又從更大的世界返回到內心的世界的。所以,在破除兩個凡是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劉再復會比文壇當時普遍存在的“撥亂反正”走得更遠。他不但“撥亂”,還問反什么“正”?教條主義的極左固然不是“正”,可登場之前早在現代革命中已經開始凝固的那一套是不是就是“正”,難道反正就是要反到那里?其實很多不滿文革極左路線的批評家對這些是沒有根本性思考的。劉再復與此不同,他不但厭棄文革的荒謬,更痛心沉思了文革禍害的久遠淵源以及它所加給文學造成災難的前因后果。這是再復的優勝處,也是再復80年代中期受到批評和磨難的導火線。但事實證明劉再復為新時期文學提出新的文學理想是站得住腳的。
在追求文學“有用”的背景下最終形成的文學觀念可以概括為“反映論”和“典型論”。細分來看,未嘗沒有幾分道理,但在作家都被組織起來而又在一錘定音的意識形態氛圍底下,這些文學觀念就只能是批評家手里的一根一根棍子,隨著政治風向轉移,打在作家或作品上,那真是滿目蒼夷。劉再復參與到文學界的思想解放和新探索,他的針對性很強,先是寫出了《性格組合論》,主張人物性格不能等同于階級屬性。人性是一個復合體,內涵深廣而又經得住時間考驗的文學形象,一定是那些寫出了人性的復雜多面性的形象。他的新觀念拓寬了作家的視野,提升了文學的品味。后來他更進一步,寫出了《論文學的主體性》,希望實現文學觀念的根本革新。他把作家的現實政治主體和作家寫作中的文學主體分開,認為兩者不能等同,本來也不一致。作家雖有政治觀念,但寫作中依然可以超越其政治觀念。他說,“作家超越了現實主體(世俗角色)而進入藝術主體(本真角色),才具有文學主體性。”而古今中外偉大的作家其實無不如此。“主體論”的用意,無非就是政治少干預而作家多獨立,還創作的本來面目。很明顯它是“補天”的。再復那時也認為自己屬于“補天派”。補天難免要換掉那些粉化了的霉石,把漏洞堵上。可他的好意陰差陽錯卻被誤成“拆天”,受到干擾和批判,甚至有人為此要起訴他。真偽不辨的世道,人真是很容易蒙冤的。
三
自從他漂流到海外,頭銜沒有了,身上的光環沒有了,幾經輾轉,他定居在寂靜的落基山下。巨大的人生落差并沒有消磨掉他對文學的喜愛,他還在思考和寫作。曾經參與現實那么深,一旦去國遠行,似乎像一顆種子離開了土壤,還會不會長呢?許多認識他的朋友都曾有這樣的關切。可是再復就是再復,他不這樣認為。種子固然離不開土壤,可這并不等于人離不開故鄉和國土。文學本來就是跨越國界的,對創作和批評來說,至關重要的土壤不是具體的故鄉故國,而是語言。語言也是一個國度,一個形而上的國度。此后的再復就是背著“語言的祖國”繼續寫作,繼續守護文學。像布羅茨基說的,背著語言的祖國,浪跡天涯。
遠行異國飄流四方是滅頂之災還是另一種幸運,這要看是什么人。對意志剛強的劉再復來說,沒有什么打擊能夠讓他消沉,相反異國的生活經驗給他打開了另一扇認識西方文明,認識文學的窗口。勤奮的再復把他的所感所悟、所思所想都寫在他的一系列著作里,去國近30年寫下的著作已遠多于國內時期。讀者容易見到的簡體中文版有三聯書店版《紅樓四書》、《劉再復散文精編》十卷、《李澤厚美學概論》和《雙典批判》等。他的文學創作和批評視野比先前更為闊大,更為深入。
自上世紀90年代初起,中國步入了市場經濟的快車道,千呼萬呼的財富白花花的銀子,終于在這曾經貧瘠的土地像泉涌般冒了出來。文學是不是從此就云散風清了呢?從市場獲得了自由是不是也意味著獲得心靈的自由?不見得。如果此前的當代文學迷失在意識形態的荊棘叢陣里,那90年代之后的文學就是迷失在市場的誘惑里。盡管是在大洋彼岸,守護文學的再復不可能不發出自己的聲音。與80年代的再復相比,這時候他更強調文學心靈的重要性。文學心靈是擺脫了所有世俗束縛之后的自由心靈。最近我還讀到他兩年前出版的新書《文學常識二十二講》。這是他皈依文學超過半個世紀感悟文學思考文學的成果,它簡約而全面,由他給香港科大學生講課的錄音整理而成。他把文學看成是“心靈、想象力和審美形式”三者的集合。心靈在文學三個基本要素中占據首要的位置。我覺得,再復的感悟是從中國當代文學前半段迷失于政治意識形態后半段迷失于市場誘惑的兩面教訓中升華出來的,它真正實現了對文學本然的回歸。因為世俗的束縛無處不在無時不在,與外在的枷鎖相比,心靈的枷鎖更關鍵。作家不能掙脫心靈的枷鎖,亦無從擺脫世俗的枷鎖,而文學的生命也就窒息了。再復點中了產生于巨變時代的中國當代文學的脈。
可以說文學心靈的自由是劉再復文學理念的核心。它既針對政治掛帥年代的偏差,也針對利益掛帥年代的偏差。再復將80年代對文學主體的論述推進到新世紀對文學狀態的論述。這些年他談論文學,常用文學狀態一詞。他說:“文學狀態,也可以說是作家的存在狀態。從反面說,便是非功利、非市場、非集團的狀態。從正面說,是作家的獨立狀態、孤獨狀態、無目的甚至是無所求狀態。”在消費至上的商品時代,文學做不了政治掛帥年代的要角了,但裝點門面附庸風雅還是可以的。文學被利用起來,投東家所好,獲一點兒資本的殘羹,于是文學淪為了商品。再復非常清醒地意識到無論西方還是東方這種文學的迷失,他甚至呼吁作家重返“象牙之塔”。這個救亡年代的貶義詞被再復賦予了新的含義。他的“象牙之塔”就是文學心靈、文學狀態。重返“象牙之塔”意味著“清貧”與“寂寞”,有誰會聽呢?至少他自己是說到做到,身體力行了,所以他看到了別人沒有看到的文學真知的光輝。
(責任編輯:莊園)
Impressions of Liu Zaifu
Lin Gang
Abstract: This is an account, by Lin Gang, of his impressions of Liu Zaifu, in which Lin talks about and discusses hi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Liu as Lius student as well as his friend, on top of describing Lius image as a man of letters in the ivory tower as well as a traveler around the world.
Keywords: Liu Zaifu, an account of ones impressions, literature, Lin G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