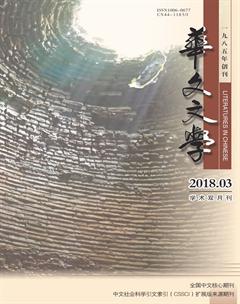“愛情”的位置
陸麗霞
摘要: “愛情”是文學的重要主題之一,不同時期的愛情觀與愛情書寫往往反映出時代特征。在啟蒙與革命思想的影響下,中國現代文學及建國初的主流文學中,愛情書寫往往處于邊緣地位;新時期以來,愛情觀發生了重大改變,愛情書寫也呈現出多元化、個人化特征。近年來很多文學作品在思考愛情本身及其所遇困境。嚴歌苓擅長寫愛情故事,她的新作《芳華》聚焦中國歷史與現實,愛情依然是其主線。小說跨越40多年,呈現了3種愛情模式,展現了不同時代的精神困境:第一種展示欲望與“崇高”的道德要求的沖突,第二種寫出商品化與個人情感的矛盾,第三種展現愛情與心靈創傷的關系。
關鍵詞:愛情;《芳華》;矛盾
中圖分類號:I10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677(2018)3-0092-06
嚴歌苓是當代海外華裔作家中高產作家之一。她眾多作品在討論男女情感問題,尤其探討個人情感與民族、國家與社會現實之間的關系,如《小姨多鶴》寫出被賣作“生育工具”的日本女子多鶴與張儉之間產生的愛情,這種愛情涉及到與民族身份、一夫一妻制等矛盾;《少女小漁》寫小漁為了移民身份,在男朋友的操辦下與當地老男人結婚,“丈夫”對小漁產生了真感情,而男朋友為現實犧牲她,寫出在生存困境中愛情的模樣;《天浴》寫到下放的女青年文秀企圖靠身體換取回成都的通行證,結果想要的未得到反而導致自己身敗名裂,真正愛她的男人按她的暗語,結束了她的生命,自己也自殺與她同葬在雪中,小說寫出精神之愛的圣潔。新作《芳華》延續對愛情的思考及對愛情困境的書寫;小說原名《你觸摸了我》(《You Touched Me》),講述了文工團幾個年輕文藝兵的青春時光,它跨越40多年,以發生在劉峰身上的3段情感經歷,描摹出不同的感情困境,反映了不同時期的精神境況。
一
劉峰的第一段感情也是最重要的一段感情是對林丁丁單方面的愛戀。這段愛情展示個體欲望與“崇高”的道德要求的矛盾。
70年代的劉峰,又被叫做雷又峰。他原是貧困縣梆子劇團翻跟頭的孩子,后來到了文工團當演員。在文工團,他業務水平并不優秀,但心地善良、經常幫助身邊的人,成為文工團的“重要”人物。在“我”初識他時,他的形象還是豐滿的,盡管處處幫助他人,受到他人贊賞,但還是有缺點的、有別人不喜歡的時候,比如錯把落后分子、偷紅薯的婦女當成是受害者而批評“我”;比如作為文工團毯子功教員,因為監督并指導文工團學員們練習他們最不喜歡的毯子功而遭到白眼。然而,事情的變化始于劉峰當選為全軍學雷鋒標兵,尤其是作為軍區代表去北京參加全軍學雷鋒標兵大會。在特定時代背景下,劉峰成為了時代價值觀的范本,他的形象一下子變得“崇高”起來,成為大家眼中的“神”。正如托馬斯·威斯科爾(Thomas Weiskel)對“崇高”高度簡潔的定義,即“崇高的最根本的訴求,就是人能夠在言語和情感上超越人性”。①在各種巡回演講、報告、表彰會等儀式中,劉峰作為“神”的形象不斷地被強化。對于劉峰,每一次表彰意味著外界“在他光榮神圣上加的枷鎖,為了他更加安全牢固地光榮神圣下去”②,也意味著一次對自我的限制。
在特定的時代,道德的“神”意味著總體的道德形式,也意味著個人的價值偏好與情感需求要得到相應的矯正。王斑曾分析“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總是匆忙地把一個個的人物捧上神壇,供我們膜拜與效仿。中國文化中對壯美、高尚的英雄人物的尋求從未止息。如果說中國現代歷史的宏大敘事是一個悲劇,那么,觀眾則是被誘導著去賦予主角以崇高的品質”。③在一次次儀式中,大眾好像觀眾,將原本豐滿的劉峰引入到更深的牢籠。
在“神”的身份下,劉峰的“本我”被無情地壓抑了。小說中,劉峰對林丁丁的愛戀始于本能的欲望,這種愛戀可以追溯到一次業務訓練。在那次訓練中,劉峰意外地看到了從林丁丁褲管里飛出來的女性核心處帶血的衛生紙。這種源于生物的愛戀,經過靈魂的醞釀出現了升華。其實他們倆都是軍官,原本是可以正經談戀愛的,但作為各類標兵模范的劉峰決定等林丁丁事業上、政治上有了進步,尤其是順利入黨后才跟她表白。當時機成熟時,他渴望釋放這種愛欲,所以有了后來的“觸摸事件”。“觸摸事件”是他對林丁丁愛戀的升華也是整本書的轉折點。故事源于劉峰邀請林丁丁去看他幫炊事班班長打的沙發,在那個相對封閉的二人世界里,劉峰覺得林丁丁入黨一事已定下來了,時機已成熟,鼓足勇氣向她表白。林丁丁頓時被嚇壞了,開始哭泣,劉峰一邊不知所措地用一只手抱住林丁丁,另一只手為林丁丁擦淚,在不經意間順勢深入了她的后脖頸、向她的襯衣下面開始進攻。林丁丁大喊一句“救命啊”后落荒而逃。她的呼叫恰好被人聽到,而林丁丁不顧郝淑雯、蕭穗子的勸阻,供出了劉峰。劉峰從此從“神”的位置上墜入“道德敗壞”的深淵,遭到文工團的批斗,并且受到了處罰:黨內嚴重警告,下放伐木連當伐工。后來,劉峰被調回野戰軍的一個工兵營,在戰場上丟了右手。
小說寫到林丁丁實際上并不排斥劉峰的身體,“她繞不過去的是那個概念:雷又峰怎么從畫像上從大理石雕塑基座上下來了?!還敢愛我?!”④在大眾眼里,劉峰是去個人的、去情欲的高度道德化的存在,林丁丁是無法接受這個“崇高”的英雄竟然變成了平凡人,竟然還有了情欲。一個人因為有了情欲而變得豐富,可是劉峰卻因為“神”的身份而受到“詛咒”,無法得到愛情,因為在那個時代,“神”怎么能有凡人的愛欲,而且人怎么能與“神”去談戀愛呢?可以說,造神的大眾在無形之中排除人的豐富性,這也是劉峰作為神的代價。
劉小楓在《沉重的肉身》中寫到現代的敘事倫理有兩種:人民倫理的大敘事與自由倫理個體敘事。在人民倫理的大敘事中,歷史的沉重腳步夾帶個人生命,敘事呢喃看起來圍繞個人命運,實際讓民族、國家、歷史目的變得比個人命運更為重要。自由倫理的個體敘事只是個體生命的嘆息或想象,是某一個人活過的生命的痕印或經歷的人生變故。⑤在這部小說,小說家對劉峰的“觸摸事件”及其對林丁丁的愛戀,絲毫沒有貶低之意,顯然,她更注重的是自由倫理的個人敘事,她在講述劉峰的故事中,讓讀者明朗那個時代里人所“面臨的道德困境”,也讓人能夠去思考自己該如何成為自我,而不是某一種既定的道德律令的復制品。在寫劉峰受到批判回歸到“凡人”,甚至在“道德”上低人一等時,小說家以懺悔的口吻,反思了當時那些參與構建“神”的觀眾,他們不念及劉峰對他們的恩惠,義憤填膺地細數劉峰的罪行,就連劉峰為他打了一個暑假沙發的炊事班班長也沒有放棄這次機會,大說劉峰的壞話;而最讓人心痛的是,劉峰自己也說自己的壞話;這種自我撕裂,讓“崇高”無處遁形。大眾在構建神的同時,渴望瞥見神作為人一面,但是當人的本我出現時,他們又集體以極端的方式將其連根拔起,不讓其回到凡人的位置。所以當劉峰被打回原形時,大眾出現了一種短暫的狂歡。這種情感的釋放,帶有長期自我平面化壓抑后的舒展。劉峰臨走時扔掉他所有的獎章,一方面是對自我的釋放,另一方面是對“神”的身份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小說還從旁側去強化這種個體欲望與“崇高”的道德要求的矛盾。小說中,那些充當審判的大眾,一方面站在道德至高點批判劉峰,但另一方面,他們不斷懷疑道德之“神”的真實性,追求與這種道德判斷相左的個人欲望。比如,一心只想嫁給某個首長做兒媳的林丁丁,一邊嫻熟地“表演”著天真無邪、“輕傷不下火線”的進步青年,一邊在幾個追求者之間周旋,權衡自己的利益,這種以物質條件為基礎的愛情,實際上是對以奉獻為價值基礎的愛情觀的解構;比如郝淑雯直接以身體誘惑與蕭穗子戀愛的少年并讓他出賣蕭穗子,“她把同情、善意,甚至崇拜都給好人”⑥,但卻愛上并嫁給軍二流子。這些都表明“崇高”背后人的欲望是無法壓制的,人的豐富性是突破符號化的理想。
劉峰原本是個善良的平凡人,因為偶在的善良品質而被推上了道德神龕,無法得到平凡人的愛情。他這一段愛情,展現特殊時代本我與超我的矛盾,從某種角度解構十全十美的“崇高”形象,所以在尊崇英雄的70年代,劉峰不可避免地成為了悲劇人物。
二
劉峰第二段感情發生在80年代末的海南,是與一個叫惠雅玲(小惠)的從事性交易的女性的一段愛戀。這段愛情展現了兩個時期價值觀的碰撞。
20世紀80年代開始,躲避崇高、反崇高的情緒興起,“反崇高的政治,即以身體對抗壓抑權威,完全被更大、更‘崇高的經濟發展、瘋狂消費的全球政治俘虜”。⑦80年代末,劉峰在海南從事圖書買賣,與惠雅玲相遇時,她正處于被侮辱被損害的位置。她冒雨尋找“客人”,被淋得人不人鬼不鬼而無處可去時,善良的他選擇幫助這位女性。于是他收留了她在家過夜,并且給了她一筆錢讓她去學點手藝。他們后來在一起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小惠讓他大腦里閃過林丁丁“一身筆挺毛料軍服,風華絕代的獨唱女兵”⑧的形象。他對小惠的感情帶有矛盾性,一方面善良讓他渴望去拯救弱者;另一方面,他不過是愛她的身體,并不是以心去愛她這個人,“身體愛身體,不加歧視,一視同仁;他身體下的女人身體是可以被置換的,可以置換成他曾經的妻子,可以是小惠的姐妹小燕或麗麗”⑨。而在情感上他對她是極端厭惡的,因為她永遠也無法代替林丁丁的圣潔,或者青春愛欲的純潔。這種情感如果再往深處挖掘,具有更深意義。他因為被塑造成“崇高形象”而失去了真實的愛情、因為表達真實的情欲而遭受生活的大落,而小惠是在商品經濟中將性作為商品進行交易的“從業者”,在小惠的身上,雖然無法滿足其對愛情的欲望,但是卻可以釋放其身體的欲望。這一段愛情,多少寫出了經濟時代,原有的“崇高”價值體系的失落。小說中多次提到他右手假肢上的破洞,小說家不惜發揮想象去重構那段故事:小惠過上了一段時間從良生活后,又重新回到酒店從事性交易。劉峰發現后,倆人發生了爭執。在爭執過程中,劉峰對小惠發了最為樸素的誓言:我吃糠咽菜都有你一口。然而此時在經濟大潮中的小惠,早已過不上這種淳樸的清貧生活,她鄙夷地看著劉峰,趁著劉峰熟睡后,將煙頭摁在他的假肢上。如果說右臂的失去是因為他表達對林丁丁的愛欲而得到印記;那么這個假肢上的傷痕,成為了他這段感情的“遺產”,這寫出了他落入凡人之后,原有的高尚品質連最基本的尊重也換不回了;同時寫出了一代人的光榮化為塵與土的悲涼,就像是故事的結尾,劉峰的女兒劉倩把他父親的經歷看成不相關的事情,甚至“在心里帶些鄙薄地偷笑”⑩,而且把年輕的犧牲者看成是多余的犧牲,看出了歷史以驚人的速度被遺忘,而留給人思考如何平凡地生活。
“妓女”曾被認為是現代社會個人自由敘事的重要極端代表之一,在這里同樣適用,她體現全球經濟時代,人處理自我身體以換取物質的自由。曾經代表公共道德的楷模與以性為交易的人并置;奉獻、同甘共苦的價值體系,與不顧道德底線地追求物質的生活態度并置,不得不說形成一種諷刺,這既是對劉峰所受懲罰的諷刺,也是對參與造神與毀神大眾的諷刺。他們兩人的感情可以說是兩個不同時代價值觀的碰撞,他們的分開也是必然的。小說寫到劉峰向郝淑雯借了一萬塊錢給小惠,打發她離開,這實際上也是劉峰自我的解脫,因為他內心不斷在情欲的解放與理性的鄙夷中游走奔波。自我商品化的小惠用這些錢做了高鼻梁雙眼皮,類似于將商品重新包裝,以便在市場上獲取更高的回報。在金錢的力量下,小惠還是從良了,經濟狀況良好的她供女兒彈鋼琴,上貴族學校,希望她將來過上與自己完全不同的“貴族”生活,這些生活細節都在向讀者展示新的價值體系的表征。小說沒有去評價小惠的追求與當年劉峰想讓小惠從良的志向孰高孰低;劉峰當年半途而廢,而經濟良好的小惠則在逐步實現自己的理想,這說明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曾經的“崇高”被不斷解構。當然,小說寫到“把這從良的種子播撒到小惠年輕蒙昧心田的是劉峰”{11},在這一點上依然可讀出小說家對于劉峰時代價值體系及劉峰所做努力的認同。
三
劉峰的人生可以說是悲劇的,但故事結尾出現了意想不到的溫情——何小曼對劉峰的愛戀,這可以說是劉峰灰暗人生中漏出來的光。這段感情源于“創傷”,而他們最終未能真正走到一起也是因為“心靈創傷”。
小說中,何小曼與劉峰幾乎是同等重要的,甚至可以說何小曼才是主角。小說對她成長史的講述幾乎是完整的。幼年時,小曼有過一段溫馨的生活,那時候,她可以無所顧忌地透支她親生父親的物質和感情。但是自從她的文人父親被劃為“右派”后“自殺”,母親改嫁給老粗廳長,悲慘的寄人籬下生活便開始了。母親后來又生了弟弟和妹妹,她的日子就更艱難,而最讓她難以接受的是母親為了維持慈母愛妻形象,根據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態度,這種“變形”讓她決定離開這個家。報考文工團是她離家的道路之一。她以自虐式的翻跟頭進入了“被虐”的文工團。在整個小說中,她的感情世界是破碎的,父愛、母愛的缺席,同伴的嘲弄與排擠,讓她成為十足的邊緣人物。然而,這個邊緣人物身上無時無刻體現著現代理性話語之外作為人的真正欲望。
何小曼對劉峰的愛戀始于劉峰對其創傷的撫慰。何小曼在文工團遭到排擠,在一次排演中,與她搭檔的男兵嫌棄她,拒絕托舉她,劉峰主動與男兵換位置、與何小曼搭檔,為她解圍,讓她感受到了安全、踏實。“從那次托舉,他的兩只手掌觸碰了她的身體,她的腰,她就一直感激他。他的觸碰是輕柔的,是撫慰的,是知道受傷者疼痛的,是借著公家觸碰輸送了私人同情的”,“這世界上,只有她的親父親那樣扛過她”{12}。劉峰對她破碎感情世界的修復,讓她對愛與安全的渴望得到短暫的滿足。所以,當大家詆毀、批判劉峰時,何小曼是唯一沒有參與批斗的,就如劉峰是與所有人站在對立面去幫助她、把她當“人”來看,她也是當時唯一將劉峰還原為人、看到了他人格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善良”的人。劉峰臨走時,何小曼主動到劉峰宿舍給他送行。劉峰被調走后,她留在了基層,因為她覺得“在劉峰被處理下放之后,就對所有人徹底寒了心”,“由于劉峰的離開,她開始對自己的身世和周遭世界生出一種厭倦,漸漸地,厭倦化為悲哀”{13}。“觸摸事件”對于劉峰是一種解脫,而對何小曼又何嘗不是,因為劉峰從此成了“人”,且與自己同等海拔的人,她可以以最感性、最安全的方式去表達自己的愛戀。
1979年,何小曼因為救一個重傷員而被新聞“夸大其詞”地報道了,一時間,何小曼成為“戰地天使何小曼”,全軍區掀起了向她學習的熱潮。在又一次造神的滾滾洪流中,她被要求四處巡回演講,而只有她自己知道她只是一個并非完滿的真實個體,她內心有太多的委屈,她太渴望那缺失的母愛。她的故事把大禮堂里的中學生們都感動哭了,但是“小曼是不會哭的,有人疼的女孩子才會哭”{14}。成千上萬的崇拜蜂擁而至,好像要把她過去所有的欺凌和侮辱都統統抵消過,但這份沉重終于壓垮了她,她瘋癲了。在她住院期間,劉峰去看望了她。要知道她住院期間只有3個人去看過她,一個是她的母親,一個是給她送去丈夫犧牲消息的野戰醫院政治處主任,還有一個就是劉峰。因為劉峰是懂她的,懂一個平凡人與英雄之間的距離,懂得“被邊緣化”的人的卑微。劉峰與何小曼的感情實際上是兩個有心靈創傷的人的相互理解與慰藉。
1998年劉峰到他侄子在北京的公司上班,第二年,小曼為了劉峰,接受了自己討厭的工作,來到北京。她是第一個知道劉峰得了絕癥的人。“她把劉峰從醫院接到兩居室,照顧他,在他被化療敗盡胃口時為他做點湯羹,在他連翻身都翻不動的時候,架著它,用一把骨頭的肩膀扛著他,在60平方米上遛彎。小曼就那樣,整整3年,為我們一百多個消費了劉峰善意欠著劉峰情分的人還情。尤其是替丁丁還情”{15}。
但是,劉峰與她并沒有真正意義上在一起,劉峰愛的能力在林丁丁喊“救命”的那一瞬間消逝。那件事給他留下太深的創傷,這種創傷往往以強烈自尊的形式表現出來,小說有一個場景是非常值得關注的,就是劉峰跟何小曼說,林丁丁從澳洲寫過信給他,還給他寄過照片,而實際上這些關于林丁丁的細節都是從郝淑雯那里聽來的,劉峰的這種表現不僅是彌補自尊,也是以虛構的形式去滿足“創傷的”夢。
何小曼的邊緣地位,讓她具有更多自我的空間。“真實”是她最大的特征,她追尋自己的內心,尋找自己所愛的男人。這種愛情讓劉峰與她的灰暗人生有了一點暖色調。她與劉峰的愛,是彼此的慰藉,是個體追求情感的滿足,是人回到本我的自由意志。
結語
以啟蒙與革命為基礎的中國現代性,追求合乎目的的線性歷史,往往將個人情感置于相對邊緣的位置。關于建國初的愛情書寫,孟繁華曾評價“自普羅文學始,革命與愛情從結伴而行到革命優于愛情并不斷得到強化,在這個年代,雖然時代環境具有不確定性和文藝政策的不斷變化調整,但作家對愛情表達的心態和觀念,仍然具有統一性和整體性的特征。”{16}自70年代末始,對個人情感的書寫,呈現了多元化、個體性的面貌。
一,“愛情”問題不再是禁忌或者政治、革命等附庸,而成為可以獨立、公開討論的話題。比如,傷痕文學作家劉心武《愛情的位置》(1978年《十月》第1期),開始反思“把愛情問題驅除出文藝作品乃至于一切宣傳范疇的結果,是產生了兩種不正常的現象。一種,是少數青年把生理上的要求當作愛情,個別的甚至墮落成為流氓,這一種我暫不愿加以研究。另一種,可就非常之普遍了——不承認愛情,只承認婚姻。”{17}小說中,孟小羽愛上烙火燒的工人陸玉春,兩人情投意合,卻被好朋友亞梅認為陸玉春的職業與家境不好,與孟小羽不般配。小說中提出了“愛情的位置是什么”的問題,孟小羽的愛情回答了,真正的愛情是地位與金錢代替不了的。張潔《愛,是不能被遺忘的》(1979年《北京文學》第11期),以自己對婚姻本質的思考為引子,講述了母親的一段柏拉圖之戀,提出“愛,是不能被遺忘的”,認為婚姻不是一種道義、經濟等交換,而是心與心的交換。張弦《被愛情遺忘的角落》(1980年《上海文學》第1期)寫到“盡管已經跨入了20世紀70年代的最后一年,在天堂公社的青年們心目中,愛情,還是個陌生的、神秘的、羞于出口的字眼”{18}。故事講述了母女兩代、3個人物的情愛經歷。青年女子存妮與小豹子產生了情愫,他們在一次私會中被民兵營長抓住了,存妮出于羞愧而自殺,不久小豹子也因此被認定為“強奸致死人命犯”而判刑;妹妹荒妹又與新上任的支部書記許榮樹產生好感,而父母卻要將她許配給吳莊三隊的一個從未謀面的人。而母親菱花是自由戀愛而結婚,但卻在經濟的壓力下,認為自己不該選擇愛情而應該選擇物質,所以逼迫女兒為生存而嫁。在掙扎與痛苦中,荒妹期盼著大地回春的第一絲信息,能夠來到這被愛情遺忘的角落。這些作家都以各自的方式,提出了“愛情”本身的重要性。
二,愛情成為人之所以為完整的人的重要部分。如張賢亮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1985年)等小說中,寫主人公章永璘在勞動改造期間,黃香久給了他愛的撫慰和性的滿足,重新激起了他作為男性的情欲與激情,讓他意識到自己不只是一個毫無性別的“勞動力”,而是有性別特征的個體。同樣,王小波《黃金時代》(1994年)中陳清揚以“偉大的友誼”的名義不斷地王二偷情,一方面因為她被大眾認為是“破鞋”,原本不是“破鞋”的她無法自證自己不是破鞋,所以她干脆出軌,以對得起這個稱號;另一方面,在故事結尾處,陳清揚主動承認她與王二的偷情是因為她喜歡。在無性的年代,搞“破鞋”要五馬分尸千刀萬剮,但是她認為如果是因為愛情,那就沒有人有權力去懲罰他們。性愛是人的本能,對基于愛的性的理解與寬容,反映出社會對人的尊重。
三,對愛情的思考與書寫呈現個人化的狀態,一方面出現以消費身體欲望為內容的寫作,如衛慧、棉棉等身體寫作;另一方面,一批作家從更深層次去思考愛情的本質,思考愛情與歷史理性,如革命、自由、進步、倫理道德等之間的關系。如史鐵生的《務虛筆記》思考愛情與叛徒、孝、政治權力等關系;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思考愛情與革命的關系等。
嚴歌苓一直關注愛情,她域外生活的經歷為其愛情書寫增加了諸如民族身份、移民生存等多重視角。《芳華》跨越了40多年,繼續書寫愛情這一主題,小說的故事背景回歸到中國歷史與當下,它以一個人物不同階段的三段愛情來反映不同時期社會精神狀態與困境:第一種“愛情”,讓我們瞥見了所謂的“崇高”與個體本我的矛盾;第二種“愛情”呈現以物質為核心的愛情觀與原有價值觀的碰撞;第三種“愛情”是讓個體情感復歸個人,讓凡人的愛情,拯救斷臂的“神”。
① 威斯科爾(Thomas Weiskel):《浪漫的崇高:超越的結構與心理研究》(The Romantic Sublime:Studies in the Structure and Psychology of Transcendence),巴爾的摩: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3頁。轉引自[美]王斑著,孟詳春譯,《歷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紀中國的美學與政治》,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版,引言部分第2頁。
②④⑥⑧⑨⑩{11}{12}{13}{14}{15} 嚴歌苓:《芳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11頁;第59頁;第164頁;第167頁;第173頁;第212頁;第166頁;第109-110頁;第120-121頁;第136頁;第209頁。
③ [美]王斑著,孟詳春譯:《歷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紀中國的美學與政治》,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版,引言部分第1頁。
⑤ 劉小楓:《沉重的肉身》,華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6頁。
⑦ [美]王斑著,孟詳春譯:《歷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紀中國的美學與政治》,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版,中文版前言第2頁。
{16} 孟繁華,《革命時期的愛情·序》,《青春小說精品讀本:革命時期的愛情》孟繁華主編.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序言第2頁。
{17} 劉心武:《愛情的位置》,《班主任》,譯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49頁。
{18} 張弦:《被愛情遺忘的角落》,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1頁。
(責任編輯:黃潔玲)
The Position of Love: On the Sentiments in Youth by Yan Geling
Lu Lixia
Abstract: Love is an important theme of literature. Views of love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the writing about love often reflect the features of an ag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mainstream literature as written in the first years of new China,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nlightenment and revolutionary thinking, writing about love is often placed in a marginal position. Since the New Period, however, views of love have considerably changed as writing about love has also become pluralistic and individualistic. In recent years, much thinking has been done in literary works about love itself and the difficult situations it finds itself in. Youth, by Yan Geling, good at telling love stories, has love as its main line of narrative, focusing on the Chinese history and realities, with a story that spans four decades in three modes of love, representing a spiritual predicament in various times: the first being the conflicts between an individuals desire and the‘sublimemoral requirements, the second,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commodification of individuals and personal emotions, and the thir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 individuals love and his or her trauma.
Keywords: Love, Youth, contradic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