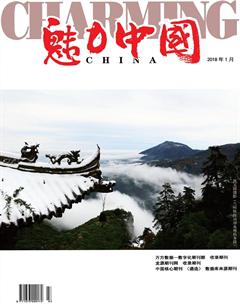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可能及必要性研究
摘要:當前我國農村正在經歷著社會巨變,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市場化的侵襲,農民傳統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發生變化,傳統文化習俗與現代文明發生沖突。弘揚新鄉賢文化,鼓勵、支持新鄉賢參與基層自治,符合當前政策要求,同時也是改善農村政治生態,實現農村政治參與多元化的重要方式。
關鍵詞:新鄉賢;鄉村治理;政治參與
2016年提交全國兩會討論的《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強調,要在“加快建設美麗宜居鄉村”中“培育文明鄉風、優良家風、新鄉賢文化”。鄉紳在鄉村熟人社會中,一個“鄉”字同本籍鄉民在血緣關系、地緣關系上,存在著強烈的情感和身份認同,在治理成本和治理能力的比較下,僵化執行強制性的國家行政權力的地方官府讓位于紳士階層,紳士階層當仁不讓的成為地方利益的代表者和實際管理者。當前農村人力資源不斷外流,新鄉賢的回歸,有助于改善村民自治方式,提升治理水平。
一、歷史依據
1.傳統社會中與國家制度相配合的鄉紳自治。
農業社會中,鄉村治理的常態實行的是一種“官督紳治”體制。皇權高度集中的統治下,紳權作為國家正式權力的有效補充,對于推動農業經濟發展、農村的和諧穩定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國古代社會是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倫理型文化,幾乎被抬升到了享有與法律同等強制性效力的高度,而在廣大基層社會中,占有文化資源的鄉紳,通過對文化資源的壟斷間接獲得了對社會事務的解釋支配權。王先明認為,“傳統中國的治理結構,上層是中央政府,底層是地方性的管制單位,由族長、鄉紳或地方名流掌握”[1]。鄉紳文化權力一體化,鞏固了自身階層的權威,作為統治階級不可小覷的附庸,無論是服務上層階級亦或是代表農民利益在與官府博弈上,成為維系鄉村社會持續運轉的中堅力量。
2.農業經濟持續發展的潤滑劑。
傳統社會經濟發展以農業為主,單一的農業經濟發展模式,使得農業發展重要性不言而喻。自然狀態下的農業生產靠天吃飯,原子化分散的農民難以有效抵御天災人禍。由于農村社會底層不存在行政單位,導致村莊范圍內的區域性農業發展在社會經濟與組織基礎方面缺乏國家財政支持。“無法形成資源集中和提取的社會渠道,沒有充分的配置性和權威性資源來構造一個統一的權力集裝箱,致使對鄉土社會的監控處于相對松懈的狀態”[2]。地方官員面對修建大型公共工程,也不得不獲得地方上有影響力和號召力的鄉紳的支持。鄉紳作為地方領袖,不具備擁有正式權力的官方身份,但掌握農民信服的非正式權威,能夠有效募集財力、人力,進行農田水利等大型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農業生產和農村基礎公共事業建設。
3.鄉土文明的傳承者,傳統禮教的捍衛者。
明清時期,封建統治者進一步宣揚傳統仁義信思想,強調君臣父子尊卑體系,在社會立碑以紀念民間大儒對鄉鄰所做的貢獻。儒家思想文化催生出的倫理型文化與傳統社會中的宗法制度共同構筑成中國傳統的道德倫理秩序。為維護體制需要的士紳階層則堅決成為文化秩序的捍衛者。費正清認為,“政府一心指望縉紳階級能維護道德或鼓舞民氣。在最高統治者的推動下,中國人偉大的向學傳統就成為教化百姓的工具,而作為地方精英的鄉紳則為鄉居日常生活樹立了榜樣”[3]。鄉紳基于此在農民默認中具備了一定的權威,作為民間知識文化的傳遞推廣者,承擔了推動民間私學、向農民傳播禮俗教化觀念的責能,滿足了農民的社會期待。
4.制度沖擊下的鄉紳治村被動撤離。
民國時期,國家政權不穩定,地方割據嚴重,鄉村基層政權內卷化嚴重,土豪劣紳趁虛而入,灰黑勢力控制了鄉村治理,治理方式以暴力強權取代了傳統說教軟治理,全面管控鄉村社會。鄉紳階層開始退出歷史舞臺,鄉紳治村與鄉村治理漸行漸遠。“原來應該繼承紳士地位的人都紛紛離去,結果便只好聽濫竽者充數,紳士的人選品質自必隨之降低,昔日的神圣威望乃日漸動搖”[4]。建國后,一系列的破舊活動和政治運動,將鄉紳歸為地主階級而遭到壓制,支撐鄉賢存在的社會基礎不復存在;伴隨行政機構自上而下深入農村,紳士階層完全消失。國家逐漸建立起一套完備法律體系,管控鄉村社會的現代化行政機構也建構完成,通過行政權力強力嵌入基層社會。
二、現實需要
1.基層民主發育不健全,灰黑勢力在鄉村“有所作為”。
鄉村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石和重要組成部分,積極推動鄉村治理向著現代化、法制化方向發展,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國士紳的一個重要特點在于“他們是唯一能合法地代表當地社群與官吏共商地方事務、參與政治過程的集團[5]。農業產業發展滯后難以吸納剩余勞動力和市場機制的誘導下,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外流,村莊留守老人兒童難以起到有效的制約和監督作用,地方宗族勢力有所起色,這種以地方宗族為代表的黑惡勢力憑借暴力威脅手段參與到集體事務管理活動中,村莊公共事務的管理權由地方大家族惡勢力把持。地方宗族惡勢力實行的專橫管理,逆社會發展趨勢,嚴重阻礙了村莊民主法制進程,加劇農村內卷化程度。
2.鄉村空心化加劇,經濟拉動力不足。
地方發展不能純粹依賴國家資源的長期輸入,要借助于國家人力物力支持,積極尋求合適出路才是重振鄉村經濟的關鍵。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熟識村情、有能力有擔當的新鄉賢,是村集體經濟發展帶頭人的最佳人選;村莊提供了滿足新鄉賢回報家鄉、實現社會價值需要的平臺,這一治理主體在為村莊尋出路、轉變村莊傳統經濟發展方式上起到建設性作用。
3.農村主流道德及價值觀異化,鄉規民約軟約束作用下降。
地方文化的保護和傳承工作存在帶頭人缺失的現實需要。市場經濟思維的泛化所造成的自利文化,在鄉村社會催生農民產生了功利化的認知與認同的標準。儒家思想控制消失和道德倫理體系坍塌動搖了農民的精神信仰,文化教化活動伴隨士紳階層消失加劇了村莊文化荒漠化,農民思想和意識形態上的松動表現在鄉規民約的約束作用下降,鄉村社會事務解決處理上“無訟”傳統讓位于經濟利益準繩,在缺失法制化評判標準的指引下,道德規勸力和文化約束力弱化反映出當前鄉村社會農民內部客觀存在的現實矛盾。
參考文獻:
[1]王先明.近代紳士[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123.
[2]張健.傳統社會鄉紳的鄉村治理[J].安徽農業科學,2009,(5).
[3]費正清.中國:傳統與變遷[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207.
[4]吳晗,費孝通等:《皇權與紳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5頁。
[5]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M].范忠信,晏鋒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83頁。
作者簡介:王生章,男,漢族,曲阜師范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政治學理論專業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