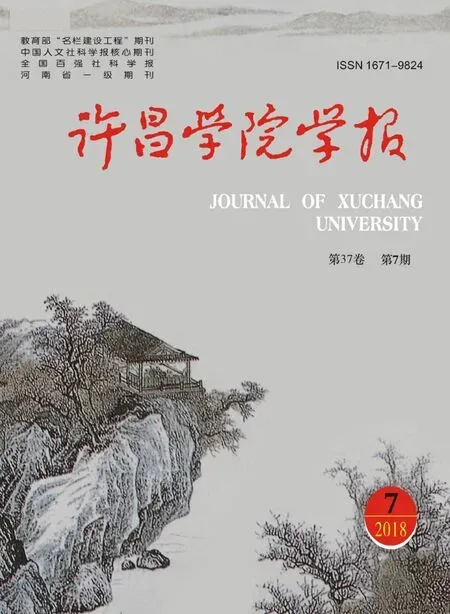北朝醫者與政治
高 貝 貝
(許昌電氣職業學院 招生處,河南 許昌 461000)
醫者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既是療君親之疾、救貧賤之厄的技藝之士,又是保身全命的養生踐行者。故世人常云,醫,“精義也,重任也”[1]自序。即便醫者擁有精專的醫療技藝和救死扶傷的強烈責任心與使命感,也無法泯滅其在世人心目中“方技(伎)”“藝術(術藝)”之士的社會身份和形象。不過醫者卻可以憑借其專業的醫療知識和技術進入上自君王貴胄、下至黎民百姓的私領域,為之治療病痛,維持生命,延續香火,并可享有相當彈性的政治活動空間,有機會獲得君王的特殊寵任而進入統治者的公領域,參與國家政務。這一特殊的社會群體擁有著雙重的身份與社會角色,其內心深處自然蘊蓄著一番精神向往與人生理想。那么,在南北朝時期醫學權力被“門閥的醫家”“山林的醫家”所占有時*參見范行準:《中國醫學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8頁。,醫者群體又是如何實現人生的意義和價值的呢?本文試以北朝醫者(即學人所說的“門閥的醫家”)為中心,從史料中梳理出醫者與政治之間的關系,以就正于方家。
一、佐助新皇登基
在君主政治時代,帝王作為國家權力的實際載體,肩負著與生俱來的神圣使命:治國安邦,垂世濟民。既然君主是天下萬民仰賴的對象,統治者只有得到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認可和擁戴,方能位居尊位,治理天下。《魏書·禮志四》記:
四年春正月丁巳夜,世宗崩于式乾殿。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與詹事王顯,中庶子侯剛奉迎肅宗于東宮,入自萬歲門,至顯陽殿,哭踴久之,乃復。王顯欲須明乃行即位之禮。崔光謂顯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曰:“帝崩而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光與于忠使小黃門曲集奏置兼官行事。于是光兼太尉,黃門郎元昭兼侍中,顯兼吏部尚書,中庶子裴俊兼吏部郎,中書舍人穆弼兼謁者仆射。光等請肅宗止哭,立于東序。于忠、元昭扶肅宗西面哭十數聲,止,服太子之服。太尉光奉策進璽綬,肅宗跽受,服皇帝袞冕服,御太極前殿。太尉光等降自西階,夜直群官于庭中北面稽首稱萬歲。[2]2806
倘若立國而無君,出現權力真空,則必然會出現混亂、動亂局勢,乃至亡國。故宣武帝元恪駕崩后,醫者王顯等人擁護孝明帝元詡承襲皇位,臨治天下。不過這次皇權交接過程中的斗爭異常激烈,以王顯為代表的外戚高肇集團同以于忠為代表的外戚于氏陣營展開殊死搏斗,其表現為即位時間之爭。從王顯、高肇系的利益角度來看,若元詡天明即位,王顯等人就可以爭取時機,把宣武帝駕崩的消息奏知中宮,讓皇后高氏出面干預,出現太后臨朝聽政的局面,若此,王顯等人既可繼續享有既得權益,又有加官晉爵進一步擴大權勢的無限可能。從于忠系的利益角度來說,迅速扶持元詡即位,他們就成為擁立新皇登基的最大功臣,既可把新皇作為他們的政治代表而牢牢控制手中,又可避免高后干預朝政,還可在今后同王顯、高肇系的爭斗中占據上風。兩大陣營各有思量,其“計劃體現了兩種前景,王顯的計劃是導致太后臨朝局面的出現,于忠等人的計劃則是由未被顧命之權臣輔政并控制朝政”[3]10。最終,因高肇在外征伐,王顯等人于朝中勢力微薄,在元詡即位時間上敗給于忠等人。
醫者王顯雖擁立新主即位有功,但在新朝尚未有所作為時就在同于忠的爭斗中敗陣而亡,“朝宰托以侍療無效,執之禁中,詔削爵位。臨執呼冤,直閣以刀镮撞其腋下,傷中吐血,至右衛府一宿死”[2]1969。同樣是參與君王權位交接,醫者王顯被下獄削爵誅殺,而徐之才卻馳騁官場,安然終老。《北齊書·徐之才傳》載:
之才少解天文,兼圖讖之學,共館客宋景業參校吉兇,知午年必有革易,因高德政啟之。文宣聞而大悅。時自婁太后及勛貴臣,咸云關西既是勁敵,恐其有挾天子令諸侯之辭,不可先行禪代事。之才獨云:“千人逐兔,一人得之,諸人咸息。須定大業。何容翻欲學人。”又援引證據,備有條目,帝從之。登祚后,彌見親密。之才非唯醫術自進,亦為首唱禪代,又戲謔滑稽,言無不至,于是大被狎昵。[4]445
醫者徐之才、天文數術之士宋景業“運用自己所了解的那些天文知識,對天道規律進行夸大和神化,并將其運用到對人和社會的認識中來”[5]116,依憑高德政向高洋進言:順應天道,取代東魏。畢竟天道“不僅富于理性色彩,代表著自然與萬物的規律,而且也是國家的‘規范’,君主只有按照這些‘規范’行事,才能體現天道的意志”[5]119。最終,高洋篡奪東魏,接受天命。高洋雖然篡魏成功,登臨寶座,在終結東魏國祚時得到了高德政、楊愔等漢族文官的大力支持,但卻遭到了勛貴勢力的強烈反對,更確切地說是遭到了晉陽軍方勛貴的強烈反對[6]241-248,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高洋篡魏事件也包含有胡漢兩集團沖突的意味[7]206。代魏成功后,醫者徐之才因“首唱禪代,又戲謔滑稽”,甚得北齊各代君主寵幸,政治上既扶搖直上,生命上又正常謝幕。
二、參與君王重大決策
帝王要依賴群臣百官的輔佐,才能上情下達,治理國家,而后方可穩居高位,長掌大權。然而在實際的社會政治生活中,帝王要想實現君權的有效統治,至少要具備獨自裁決日常行政事務的能力,即“獨斷”的能力:“其一,君主在政治決策的時候,不為群臣左右,保持判斷的獨立性”;“其二,君主必須始終親自把握最高決斷權,在決策過程中保持絕對的主導地位”[5]236。帝王只有具備了“獨斷”的能力,才不至于遇事倍感壓力,無所適從。《魏書·術藝·周澹傳》云:
周澹,京兆鄠人也。為人多方術,尤善醫藥,為太醫令。太宗嘗苦風頭眩,澹治得愈,由此見寵,位至特進,賜爵成德侯。神瑞二年,京師饑,朝議將遷都于鄴。澹與博士祭酒崔浩進計,論不可之意,太宗大然之,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也。”詔賜澹、浩妾各一人,御衣一襲,絹五十匹、綿五十斤。[2]1965
神瑞二年(415)京師暨并州地區發生嚴重饑荒,引發嚴重的社會政治危機,太史令王亮、蘇垣、華陰公主等人主張放棄平城而遷都鄴城。遷都固然可解明元帝拓跋嗣的燃眉之急,但會帶來嚴重的后果,故崔浩、醫者周澹二人提出定平城為京都的策略。他們的策略既符合拓跋統治者的需要,在當時又有切實可行的現實條件。第一,當時鮮卑軍隊以騎兵為主,于沖鋒陷陣方面擁有很強的戰斗力和威懾力;第二,平城位于畜牧業和農業交匯地帶,可以為農業和畜牧業的發展提供保障;第三,平城于軍事方面有優越的戰略位置;第四,定都平城,建立偌大且穩固的根據地是拓跋統治者早已有之的想法*參見嚴耀中:《從“定都策”說崔浩》,《許昌學院學報》2017年第3期。。明元帝拓跋嗣面對著這份理清言明的固守而非遷都的策略,甚感欣慰,最終拒絕了華陰公主等人的意見,采納了周澹、崔浩二人的建議,分民就食山東三州,以解饑荒。
明元帝裁決是否遷都的理政舉止符合“兼聽獨斷”的模式。當君主做出重大決策時,要善于傾聽多方諫言,之后再做出裁決,切忌輕信近臣,被他者左右判斷,失去最終決斷的主導權。《魏書·外戚·高肇傳》曰:
肇出自夷土,時望輕之。及在位居要,留心百揆,孜孜無倦,世咸謂之為能。世宗初,六輔專政,后以咸陽王禧無事構逆,由是遂委信肇。肇既無親族,頗結朋黨,附之者旬月超升,背之者陷以大罪。以北海王詳位居其上,構殺之。又說世宗防衛諸王,殆同囚禁。時順皇后暴崩,世議言肇為之。皇子昌薨,僉謂王顯失于醫療,承肇意旨。[2]1830
宣武帝重用外戚高肇,初衷在于集中君權,反而卻助長高肇權勢日漸膨脹,致使高肇相繼對統治集團中妨礙其權力提升的恩幸、諸王、皇后于氏及其家族三股勢力予以致命打擊*參見張金龍:《北魏政治史》第8冊,甘肅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7頁。。醫者王顯黨附于外戚高肇,極有可能利用醫療之便謀殺于皇后之子元昌,讓于氏家族在權力斗爭中失去重要籌碼。皇子殞命,宣武帝竟不追責,似乎說明外戚權勢過盛,已可專斷皇權,實則不然,“高肇專權是宣武帝時期北魏皇權政治的體現,它適應了宣武帝加強君主專制統治的需要,高肇權力的膨脹是臣下權力的高度發展,而不是對君主集權的離心傾向”[8]80,故外戚權力依舊在皇權約束之下,對國家政令的決策、執行都沒有非常嚴重的消極影響,宣武帝沒有聽從高肇建議把于忠逐出朝廷,即是保持判斷獨立性的明證。當然,君王作為最高統治者,在做出最后裁決之前,也會親自調查,若情況屬實,可聽從百官言論,如情況不符,可全權否決,給出切實可行的方略,否則,其盲目裁決將會釀成悲劇。《北齊書·崔季舒傳》記:
祖珽受委,奏季舒總監內作。珽被出,韓長鸞以為珽黨,亦欲出之。屬車駕將適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為壽春被圍,大軍出拒,信使往還,須稟節度;兼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云大駕向并,畏避南寇;若不啟諫,必動人情。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唐邕、段孝言等初亦同心,臨時疑貳,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遂奏云:“漢兒文官連名總署。聲云諫止向并,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帝即召已署表官人集含章殿,以季舒、張雕、劉逖、封孝琰、裴澤、郭遵等為首,并斬之殿庭。[4]512-513
祖珽與陸令萱之爭,就其性質而言,至少有胡漢沖突說[9]92、內廷派系爭斗說[6]383-392。暫且不論祖珽與陸令萱之爭,就醫術之士崔季舒等人諫阻后主大敵當前不可避難晉陽一事來看,其做法實屬為國效力,冒死諫言,而韓長鸞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極盡誣陷之能事,慫恿后主屠戮崔季舒等人。最高統治者應該明白,“‘兼聽獨斷’作為一種決策模式,既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政策制定的有效性,同時又維護了君主個人的絕對權威”[5]237,只可惜后主高緯沒有領悟“兼聽獨斷”的真諦,故在決策前沒有廣泛征集意見,沒有切實把握全局,就對崔季舒等人痛下殺手,致使朝廷損失一批能人賢士。
三、涉入君臣權力之爭
王權至上作為一種思想觀念,在整個傳統社會中幾乎令人無法置疑。“全國一切的最高所有權屬于王,臣民的一切是王恩賜的,這兩種觀念的結合,把王置于絕對的地位,為君主專制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依據”[10]223。這種理論自然得到統治者的普遍認可,其目的皆在于在政治決策過程中充分維護帝王的絕對權威。《魏書·景穆十二王·陽平王新成附子衍傳》載:
頤弟衍,字安樂,賜爵廣陵侯。位梁州刺史,表請假王,以崇威重。詔曰:“可謂無厭求也,所請不合。”轉徐州刺史,至州病重,帝敕徐成伯乘傳療。疾差,成伯還,帝曰“卿定名醫”,賚絹三千匹。成伯辭,請受一千。帝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以是而言,豈惟三千匹乎?”其為帝所重如此。[2]442
這一君臣醫療救護事件的性質并不單純。眾所周知,在政治利益共同體當中,“群臣百官是協調君令民情的必要環節,是實現有效的君權統治的保障。如果臣的環節發生故障,則直接影響國事安危”[5]254,故君主必須依靠或利用群臣,有功則賞之,有罪則罰之,恩威并施,方能駕馭百官,進而維護君主的權威和實現有效的統治。反觀元衍主動請封王爵一事,實屬否定君主專制的理論,挑戰帝王的至上權威,企圖左右朝廷加官晉爵大事,遂遭請封不果而轉調他州的責罰。元衍到徐州任上患病后雖得到孝文帝派遣醫者前去療疾的寵遇,但醫者徐謇診候救護的醫療實踐背后蘊含著三層含義:皇親罹疾,天子遣醫前去救護,以示優寵;臣子請封不遂,難免心有不甘,由此與帝王結怨也不無可能,君王派醫前往療病,以期彌平君臣之間緊張的政治關系;最高統治者號令全國,大權在握,豈容他人染指,左右朝堂?皇帝遣醫前去診候,不無窺探臣子最新動向之用意。無論孝文帝出于何種心態,其派遣醫者徐謇前去療疾的行為都在于守護皇權,維護自己的權威。

世宗自幼有微疾,久未差愈,顯攝療有效,因是稍蒙眄識。又罷六輔之初,顯為領軍于烈間通規策,頗有密功。累遷游擊將軍,拜廷尉少卿,仍在侍御,營進御藥,出入禁內。[2]1969
景明二年(501)正月宣武帝巧妙地利用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和禁衛長官領軍將軍于烈的有力支持,在醫者王顯互通宮廷內外傳遞信息的忠心輔助下,成功地發起政變,奪取了孝文帝所設立的顧命大臣的政治權力,開始享有治國理民的最高統治權,并努力建構君主臣輔的權力再分配體系。
統治者既諳熟君臣關系處于一種經常性的主次位序互換狀態中,又深知丟掉權力后的慘痛結局,故帝王們為了坐穩皇位,牢牢地把握手中的權力,永享治國理民的統治資格,都千方百計地防范他者覬覦皇位,侵奪至高無上的皇權。一旦出現竊取君權的政治勢力,在位帝王為固守一己之利,即不惜大肆殺戮。《魏書·術藝·王顯傳》曰:
顯每語人,言時旨已決,必為刺史。遂除平北將軍、相州刺史。尋詔馳驛還京,復掌藥,又遣還州。元愉作逆,顯討之不利。入除太府卿、御史中尉。[2]1969
永平元年(508)皇弟京兆王元愉叛亂,僭號稱帝,卻因勢單力薄,最終“在方鎮監控體制和皇帝狡詐權謀的聯合作用下戰敗身死,近屬宗王與河北士族則廣受株連”[12]。元愉之所以謀叛,敢于否定宣武帝的權威,自然“是對高肇專權、排擠宗室的政策不滿”[8]181的正面回應,但雙方沖突的實質在于宣武帝壓制宗室和鞏固皇權的策略,努力顛覆“前朝以近屬宗王為藩屏的權力體系,傾力打造外戚、恩幸、疏族三位一體之新格局,從而實現皇權的最大化”[12]。不過宣武帝在伸張皇權的過程中卻遇到了京兆王元愉的挑戰,忠誠于王權至上的官員如相州刺史王顯自覺或受命擔負起平叛職責。醫者王顯雖然征討元愉不利,卻因是宣武帝心腹近臣而被調任中樞,任太府卿、御史中尉。值得注意的是,對各級官吏進行監督糾彈是御史中尉的基本職能,而在北魏時期“在發生反叛時御史中尉及其屬官往往受命平叛”,“尤其對于地方長官的反叛,御史臺官員參與或主持平叛,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對反叛者進行審理,糾出參與反叛的成員并繩之以法”[8]188。若再聯系景明二年(501)宣武帝廢黜顧命宰輔大臣,奪權親政,王顯參與其中頗有密功,就不難想見宣武帝此時委任王顯為御史中臣,意在糾治叛黨和宗室勢力的政治用心。王顯走馬上任后,也沒有辜負宣武帝重托,“及領憲臺,多所彈劾,百僚肅然”[2]1969,盡力維護帝王的尊位和權威。《北齊書·斛律金附子羨傳》記:
羨未誅前,忽令其在州諸子自伏護以下五六人,鎖頸乘驢出城,合家皆泣送之至門,日晚而歸。吏民莫不驚異。行燕郡守馬嗣明醫術之士,為羨所欽愛,乃竊問之,答曰:“須有禳厭。”數日而有此變。[4]228
北齊后主高緯殺害斛律光,其弟斛律羨因受牽連而蒙難。斛律氏家族被殺事件,既與北周韋孝寬的離間計有關,又與內部祖珽、穆提婆等人聯合陷害相涉,但關鍵在于“斛律光沒有處理好與高齊皇族之間的婚姻關系,成為勢力強大的外戚家族,功高震主,使北齊后主感受到潛在的威脅”,“雙方也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隔閡乃至矛盾,而這種矛盾在一定條件下必然會激化,要解決矛盾最后只能是一方將一方罷免廢除甚至將一方殺戮”,最后北齊后主高緯血洗斛律氏家族[13]。斛律羨被殺之前,曾行禳厭之術,希冀消災祛禍,為友人馬嗣明所知。醫者馬嗣明是否知曉斛律羨消災祛禍為何事,是否卷入到后主高緯與斛律氏家族之間激烈的權力斗爭中來,都已較難尋蹤覓跡,不過醫者徐子范卻親自參與了后主高緯殺害宗室高長恭的政治斗爭事件。《北齊書·文襄六王·蘭陵武王孝瓘傳》載:
芒山之捷,后主謂長恭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及在定陽,其屬尉相愿謂曰:“王既受朝寄,何得如此貪殘?”長恭未答。相愿曰:“豈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見忌,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愿曰:“朝廷若忌王,于此犯便當行罰,求福反以速禍。”長恭泣下,前膝請以安身術。相愿曰:“王前既有勛,今復告捷,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勿預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寇擾,恐復為將,嘆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武平四年五月,帝使徐之范飲以毒藥。長恭謂妃鄭氏曰:“我忠以事上,何辜于天,而遭鴆也。”妃曰:“何不求見天顏。”長恭曰:“天顏何由可見。”遂飲藥薨。[4]147
君主說臣子為國家征伐外敵為“家事”,是君對臣的客氣話語;臣子稱為國家驅敵是“家事”,在帝王看來就是大逆不道。高長恭軍功卓著,卻在后主高緯面前稱驅敵征討為“家事”,這就犯了大忌,深遭皇帝忌恨。段韶晚年病重,將軍隊指揮權交給高長恭,以致觸到后主痛處,畢竟高長恭的兄弟高孝珩、高延宗同時參加過擁立高儼而廢后主的政變,如若高長恭也有類似看法,那么,對于后主而言,手握兵權的高長恭自然是極其可怕的人物,勢必除之而后快*參見王怡辰:《東魏北齊的統治集團》,文津出版社2006年版,第378頁。。故后主派遣醫者徐子范前去毒殺高長恭,解除來自宗室內部的有力挑戰,維護自己有效的統治,固守武成帝高湛一系的至高皇權。
四、伴駕外出
天子出行,或視察州郡,體察民情,推行教化,或征伐異己,揚威顯盛,安境靖邊,皆在于安邦治國,鞏固皇權。不過對于古人而言,離開自己熟悉的地方而去較不熟悉或完全陌生的地方,都每生恐懼之心。這倒不是說“熟悉的地方,非無危險——來自同人或敵人,自然的或‘超自然’的——然這宗危險,在或種程度內是已知的,可知的,能以應對的。陌生的地方卻不同:那里不但是必有危險,這危險而且是更不知,更不可知,更難預料,更難解除的”,尤其那些懷有異心的人和自然災害,“在僻靜處,在黑暗時,伺隙而動,以捉弄我,恐嚇我,傷害我,或致我于死地為莫上之樂”,故“古中國人把無論遠近的出行認為一樁不尋常的事”[14]5。于是,君王要安然外出歸來,其出行隊伍中至少有醫者隨行伴駕,以備外來各種力量傷害營療之需。《北史·藝術·馬嗣明傳》云:
武平末,從駕往晉陽,至遼陽山中,數處見榜,云有人家女病,若能差之者,購錢十萬。又諸名醫多尋榜至是人家,問疾狀,俱不下手。唯嗣明為之療。問其病由,云曾以手持一麥穗,即見一赤物長二尺許,似蛇,入其手指中,因驚倒地。即覺手臂疼腫,月余日,漸及半身,肢節俱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絕。嗣明即為處方,令馳馬往都市藥,示其節度,前后服十劑湯,一劑散。比嗣明明年從駕還,此女平復如故。[15]2976
晉陽是北齊高氏一族隆興發家之地,幾代帝王多有自鄴幸晉陽之舉。武平末年,醫者馬嗣明伴駕至晉陽,途經遼陽山中,救療患病之女,以顯皇恩浩蕩,關心民瘼。雖然上述材料中沒有透露醫者馬嗣明在出行中救療后主高緯的點滴信息,但從醫者徐謇救護孝文帝元宏的醫療案例中可以找到醫者陪王外出的用意和目的。《魏書·術藝·徐謇傳》曰:
二十二年,高祖幸懸瓠,其疾大漸,乃馳驛召謇,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數百里。至,診省下治,果有大驗。高祖體少瘳,內外稱慶。九月,車駕發豫州,次于汝濱。乃大為謇設太官珍膳,因集百官,特坐謇于上席,遍陳肴觴于前,命左右宣謇救攝危篤振濟之功,宜加酬賚。……從行至鄴,高祖猶自發動,謇日夕左右。明年,從詣馬圈,高祖疾勢遂甚,戚戚不怡,每加切誚,又欲加之鞭捶,幸而獲免。高祖崩,謇隨梓宮還洛。[2]1967、1968
孝文帝把消滅南朝統一全國作為人生最大的政治志向,一共發起三次南伐戰爭,尤其第二次南伐戰爭將近一年半,“是孝文帝三次南伐中時間最長,同時也是成效最為突出的一次,南齊沔北五郡被劃入北魏版圖,保證了洛陽南大門的安全”[16]266。不過于第二次南伐戰爭中,孝文帝病重,急詔醫者徐謇不遠萬里前來療疾,爾后陪伴孝文帝北返,并一路悉心救護。至太和二十三年(499),南齊王朝試圖挽回戰場頹勢,抱病在身的孝文帝帶著醫者徐謇再次南伐,雖然孝文帝在戰場上“成功地阻止了南齊反攻的圖謀,有效地鞏固了遷都后南伐戰爭的成果,維持了南北朝之間重新形成的邊境線”[16]303,卻在身體健康方面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因病情加重而亡于途中。醫者徐謇也結束其隨軍診候療治孝文帝病痛的重大使命,隨梓宮還洛。醫者姚僧垣也有相似隨軍救護最高統治者的醫療實踐,戰后便與圣駕一起回京。《周書·藝術·姚僧垣傳》記:
四年,高祖親戎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瞼垂覆目,不復瞻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垣以為諸藏俱病,不可并治。軍中之要,莫先于語。乃處方進藥,帝遂得言。次又治目,目疾便愈。未乃治足,足疾亦瘳。比至華州,帝已痊復。即除華州刺史,仍詔隨入京,不令在鎮。[17]842-843
建德四年(575)武帝宇文邕突然誓師大舉伐齊,后罹疾退兵,無功而還。至于武帝罷兵理由,頗令呂思勉先生質疑:“是役也,周武帝謂有疾故退師,恐系托辭。或謂以淺攻嘗之,亦未必然。以予觀之,似以河陰距長安較遠,應接非易,恐戰或不捷,復為邙山之續,故寧知幾而退也。”[18]666呂先生之說甚是。建德三年(574)以后北周在齊周對抗中雖已取得優勢,但“北齊的精兵多置于西邊,北齊對陳并未盡全力;但北齊之對北周則迥然不同,始終視之為頭號大敵,全力以赴”[7]134,故北周想要吞滅北齊也絕非易事,在此次戰爭中無獲而歸也就不難理解了。不論齊周雙方備軍力量如何,也不管周武帝身體狀況如何,醫者姚僧垣隨武帝宇文邕出征卻是不爭的事實,其職責自然是診候療治病者和傷員,尤其是救護御駕親征的帝王,以確保君主生命周全,進而穩固軍心,奮勇殺敵,或開疆拓土,或平亂安境。
五、受命療治同僚
醫者掌握著一定的醫療技術,又熟諳人身病理,再加上豐富的療疾效驗,往往在疾病療治上發揮著重要作用。故統治者也往往運用太醫屬官或醫藥之事,針對不同的對象,采取非常態性的醫療救護措施,進而達到化解潛在沖突與彌平緊張關系的目的*參見金仕起:《古代醫者的角色——兼論其身分與地位》,《新史學》第6卷第1期,1995年,第21~24頁。。如孝文帝元宏派遣徐謇前去探視療治廣陵侯元衍,即有彌平君臣之間緊張的政治關系的用意。前文已述,不再復贅。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看似偶發的、具有權宜色彩的醫療救護措施,實則為最高統治者治國理政的政治藝術再現,目的在于協調君臣關系,守護皇權,傳遞一姓帝王基業。《魏書·術藝·李修傳》載:
先是咸陽公高允雖年且百歲,而氣力尚康,高祖、文明太后時令修診視之。一旦奏言,允脈竭氣微,大命無遠。未幾果亡。[2]1966
咸陽公高允年事已高,勛績卓著,孝文帝、文明太后時常向其咨詢國家政事。當高允身體微恙時,孝文帝、文明太后派遣李修前去診候療疾,以示對老臣的優寵和禮遇。當然,最高統治者寵遇大臣的具體醫護舉止還有遣太醫送方藥,遣使存問、賜醫藥等。《魏書·程駿傳》云:
初,駿病甚,高祖、文明太后遣使者更問其疾,敕御師徐謇診視,賜以湯藥。[2]1349-1350
《北齊書·儒林·張景仁傳》曰:
景仁多疾,每遣徐之范等治療,給藥物珍羞,中使問疾,相望于道。[4]591
醫者所固有的知識結構和技藝,就是驅除疾病和維護生命的知識和方法,尤其在醫藥不甚發達和醫藥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統治者派遣名醫前去悉心救護罹疾大臣,既可彰顯君王優寵患病大臣之情,又可無形之中固化或升華大臣忠君報國之志。進而言之,君王遣醫賜藥療護大臣的行為實則離不開情感的交融和利益分配,即“情感為其表,實利為其里”[5]259。
在方術伎巧之于用而往哲輕其藝的社會氛圍中,北朝時期大多數醫者本著治病療傷的利人操守和高尚的醫德情操,進入罹疾患病者的私領域,為之治療病痛,維持生命,延續香火。醫者憑借其專業的醫藥技能,因醫療實踐之便而獲得最高統治者的特殊寵任,進入君王的公領域,參與國家政務,或佐助新皇登基,或參與君王重大決策,或涉入君臣權力之爭,或伴駕外出,或受命療治同僚,從而在最高統治者的優寵下,在至上皇權的庇佑下,實現自身在官場上的政治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