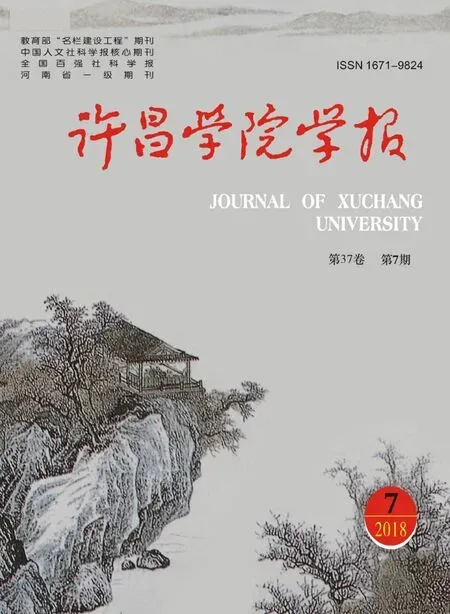資源型地區產業扶貧的成效評價與優化路徑
——以山西省為例
姬 超
(1. 許昌學院 中原農村發展研究中心,河南 許昌 461000;2.山西大學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新時代下,精準扶貧已經成為中央和地方政府治國理政和日常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實現全國“共同富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的必然要求[1]。當前,區域之間、城鄉之間的非均衡發展帶來的貧困差距日益成為制約我國經濟和社會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2],全面減貧已是大勢所趨。我們認為,中央對各地減貧和扶貧成效進行精準評估必將常態化,全面貫徹習近平精準扶貧思想,高效治理貧困,也將成為地方政績考核的重要方面。在精準扶貧的核心理念指導下,各地還要結合地方實際,建立并完善配套的扶貧體系。其中,產業扶貧是形成貧困地區內生發展動力,從“要我脫貧”向“我要脫貧”轉變,實現永久脫貧的根本之路。那么,對于資源型地區而言,什么樣的產業是適應當地的?在產業扶貧過程中還存在哪些問題?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本文作者于2016年7月至9月深入山西省貧困村(晉北22個,晉中22個,晉南34個),對貧困農戶和村干部進行了系統的訪談和抽樣調查,在此基礎上對山西省產業扶貧的經驗和教訓進行了較為客觀的評價,以期為其他資源型地區更好地開展扶貧工作提供參考建議。
一、山西省貧困村的基礎稟賦狀況
(一)地偏山多,生活性勞動擠出了大量生產性勞動
致貧原因多種多樣,偏遠的地理位置多是造成貧困的初始因素,土壤貧瘠和交通不便將這些地區隔離在現代社會之外。我國資源型地區大多位于老、少、邊區域,資源型村莊在所有的貧困村中占比71%。其中,屬于山地類型的村莊占比71%,其次是丘陵類型的村莊,占比17%,剩下的貧困村散落地分布在高原、平原地帶。對于山西省而言,大多數貧困村以農業生產為主(農業區比重達到95%),而且自然和地理條件較為惡劣。
生活環境方面,山西省貧困村的住房以磚木(占比33%)和磚混(占比52%)結構為主,采用現代鋼筋混凝土結構的房屋很少。樓房在貧困村中很少見,大多數村民生活在平房(42%)和瓦房(24%)里,還有27%的貧困村村民住在窯洞中。絕大多數的貧困村實現了電力覆蓋,在家庭取暖上,使用傳統的火炕(墻、爐)設備的村莊比重為82%,使用暖氣和空調的村莊數量還很少。飲用水上使用自來水的貧困村比重為59%,剩下的則是使用井水、湖泊水、塘水等自然水源來直接滿足用水需求,部分村莊在飲用水上還存在很大困難,甚至飲用水存在污染問題。在用于生活的能源燃料上,使用電、沼氣和液化氣(天然氣)的村莊數量還很少,大多數村莊使用柴草和煤炭。
傳統的生活方式不僅為貧困村民的人身安全帶來了很大隱患,還將大量勞動力綁定在煩瑣的生活性勞動而不是生產性勞動中。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下,許多村民對當前的生活狀況產生了很大不滿。調查顯示,表示對當前生活狀況不滿意的貧困村比重為31%,表示滿意的貧困村比重為35%,剩下的則表示一般;感覺當前生活壓力很大和較大的貧困村比重為63%,表示當前生活壓力很小或沒有壓力的貧困村比重不到7%。
(二)人口和勞動力結構總體合理,部分村落空心化端倪顯現
人口和勞動力結構是影響地方發展的關鍵因素。從當前來看,山西省貧困村的勞動人口數量總體較為充足,喪失勞動能力和常年生活困難的人口總體可控。大多數貧困村中完全不具備勞動能力的人口比重在20%以下,常年生活困難的人口比重大多也在20%以下。但是,在貧困人口較多的村莊,表示常年生活困難的人口比重顯著大于喪失了勞動能力的人口比重,表明喪失勞動能力并非導致貧困的唯一原因。事實證實了這一論斷,貧困村中許多具有勞動能力的人并未完全投入到能夠創造更多勞動價值的產業勞動中去,許多村民雖然具備勞動能力,卻是將勞動投入到了家務和生活事務,勞動資源事實上處于一種閑置或低效配置狀態。
山西省貧困村的老齡化總體處于較為合理的水平,大多數貧困村(56%)的老年人口占全村人口比重低于20%,35%的貧困村的老年人口比重在20%~40%之間,另有10%的貧困村的老年人口占比超過了40%;與此同時,大多數貧困村的兒童數量遠遠低于老年人口數量,89%的貧困村的兒童數量占全村人口比重低于20%,兒童數量占比20%~40%的貧困村不到7%,兒童數量占比40%以上的貧困村僅有4%。老年人和兒童數量的極大反差反映出了一個潛在的勞動力隱患,隨著老年人口的不斷增加,適齡勞動力的增長不能相應地彌補這一缺陷。從長遠來看,這些貧困村將會面臨空心化問題。
(三)區域差異顯著,晉南脫貧任務更加艱巨
分區域來看,晉北、晉中、晉南的貧困村的人口和勞動力結構存在很大差異,精準扶貧需要重視這種個體差異,在不同地區采取有針對性和差異化的扶貧措施。老年人口占比超過40%的貧困村全部位于晉南,老年人口占比在20%以下的貧困村大多位于晉中,老年人口占比在20%~40%之間的貧困村大多位于晉北;兒童人口占比在40%以上的貧困村大多位于晉中,兒童人口占比在20%~40%之間的貧困村同樣位于晉中。這一比較結果顯示,與晉北和晉中相比,晉南將面臨更為嚴重的老齡化問題,適齡勞動力稀缺問題在晉南將會更加嚴重。與此相對應的是,晉南無勞動能力和常年生活困難的人口和村莊比重更大,晉南的脫貧任務更加艱巨,晉中次之,在扶貧資源的配置過程中,有必要進行相應的傾斜。
二、山西省產業扶貧的主要方法和效果
目前,山西省近半數的貧困村已經開展了產業扶貧項目,但在不同區域存在很大差異,晉北地區開展產業扶貧的貧困村比重達到了65%,晉南和晉中地區開展產業扶貧項目的比重分別只有34%和38%,遠低于晉北。
(一)扶貧多措并舉,產業扶貧最受地方歡迎
為了實現精準脫貧的宏偉目標,山西省實施了生態補償、產業脫貧、轉移就業、教育脫貧、技能培訓、易地扶貧、社保兜底、金融扶貧、基礎設施建設等多種形式的扶貧舉措[3]。與其他形式的扶貧相比,產業扶貧的效果最優,對村民的吸引力也最大(表1)。分區域來看,無論是晉北,還是晉南和晉中,產業扶貧在地區扶貧項目中的比重都顯著高于其他形式的扶貧項目(表2);此外,從收入水平、年齡、受教育水平來看,產業扶貧都是所有扶貧項目中最受支持,也是開展最為廣泛的扶貧項目。

表1 山西農民最需要的幫扶措施

表2 山西省不同地區參與精準扶貧項目的情況(單位:%)
(二)激發村民參與熱情,助推村莊內生發展
產業扶貧需要貧困村民的廣泛和主動參與,這樣才能充分發揮產業扶貧的效果。根據調查結果,大多數產業扶貧項目在開展過程中都會召開會議,廣泛聽取貧困村民的意見和建議。在發展涉農產業的意愿上,絕大多數(96%)村民表示是自愿行為,不同收入水平的村民在這個問題上也未表現出太大差異(表3),反映了大多數村民對涉農產業的認可,認為涉農產業是一種行之有效的脫貧之路。在發展涉農產業過程中,大多數村民并未獲得政府任何獎勵,這就進一步加強了上述論點。產業扶貧是貧困村民發自內心認可的扶貧方式,因而也更容易形成內生發展動力,真正提高村莊的內生發展能力。

表3 不同收入水平農戶自愿發展涉農產業情況(單位:%)
(三)因地制宜,實現產業扶持政策的精細分類
不同收入水平的村莊對產業扶持政策的訴求存在很大差異(表4)。大多數低收入村民最希望獲得的是扶貧信息,相比資金,首先政府提供扶貧信息和精確扶貧對象對他們而言更加關鍵。中低收入村民最希望獲得的是技術指導,中高收入和高收入的村民反而對資金的需求最為迫切。這就需要在產業扶貧過程中,進一步重視扶持政策的精準度,審慎分類,精細施政。
在政府扶持的產業類型方面,種植業是多數貧困村希望獲得支持的產業類型,其次是農產品加工業、養殖業和旅游業。分區域來看,種植業依然是各地最希望獲得扶持的產業類型,但對于晉北地區而言,養殖業是當地貧困村接下來最希望獲得扶持的產業類型,而農產品加工業是晉南和晉中地區貧困村接下來最希望獲得扶持的產業。

表4 不同收入水平村民對產業扶貧政策的需求類型(單位:%)
三、山西省產業扶貧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
通過產業扶貧,山西省廣大貧困村獲得了許多新的發展機會。村民在產業扶貧的帶動下,收入水平有了很大幅度提高,產業扶貧的成效有目共睹。與此同時,我們在調查中也發現了產業扶貧過程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和不足。
(一)集體產業發展不足,制約貧困村民協同致富
大力發展集體經濟是產業扶貧的首要之義。對于大多數貧困村而言,資金和信息獲取能力都極為有限,承受市場風險的能力也較弱,通過發展集體經濟將村民組織到一起共同發展是扶貧的第一選擇,也是符合大多數村莊實際的扶貧方式。盡管大多數村民認為發展集體經濟很有必要,但是在現實的經濟活動中,他們或者不知道應該發展何種集體產業,或者缺乏足夠的組織動力,集體經濟在許多村莊并未如想象中那樣蓬勃發展。
1.集體經濟在山西省廣大貧困村尚未得到有效組織和發展。根據我們的抽樣調查,山西省超過半數(55%)的貧困村沒有集體經濟,30%的貧困村不清楚本地是否有集體經濟,明確表示存在集體經濟的貧困村比重不到15%,表示參加集體經濟的村民數量也很少,75%的村民明確表示沒有參加集體經濟。分區域來看,晉北和晉南擁有集體經濟的貧困村比重顯著高于晉中。盡管晉北貧困村的集體經濟比重高于晉中,但晉北加入集體經濟的村民數量比重并不高,反映了許多地區的集體經濟流于形式,村民加入的積極性不高。
2.缺乏高附加值集體經濟影響村民的參與積極性。如果不同類型的村民都對參加集體經濟缺乏興趣,很可能是因為集體經濟能夠創造的收益有限。事實上,對于山西省大多數貧困村而言,能夠帶動村莊發展的有效產業并不多,煤炭市場不景氣的時候更是如此。在這種條件下,現有的集體經濟附加值較低,大多數村民參與的集體組織局限在農民專業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和集體企業的比重很小。另外,大多數參加集體經濟的村民只能通過提供勞動力和土地獲得分紅,獲得的收益是很有限的,且有很多村民根本不清楚所加入的集體經濟的收益來源[4]。
根據我們的調查結果,大多數村民加入集體經濟組織的目的是為了發展種植業(占比91%),也就是傳統的農業耕作范疇,產業形式單一,林業、養殖業、傳統手工業等形式的集體組織非常有限,幾乎為0,缺乏高附加值的工業和服務業,傳統的集體產業已經不能滿足貧困地區的發展需求。
3.激勵不足導致集體經濟的組織類型單一。山西省貧困村的集體經濟不僅形式單一,而且缺乏有效的組織者和帶頭者,村干部是絕大多數貧困村集體經濟的組織者和帶頭者。但是事實上,村干部組織集體經濟更多的是響應上級號召,其出發點并不在于發展村莊經濟,同時也缺乏足夠的動力和能力,因而這種類型的集體經濟常常面臨適應性問題,白白浪費了許多集體資源。
與此同時,在現有的村莊環境和資源條件下,大多數村莊獨立發展特定的產業都面臨很大的市場風險,沒有相應的政策扶持是不現實的。但是,政府對集體產業的扶持顯然是不到位的,或者存在很大的模糊之處,未能落到實處。僅有18%的村民明確表示集體經濟享受過政策扶持,18%的村民明確表示集體經濟沒有享受過政策扶持,64%的村民表示不清楚。
在有限的政策扶持中,政府將重心放在了資金扶持上,其次是種苗幼崽補貼、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提供市場信息和交易對象,而對生產資料和工具、貼息貸款、技術指導和培訓的扶持力度還很不夠。再加上現有的補貼由于額度有限,很難在根本上形成集體經濟發展的充足動力,許多資金實際上是打了水漂,形式上的支持不但無助于集體產業的發展,反而浪費了有限的資源[5]。
(二)缺乏有效組織和實際帶頭人,村干部主導引發干群矛盾
在貧困村,大多數村民的經濟實力有限,其能力也不足以單獨支撐某個產業項目的開展,項目失敗的風險更是大多數村民無法承擔的,因此成功的產業扶貧首先需要一個合適的組織和帶頭人。但是,大多數貧困村沒有有效的組織和帶頭人,有45%的貧困村沒有帶頭人來組織發展精準脫貧項目。其中,56%的晉北貧困村有項目發展帶頭人,64%的晉南貧困村有項目發展帶頭人,均高于全省平均值,41%的晉中貧困村有項目發展帶頭人,低于另外兩個地區,也低于全省平均值。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貧困村雖然有項目帶頭人,但主要都是村干部主導的,村干部一方面負責村莊事務,另一方面也帶頭組織專業合作社和企業,成為某個領域的專業大戶。這樣的組織安排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村干部熟悉相關扶持政策,擁有更多的信息優勢,但也為村干部趁機攫取村莊公共利益埋下了隱患,甚至成為干群矛盾的導火索[6],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村民參與扶貧項目的積極性。在扶貧過程中,許多村民認為能夠參與到扶貧方案制定或討論中的機會非常有限,甚至根本沒有機會參與其中。
(三)資金投入不足,激勵不當影響脫貧積極性
在貧困村進行產業投資的市場風險很大,因此需要政府給予充分的激勵,以此降低產業投資成本,同時鼓勵貧困村民積極投入到產業扶貧項目中進行主動脫貧,而不是一味地享受政府“輸血式”扶貧。但是隨著政府“輸血式”扶貧思路的改變,政府對貧困村的資金投入大幅減少。事實上,無論何種形式的扶貧都離不開大量資金投入,需要審慎的是資金投入的方式、方向。我們在調查過程中發現,60%的貧困村民表示在脫貧后沒有獲得上級政府的獎勵,晉中和晉南的這一比例就更低了,從而挫傷了貧困村民主動脫貧的積極性,不脫貧反而能夠享受到一些好處,脫貧后反而享受不到了。
那些脫貧后獲得上級政府獎勵的主要是些優惠政策,甚至是口頭嘉獎,并不能帶來實質性好處,缺位或錯位的激勵方式無法有效帶動貧困村民主動脫貧的積極性,浪費了大量的扶貧資源[7]。分區域來看,晉北獲得資金獎勵的比重顯著高于晉南和晉中,對貧困村民主動脫貧的激勵作用前者明顯比后者更大,這也是晉北扶貧效果優于晉南和晉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產業扶貧對象不精準、產業扶貧信息無法獲知、推行的扶貧產業不符合村莊或農戶發展需要、扶貧資金或補貼發放滯后、缺乏技術指導和培訓等,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貧困村民主動參與脫貧的積極性。
(四)村民對扶貧效果的認可度不高,政府配套扶持項目不足
精準扶貧工作開展以來,盡管政府認為對扶貧已經不遺余力了,也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是從扶貧效果的調查數據來看,許多村民對地方政府扶貧的認可程度并不高,特別是配套的扶持項目嚴重不足。例如民生和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扶持力度不大,影響村民對政府扶貧的認可。69%的貧困村民認為政府幫扶農業的項目個數為0,28%的貧困村民表示政府幫扶農業的項目在5個以下,85%的貧困村民表示政府幫扶工業的項目個數為0,99%的貧困村村民表示政府幫扶的旅游項目個數為0。如果說個別貧困村不具備產業扶貧的條件,那么還有72%的貧困村民表示政府沒有組織過任何技能培訓,85%的貧困村民表示政府沒有組織過外出務工培訓,64%的貧困村民表示政府沒有幫助解決低收入戶的住房困難問題,78%的貧困村民表示政府硬化道路公里數為0,95%的貧困村民表示政府建設的小型農田水利項目為0。
四、山西省產業扶貧的改進方向和政策著力點
(一)以產業扶貧為主,加強配套扶貧項目的協同建設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在眾多扶貧項目中,產業扶貧已經成為最受群眾歡迎的扶貧手段,也是從根本上實現貧困村脫貧,形成村民內在發展能力的重要舉措。問題的關鍵在于什么樣的產業項目才是符合當地實際情況的。對于很多貧困村而言,發展的初始資源極度匱乏,按照市場運行規則,以盈利為目的的產業不可能選擇這些地區。為了彌補這一先天缺陷,首先是要降低企業運行的成本。即使有合適的扶貧產業,投資者不可能承擔過多的公共設施建設投入責任,例如電力、公路、生活和生產性用水、娛樂、購物、餐飲等,這些配套項目對于吸引外來企業和外來人力資本必不可少。因此,產業扶貧也是一項系統工程,簡單地引入項目和相關企業多半不能奏效,還要由政府出資或者引進新的資本進行配套建設[8]。其次,為了減少產業扶貧的風險,在主導性產業建設的同時,還要統籌資源分配,加強配套設施的協同建設,只有科學規劃,多管齊下,才能推動產業扶貧的順利進行。
(二)重視區域間差異,鼓勵高附加值產業入駐貧困村
由于扶貧資源有限,為了獲得更多的資源分配權,許多地方官員頻繁活動,這就為權力尋租創造了條件,同時導致地區之間、部門之間的關系趨于緊張,不利于扶貧工作的協作開展。為了避免這種矛盾,主管部門對許多扶貧資源進行了平均分配[9],扶貧政策也是相同的。但是,山西省不同區域之間的差異非常顯著,資源稟賦很不相同,發展階段和發展形態各異,在扶貧過程中搞平均主義并非一個合適的選擇。平均主義雖然化解了資源紛爭矛盾,同時也將有限的扶貧資源進一步稀釋了,導致資源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其結果就是,看似每個貧困戶都在扶貧政策中得到了一定好處,卻不能從根本上改變貧困局面,反而助長了個別貧困戶的懶惰之風,只知道一味地向政府討要扶貧款。
為了實現精準扶貧的目標,就要重視區域之間、貧困村之間、貧困戶之間的個體差異,根據其具體特征,細化扶貧資金的數量以及扶貧政策的優惠程度,制定差異化的扶貧方案,精確劃分扶貧資金和政策的投入區間。進一步地,為了更有效地利用扶貧資源,發揮資源的乘數效應,還要根據各地實際,重點扶持一批高附加值的產業項目,例如農產品加工、旅游等能夠拉長產業鏈條,帶動更多的人就業創業。
(三)激發村民能動性,以反向激勵促進村民主動脫貧
在很多扶貧項目中,貧困戶都是被動地參與其中,從扶貧方案的制定、項目的選擇到實施,他們都未獲得足夠的尊重。首先在個人情感上就對扶貧項目沒有太多的好感。事實上,貧困戶才是脫貧過程中最重要的參與者,越是能發揮他們的主動性和能動性,扶貧的效果也就越好。因此,從扶貧的開始階段,就要把貧困戶納入進來,使他們參與扶貧項目的討論、扶貧方案的制定,同時在扶貧的整個過程中,要尊重并充分保障村民的知情權。這就需要嚴格規范管理扶貧產業和相關項目建設,使得扶貧流程標準化、規范化、可操作化和精細化。
還有一些貧困戶,即使具備脫貧能力或者在事實上已經脫貧,仍然千方百計地隱藏脫貧事實,繼續從國家扶貧政策中獲取補助。目前,國家和地方扶貧政策大多是針對貧困戶制定的,缺少脫貧之后的相關政策。從收入水平來看,許多貧困戶在脫貧之后的收入并不比貧困戶高多少,甚至存在所謂的“數字脫貧”現象[10]。一旦取消對他們的政策補助,或者出現一些意外情況,這部分人群很容易重新陷入貧困。出于這種擔憂,許多貧困戶在心理上對脫貧的積極性并不是很高。為了充分激勵村民脫貧,建議實施反向激勵法,改變以往只對貧困戶進行救濟和扶持的做法,在政策上向那些愿意脫貧、主動脫貧并且成功脫貧的村民傾斜,通過反向激勵法,實現從“要我脫貧”到“我要脫貧”的轉變。
(四)精確識別帶頭人,轉變政府自上而下的扶貧思路
個體之間存在廣泛的差異性,每個貧困戶的能力、家庭條件、性格等都互不相同,在脫貧過程中,如果沒有一個帶頭人帶著村民參與產業扶貧,很多村民是不敢邁出第一步的。目前,充當這個帶頭人的以村干部為主,但是很多村干部并非合適的帶頭人,他們更多的是在執行上級政府命令,或者試圖憑借信息優勢獲得個人收益,并不能真正帶動全體村民實現脫貧目標。為了更精確地識別致富帶頭人,在政策制度上需要重新設計,激勵那些真正有能力并且愿意帶領村民脫貧的人站出來。例如,傳統的扶貧方案中,政府要么將扶貧款分散發放給每個貧困戶,要么引進幾個產業項目,將重心放在了投資者身上,從而偏離了既定扶貧目標,轉向了地方發展目標。在地方發展目標的導向下,外來投資者很可能轉向攫取村莊公共資源和 村民利益,不能真正實現精準扶貧的目標。
為了實現地方扶貧目標和地方發展目標的統一,將產業和貧困村民的利益切實綁定在一起,就要轉變政府一刀切式的自上而下扶貧思路,將扶貧的主導權交給脫貧主體。例如,政府可以確定具體的扶貧項目,以項目包的形式進行外包,承包特定扶貧項目的帶頭人需要簽訂責任書,由承包責任者與村民談判、合作,同時還要保證村民同等的談判權、話語權和話語權,最后根據村民脫貧程度進行付費,并且給予相應的獎勵或懲罰。這樣一來,政府就將扶貧的主導權交到了真正有能力帶領村民脫貧的人手中,避免了資源低效配置,政府的角色也回歸到了扶貧的引導者和監督者上來,能夠更有效地實現精準扶貧目標。
(五)促進主體間互動,政府、企業、村民多元化合作
最后,精準扶貧與傳統扶貧的最大不同之處在于,傳統扶貧更多的是政府單方面的“扶”,精準扶貧的要義在于扶貧者和脫貧者多方面的協作。只有主動合作,密切配合,積極參與,才能真正做到有的放矢,準確識別“誰來扶”“扶誰”“怎么扶”“用什么產業扶”以及“扶的效果怎么樣”。為了做到這一點,促進主體之間的互動,就要政府主動放權,明確各方的權利和義務,讓真正想脫貧和能夠帶領村民脫貧的人積極參與其中,為他們創造發揮才能的條件。同時,還要通過各種手段,吸引更多的外來企業和社會力量,根據各個地方的實際情況,發掘村莊潛在的脫貧因子,實現產業扶貧的多領域合作和多元化合作。
EffectivenessEvaluationandOptimizationofIndustrialDevelopmentforPovertyReductioninResource-basedRegions: Based on the Example of Shanxi Province
JI Chao
(1.R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Central Plains, Xuchang University, Xuchang 461000, China; 2.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realizing the grand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country and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Among them,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is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impetus to the poverty-stricken areas. For resource-based areas,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its own uniqueness. A singl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a fragil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ve added new difficulties to its elimination. Based on the sample survey in Shanxi Province, the main reasons that restrict the effectiveness of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esource-based areas include: a serious shortage of coll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especially lacking high value-added industries; passive participation of villagers in poverty reduction and poor motivation; lack of effective driving force; inappropriate incentive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lack of industrial support projects.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we need to further stimulate the initiative of villagers, pay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ces among regions, introduce adaptive industri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at the same time,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ancillary projects and establish a diversified cooperation mechanism among governments, enterprises and villagers.
Keywords:resource-based areas;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subjective initiative; multiple coope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