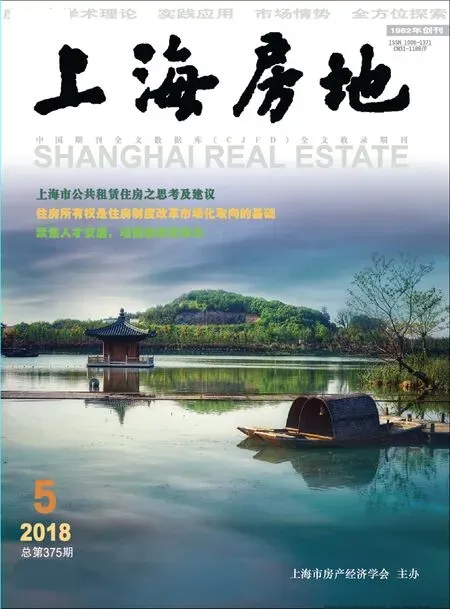住房所有權是住房制度改革市場化取向的基礎
——紀念住房制度改革40周年
文/穆子犁

1978年9月13日到18日,鄧小平同志在6天時間里馬不停蹄地視察了本溪、大慶、哈爾濱、長春、沈陽、鞍山等6個地方,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聽各地負責人的匯報,一路發表講話。談到中國落后的現狀時,鄧小平痛心地說:我們太窮了,太落后了,老實說對不起人民……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們一定要根據現在的有利條件加速發展生產力,使人民的物質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點。在此期間,鄧小平提出解決住房問題路子可以寬些的思路。他說:“住宅問題,要考慮城市建筑住宅分配的一系列政策。城鎮居民個人可以購買房屋,也可以自己蓋;不但新房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性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10年、15年購買不限。住房出售以后,房租恐怕要調整,使人覺得買房劃算,因此要研究逐步提高房租,房租太低人們就不買房子了。”鄧小平提出住房制度改革向市場化方向發展的思路后,決策層在總結“住房商品化”理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全面推進住房制度改革,從提租增資、出售公房,到停止實物分配、實施貨幣分配,建立了多層次的住房供應體系,實施住房保障制度,我國住房制度有了歷史性的突破,從此開創了我國住宅業發展的新局面。
一、 住房制度改革以住房商品化發軔
住房商品化實質就是住房市場化。市場有多種含義,這里說的市場,是指以商品等價交換為準則的經濟活動方式,即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極大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事實已被歷史與實踐所證明,中國要盡快解決住房的燃眉之急,必須追求效率優先,走市場經濟之路,激發市場的活力來生產更多的住房,以滿足社會的需求。說市場經濟是一種有效率的機制,是因為市場經濟的核心機制——價格體系——是有效率的信息交流傳遞機制,價格作為市場交換過程的指南針,一方面反映出生產的機會成本和商品的稀缺程度,另一方面反映個人的支付意愿,表明需求方對商品的估價。因為這些特征,價格在市場上發揮兩大功能:在商品市場上引導市場參與者解決“生產什么、生產多少、如何生產”的方向性問題(協調功能);在要素市場上,價格成為對各種生產要素在生產過程中貢獻大小的一種評估,決定著初次收入分配(分配功能)。在每一個市場上,買方和賣方都根據相對價格的變化作出自己的決策,買賣雙方的決策組合決定著價格的結構。價格的變化引導著買賣雙方行為的改變,從而使市場具有了一種走向均衡的趨勢。市場經濟之所以能夠使資源配置以最低成本取得最大利益,是因為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有關資源配置和生產的決策是以價格為基礎的,而由價值決定的價格,是生產者、消費者和生產要素所有者在市場自愿交換中發現和形成的。
住房制度改革走住房市場化之路,還能夠通過市場競爭發現市場、提高效率和完善質量。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內在特征,它迫使市場參與者努力尋求與其他生產者有差異的創造性行為,以更低廉的成本進行生產(工藝創新),或者在已有的價格水平上改善產品、開發新產品(產品創新),從而一方面使成功者獲得更大的市場份額和營利空間,另一方面推動社會技術的進步。綜上所述,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其實質就是讓價值規律、競爭和供求規律等市場經濟規律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住房制度改革走住房商品化之路,還在于破除福利分房的各種弊端。在分配住房的過程中充斥著利益的博弈,人情厚薄、彼此親疏等人際關系成為分房的“潛規則”,不少人為分房彼此猜忌、勾心斗角,成為一個單位、團體人心渙散的根源,而個別單位的分房執行人則成了“近水樓臺先得月”者,有的甚至將手中的權力作為“尋租”的工具,腐敗由此產生。
現在看來,住房制度改革走住房商品化之路,不僅是改革開放之初我國以公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的必然趨勢,也是解決住房制度改革效率與公平問題的必然選擇。這是住房制度改革堅持的一條正確道路。40年的市場經濟發展,“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了巨大的生產力,住房生產已經基本滿足民眾的居住需求,住房制度改革的市場化取向是取得顯著成效的根本前提。
二、住房商品化改革的基礎是住房所有權
住房是家庭賴以穩定存在的基本物質要素,每個家庭擁有一套合適的住房成為社會進步的目標。一個沒有住房的家庭,不僅不能獲得住房提供給家庭成員的各種庇護,家庭的正常生活秩序不能得到保證,而且還可能引起家庭成員間的感情淡化、聯系松散,家庭結構的不穩定性也會增加,甚至導致家庭解體。1949年后,公有住房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使家庭穩定存在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國長期以來實行的是政府和單位包下來的福利分房體制,職工支付很低的租金享有住房使用權,這樣的體制不但不能形成擴大再生產的能力,而且難以維持簡單再生產,不可能形成住宅投入產出良性循環的機制,公房建設和分配的制度走進了死胡同,住房制度改革勢在必行。
住房制度改革能贏得民眾擁護的基礎是獲得住房的所有權。與擁有公有住房使用權截然不同的是,通過房改售房或市場交易得到的住房,擁有的是住房所有權,由住房所有權派生出的占有、使用、收益、處分這四項權能與財產權是相生相伴的。這個簡單的事實讓不少人形成這樣的思維邏輯:市場化的住房制度改革將住房與市場緊密相連;住房不僅是遮風避雨的棲居之地,還是極具財富意義的不動產;擁有住房所有權即擁有財產權,住房可以通過市場交易變現。于是,在住房財富效應的吸引下,敢于吃蟹的人總是先知先覺,躍躍欲試,后來者在“買房合算”還是“租房合算”的一番精明比較之后,也匯入了住房制度改革的洪流之中,先是踴躍購買原居住的公有住房(在北京,當初幾萬元購買的公有住房,現在的市場價格已達到上百萬),后是紛紛涉足商品住房市場(自住需求、投資需求、投機需求,不一而足)。由于住房是人們必需的生活用品,市民只要經濟能力許可,都會把大部分積蓄用于購置住房,而同時,由于土地資源的緊缺,且由于不動產的特定屬性,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住房價值不會因為持續消費(利用)而降低,住房價格整體呈上漲趨勢,不動產的保值功能又推動家庭財富積累垂青于購置住房,住房便逐漸成為普通居民家庭價值最大的財產。
住房制度改革以市場化取向為發軔,最初的動力源于住房所有權,而由住房所用權延伸的財富效應竟會如此強勁——極大改變了城市居民的住房緊缺狀況,是始料未及的。但是市場經濟以商品交換為紐帶、以貨幣為媒介、以市場調節為主導、以市場競爭為動力的特征,決定了它是一個以商品和貨幣為價值尺度的經濟運行機制,這個機制不能解決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難問題,這就需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要在保證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市場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即按照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讓全體人民住有所居”要求持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