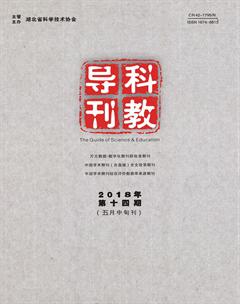關于大學生網絡公開課學習行為的社會學思考
賀靈敏 胡俊生 陳小鋒
摘 要 “互聯網+教育”已成為教育發展的新趨勢,它有助于打破區域教育資源分布不均。運用擬劇論、“鏡中我”等社會互動論對陜西高校“爾雅通識課”的學習情況的分析,認為互動平臺主體的割裂化設計、“公共—私人”領域的檢測體系的不連貫、線上與線下學習內容的撕裂、同輩群體的負向示范效應是造成學生網絡平臺學習行為形式化、學習內容碎片化、學習互動效果差、學習目的功利化的原因。因此,通過構建良好的宿舍文化,提高同輩群體的正向示范作用,凸顯平臺學習主體化設計,建立更加合理的學習效果評價、檢測機制,強化“線上與線下”學習的聯動功能,提高高校學生對“爾雅”等網絡教育資源的有效利用率。
關鍵詞 爾雅通識課 前臺—后臺 鏡中我 學生主體化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400/j.cnki.kjdkz.2018.05.002
Abstract "Internet + education" has become a new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which helps to break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regional education resources. Using the theory of dramatization, "in the mirror" and other social interaction theories of Shaanxi University's "Er Ya General Education" analysi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split platform design of the main body of interactive platform and the detection system of "public-private" domain are not. The coherence, the tearing of online and offline learning content, and the negative demonstration effect of peer groups are the reasons that result in the formalization of learning behaviors of students' online platforms, the fragmentation of learning content, the poor effect of learning interaction, and the utilitarian purpose of learning. Therefore, by building a good dormitory culture and improving the positive demonstration role of peer groups, it highlights the design of platform learning, establishes more reasonable learning effect evaluation and detection mechanisms, and strengthens the linkage func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learning,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effective utilization of "Er Ya" and other online education resources.
Keywords general class; in the mirror; in the front desk-the background;?interactive subject
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CNNIC)所發布的“第3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調查報告”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12月,中國網民規模達6.88億,互聯網普及率為50.3%,半數中國人已接入互聯網。其中,學生群體占網民數量25.2%”。[1]這為網絡教育的發展提供了契機。各高校也緊跟網絡教育的大潮,積極推動、拓展網絡課程及相關資源以供學生獲取更多的學習資源。“爾雅通識課”等網絡公開課就是在“互聯網+教育”的背景下蓬勃發展起來的。
1 大學生網絡公開課的學習行為
陜西高校先后在2003年就開發并投入大量資源開發網絡教學平臺和引進相關網絡課程,自2013-2014學年開始學校響應教育部文件在校內開展爾雅通識課,希望借此彌補學校師資力量的局限性。在此背景下,采用整群分層隨機抽樣方法,分別對西北大學、西安工業大學、陜西科技大學、延安大學、思源學院當場發放和回收問卷。在校園內共發放調查問卷700份,回收問卷690份,回收率95%。其中有效問卷680份,有效率達到94.7%。訪談10名學生。學生縱跨大二至大四,學科橫跨文史類、理工類和體育藝術類。通過問卷和訪談相結合的方式,對陜西5所高校近700名學生學習“爾雅通識課”(以下簡稱“爾雅”)的行為進行調查,發現延安大學學生在“爾雅”等網絡平臺的學習行為存在以下特點。
1.1 形式化趨勢
“爾雅通識課”學習的形式化主要體現在學習行為的虛化和學習內容檢測的形式化兩方面。在爾雅課程的學習中,學習行為的虛化主要表現為“聽課采取刷課”行為;學習內容檢測的形式化主要表現學生在完成“爾雅”課程的作業和作答考試題目時,許多學生利用答題軟件或爾雅題庫檢索關鍵詞、核心句等方式尋找答案而不是學習、思考獲取答案的現象。“刷課”包括兩種行為方式:一種是指學生將課程視頻保持觀看學習狀態,但其并不聽課而是做其他事情,這可以被稱為“放置式”刷課;另一種是直接通過網絡購買等形式完成課程。
由表1可發現,學生的“刷課”行為和檢索答案的現象比較普遍。也就是說,大多數學生在不需要對學習內容了解的情況下,通過題庫檢索即可獲取答案。這一軟件漏洞加劇了學生網絡學習形式化程度。
1.2 學習內容碎片化
與傳統課程教學模式相比,“爾雅”等網絡公開課具有便捷性等特點。學生學習可以不受時空限制,但大多數學生通過爾雅平臺學習的時間基本都是分散在課余時間內。采取合理計劃,分散學習的學生占19.4%,選擇某一時間段集中學習的學生占39.5%,選擇有空就學的學生占38.9%,選擇其他的學生占2.2%。尤其是在網絡課程快要結束前的一段時間,51.8%的學生會選擇集中周末瘋狂學習或“刷課”。利用空閑、零散時間易導致學習內容的碎片化。碎片化的學習一方面滿足了學生信息量的獲取需求,但另一方面,與傳統課堂教師規律化、集中化、體系化的授課相比,爾雅等網絡公開課難以讓學生對學習內容進行體系化把握。
1.3 學習目的功利化
學習動機對網絡課程學習具有驅動、導向以及維持的作用。它包括內源性動機和外源性動機兩種類型。內源性學習動機是指在內部動力的驅使下滿足內在需要而主動進行學習的一種認知動機,具體包括提高技能,學習新知識,滿足學習興趣等;而外源性學習動機是指受到外在條件壓力或期待而進行被動學習的一種動機,如考試壓力,就業壓力,來自父母的期望等。[2]內源性學習動機可以使學生產生強烈的求知欲和學習自主性,并主動地采取各種方式去獲取有關網絡課程的知識和信息,并對它們進行有意義的建構。而學生通過“爾雅”進行學習的動機呈現這樣的發展趨勢:初期學習時內源性學習動機較強,隨著學習時間的增加,中后期則以修夠學分為主的外源性動機占據主導地位。“學習爾雅通識課的主要目的”是完善知識結構,學習先進知識的學生占20%;認識學友占10.2%,完成學分要求的占61.7%,其他目的占6.1%。超過一半的人都是為了完成學分而進行學習,這本身就帶有一定的功利性質。
1.4 學習互動效果差
學習的有效途徑之一就是質疑,通過質疑來詢問和討論,從而形成自己對某一問題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傳統授課模式中,教師一方面可以通過觀察學生的精神狀態、眼神、肢體語言、回答問題的情況等方式來猜測學生對所授知識的把握從而調整授課內容;另一方面,學生也可以就課堂產生的疑問在課間與課后第一時間與教師進行深入探討。但網絡課堂卻沒有這樣的效果,學生通過“詢問區”留言被回復的幾率特別低。如表2所示,在很多受訪的學生中普遍反映當在網絡課程學習中遇到問題或不懂的知識點,有6.7%的學生經常向老師詢問,有62.2%的學生偶爾詢問,還有31.1%的學生從不向老師詢問。參與同學之間的討論和互動中,經常參與討論的占6.7%,偶爾參與的占73.9%,從不參與的有19.4%。爾雅等網絡公開課與傳統課堂相比,其師生互動性較差。
2 影響大學生網絡公共課學習的要素
2.1 互動平臺主體割裂化設計
互動是指個體之間、個體與群體、群體與群體之間通過媒介而產生相互作用的交往過程。爾雅課程平臺的互動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學生與學生在問題區與討論區的互動和學生與教師在問題區的互動。他們的互動媒介是文字和表情。庫利的“鏡中我”理論認為,“人的自我是通過與他人的互動形成的,包括三個階段:關于他人如何認識自己的想象;關于他人如何評價自己的想象;自己對他人的這些認識或評價的情感。”[3]學生在提問區發出疑問時會想象教師對其的反應,當學生經常得不到回復時,學生根據教師不回復的態度判斷教師對學生提問這一行為生成一個自我評價:我提的問題沒有意義。而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爾雅課程技術平臺設計的缺陷造成的:爾雅課程的內容是提前錄制好的。因此,學生所提問題被回復的幾率就全憑教師上網觀看的興趣,間接地造成了互動平臺問題區的問題率與答復率嚴重失衡。
2.2 “公共—私人”領域監測體系的不連貫
戈夫曼從靜態互動視角提出了“擬劇理論”,他認為人們是戲劇中的演員。他們把針對陌生人或偶然結實的朋友的行動稱為“前臺”行為。只有關系更為密切的人才被允許看到“后臺”正在發生的一切即了解行動者的真實情感。而前臺與后臺就是做出特定表演的場所。大學生在爾雅平臺學習過程中前臺就是爾雅平臺的討論區等公共區域,而后臺就是爾雅平臺的在線學習、答題等私人領域。公共區域的“前臺”是顯性的,私人區域的“后臺”是隱性的。學生在前臺所發出的文字、表情是可以被其他學生或教師所觀察到的,所以他們會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行為即提有意義的問題。而學生在線觀看視頻及在線考試等行為是沒有其他人圍觀的自我行為,加之學生自律性較差,刷課、代刷課、利用答題軟件做作業和考試等行為的頻率就相對較高。
2.3 “前臺—后臺”的一體化負向示范效應
同輩群體又稱同齡群體,是由一些年齡、興趣、愛好、態度、價值觀、社會地位等方面較為接近的人所組成的一種非正式初級群體。高校里對學生思維影響比較大的是教師和同輩群體。而同輩群體中最具影響力的便是舍友。宿舍是“前臺”與“后臺”統一的場所。宿舍成員既將自己“前臺”的好形象展示出來,同時又因宿舍是學生日常生活世界的主要場所,所以“后臺”的日常化行為也被自然地展示出來。在宿舍這樣相對封閉的環境中,舍友之間的互動頻率較其他學生群體而言是最高的,所以,經過長期頻繁的“前臺”與“后臺”的互動表現,他們極容易自然地尋求行為一致性的趨勢和從眾行為。“刷課”、“代刷課”現象一經出現,便極易在舍友間傳播與模仿。
2.4 線上與線下學習的撕裂
爾雅等網絡公開課設立的初衷是完善大學生的知識結構,提高欠發達地區高校的師資力量,均衡高校優質教學資源的獲取度。大多學校對“爾雅”選修課程的要求設置為:“一旦選擇不能更改;每人每個學期至少修爾雅課程達到4個學分,如沒修夠,下學期補修或者以其他方式(如考駕照等)獲取學分”。但這就造成學生對爾雅課程重視度低的現象。而一次選擇權的選課設置會讓學生在選擇不敢興趣或者難度較大的課程后無法修改導致學生學習興趣低。加之,學生線上學習的內容在線下很難有渠道整合,甚至跟專業完全不相符,所以,采取“刷課、利用答題軟件考試”等方式獲取學分的現象就越來越多。
3 加強大學生網絡課程學習的對策
3.1 構建良好的宿舍文化,提高同輩群體的正向示范作用
同輩群體的特性使之更能滿足大學生心里和情感需求,通過成員交往更易給成員帶來歸屬感和安全感,群體互動產生的文化對成員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產生重要影響。“高校宿舍文化是指大學生在宿舍這一特定環境共同學習、共同生活過程中形成的生活環境、文化氛圍和精神環境。它是一種無形的感染力、向心力、約束力、驅動力,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對大學生產生影響。”[5]刷課等負向行為高的宿舍往往是學習氛圍稀薄,游戲等亞文化為主的宿舍文化。所以,學校各層面應從構建良好的宿舍文化入手,引導宿舍成員正向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激勵大學生利用爾雅等優質教育資源充實和完善自己的知識結構。
3.2 完善網絡課程交流互動平臺
針對師生互動的割裂現象,通過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理念完善爾雅等網絡課程的互動平臺。一方面,嘗試改革爾雅等網絡課程的輸出技術,增加符合學生興趣的新互動技術如彈幕技術。教師授課錄制采取直播方式,學生可通過“彈幕”等方式直接提問,讓課堂疑問在第一時間得到回復以增強學生的興趣,提高學生的課堂參與度。另一方面,建立互動交流激勵機制。利用數據平臺,對發起相關討論主題的學生進行學分激勵。最后,利用大數據平臺,建立課程教學活動評價機制。通過大數據找出學生評價較高的授課方式,以及教師回復學生問題的頻次等內容引導教師對線上課程的關注度,授課方式與技巧的提升,提高對學生問題的回復度。
3.3 建立更加合理的評價、監督體系
針對學生自律性差的特性,建立更加合理的監督體系是必不可少的。傳統課堂的監督主要是靠教師對課堂的管控和考試,而爾雅等在線課堂很明顯是不具備對課堂的全面監控,所以,打破并拒絕將傳統以考試為主的知識評價體系延續到爾雅等網絡課程的評價、監督體系中。一方面,增加學生有特色的主題報告、視頻報告或者學生有意義的主題倡導等多元化知識評價體系以強化學生對知識的深度理解。另一方面,如必須采用考試方式對學生知識掌握程度進行考察,則通過改進平臺設計,將題庫的練習時間和考試時間切斷。即題庫用作平時鞏固知識的平臺,而考試時間段內看題庫的檢索功能處于關閉狀態以規避“刷課卻高分通過”的現象。
3.4 強化線上與線下授課模式的聯動功能
爾雅等網絡課堂與傳統課堂的割裂,讓學生產生“爾雅等線上課程是次要的,學分修夠即可”的想法。而線下的傳統課堂由于師生互動及時等各方面原因讓學生更加重視。所以,要發揮爾雅等線上課堂的資源優勢就需強化爾雅等線上授課模式與傳統課堂等線下授課模式的聯動功能。一方面,在校內舉辦“爾雅通識課主題研討會”等方式吸引學生線上線下學習一體化,提高學生對爾雅等網絡課程的認知度和歸屬感。另一方面,改變爾雅課程選課平臺設置,對選修科目進行學科傾向性引導。通過增加學生選課的修改權限,讓學生有更大的選擇權,選擇其感興趣的課程以增強其課程參與度。同時,在校教師應鼓勵學生觀看相似或相關課程,引導學生將線下課堂內容與線上課堂內容有機結合在一起,增強學生的專業素養。
4 結語
為了更好地引導學生利用爾雅通識課等網絡教育資源,爾雅公司應改善平臺設計,同時高校也應該加強對學生的引導,實現“互聯網+教育”的效用,提高優質高校資源的流動率和功能效應。
參考文獻
[1] 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CNNIC).第3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EB/OL].http://www.cnnic.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601/t20160122_53271.Html.
[2] 李美輝.米德的自我理論述評[J].蘭州學刊,2005(4):66-69.
[3] 李玉斌.大學生網絡學習調節機制研究[D].蘭州:西北師范大學,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