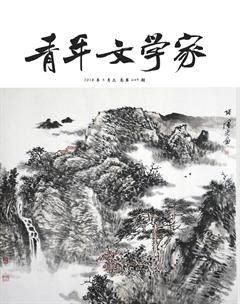家
吳越
如今,我們有很多機會見識別人的家。
可我們還是想回到自己曾經的家——曾住過的屋宅。我母親與姨媽們把臂同游的一個固定路線是:先坐地鐵(以前是坐公交車)再步行,到過去住的那棟滬上著名公寓,默默凝視某個轉角處的窗臺——那是她們曾經的家。恍若一個一分鐘的儀式,與昔日顧盼于窗前的明眸少女交換一些對生活的新看法,接著便轉身離開,去哈爾濱食品廠買點心,去婦女兒童商店試衣服,然后回到各自現在的家……
人人都有自己最珍愛的瞬間。我不由也想起我曾經住過的那些家:小學前,住在可以望得見長江支流的六樓上,小家陽臺上開滿月季花,我蹲在花旁專注地往樓下看,從猶如過江之鯽般騎著自行車下班的女性中準確地找出那一個,大喊一聲:“媽媽!”上小學后,搬進窗前栽種著大葉芭蕉的一樓的家,秋涼夜雨打芭蕉,躺在竹篾席上攤開手腳,貪最后一點不會令人感冒的涼意才入睡。
過了若干年,偶有機會回訪。一個簡單的事實是:那里不再是你的家。站在柏油馬路道牙子上,抬頭看六樓的家,找那個陽臺,看到被人家封了起來,又發現無數高樓拔地而起,猜想在那屋子里再也聽不見江聲。或者是,潛入家屬宅院,尋找一樓的家,敏感地發現窗框刷了別的顏色,接著房間里開了燈,影影綽綽中有人說話、走動……你醒過神來,該離開了。
一生很長,可能會有好幾個家。有的雖然易主,但畢竟墻檐依舊;有的則風流云散,再也無跡可尋。國慶長假前,美女同事突然決定買高鐵票回老家看一看即將被拆除的祖屋。她從小由祖父、祖母帶大,贛南鄉間的秀美風土,老屋庭院里的柿子樹和板栗樹,以及棲息在樹上的鳥兒,常常以各種情形入夢來。幾年前,祖父去世,而后不久,祖母去世。美女同事非常不安,她問:“我以后還能回哪里去尋找往日時光?”我說:“你只有多拍些照片,和自己的腦子一起努力,把記憶留得深刻些。”
最后想講一個關于家的小故事。2007年,日本喜劇演員田村裕出了一本名為《無家可歸的中學生》的小書,書打開,第一行字就是“沒有家了”。時間回到1992年7月某一個炎熱的傍晚,日本大阪吹田市一個13歲的男孩參加完初二第一學期的結業式回到家,發現家具被搬到家門外的走道上,父親以旅游巴士導游介紹風景名勝式的手勢對3個孩子說:“正如各位所看到的,雖然十分遺憾,可是已經無法再進家門了。我知道今后將會十分辛苦,但是請各自努力繼續活下去……解散!”解——散?十幾年后,田村裕還是無法理解父親怎么說得出這樣的話,并且說完就“三步并作兩步,不知道上哪兒去了”,扔下兄妹三人。倔強、不想給人添麻煩的小男孩,相信自己能夠在家以外的地方生存下去,他帶著剩下的最后一點零錢,“住”進了公園的滑滑梯里,乞討、撿食,甚至吃草,足足撐了一個多月,才被朋友發現,接納到朋友家中寄住。最終,三兄妹再度團聚于好心人為他們付租金的小屋,并各自闖出一片天地……這本書迄今已經賣出200多萬冊。
許多人由此發現了家的真諦:只要珍惜人世間相親相聚的緣分,家是不會失去的,那些存在和已經不存在的、過去的家,最后都重疊在了今天的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