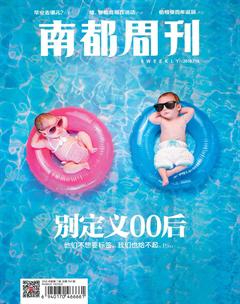伊斯坦布爾印象
嗚咦嗚咦
伊斯坦布爾的日與夜,有著不可說的秘密。
置身其中,這座城就如一臺破舊又精密的龐大機器,將古羅馬廢墟的殘敗、清真寺群的神秘、博斯普魯斯的從容不凡、大巴扎的煙火氣……在扭曲的晨靄和此起彼伏的朝拜聲中依次托出,過載的信息分分鐘讓你宕機。再遭遇一下每日例行公事的大塞車,恍惚之間讓人不禁拋出經典三連:我是誰,我在哪兒,我要干嘛。
1481
白光透過有51個孔隙的圓形穹頂,灑在我臉上,無法分辨是天光還是人造。水滴從天而降,半晌,滴答。銅盆輕輕叩擊著大理石板,半身赤裸的男侍浴師正在神情嚴肅地做著按摩前的準備工作。
我正仰面躺在加拉塔薩雷土耳其浴室 (Galatasaray Hamami)的暖室中心,一個方方正正的六角石臺上。這個被稱作“Gbekta”的石臺約半米高,每條邊容得下兩人的樣子。往上面一躺,脂肪就在高溫石板上發出有力的滋滋聲,對于遠道而來的客人,驚叫是不可避免的。呵,羞澀又敏感的肉體啊。
熟讀金庸的朋友對描述古墓中的寒玉床不陌生,Gbekta剛好相反。據說土耳其本地人喜歡這樣的高溫(土耳其烤肉了解一下),在這個暖室,你先得充分出汗,再沖洗身體,為全身按摩做準備。不過,土耳其浴可愛之處在于,相比芬蘭浴,它不打算把我塞進一個窒息的蒸氣桑拿房(那簡直就是地獄)。只要你愿意,隨時可以跳下烤肉架,飛快地擰開飽經摩挲的黃銅水龍頭,抓起有底紋的銅盆往身上潑水。
趿著木屐,我盡量克制地在浴室里打望,揣摩這個號稱具有500年歷史、貝尤魯區最悠久的土耳其浴室有何玄妙。
相傳,奧斯曼蘇丹巴耶濟德二世在此地巡游,經過了一個茅舍,其主人正是威望頗高的苦行僧詩人俞巴巴(Gül Baba),曾追隨巴耶濟德二世的父親出生入死。巴耶濟德二世就問他有什么愿望還沒實現。后者答道,希望這里有一個庫里耶(Külliye,伊斯蘭文化中的一個建筑概念,以清真寺為中心的建筑群),旁邊有帶圓頂的土耳其浴室,以及一個能世代傳承的學校。
1481年,俞巴巴的愿望實現了,學校和土耳其浴室都建成了,浴室附近正是今天的加拉塔薩雷中學,而以前這個浴室也給學生提供了清晨沐浴之處。
這處建筑已于1965年翻新,除了明顯的游客臉,你看不到任何學生模樣。
讓我略驚奇的是,和一些同樣老資格的土耳其浴室不同,這所浴室竟是男女共浴。尺度到底有多大,就請讀者親自去體會吧。容我引用一段旅行作家毛豆子的描述:
“讓我們回到那張猩紅的,有 S/M 即視感的皮質床上……我的眼睛合著,但能感受自己的背脊正在被非常賣力地揉搓著,這不禁讓我想起魚市里伙計洗魚的架勢。就在我身上的揉搓稍微停頓一下的時候,我忍不住睜開了眼睛,并不禁暗暗一驚:一對碩大的乳房正在我眼前劇烈抖動,它們和我背脊上正感受到的一種名叫‘Kese的傳統手套的摩擦處于相同的振頻,我覺得自己此刻仿佛置身于一幅真正的奧斯曼時期的世俗風情畫中。”
內室探索完,我推門離開Hamam進入冷卻區,另一個國營臉的侍浴大叔指指右側的水池,讓我仿效前面的人沖淋。呆!一大缸冷水當頭澆下,你有考慮過烙鐵的感受嗎。
末了,用浴巾把自己裹得像個粽子,我躺進獨立的木隔間里(不是棺材)。小床妙不可言,適宜小憩。此時此刻,應許之地。透過雕花的窗欞,大廳中間的泉眼汩汩,間或飄來宣禮塔的催禱聲,撫慰著我疲憊的神經。
貓
在谷歌瀏覽器輸入伊斯坦布爾,排名前三的聯想詞是:伊斯坦布爾之夜、伊斯坦布爾奇跡、伊斯坦布爾的貓。
起初還不以為然。
直到我檢閱相機里的照片,充斥著各色求關注的小可愛,才意識到這句話的力量——“沒有貓咪,伊斯坦布爾的靈魂亦不再完整”。
熙熙攘攘的街道,貓咪們怡然自得,大搖大擺地穿行其中,似乎它們才是伊斯坦布爾的主人。路邊隨處可見給流浪貓準備的干糧、庇護所以及飲水容器,以及醒目的告示:“這些杯子是為它們準備的。如果你下輩子不想為一杯水而掙扎的話,請不要動這些杯子!!!”。
要是你想擼貓,去社交媒體上看看總是沒錯的。在臉書,伊斯坦布爾人建立了一個“Cat of Istanbul”的賬號,現在超過7.9萬名粉絲;在Ins,有1.5萬人關注并分享著城中名貓。可以說,貓與任何景點同在。
2016年,城中一件大事是網紅貓“湯比利(Tombili)”的離世。這只斜靠街邊的肥宅一臉超然,成為了轟動一時的表情包。它死后,卡德柯伊區也在原處立起紀念銅像,供人緬懷。后來銅像失竊,當地媒體甚至發文呼吁,最終盜賊良心發現,銅像被偷偷地原路奉還。
著名問答網站Quora上,很多人提了同樣的問題:伊斯坦布爾到底有多少只貓?
排名第一的答案是——220萬只。
有人感慨,浪跡歐洲二十國,從沒哪國如此多貓。
媒體報道稱,伊斯坦布爾的貓逾十萬只。更多的當地居民認為,根本沒法對半家半野的貓咪做官方統計,子又生孫孫又有子,無窮匱也。哪怕當地人開始為母貓做絕育手術,“單單在我住的那條街上,就有至少50只流浪貓。”伊斯坦布爾居民厄蘭齊吐槽。
2016年,一部名為《貓(Kedi)》的土耳其紀錄片,透過7只貓的視野,來呈現伊斯坦布爾的市井氣。女導演切達·托倫(Ceyda Torun)的鏡頭下這些大膽、乖張又特立獨行的動物從容應付著大都市的生活,與人若即若離地互動。人們給它們喂食的同時,不免思考起人生、愛與上帝。托倫的鏡頭會讓你感覺你就是一只貓,搖搖晃晃跟在前面的貓屁股后面,有時突然沖上屋頂,從高處俯瞰金角灣。
穆斯林國家中,土耳其的愛貓之情并非惟一。
伊斯蘭教相信貓是圣潔的動物;在《圣訓》(穆罕默德言行錄)中,就有很多先知愛貓的例證。例如,穆罕默德曾在起身禱告之時,為了不打擾在他長袍上打鼾的貓,剪斷了自己的袖子。另一則傳說則是,曾有致命毒蛇想襲擊穆罕默德,而阿布·忽雷刺的寵物貓將其救下,于是,深受感動的先知祈愿,讓貓擁有化險為夷的能力。
追溯起來,伊斯坦布爾與貓的糾葛甚至早于土耳其共和國。在鄂圖曼帝國時期,虔誠的信徒就通過當地的慈善機構vakif照料貓;相比之下,中世紀的歐洲城市通常恐懼貓,甚至將其邪惡化。
伊斯蘭世界將貓視為守護者,更多是基于鼠患。早期的商船帶著貓,在伊斯坦布爾這里頻繁貿易,到港后這些自由的靈魂就不受管束了,水手返回船只,可貓咪們相愛了,它們在伊斯坦布爾扎下根來。此后,貓咪繼續守護這座城,防止圖書館被鼠輩啃噬,保護市民免于鼠疫之苦。
現在的伊斯坦布爾溝渠甚多,貓仍干著捕鼠的老本行,伊斯坦布爾人卻把它們上升到更高的層面。正如托倫所說,“街頭動物某種程度上就是一個國家的文化象征。貓,不僅僅是貓,它代表著莫可名狀的混亂、文化和獨特,這也是伊斯坦布爾的本質。”
船夫:“人們總會帶一只貓上船,對我來說它就像念珠。”
服裝店主:“貓會發出正能量,吸收你所有的負能量。”
魚販:“不愛動物的人,也不懂愛人。”
亦有人認為,貓是上天派來的使者,默默檢視著人類。
在影片《貓》結尾處,有句很觸動主子的旁白,“一只貓在你的腳邊喵喵叫,望著你,就像是生命在對你微笑。那些幸運的時刻,讓我們意識到,我們還活著。”
從博斯普魯斯到獨立大街
六小時前,我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大橋上差點把自己憋死。
這里正在舉行一場跨越兩個大洲的馬拉松賽事。與其說是參賽,不如說我們都是嘉年華的一員。伊斯坦布爾馬拉松就像一個流動的大派對,在正經的運動員出發后,每個路人都加入到狂歡的人流中。
博斯普魯斯海峽美如畫,深秋的歐亞大橋涼風刺骨。很快,我的問題變得再實際不過,哪里有臨時洗手間。身處游行隊伍,很難想象有人能在踏上這座1560米的大橋后,膽敢眾目睽睽之下對著橋下撒野。再說,橋邊是圍欄覆蓋的,每隔百米就有警衛守護。
我厚起臉皮向警衛詢問洗手間。對方攤攤手,回復沒有。
那你們怎么解決?我滿腹疑惑,只好痛苦地向前尋路。
突然,一個當地電視臺的主播攔住我,要采訪我關于這場賽事的感受。本能地恭維了幾句之后,我就為自己的不誠實羞愧起來。洗手間他媽的在哪兒。這樣的心聲講出來,很土耳其。
眼下的土耳其人,都是天生的樂天派,和帕默爾所描述的,飽含憂愁的伊斯坦布爾來自兩個世界。有的家庭自帶著塑料布、啤酒和煙肉,在橋邊席地而坐,享受著沒有車來車往的秋日;橋下的草地更是人滿為患,踢球的小孩子盡情嬉戲;間或出現的陽光中,情侶們光著腳,安靜地依偎在一起。
可是,依然沒有洗手間這個人類最偉大的發明。
一再詢問無果后,我決定自救。一個瓶蓋給了我微弱的希望,我逆人流而上,努力回憶:被遺棄的礦泉水瓶、橋墩旁的救護站……它們很快就變成了可行的計劃。
人潮依然洶涌,我急切地躲在救護站的車輛背后,通過這個600ml的瓶子,首次發現了膀胱的容積。待我蓋好蓋子,往旁邊的地面一看——竟然已有三四個同樣的裝著橙黃色液體的塑料瓶,安靜地等待著它們的新伙伴。
呵,并不是每個伊斯坦布爾人都有一個異常強勁的膀胱呢。
很快,同行小伙伴開始為洗手間的事情發愁了。畢竟,很多土耳其人,老老小小,已經翻越鐵絲網,不顧顏面地進入小樹林解決問題。
正當我們面面相覷時,一個志愿者告知,前方2000米有個醫院,那里才有洗手間……我突然想起那句話,關于貓,關于混亂的本質。
幾千米后,馬拉松還在松松垮垮地繼續,隊伍已經變得支離破碎。當我們看到土耳其導游在路邊招手時,頓時有了獲救的感覺。一行人從岔路逃脫,把比賽拋到腦后。
我們的土耳其導游江導是個中國通,身材在中國人里也算不上高大,可想而知在挺拔的土耳其人中是多么異類的存在。他在北京學過中文,說一口非常流利的普通話,更難得的是懂各種中國互聯網用語的梗。
當同行的姑娘們忙于嘗試冰淇淋,和突厥血統的帥小伙們拍照時,我和他在塔克西姆廣場邊傻站著,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天,從他支持的主隊貝西克塔斯,說到伊斯坦布爾不時發生的恐襲事件。
我問他敘利亞難民問題。眾所周知,土耳其是難民進入歐洲的唯一緩沖區。難民在2017年也是土耳其和歐盟的一大爭議。江導頓時提高音量,說土耳其當然要幫助難民。他把怒火撒向歐盟,堅持認為后者向土耳其承諾的難民安置援助資金,都是空頭支票。
如果有機會去了解土耳其復雜的統治史,你會發現,這個宗教世俗化的國家,其立國之本就是團結異族。從希臘羅馬奧斯曼帝國一路走來,處于亞非拉接壤的土耳其,從文字語言到習俗宗教,都是兼容并包的。
游牧民族的特質,比如無償幫助他人,在現代土耳其依然暢行無阻。縱然,有難民在土耳其偷雞摸狗,有吉普賽人干些非法勾當,伊斯坦布爾亦不排斥他們。
我也問江導,是否信奉伊斯蘭教,如何看待異教。
他的回答就和這座城市所呈現的一樣:信則有,不信則無;你信這個很好,他信那個也很好。
和我在伊斯坦布爾所看到的保持了一致性:清真寺林立,天主教堂、猶太教堂亦不遜色。這也是最讓我覺得她卓爾不群之處,那種超大尺度的包容。
時針指向了9點,我們不再交談,默默地吹著夜風,耐心等待旅伴,就像博斯普魯斯海峽兩岸的垂釣者一般心平氣和。
姑娘們消失無蹤,獨立大街上的人流從未停住步伐。土耳其人走路帶風,如同趕路的旅人。仿佛重現,四十年前,最后一列東方快車從此地駛出,消失在那些混亂而迷人,充滿躁動的夜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