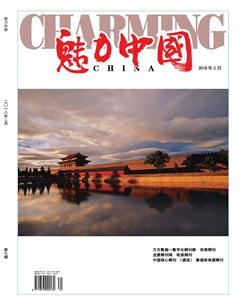從竹林七賢 看古代文人的命運抉擇
自古亂世出文豪,好像是個規律。就像如今還有人懷望民國黃金十年,說民國出了很多大師,胡適魯迅徐悲鴻。誠然,兵荒馬亂,不管內憂還是外患,民眾總要承受更多的苦難,自然會使人深刻思考苦難的源頭,探求新的人生方向,并用華美的語言或其他的藝術方式表達出來,無意間流傳百世,成為大師,亦或圣賢,如春秋之孔丘,戰國之孟軻。可以說大師的誕生既要當時的歷史環境,又要有廣泛的知識分子作為群眾基礎。魏晉就是這樣的時代,先有建安七子,壯志凌云,后有竹林七賢,閑云野鶴。各自才情八斗,但因個人選擇和時代境遇,其各自命運大相徑庭。
知識分子在中國的歷史上,一直屬于社會特殊階層。不管盛世亂世,只能或隱或顯,因為沒有勞作的概念。所以對于自己人生的選擇只有一個問題,做官還是不做官?身處魏晉時代的七賢,也不得不做出這樣的抉擇。常言說:有道則顯,無道則隱。其實也沒那么簡單。文人選擇顯與隱,主要依據自身對政治時局的判斷。魏末時代,司馬逐步掌握朝政,曹(司)馬爭斗激烈,政治陷于昏暗。很多文人對時局不滿,隱于荒野民間,其中竹林七賢就是其中最具影響力的群體代表。笑聚竹林,調侃時政,把酒為歡之余,堅持文藝創作。七人之中,出身秉性三觀各不相同,嵇康乃曹操之曾孫女婿,山濤是司馬家的表親,阮籍阮咸則是建安七子阮瑀的子孫,這一切并不影響彼此的交往,共同的愛好及對時局的共同迷茫,讓大家親密無間。
好景不長,隨著時局的變化,司馬終占上風,徹底摧毀了曹氏集團的勢力,完全的控制了局面。作為社會名流的七賢再也無處出藏身,必須做出政治上的抉擇。作為精神領袖的嵇康不改初衷,拒不合作,選擇了死扛。當好友山濤入仕并舉薦他時,依然回絕,寫下著名的《與山巨源絕交書》,終為司馬昭所害。
臨刑,嵇康凜然自若,為送別的好友和眾多的粉絲彈奏一曲《廣陵散》,其悲壯豪情絲毫不遜于戊戌變法中的譚嗣同。嵇康之死為西晉王朝日后的沉淪和覆滅敲響了哀鈡。阮籍不肯入仕,每日飲酒彈琴,時時伴以長嘯(大聲的吹口哨),以至于影響當時的文藝青年圈內盛行口哨之風。為了避免像嵇康一樣的被殺,阮籍不惜裝瘋賣傻,但無法擺脫心靈的煎熬,最后抑郁而終。劉伶更是沉迷杯中,長醉不醒,最后應了那句“古來圣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
山濤雖然和表親政見不同,但還是選擇了二次做官,仕途還算順利。做官期間為政清明,做了很多好事,舉薦了很多人才。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扶養了嵇康的子女,并舉薦了嵇康之子為官。充分體現了他對好友的情誼以及君子和而不同的情懷。
無論出于主動還是逼迫,向秀、阮咸、王戎先后都選擇出世為官。其中王戎做官最大,也是七賢中唯一受到后人鄙夷的一位,筆者覺得這可能是與古人士大夫的價值觀念相抵有關。王戎沒有留下什么作品,但極善言辭,官場商界都如魚得水,甚至在危機四伏“八王之亂”當中也能左右逢源。總之,按照當今社會的標準,王戎算得上成功人士,算是“混的最好的”(在此絕無貶義)。王戎娶了富商之女,夫妻倆感情甚好,經常一起深夜數錢,“卿卿我我”的典故就是出自王戎之筆,算是留給后人的文化遺產吧。
阮咸、向秀仕途一般,均沒有大的成就。一次轉崗途中,路徑故地,向秀思念舊友嵇康、呂安(嵇康是因呂安案受牽連而死),悲感交加,寫下了著名《思舊賦》,以表達對舊人的懷念之情。
往事越千年,風流倜儻的竹林七賢留給后人巨大的精神財富。每位賢者,因境遇和天性做出了不同的抉擇,或剛正,或通達;或悲郁,或豪情;或清明,或昏濁,在我看來,都是精彩的人生。生活的時代你無從選擇,因此無所謂幸與不幸。今人在科學上、在技藝上有所精進,但在思想的深邃和情懷的博大方面,我們遠不如古人,因為我們太多的流于俗媚,陷于功利。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留給我們寶貴的財富,愿與諸位朋友共享共勉。
作者簡介:陳明,(筆名滄海)男,1967年8月出生,籍貫河北省遷西縣,自由撰稿人,留英碩士,愛好金融、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