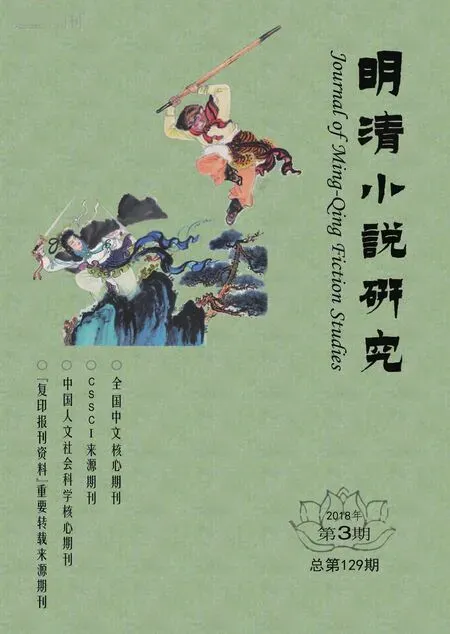晚清滬外小說專刊《揚子江小說報》研究
· ·
內容提要 《揚子江小說報》是宣統元年(1909)在湖北漢口出現的一個小說月刊,它在社會內憂外患和小說專刊不景氣的背景下創辦,以開啟一般國民民智為宗旨。胡石庵等報社同人在創刊時總結之前小說專刊辦刊的經驗教訓,對《揚子江小說報》的刊物風格特色進行了定位。《揚子江小說報》刊載的小說作品大體呈現出政治宣傳與趣味性相結合的風格特色,這一特色的形成與以胡石庵為核心的小說作家群的創作思想與主張有關。《揚子江小說報》發行時間不長,出版五期后停刊。
宣統元年(1909),在湖北漢口出現了一個小說月刊——《揚子江小說報》,由胡石庵創辦。《揚子江小說報》是創刊于上海之外的為數不多的小說專刊中的一種,它在發行過程中社會反響不錯,“銷數日有進步,海內人士以書相譽者,日凡數起”,頗有研究價值。但由于資料等種種條件的限制,到目前為止沒有人對其做過專門研究。《揚子江小說報》為什么創刊?它是怎樣的一個刊物?刊登的小說作品有何特色?為什么會有這些特色?這些都是需要解決的問題,筆者根據現有資料嘗試對上述問題進行解釋。
一、《揚子江小說報》之誕生
宣統元年四月初一日(1909年5月19日),《揚子江小說報》第一期出版。在第一期中,共刊載了七篇發刊詞,數量之多、內容之豐富,在中國晚清小說刊物中絕無僅有。即使晚清四大小說刊物(《新小說》《繡像小說》《月月小說》《小說林》),也只有一到兩篇發刊詞,而清末創刊的《小說時報》和《小說月報》沒有發刊詞。這些小說專刊的發刊詞只談到小說的某一方面,或是小說功用(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或是小說的文學特質(黃人《小說林發刊詞》)。而《揚子江小說報》七篇發刊詞分別從小說起源、小說自身風格、小說功用等方面比較全面地闡述了報社同人對小說的獨到理解。《揚子江小說報》刊登這七篇發刊詞充分看出胡石庵等同人要認真辦好這個刊物的決心。
《揚子江小說報》第一期上還刊登了一個“中國小說報調查表”,這是陶祐曾在宣統元年(1909)四月對當時小說專刊停刊情況的一個調查。這個調查表是我們理解發刊詞的線索,有助于我們理解胡石庵等報社同人為什么要辦《揚子江小說報》,他們要把《揚子江小說報》辦成什么樣。
中國小說報調查表


從調查表可以看出,自《新小說》創刊之后,小說專刊不斷涌現。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梁啟超發起“小說界革命”之后,更多的人了解到小說的功用。小說可以“維持社會,鼓吹文明”,“促國民于進化之域”,“小說偏于改良社會”,“天地間足以洗剔頑錮之腦氣精,變更腐敗之習慣性者,小說之能力也”。隨著人們對小說功用的了解和小說地位的提高,小說專刊也就隨之多起來。當然所有小說專刊并非同時存在,往往是一個小說專刊停刊了,另外一個小說專刊又創辦了,同時發行的不過一二種而已。
從調查表“存佚”一欄可知:截止到宣統元年(1909)四月,《新小說》《繡像小說》《新新小說》《小說世界日報》《小說世界》《新世界小說社報》《小說七日報》《月月小說》《小說林》《競立社小說月報》《白話小說》等大部分小說專刊都已停刊。小說專刊發行不景氣。
此時的社會正內外交困。中國遭受外國列強的侵略,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中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傳統教育落后,不能隨時代變化而變化,民眾愚昧,民智不開,政界腐敗無能:
歐風凜冽,漢水不波,美雨縱橫,亞云似墨。憐三家之學究,未諳時勢變遷;笑一孔之儒林,難解《典》《墳》作用。以致神州茫茫,夥醉生夢死之徒;政界昏昏,盡走肉行尸之輩。
在社會內憂外患,在小說專刊不景氣的背景下,胡石庵等同人覺得他們有責任和使命重振小說專刊。用小說刊物來改良社會,開啟民智,拯救民眾于危難之中:
本社胡君石庵睹茲現狀,時切杞憂,爰集同人,共襄偉業;挽狂瀾于稗海,樹新幟于漢皋,半月成編,一月出版。
從調查表“發行所”一欄可以看到小說專刊基本上都創刊于上海,胡石庵等同人意識到了這種發行布局的不足:


為什么小說專刊主要集中在上海呢?這與上海具備了兩個辦刊條件有關。一是有人,在近代大批人才集中在上海,里面不乏有志于小說創作、推廣小說的人;二是出版便利,上海最早實現了印刷業近代化改造,出版業已經很成熟。相比上海,胡石庵等同人決心在漢口辦小說刊物很難能可貴。雖然漢口經歷了印刷業近代化改造,但是還不成熟。而且漢口不像上海一樣人才集中,胡石庵在漢口辦小說刊物面臨缺人的情況。他四處找人,辦刊過程很難。《揚子江小說報》的編輯群體除了胡石庵以外,還有范韻鸞、余德元、陶祐曾、鳳曾敘等人,但《揚子江小說報》的運作主要由胡石庵和他的徒弟高楚觀來具體負責。
“中國小說報調查表”的刊登說明胡石庵等同人在總結之前小說專刊辦刊的經驗教訓,以便于辦好自己的小說專刊。他們在總結前人辦刊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辦刊目的,對《揚子江小說報》的刊物風格特色進行了定位:

胡石庵等同人想把《揚子江小說報》辦成一份題材豐富、淺近易懂,有閱讀趣味,能夠開啟民智的小說刊物。具體說來,在題材方面,無論人物,還是科學、地理、理想、家庭社會方面的小說,無論譯述還是自著,都會被編入《揚子江小說報》。語言上用白話行文,淺顯易懂。還要有閱讀趣味,使讀者在“詼諧滑稽之間”而“啟發其神智,鼓舞其熱腸”。
二、《揚子江小說報》之作品
如上文所述,胡石庵等同人在《揚子江小說報》創刊時對其風格特色進行了設定。那么在實際辦刊過程中,《揚子江小說報》是否呈現了預設的風格特色呢?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從小說作品入手。小說刊物的風格特色主要由其刊載的小說作品的風格來體現,換言之,小說作品是什么風格,小說刊物也就是什么風格特色。
《揚子江小說報》發行了五期,共刊載小說十五篇,包括愛國小說、哀情小說、偵探小說等等,有自著也有譯述,大部分小說沒有刊完。《揚子江小說報》中的小說作品大體呈現出政治宣傳與趣味性相結合的風格。

這部書,便是說西歷紀元以前五百余年間,古羅馬帝國一段事跡。這羅馬帝國自紀元前七百五十三年起,至紀元前五百余年間,已易君六位,忽然生出一個暴亂之主,行纂(篡)逆之事,握住羅馬君主大權,橫行無忌,上下離心,外患紛起。眼看著羅馬帝國危亡旦夕,卻虧有數位豪杰之士,仗一片愛國熱忱,逐暴君,行新政,御強敵,救危城,奇情俠行,照耀千古。
這篇小說雖然表面上講的是羅馬帝國,實際上是在影射晚清政府。說“卻虧有數位豪杰之士,仗一片愛國熱忱,逐暴君,行新政,御強敵,救危城,奇情俠行,照耀千古”,其實是在暗示孫中山等人革命活動的合法性。小說回目對仗工整,例如第一回回目為“月神廟琵琶擅頓老,風人堡寶劍賣侯生”。無論寫人還是寫物,描寫細致。例如寫到月神廟:“修得十分宏大,周圍有數里方圓。內中亭臺樓閣,曲徑回廊,小橋流水,陡壁飛泉,另有一番妙景。”美輪美奐,引人入勝。寫到刺客:“這人的面容生得粗眉圓眼,獅鼻虎腮。一張面皮如潑血的一般,嘴上堆著一部紺色的胡須。用線扎成個小辮,繞在項上。一手提著刀,一手拿著火種。”兇神惡煞,惟妙惟肖。故事情節曲折婉轉,小說主人公亞樓和威士忌在尋找黑衣大俠的過程中,先遭遇刺客,后被囚禁,險象環生,描寫精彩。無論從描寫還是故事情節來看,都很吸引讀者閱讀。這篇小說做到了政治宣傳與趣味性的完美結合,它不僅在創刊號被放在第一篇,以后四期仍是第一篇,顯示了這篇小說的重要性,表明這篇小說的風格就是《揚子江小說報》的主導風格。
受當時政治形勢的影響,為了避免政府當局的查禁,有些小說作品政治宣傳比較隱晦,需要細細體味。《蜂蝶黨》和《新炸彈》便是如此,它們是兩篇翻譯偵探小說。《蜂蝶黨》為文言文,講述的是政府當局偵探革命黨人活動的故事;《新炸彈》為白話文,講述的是用炸彈暗殺政府要員的故事。第一篇小說中政府當局與革命黨人斗智斗勇,第二篇小說中兇殺案不斷發生,驚險刺激,兩篇小說趣味性都很強。表面看來這兩篇小說講的都是國外的事情,似乎與中國無關。可細細想來,國外有那么多可以翻譯的小說,為什么譯者偏偏選擇這兩篇翻譯呢?他們當是有意為之。兩篇小說的故事很容易讓讀者聯想到當時國內動亂的社會形勢,讀者會覺得黨派和暗殺在國外也有,中國也可以有,反映了中國革命黨人活動的合理性,也從某種意義上說明了炸彈和黨派是改變國內形勢的方法。
不過有的小說政治意味比較明顯,如《紅發會奇案》。它也是一篇翻譯偵探小說,講述的是銀行失竊,福爾摩斯探案的故事。譯者在為這篇小說作的序里點明了翻譯這篇小說的目的:“鼓舞其(一般國民)崇拜英雄、提倡偵探之主義焉”。而且小說翻譯的文筆優美,引人入勝。

另外一種情況是小說只講趣味性,它們通過豐富的故事情節、精彩的描寫、優美的語言等來吸引讀者閱讀,政治意圖不明顯或者沒有。如《梨云劫》,它是一篇翻譯小說,標“哀情小說”。它講述的是美國小爵爺瑪麗和平民女雅梨的感情故事。故事情節曲折婉轉,瑪麗和雅梨遭遇種種困難,情路坎坷。小說語言優美,寫到春景:“……綠楊織得像金線一般,桃花如幄,芳草鋪茵。”讀起來會有一種愛不釋手的感覺。再如《鐵血宰相恩篤俾士麥軼事》,用文言文寫成,標“言情小說”。它講述的是鐵血宰相俾士麥的愛情故事。俾士麥作為一個著名的政治人物在中國知名度很高,講述一個名氣大的政治人物的愛情故事,能夠滿足讀者的好奇心理,而且譯筆優美,對讀者有很強的吸引力。兩篇小說的政治意味不明顯,趣味性突出。這類小說刊登的目的可能就是為了吸引讀者,增加刊物的發行量,畢竟小說專刊的發行需要市場。
與梁啟超提倡“小說界革命”時僅僅把小說作為政治宣傳的工具,而忽略小說的趣味性相比,《揚子江小說報》中的小說作品有了很大的進步。

總體而言,《揚子江小說報》在實際辦刊過程中通過小說作品體現出來的風格特色與其創刊時設定的風格特色基本保持了一致。
三、《揚子江小說報》之作家群
一個小說專刊的正常發行,離不開一個固定的作家群。《揚子江小說報》當然也不例外,以它為陣地,形成了一個小說作家群,包括胡石庵、高楚觀、范韻鸞、陶祐曾、李涵秋等人。

胡石庵的身份與梁啟超很相似,都不像包天笑一樣是書齋里的作家,他倆都通過寫小說為自己所從事的政治活動服務。然而他們之間也有不同,就拿兩人的小說創作來說,梁啟超創作的多為政治小說,缺乏趣味性,而胡石庵創作的小說作品講究趣味性。
作為《揚子江小說報》小說作家群的組織者,胡石庵為什么要找這些作家呢?首先胡石庵認識他們,再次他們和胡石庵在小說創作方面有著相似或者相近的創作思想和主張。
高楚觀是胡石庵的徒弟,他經常跟著胡石庵學習寫小說,難免會受到胡石庵小說創作思想的影響。譯作《新炸彈》和《鐵血宰相恩篤俾士麥軼事》很好的體現了高楚觀的創作思想,兩篇譯述的很有趣味性。而且《新炸彈》更有政治意味在里面,暗示了革命黨人暗殺活動的合理性,這正是他選擇這篇小說翻譯的原因。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他們小說創作的思想和主張相似或者相近,因而能以胡石庵為核心形成一個小說作家群。他們都基本主張小說應該具有政治性和趣味性,這也就決定了《揚子江小說報》小說作品的風格特色。
《揚子江小說報》小說作家群中有些小說作家不在漢口,胡石庵一般會通過在報紙上發“啟事”的形式與他們聯絡。例如在宣統元年七月十九日(1909年9月3日)的《漢口中西報》上,就有“石庵啟事”:“報癖君鑒:聞小徒楚觀言,君近握《自治報》筆政,至喜慰,湘中報界從此吐光彩矣。《揚子江》四期已郵寄,收到否?《紅發會》已完,續稿望賜下”。這是他們之間聯系的重要方式。
結 語

注釋
:① 《〈揚子江小說報〉四期出版》,《漢口中西報》1909年8月16日。
② 此調查表中的小說報不全,據筆者統計,除表中12種小說報之外,還有寧波的《寧波小說七日報》,粵港地區的《粵東小說林》《中外小說林》《新小說叢》《廣東戒煙新小說》和《小說世界》等。
③ 《新小說》創刊于日本橫濱,后遷至上海發行。
④ 《小說世界日報》出現時間應為光緒乙巳三月十五日(1905年4月19日)。
⑤ 該表調查于宣統元年(1909)四月,此時《月月小說》已經停辦。
⑥ 原調查表中《白話小說》和《揚子江小說報》的“存佚”欄情況顛倒,本表予以更正。
⑦⑨⑩ 報癖(陶祐曾)《〈揚子江小說報〉發刊詞》,《揚子江小說報》1909年5月19日,第1期。